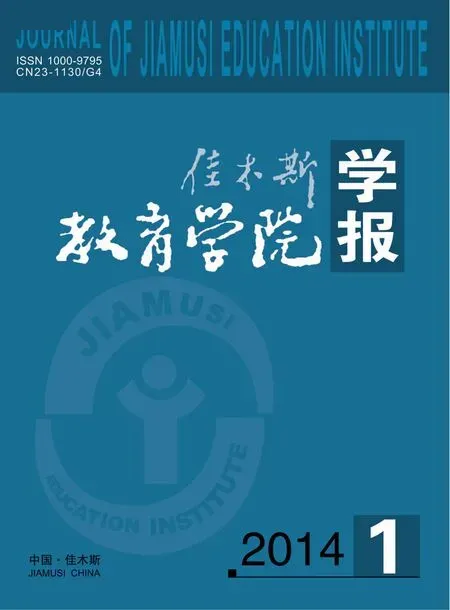男权文化的温柔渗透
——以“香港先生选举”节目为例
2014-04-17姚少霞
姚少霞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东广州 510225)
男权文化的温柔渗透
——以“香港先生选举”节目为例
姚少霞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东广州 510225)
香港先生选举以男性作为审美客体,女性为评判主体,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女性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本文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从生物学、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该活动并没有改变女性从属地位和遭遇物化的结局。事实上,女性同胞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她们缺乏自我救赎的意识,甚至自我诋毁,否定自己。
香港先生选举;女性主义;审美客体;主体性;救赎
一、男色消费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Mr. Hong Kong Contest)由香港无线电视于2005年创办。比赛评委为清一色女性。专家评委主要由历届香港小姐和二、三线艺人组成。此外节目公开招募的六百至八百位女性观众充当现场评委。比赛设有多个环节,如时装表演、泳裤展示、急智问答、才艺表演等。其中泳裤展示环节是每届选举中必不可少的。在该环节中,赛事主办方为了加强视觉效果,利用喷水,让选手们看起来更加性感。在2010年香港先生选举中,无线更是首次采用3D技术,更为真实地向千万电视观众展现所谓的男性的刚强。香港先生选举活动以男色消费为噱头,赋予女性评判决定权,似欲彰显女性主体地位。
二、女性主体?
然而,女性就当真获得自主权了吗?在香港先生选举活动中,女性的作用只是用来衬托男性的身体,其主体地位缺失;并在大众消费文化的作用下不幸被物化,丧失灵魂。
1.女性的从属性
“威严”与“权威”是评委一般所具备的形象。但在节目中,女评委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评委形象。她们的言语充满挑逗,并借机接触男选手的身体。按生物学理论,她们的言行属于现代的性崇拜(sex worship)。
而关于性崇拜,弗洛伊德在其代表作《性爱与文明》中也有所提及。但他仅限于女性对男性的“阴茎嫉妒”(penis envy)。他认为只有男人才有原欲(libido),男性在性方面是主动的,而女性是被动的(1996)。他把女性塑造为有“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的不完整的男人[1]。
女性主义对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phallocentrism)表示反感。盖伊·鲁宾批判弗洛伊德理论,认为它“描述了男性生殖器文化如何驯化了妇女,以及这种驯化对妇女所造成的种种影响”[2]。露丝·依利格更具体地指出,弗洛伊德把男性性器官“看成惟一有价值的性器官,而女性的性器官只是一个负责传达男性性生活信息的信封,女性的性是一种缺乏、萎缩和对男性性器官的嫉妒。”[3]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并没有摆脱弗洛伊德所谓的“阴茎嫉妒”与“阉割情结”。活动的高潮是泳裤环节。在该环节中,女评委显得格外兴奋。有的因失去理智而忘记评分;有的甚至呼吸急促,需要使用氧气面罩。可见,主动发出信号的是男性,被动做出反应的依然是女性,她们会作出各种不理智的崇拜行为。女性始终依附着男性,为男性传达信息。受男性生殖文化驯化,女性的性主体地位缺失。
2.物化的女性
“物化”的概念首先由卢卡契提出。他认为,市场经济促使人的行为已经脱离了人本身而变成了商品,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商品,接受市场调控[4]。在男性社会中,物化更是男性霸权否定女性主体性的普遍社会现象。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中,女评委的服装造型及言谈举止无不体现其被物化、被奴役的痕迹。在比赛现场,女评委佩戴华丽的珠宝首饰,穿着各类性感的名牌服饰,有的甚至频频更换礼服,吸引媒体和观众的目光,以满足他们的感官需要。传播媒体、商家和广告商也从受众眼球经济中实现其利润。女评委们穿戴的首饰、服装多为赞助商提供,贴上商家的标签。她们成为强烈的视觉符号,以“美”的形式,掩盖其沦为消费品的实质。
评委对选手的评价空洞。除了“性感”、“阳刚”、“帅气”之类的词语,没有其他有深度的建议。她们只会表达喜欢和请求,没有否定和拒绝,完全陷入了程式化。仿佛没有思想和灵魂。或者说,她们的思想和灵魂被深深地掩埋在父权制消费模式的混沌之中。
从2005年首届香港先生选举到2011年共七届赛事中,男监制和男编导居多,期间只出现一位女监制。换句话说,掌握该节目主导权仍然是男性。而该节目的评委皆为二、三线女艺人。毕竟她们年轻漂亮,具备“花瓶”形象,正符合男人们所设定的女人特质。西蒙·波娃曾经说过,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而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5]。“妩媚”、“矫情”和“肤浅”正是男人预设给女人的形象。此外,她们长期徘徊在二、三线,需要出镜的机会,只好配合制作方。事实上,不少女艺人赛后承认,她们是奉命活跃气氛。这些许体现出她们那么一点无奈。但在物质社会的今天,为了追逐名利,她们只好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意志为代价。
可以说,女评委的形象依照男性所设定的女性特质来进行包装,她们的语言行为也听从男性的命令,接受他们的规范。她们没有自由意志,淹没在冰冷的物质世界中,以致自己也不幸沦为其中一员,被无情地加以利用。
三、自我救赎意识的缺失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宣称男人的命运掌握在女人手里,充分给予女性自主权,迎合女权主义。但其实节目无处不丑化女性,并凸显出女性的无知、自我沉醉和缺乏救赎意识。
女性拒绝自我救赎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不作为,即对现实妥协,接受既定程序,对争取主体性方面采取消极、甚至逃避的方式。第二种笔者称之为反作为,即不但不承认女性的主体性,而且从男性的角度审视女性,并进行自我诋毁。传统观点认为,女人的“身份”是男人塑造的。但是如果女人自己也认同这种被强加的身份,并且参与促成这一过程,那么将会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这体现男权文化对女性心理的逐渐腐蚀与渗透,使女性同胞们潜意识认为男权中心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忽略自己内部的声音。铁凝曾经说过:“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6]可见,女性自省是其自我救赎的关键。
女性要真正摆脱奴役与压制,就不能把自己客体化,必须确立自己的主体人格;要克服对男性的依赖,不以其为救赎,只能自我救赎。张洁曾说过,女性自己的缺陷只有自己修正,否则只怪自己不争气,甘为“花瓶和贱货”。[7]可是在香港先生选举中,女评委的言行却并没有丝毫觉醒的迹象。她们有的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只是充当一个花瓶摆设。当镜头掠过的时候,摆弄出各种优雅的姿态;当主持人询问其感受的时候,她们支支吾吾,语无伦次。有的女评委则行为相当夸张,为了获得出镜机会,讨好电视节目制作人,不惜降低身份,损毁自我形象,来迎合男性霸权文化。更为可悲的是,女评委们一脸陶醉、享受的样子,似乎察觉不出问题所在。或许她们压根没有意识到女性也需要有自己的身份,一种不附和男人的独立自主的身份;女性也需要有自己的声音,一个完全发自自我内心的,不被抑制、忽略的声音。又或许以上这些她们都了解,只是在大环境下,她们只好服从。她们所体现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自己性别的不信任。
四、结束语
本文透过香港先生选美活动的文化现象来分析男性选举活动的实质。当男性也沦为审美客体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女性获得主体地位。相反,这只是男权文化采取的“温柔的演变”。而女性却缺乏自我救赎的意识。
[1]弗洛伊德.夏光明,王立信,编.弗洛伊德文集:性爱与文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86.
[2]约瑟芬•多诺万.赵育春,译.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47.
[3]肖巍.女性主义对“性生物决定论”的挑战[J].河北学刊,2001,21(1):53-56.
[4]张峰.一曲女性物化的悲歌——评约翰•福尔斯的小说《说藏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6(5):82-85.
[5]宿春礼,编.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书[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27.
[6]铁凝.玫瑰门(写在卷首)[А].铁凝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7]张洁答香港记着问:谈女权问题与“女性文学”[C].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9(12).
The tender permeation of male-dominated culture -- A case study of Mr. Hongkong Contest
Yao Shao-xi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25, China)
In Mr. Hongkong Contest, men appear as aesthetic object while women judging subject, which breaks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Nevertheless, it doesn’t mean that women gain much more subjectivity. Mr. Hongkong Contest is an interesting cultural phenomenon which can be scrutin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xual biology and sociology on the basis of feminism theori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it never brings any improvement for women’s position. Neither does it prevent the tragedy of women’s materialization. What is worse, women lack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redemption and have been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 of self-destruction.
Mr. Hongkong Contest; feminism; aesthetic object; subjectivity; redemption
G1
A
1000-9795(2014)01-0491-02
[责任编辑:陈怀民]
2013-12-02
姚少霞(1981-),女,广东南海人,助理研究员,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和教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