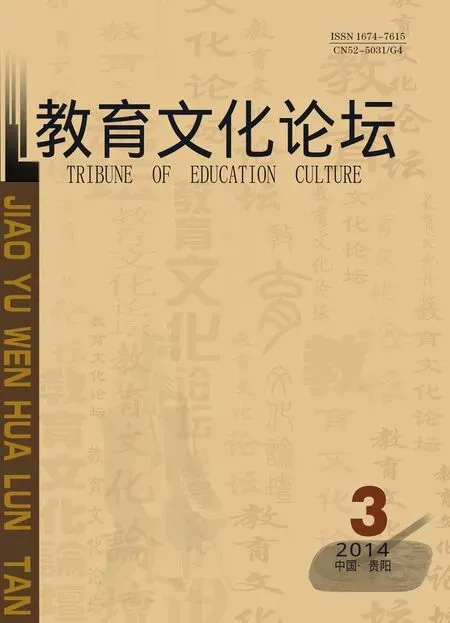湖湘教育传统与当代湖南教育
2014-04-17伍春辉
伍春辉
(长沙师范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00)
广言之,传统是特定的国家、民族、地域历代传承、沿袭至今的全部历史积淀,包括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及行为方式等。作为其中重要方面,传统教育是过往形成并流传下来的教育思想、制度、方法融汇而成的教育体系,一般意义上中国传统教育主要指以儒学为主体的古典教育实践与思想。教育传统是对传统教育的抽象,是传统教育中特色化的“沉淀物”,体现其中核心精神、主流特征、价值观念、基本旨趣与倾向,它既是对特定时代特定教育体系的概括、提炼、总结和抽象,同时蕴含着对教育本质与规律认识的智慧。
中国教育传统是以儒、道、佛文化核心为主体而组成稳定的精神流程,以个体生命关怀为出发点,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为基本旨趣,以立人达人的道德感、责任感、使命感和人格陶冶为核心内容,包括有教无类、尊师重教;因材施教,学以致用,也包括尊重权威,步法先贤,“思不出位,行不逾矩”等等。
教育传统存在于历史,也存在于现在和将来。理性正视教育传统资源,审视与梳理其线索、精华、智慧,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教育现代化的“活水源头”,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启动一个多世纪以后,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最迫切的历史使命之一。
一、传统教育与教育传统
传统教育是教育传统的载体,教育传统是传统教育的积淀。很大程度上,教育传统是文化传统在教育领域的投射。我国古代家教传统,从《颜氏家训》(颜之推)到《家范》(司马光)、《袁氏世范》(袁采),其中所阐释的伦常关系、治家治学和身心修养之道,无不被打上家国一体文化传统的烙印。教育传统影响教育发展面貌,进而影响民族文化与心理的形成。日本武士教育传统在推动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同时,其中消极因素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殃及亚洲乃至世界的渊薮;坚信“世界只是因为学童的呼吸而存在”的教育传统,成为几千年来历经劫难的犹太民族维系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的无形力量,让“只拥有阳光、沙漠和人脑”的以色列(开国总理本- 古里安语)成为“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
对传统教育的解读、把握,对教育传统的传承、舍弃,一直伴随我国传统教育现代转型进程。作为变革的基础,传统在现代化初期以对立面的障碍形态存在:因为难以割舍,所以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迟迟不能起步,才有貌似中庸实则保守的“中体西用”。至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传统更是为激进者视为沉重包袱而遭到彻底否定,空疏、陈腐、摧残人才,几乎成为多数精英批判传统教育的众口一词,“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寸之余地”(陈独秀)。这固然与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韦伯(Max Weber,1864-1920)等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现代性”的论调有关,更多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愤懑,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此后美国人列文森(Joseph Richmod. Levenson,1920-1969)关于中国只有置于“传统断裂”环境中,“改变他们的文化价值”才能迈向科学取向的文明社会之论,成为新一轮虚无主义者的理论支撑。也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现代性”弊端日益暴露和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影响不断扩大,中国传统文化逐步得到重新认识和评价。蔡元培一面力倡以欧洲大学为模式改造北京大学,同时把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与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教育、美之服务社会结合起来的教育视为最理想的大学教育;梅贻琦则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便是现代大学内涵的最佳诠释。此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的普世价值在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中引起共鸣。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1934)便认为,“中国过去文化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不会阻碍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化,实际上反而会帮助这种转化,并在指导转化中起重要作用”。
坚守还是舍弃传统,这一问题至今仍在困扰着包括中国在内,依然行进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和民族。传统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指向和影响未来。作为一种承载、延续民族文化与精神的“活的价值系统”,传统经岁月的洗礼与选择,其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合理性甚至优越性。譬如缘于我国先秦时代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有教无类”,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一定历史条件下生气勃勃的思想、制度和方法,随着时势的变化也会失去活力,成为落后、腐朽的历史负担。教育传统是流动的,也是相对的,它不断吸取每一时代的新鲜内容,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我国传统教育开始现代化转型的同时,新的、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传统开始形成,譬如高等教育传统,便是历经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变革的种种冲突和洗礼而逐渐形成的,包括爱国和革命,追求真理、重视学术,既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又重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等等。
我们无法选择传统,正如无法选择历史一样。传统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正身处的现实。教育传统存在于已经制度化、系统化和见诸书面文献的思想观念,更多潜在于非制度化的教育行为方式和教育习俗之中。譬如科举作为制度终结百余年后,与之相随的意识、观念、习惯仍在影响民众心理深层——每年高考前后,媒体沸沸扬扬的关于“状元”、“誓师”的炒作,公务员招考火爆的场面便是证明。回避甚至切断传统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作为现代化教育的源头,构成现代化教育的典型特征,包括世俗化、民主化、科学化、福利化,来自于更为广义范围内的教育传统——古希腊教育的全面发展观念、古罗马教育的世俗化倾向、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理性精神、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 今天的欧洲依然珍视传统,视苏格拉底、柏拉图为精神源头;过去的数十年间,我国台湾地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固守,对社会的稳定、民众文化素质与道德水平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借鉴。遗憾的是,20世纪新文化运动与“文革”两轮对于传统彻头彻脑的批判甚至戕害,其惯性影响至今。近20年来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从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教育理念和话语体系,甚至种类繁多实则大同小异的《教育学》教材,基本是全盘输入西方教育的结果。除了一些口号式的提法,在转化教育传统资源上我们乏善可陈,甚至弃之如弃敝履,对此有人尖锐指出,“中国教育学界在错误的教育学观指导下长期以来对于外来教育学抄袭多于创造、对于传统教育学否定多于继承”。譬如我国建国以后形成了三级师范教育体系与教师教育传统,包括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全方位专业能力培养,强调通识教育传统,注重教师理想信念与职业道德培养等,然而就在创新、变革的旗号下,伴随一大批师范院校合并、更名等方式的“综合化”发展,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却在逐渐消退,直接导致了师范生教师教育专业素养整体降低。
对待传统的理性态度,远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所能涵盖全部,简单两分法只能导致因矫枉过正而迅速枯竭。这是一个在全面根源性丢失、没有扎实落脚点的浮躁时代,一部分以保存、复兴古典传统为口号与噱头的商业化炒作之外,更多是以前卫、先锋为标榜,否定性、排斥性先入为主的对于传统的批判甚至嘲讽。普利兹克奖获得者、中国美术学院王澍教授曾说,只有对一个东西介入到很深的程度,才有批判的可能与资格;他的教学过程中便有让学生跟传统的工匠学木工与砌筑的环节。对于依然行走在通往现代化转型道路上的中国而言,新文化的构建离不开对传统的理解和继承,对传统辩证的、审慎的认识与合理吸收,会更加丰富和充实文化特色,形成包括教育传统在内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在,当然也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的是合乎教育本身发展规律逻辑的继承、扬弃和发展,譬如书院传统,其专重人文固然有其弊端,但其重视道德修养和人格陶冶无疑为当代中国教育提供了极好的参照与借鉴,关于此,青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即使是饱遭诟病的私塾,其寓道德教育于教学过程,体现因材施教的个别教育,同样对今天的教育具有借鉴意义。至于其中已经失去了活力,甚至成为教育现代化障碍的部分,包括权威主义、功利主义等与现代教育要求格格不入的部分,当然是当断即断。
二、湖湘教育传统与当代湖南教育
教育传统凝聚着一个国家、地区、民族的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甚至自然生态相关联的“本土”、区域特色,总是“身在某处”或“归属某群”,与特定文化或地理区域中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教育习俗相关。这种“地方性”是一种教育传统区别于另一种教育传统的重要依据,也是教育本土化追求的精神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东方重群性塑造、人伦教化,西方重个性培养、知识陶冶。从一个国家来看,我国地域辽阔,差异性的经济、文化背景下不同区域教育传统同样体现差异性的地域特征。湖南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及适宜的气候条件,典型的内陆地区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下形成了以重教兴学、磨血育人,经世致用、重视事功的教育传统。湖南自近代以来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莫不得受惠于求仁履实、重教兴学的湖湘教育传统,与此同时其中的惰性和保守性,又使得湖南教育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每一次深层次的改革都显得异常艰难。对几千年积淀起来的、凝聚着湘人智慧与血性的教育传统进行现代诠释与传承,对于依然行进在教育现代化转型路上的湖南仍有重要意义。
第一,弘扬重教兴学、磨血育人传统,依然是建设教育强省的题中之义。教育的发展不能光靠教育从业者单方面努力,也不能靠政府行政命令强制推动,它更需要民众理解、支持教育的良好发展氛围。特定的文化与地域条件下,湖南人重教育。自南宋胡安国、胡宏父子“卒开湖湘之学统”,此后张拭在长沙创设城南书院,掌教岳麓书院,“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者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自此湘学大盛,人才辈出。“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无数湖湘先辈矢志求道精神的激励和感染下,三湘大地逐渐形成重教兴学、磨血育人的民风传统。在民间,湖南人改变命运的途径中,读书然后入仕然后光宗耀祖改变家族、乡梓命运,可能是最佳甚至唯一选择。因而无论是富家大户还是贫苦人家,对儿孙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自东汉初年出现学校教育以来,先贤学子、社会绅民、开明官吏重教兴学者骆绎不绝。至晚清时私学遍布全省城乡,仅族学一项,全省160大姓,691个分支共有族学1144所。重教的风气也与历届湖南主政者及各级官员重视教育有关,传统时代的政府官员大多科举出身,在社会事务范围相对狭窄、经济促进空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维护一方稳定之外官员大多能自觉把“兴教一方”视为己任。近代湖南的陈宝箴、端方、赵尔巽、谭延闿,甚至政声不佳的庞鸿书、俞廉三、何键,也多有兴教之举。教育现代化转型闸门开启之后,从政府到民间浓厚的重教风气,锤炼了朱剑凡、胡元倓、禹之漠、陈润霖、何炳麟、徐特立、罗辀重等一批淡泊名利、个性鲜明而又充满血性的教育家们,志存高远,“磨血”育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湖南教育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在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巩固、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高等教育规模提升等各个领域成绩斐然,迄今各类学生规模达1100余万人,教育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8%,湖南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教育大省。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这期间一方面是被误读的“教育产业化”的导致教育成本直线上升,普通民众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是大跃进式的教育规模扩张,造成大批教育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特别是最近几年里非理性扩招狂潮下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愈演愈烈,一方面是读不起书,另一方面是读了书却找不到出路,民众是天生的经济学家,算算眼前的经济账,考虑种种机会成本,新一轮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也就不足为怪了。特别在农村,要么考一所好学校,追求升学率便成为部分农村学校(或曰之优质、示范性学校)的第一选择;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听之任之,重教风气与传统自然打了折扣。
教育发展的氛围,首先在于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苗头,折射出转型期教育政策的错位导致民众对于教育改变命运预期值的降低,对于正处于发展关键期的湖南教育,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湖湘教育传统中“磨血兴学”的有志之士日渐稀疏。在“教育产业化”的喧嚣中,让人寒心的是,不但多数私立教育机构,甚至不少国有名校的主持者们也变着法子赚钱,旧时代曾经广遭非议的“学店”时下并不鲜见,对此,诸如“炮轰教育”等各种尖锐的批评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把教育列为当今最腐败、潜规则最为盛行的行当之一。对此,值得反思的不仅仅是教育界——当基本的办学条件无法满足,当教师的基本生活尊严不能保障,当弄钱成为校长的第一要务,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乔布斯之问必然“绵绵无绝期”。相对于湖南教育强省的蓝图,无论是基础教育的投入、高等教育的规模与结构,还是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湖南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弘扬重教兴学、磨血育人的传统,依然是其中重要的题中之义。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公开舆论场上教育的重要性不容置喙,但转型期浮躁、功利的世风下,政府不应再以穷省办大教育的省情为托辞推诿谋划、改革、发展教育之责,也不能站在遥不可及的高处,以倨傲施舍的心态对待教育,而应把其作为最重要的民生,俯下身来,放低身段,真正以民众的满意度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通过理性而有力的政策规范、舆论引导,营造党政主导、部门联动、全民参与共建教育强省的合力与氛围。
第二,拒绝“经世致用”庸俗的功利主义误读。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也是湖湘教育传统的标志性特征,强调为学应着眼于实践,“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受此影响,湖湘学子中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既心怀天下又具真才实学和远见卓识,能担治国安邦之责的经世人才。
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近年来教育领域功利主义的盛行,或者可以视为对经世致用庸俗的误读。我国自古以来的教育传统之一,是高扬重德轻利价值取向的同时,功利主义一直是左右教育发展的外在动力。急功近利、缺乏理性是每一个时代转折期的典型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世俗功利而重视投入教育本无可厚非,但一味追求世俗功利,将会使教育变得淡然无味,最终丧失其本质。过度功利必然导致短视。无法否认的是,从宏观政策制定到微观教育管理,近年来湖南教育发展过程中短期行为并不鲜见。以高等教育发展为例,扩招浪潮带动湖南高等教育入学率以几何级数逐年跃进,过程中很多高校在办学思路、专业设置、人才争夺等各个方面,从短期利益出发,或急功近利,或贪大求洋,甚至互相倾轧。从老牌综合性大学到新升格的高职高专,脱离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不顾师资、硬件离“大学”层次的差距,专业开设以“热门+有用+时髦”为导向,而之前完善的、行之有效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师范大学——师范专科学校——中等师范)逐渐淡化,师范类专业纷纷改弦更张,中文改文秘,历史改政法,当弊端渐显,依然不从师范体系的修复与完善方面下功夫,而采取更为短视的“特岗教师”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每年成千上万进入其他行业受阻且未受过严格师范教育者进入农村教师序列,给本就不平衡的城乡、区域基础教育发展新的更大的不均衡埋下伏笔。今人强调经世致用传统在湖南教育领域的传承,当然是“药方只贩古时丹”之外,追求与“世”联系更为紧密、更为长远、更能理性地体现“用”,实实在在办教育,办实实在在的,更加多样、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满足做表面功夫、一味着眼短期利益的崇尚虚文、形式主义的教育。
第三,教育不能绕过政治,但不能过分搅合政治。近代以后时局动荡、政治纷争的大背景下,精英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的舞台、空间被放大,湖南社会变革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精英,无论是进步还是守旧,都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湖湘前辈的政治事功和政治声望,激励着无数湖湘后辈前赴后继,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为最高追求。在这种对于政治过度热情的文化氛围里,教育也被打上浓厚的“重政治”的印记,也伴随着传统教育的近代转型过程。在对政治过度热情的文化氛围里,一批教育界精英自觉或不自觉搅合到政治中来。如胡元倓既为端方、赵尔巽所倚重,立宪、革命各派的黄兴、谭延闿也努力争取他的支持,并且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何键主政的三十年代。胡元倓一生淡泊仕途,但始终与官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全省教育界有着分量极重的话语权,其态度对整个湖南教育界乃至政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官本位盛行的社会里,通过参与政治争取话语权,尽可能为教育发展谋求有利的外围环境,也不失为新教育推进的有效路径之一。这就不难理解,民国前期省城长沙的私立名校,董事会领衔者大都是胡元倓、贝允昕等新派士绅,在一个动乱成为常态的社会里,只有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新生的教育才得以勉强在夹缝中生存。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方面,教育不可能游离于政治之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治国理念甚至还影响到教育方法,“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教师照本宣科的灌输,学生死记硬背。但教育作为具有独立功能、独立作用的社会事业,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作用以及运行规律。教育既要参与政治,以教育回报社会、改造社会,但一定要保持适度的独立,傅斯年先生早在30年代初便呼吁“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过分搅和、热衷政治,便不利于教育的发展,把教育办成四不象。湖南人喜欢讲政治,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王东京先生关于湖南人思维方式中“等级观念”、“重官”“挤官道”的描述,同样盛行于湖南教育界。湖南人喜欢“讲政治”,教育界有教育界的政治,近年湖南取消了中小学校长行政级别,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官本位、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教育界变了味的“讲政治”之风,甚至较其他领域尤烈,如果教育界仍然沿袭以往政治上的“路径依赖”,教育离开自身的轨道,而以行政官员的需要和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权是重,惟官是大,教育是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
[1] 顾明远.教育大词典(增订合编本)[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1998: 732.
[2] 丁钢.历史与现实之间[M].北京:教育出版社,2002:26 .
[4]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0: 11-12.
[5]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1989:62-63.
[6] 顾明远.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演变和形成[J].高等教育研究,2001(1).
[7] 丁钢.略论教育传统与变革[J].中国教育学刊,1992(2).
[8] 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351.
[8] 程敏,孙侠.教师教育传统的消退与重构[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 2 .
[9] 程亮.论教育传统[J].教育发展研究,2005(6).
[10] 王东京.市场经济与湖湘文化取向[N].湖南日报,2003-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