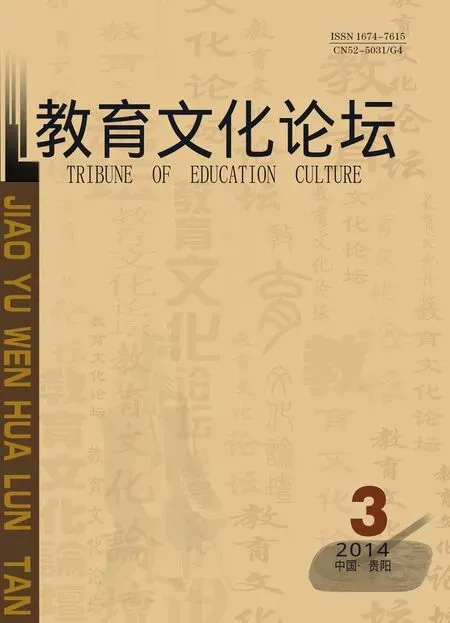生命与仪式:教育人类学视阈下的湘西土家族丧葬文化
2014-04-17黄亦君
黄亦君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发展研究院, 贵州 贵阳 550028)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沿袭下来的传统习俗多种多样,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中,湖南湘西一带土家族的丧葬文化蕴含着较强的宗教和民俗色彩,具有强烈的生命教育及警示意义,对人之生死观、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伦理道德等方面均颇具启迪。教育人类学是在学术研究的范畴中将教育学与人类学有机结合,运用人类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来思考、解读和考察教育领域及其相关区域内的一些重要问题,以揭示教育与人、教育与文化、教育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一门应用性学科。鉴于教育人类学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用教育人类学的视角解读相关的民俗问题,无疑是一件较有意义的事情。
一、边城:湘西及其丧葬生态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1]
——沈从文:《边城》
这是沈从文在其名著《边城》中对湘西的一段深情脉脉的描写。从沈从文饱含真情、充满诗意的笔触来看,湘西是一个充满着民族风情、弥漫着民俗画卷的地方,风景秀丽,山水人文叠翠,多姿多彩,婉约而不失秀美,多情而不失雅致,和谐而不失灵动。湘西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据统计,现今有土家、苗、汉、白、瑶、回、蒙、壮等43个民族居住于湘西,其中土家族是湘西的世居少数民族,也是湘西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约为110.69万人,占湘西总人口的54.83%。奇特的人文环境和自然条件酿就了湘西少数民族独特奇妙、五彩缤纷的民族习俗,其中,土家族的丧葬习俗更是以其诡异、奇妙、仪式繁多、承载大量的文化因子而具有浓厚的神秘与蒙昧色彩。当代湘西土家族以“土葬”为其主要的丧葬形式。在他们的眼中,丧葬仪式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死亡事件,而是颇具文化色彩,他们将之俗称为“白喜事”、“白会”、“老龙归山”等,其中“白喜事”尽人皆知,流波甚广。传统的湘西土家族丧葬仪式是土家族人过世之后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尽管复杂、内容繁多、仪式庄严,但任何一个生活在湘西的土家族人都不能绕过也无法绕开这个仪式。
死亡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湘西的土家族人也不例外。从正常的情况来说,一旦土家族老人身体开始老化,家里人就会为老人开始准备棺材、制作寿衣。这并不是对老人的不敬,相反这是对老人及其生命的尊重。从制作寿衣开始,湘西土家族的丧葬仪式其实就已经拉开了帷幕,丧葬的前奏开启了。这就是丧葬的第一个阶段。老人一旦去世,迅即就进入丧葬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被湘西的土家族人称为“入敛”。在“入敛”这个阶段,逝者被请进棺材。进入棺材之前,生者为逝者穿先前制作好的寿衣,必要的时候,还要对逝者进行梳洗,以祛除逝者身体上的污垢。“入殓”之后,进入第三阶段即“停丧”阶段。这个阶段异常重要,仪式繁多,是生者对逝者的尽孝阶段,“多请土老师念经。僧道开路。土老师念经多歌唱开天辟地神话、民族迁徙、颂祖先及死者功绩等悼词。‘丧事尚歌谣’,晚上要唱‘孝歌’,打夜锣鼓以歌丧”。[2]第四阶段是“出殡”阶段。这个阶段通俗地称为“下葬”阶段。这个阶段是丧葬仪式中的最主要的阶段。丧葬中一切仪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下葬”。“出殡时,土老师饰为死者,死者为女,土老师负被、鞋;死者为男,土老师则负烟袋、弯刀,家属环绕哭吊。吊毕,即焚毁土老师背负物件。并椎牛羊祀神。然后,由僧道‘发引’、‘下葬’。对非正常死亡者则请土老师‘上刀梯’超度以葬。坟莹‘富有者石坟萤,状如山中城,以碑表示家族之盛。穷者往往以草席薄棺为之’。贫富墓室规模及形制差别较大。丧礼繁简,亦很悬殊”。[2] 284最后一个阶段是“回灵”,“回灵”其实包含着两个程序,一是孝子的接灵,也称为安灵。接灵是生者接放逝者的灵牌,将之安置到一个合理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是被安放在祖宗牌位放置处。二是圆坟,这个阶段必不可少,并且是生者对逝者表达哀思的地方,法师、道士其实已经不处于重要位置,孝子与逝者的亲人成为仪式的操作者。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祭祀。有“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之分,每一个七均要举行仪式,诸如烧纸钱、祭祀供品、上香等。这个仪式大概要持续三年,三年期满以后,生者会请道士、法师将逝者的灵牌烧掉,换上红纸黑字的灵位,以安顿好逝者的灵魂,让逝者及其灵魂尘归于尘,土归于土,安静而又平和地走向人生的结尾。此时,所谓的丧葬仪式基本结束,“白喜事”也告一段落,生者与逝者之间告别仪式至此有了一个圆满、皆大欢喜、合乎情理的结果。以后的许多时候,生者在对逝者寄托哀思时,一般都会选择在清明上坟,以祭奠逝者,追思着关乎逝者的一些美好记忆。
二、生命教育与丧葬仪式
法国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曾经指出:敬畏生命是“世界中的大事”。[3]事实上,自从人类文明开启以来,对生命的敬畏就一直是人类文化讨论和重点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生命的敬重是生命变得有意义、有人生启示的开始。在对生命的尊重里,生命一步步走来,并逐渐在日益褪去的岁月里磨练人生、享受人生赋予的其它涵义,包括对自然的顺应、对天时和地利的感知、对社会的觉悟等。因此,可以这样说,体验生活是生命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问题在于,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它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和现在对于生命来说是能够感知和触摸的存在,而未来是生命的必然走向,它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生命的归属。值得指出的是,生命的未来是确定的,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死亡是生命的最终归属,并且是必然归属。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就曾经说过:“至于生者,应尽速回到原来的场所”。[4]在这里,“原来的场所”其实是指人死亡后被安葬入土的地方,入土为安成为生命结束的状态。必须注意的是,索福克勒斯的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即死亡对于任何一个生命实体来说都是必然的,没有死亡的生命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死亡,生命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正是因为有了死亡,才有对生命的肯定。
生命结束后,如何处理作为生命承载物的身体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湘西土著居民中,土家族人以举行丧葬仪礼来表达对死者的尊重与敬仰。一般来说,习俗的“道德教化作用并不在于它是伦理价值的前提,而在于它对世俗道德标准的强化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并且,这种辅助作用是非常必要的”。[5]事实上,湘西土家族人的丧葬仪式并非简单的下葬,如果借用教育人类学的知识,它甚至具有强大的生命教育及警示意义。
第一,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关照。生命存在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等问题一直是教育人类学及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自然现象。任何一具生命都有走向死亡的一天,而且必须会走向死亡。但问题在于生命消失之后,如何将生命的价值留存于世界,如何让生命的意义得到最大的发挥,如何让生命给予世界更多存在的价值,如何让生命创造的精神遗产泽被后人,这却是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之一。湘西土家族人对于逝者的丧事一般按照程序进行操作,特别是在当代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环境下,对于丧葬仪式更为看重。丧事一般从逝者死亡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这个过程是持续不断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它远没有结束的一天,只有一个开始。因为即使是在逝者的尸体被安葬后,以后每一年的清明节及一些重要的或者特殊的场合,对逝者的墓地都要进行祭扫,其实,这不仅是一种仪式,而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当然,对逝者生命的尊重着重表现在其丧葬仪式上,尽管仪式宏大、神圣,但每一个细节均透露出对生命的尊重,例如入殓前的洗涤、净身、穿衣,下葬时的鸣炮送行、杀公鸡祭祀,等,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孝子的祭文,从逝者生前做的每一件事回忆起,如带给生者精神上的鼓励、物质上的馈赠,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如泣如诉,令人无限唏嘘,感怀不已。无疑,这是对生命价值一种极大的肯定与赞许。重要的是,这种对逝者生命的尊重、对逝者生命价值的肯定教育了下一代,让生者更懂得珍惜生命,珍惜生活,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第二,爱的教育的阐发与弘扬。应该承认,任何一种仪式,不管是祭祀仪式还是礼拜仪式,其实都是爱的教育的升华与感悟。在仪式中,爱的教育无处不在,它是贯穿仪式始终的一个重要元素,并且,在仪式的行进与演化当中,爱或者关于爱的因子是其中主队因子中最不可或缺的。因为,在世人看人,对逝者的怀念与追思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爱渗透在仪式中,让爱的元素潜移默化生者,使生者感受到爱的教育,如此,才能达到仪式说需要的效果。事实上,通过仪式中的爱的教育,可以促进生者与生者之间、生者与社会、生者与逝者之间或者机构的沟通,从而进一步增进社会的和谐度。在湘西土家族人的丧葬活动里,这种爱的教育应该是俯首皆是。比如,在丧葬仪式的第二个阶段“入殓”,对逝者的身体的清洗,寿衣的制作、上身,棺材的抬放就是爱的表达,生者对逝者的爱意弥漫在仪式的整个过程,让生者并不觉得逝者已经逝去。当然,表现最突出的莫过于“下葬”阶段,这个阶段是逝者身体入土为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逝者的亲朋好友基本聚集在逝者的亲人家庭,对逝者告别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但正是这种告别,恰恰体现了生者的爱既有亲人之间的爱,也有朋友之间的爱,有夫妻之间的爱,还有普通人之间互相合作的爱。丧事加强了亲朋好友的联系,增加了亲属之间的感情。家族成员因为丧事而聚集在一起,共同商量丧事的操办、功果的仪式繁简等,团结度、友好度、合作度在磨合中自然增加,许多个人恩怨因为丧事的操办而“一笑泯恩仇”,爱意氤氲,无处不在,爱的教育,竞相释放与张扬。
第三,中国传统孝道的教育与传承。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孝”。中国古代的帝王也一度推崇“以孝治天下”。“孝”甚至成为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准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湘西土家族人无疑继承了“孝”的传统。湘西土家族人对孝的弘扬表现在多个方面,丧葬仪式也是其中的一面。应该说,“孝”贯穿了湘西土家族人丧葬仪式的始终。从第一个阶段子女为正在老去的老人制作寿衣、准备棺材开始,“孝”的元素其实就已经贮存其中。到“入殓”时,生者要满怀深情地对逝者的遗体进行告别,以表达自己对逝者的怀念,“孝”意延绵。第三个阶段是“停丧”阶段,“孝”道在这个阶段被表达的淋漓尽致。停丧期间,孝子孝女要守灵,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应该通宵不眠,彻夜不休。孝子主要负责接待来宾,行跪拜礼;孝女则放声大哭,哭得越厉害,其孝顺的程度越显著。尽孝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祭祀。孝子孝女要定期地扫墓,以表达孝心。通过一系列的丧葬活动,土家族的民俗文化、地方规则和相关的伦理原则等直观、生动、富有趣味地传授给了下一代,使生者得到了真实而又富有传承意味的“孝悌”观,从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增加了社会和谐,深化了地方教育的内涵。
三、湘西土家族丧葬仪式教育功能的启示
湘西土家族丧葬仪式蕴涵了丰富的文化与社会内涵,充分展现了湘西土家族关于社会与人、生命与死亡、生命与神灵之间的深层思考与终极追问,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教育启示。
其一,关于死亡与生命的辩证思考。在西方学术界,对死亡与生命的思考是哲学家一直不甘沉沦的重大话题之一。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认为:“在我们身上,生与死始终是同一的东西。”[6]黑格尔说:“人具有两种特性:有生也有死。但对这事的真正看法应是,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7]费尔巴哈也说:“死本身不是别的,而是生命的最后的表露,完成了的生命。”[8]海德格尔也说:“只要此在存在,它倒始终就已经是它的尚未,它同样也总已经是它的终结。死亡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的不是此在的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一种向终结存在。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优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9]显然,哲学家这种对死亡的思考,是基于对生命与死亡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来的。死亡与生俱来,任何人都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生命与死亡相伴而生,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值得指出的是,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立即终结,在某种情况下,死亡之后,人的精神与灵魂会代替生命继续存在,会继续发挥其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过,当死亡真正来临时,任何一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恐惧,并且,即使是在面对亲人尸体的情况下,这种感觉也不例外,而且异常真实。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就曾经指出:对于死亡的态度极其复杂,甚至于互相矛盾,一面是对于死者的爱,一面是对于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依然凭式在尸体的人格所有的慕恋,一面是对于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惧:这两方面似乎是合而为一,互相乘除的。这种情形都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反感与恐惧同真诚的爱恋混在一起。[10]
在湘西土家族的丧葬仪式里,生命始终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例如,有首土家族丧歌这样唱的:“新亡进房举目望,看见帐子看见床……新亡悲切辞牙床,再不床上把福享;今日一别各一方。床帐是他亲手创,留给子孙万年长。”在这里,土家族人丧歌的主基调已抛却了对死亡和地狱的恐惧,转而体现了生死相隔之间,生者对逝者生命的深深地流连与眷恋、尊重与怀念。重要的是,土家族丧歌并没有一般死亡意义上的阴森与恐怖,相反,逝者留给了生者太多的遗产,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安慰等,这些,恰恰是逝者对于生者的遗赠,生者应该珍藏,心存感激与怀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家族的丧葬仪式已经超越了生死之间正常的生理现象,从文化的角度回答了生命与死亡这个重大问题,并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死亡的追究进行了新的阐释。
其二,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追问。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人从其出生伊始就生活在社会之中,并随着其不断成长而纠结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教育其实也是生命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湘西土家族人的丧葬仪式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各个方面,并成为处理丧事不可忽视的重要因子。一场丧事其实就是一场土家族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交往、合作和沟通的活动。在丧葬之中,几乎任何一个仪式、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他人的参与、他人的协同、他人的合作,否则,工作或者仪式的完成就不可能趋于完美。重要的是,每一项仪式几乎是生命与社会关系的再次演示。例如,逝者在入殓前进行清洗,以洁净的身体进入极乐世界,这是一种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既展现了逝者的尊严,也表达了社会对于逝者的认同与肯定。再如,做功果,既是一种正常的丧葬仪式,但更重要的却是向西方佛祖所在的世界宣告又一具生命走到了终点,在这具生命完结之时,做一些必要的佛事进行超度,慰告亡灵,无疑展现了逝者在生前对社会的贡献。而生者,在对逝者祭奠的一系列仪式中,既寄托了对逝者的思念,也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告知和教育年轻一代人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发奋进取,改造社会、改造自己、改造环境,力争在社会中留存自己的足迹,以免空留遗恨,徒生悲切。
其三,关于生命与神灵的探讨。按照灵学家的分析,生命与死亡的联系纽带是神灵。生命结束后,身体归于死亡、归于寂静、归于泯灭。但身体的死灭并不代表生命从此归于沉寂,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死亡后,灵魂仍然存在,并代替身体在世界穿行和游走。这时候,灵魂成为肉身的替代品,与生者相伴,护佑生者。佛语有云:灵魂不死,生命永恒。说得正是这个道理。对于湘西土家族人来说,生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存在的价值不断得到显现。由于价值的不断被创造,生命会被尊重,被敬仰,被歌颂。而当生命死亡后,其价值不会顿然消失,因为灵魂的存在,生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不断地对身体寄托的生命进行演绎。从而,生命与灵魂在轮回中流转。因此,当湘西土家族人的亲人一旦逝世,生者往往会对逝者做法事。在这个有着浓厚佛教意味、极度庄严的道场里,逝者的肉身被装殓,并被不断前来吊唁的人告别和默哀。重要的是,这种法事有着极强的灵幻色彩,一方面,这是土家族人的风俗习惯,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以超度亡灵的方式让逝者解脱生前所造之罪孽,脱离苦海,让灵魂进入天堂,而不至于下地狱,或者说沦为孤魂野鬼,飘荡于空灵虚无的世界。凡在这种场合为逝者烧寄的大量纸钱,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纸钱,而成为逝者进入天堂的敲门砖,既可以慰告死者的灵魂,也能够让逝者在阴间有钱享用,不至于受苦受难、穷困潦倒、孤苦一世。在选定坟茔时,法师还须口中念念有词:“四水东流去,南柯梦里亡,白云风飘飘,何处是家乡”。这一方面是劝谏、教育和警示世人在世时必须一心向善,否则人死后将无依托之所,缺乏可寄居之地;另一方面,则是祷告灵魂,在居无定所之时,家乡永远是逝者的家乡,家乡永远为逝者开放,可以安放逝者的灵魂,成为逝者坚定的依靠。从而,一种温情脉脉的教化姿态氤氲四周,充溢四野。它在警示世人,生命诚可贵,但珍爱生命,和谐相处,让生命存在的价值得到极大程度地展现仍然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61.
[2] 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84.
[3] 【法】阿尔贝特·敬畏生命[M],史怀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19.
[4] 何显明,余芹.飘向天国的驼铃:死亡学精华[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64.
[5] 黄亦君.教育·教化:宗教与青岩地方社会[J].教育文化论坛,2013(06):131.
[6] 段德智.死亡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49.
[7] 【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7.
[8]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8.
[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7:294.
[10]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0.
[11] 【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