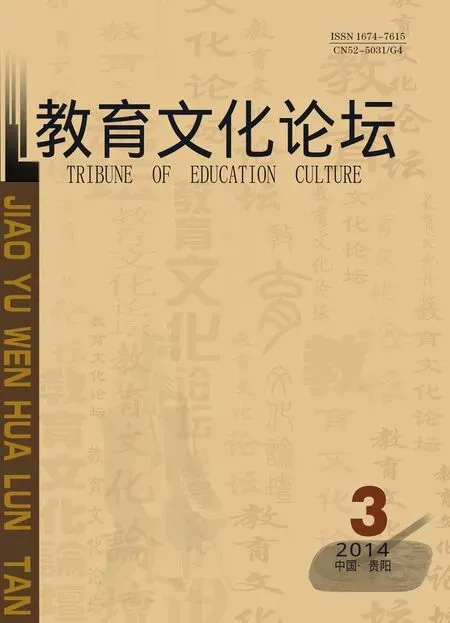《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对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2014-04-17谢芝
谢 芝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是一本由民国时期大夏大学学者吴泽霖、陈国钧等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关于贵州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论文集。文集于1942年8月作为“苗夷研究丛刊”之一种由贵阳文通书局印行。文集共收录论文51篇,可以说是当时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田野调查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学术性价值的成果之一,对于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而其中对于贵州苗夷教育的调查及其研究成果,对于当代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贵州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仍然具有多方面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出台之时代背景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内容涵盖贵州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地理分布、语言梗要和习惯法等各个方面。斯时,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沦陷区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迁到西南诸省,为国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在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迁到贵州办学的上海大夏大学,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最为全面和深入。
大夏大学迁黔以后,即“以研究西南各种问题为务。西南各种问题中,尤以苗夷问题为最重要”,于是成立社会研究部,对贵州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1]之后又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 展开大量的田野调查。在对贵州苗夷地区的调查期间,吴泽霖、陈国钧率先垂范,深入苗夷地区,“不惜心力与时间,风餐露宿,博采周咨,阅时四年”,取得丰硕成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特别是陈国钧和吴修勤等学者对于贵州苗夷教育的论述,切合实际,内容具体,观点鲜明,影响较大。
文集中陈国钧“贵州省苗夷教育”一文,主要介绍了民国时期贵州省的苗夷教育状况,并列举贵阳初小、荔波初小、台拱初小等12所专收苗夷子弟小学的学员和教员基本情况。从该文可知,民国时期,贵州省的苗夷教育受到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杨森以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1935年,蒋介石出于各方面原因考虑,对于苗夷教育颇为关注,提出“在贵州教育经费中每年至少应提出十万元,为苗夷教育经费”的训示。[2]1937年,杨森奉蒋介石令追剿红军并驻署安顺,目睹苗夷生活苦难,便垂询地方政府,开办教育事业:任命杨君为苗夷教育董事长兼安顺苗夷文化促进会会长;提供教育经费,建立小学,专收苗夷子弟;任命军官为教员,迫令该地所有失学儿童和不识字之成人入学接受教育。此后,贵州省政府先后于贵州民族教育开展了系列工作:1936年成立省特种教育委员会,专门推进苗夷教育事宜,创办了12所民族小学,专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1938年和1939年成立了贵州省民俗研究会和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研究、传习民族语言;1940年,成立边地教育委员会,“请省中对于边教与苗夷生活素有研究者为委员”,“指导推进本省边教之最高机关,并由各县分设施教区,以为实施边教之中心,逐年增设苗夷小学,普及全省各苗夷区,原则上已达到与汉族同化。”[3]1941年,贵州苗夷教育相比1938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已渐成蓬勃之象”,除了原有的贵阳初小等12所小学外,贵州省教育厅在苗夷聚居人数较多的地区,增设同等初级小学多所,苗夷学生数大增。该年苗夷学生数量已达到2045人,相较于1938年增长29.93%。教员67人,相较于1938年增长32.84%。教育经费41104元,相较于1938年增长32.25%。[4]可见,苗夷教育问题,已由口号付诸于实际行动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就。
二、《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中关于民族教育的论述
在该文集中,陈国钧的“贵州省的苗夷教育”、“边民教育之借鉴”、“石门坎苗民教育”、“如何训练苗族妇女”4篇文章和吴修勤的“怎样训练苗夷族的干部”一文,均运用大量笔墨论述了当时苗夷教育的发展概况,尤其在文章结合当时抗战救国的具体国情,指出了发展苗夷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对如何发展苗夷教育提出了若干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意见和见解。
一是结合当地实际,主张大力发展苗夷教育,化愚昧为文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贵州苗夷居住地大多处于偏远山区,和外界沟通甚少,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发展苗夷教育,应从苗夷地区实际出发,结合苗夷地区文化特色,因材施教。而当时政府所办的一些民族学校里,“所教课本均采用汉字,教材内容与实际环境相隔离,每学就忘,边民自己甚为苦,所用题材,每强以汉人生活灌注边民脑际,边民饮食为青稞、酥油而强教以水稻菜蔬;边民所住为石泥村社,而强教以高楼大厦;边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强教以电灯瓦斯,床桌窗椅;边民之交通工具为牛马牲畜,而强教以船车飞机。使边民懵然如堕云里雾中。”[5]于此情况,该书作者不吝笔墨,以较大的篇幅对如何在苗夷地区施行教育作了具体的介绍。如陈国钧在“贵州省苗夷教育”一篇中论述了推行贵州苗夷教育的基本原则,即尊重苗夷固有的社会地位、文化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相应对施教者提出要具有因时、因事、因人制宜的创造精神要求。陈还指出,在推行苗夷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改编教科书,编订适合苗夷民的教科书以及读物,教科书的取材要多用苗夷的风俗习惯内的事实,如当地神话、传说等,要将苗夷民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性如自然地理环境、民族宗教因素、民俗风情等等掺入到该地的教科书中去,使得教材通俗易懂且内容易吸收。
同时,陈国钧等在贵州考察时发现,贵州苗夷地区没有自己的文字,“迄今犹保存结绳记事,木刻为契之遗风”,[6]能识字者少,用之者更少,苗夷儿童从小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是跟着长辈“于无意间”学习一些简单的基本的生活技能。由于缺乏正规教导,苗夷民虽然质直且诚朴,但“知识稍差,缺少判别的能力”,导致“性形古拗,遇事迟疑”,亦缺乏进取向上的精神,安于现状,事事按照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规章办事,往往不知变通。而且苗夷社会,崇尚种种迷信,大病小病习惯求助于鬼神。若在苗夷地区广兴教育,不仅可以教化民众,传授知识,扭转苗夷地区无人识字的落后局面,“铲除”文盲,提高苗夷族民族文化水平,还能却除迷信,化愚昧为文明,传授其基本的医药知识,使民众明白有病需看医,对症下药,而不是寄希望于“鬼神鬼婆”。另外,在苗夷地区发展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封建思想,如女子读书无用、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这些唯有通过教育方能教化民众,使其明白女子同男子一般,均是“救国的重要分子”,均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均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苗夷地区,女子生产后不注重修养,产后不出一周即上山樵采下地耕作,对身体伤害极大,而且苗夷地区怕多生子女,往往将婴孩腻死或者杀死,杀婴之风盛行,通过教育,可以在苗夷地区传播生育知识及合理正确的避孕方法,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在苗夷地区广兴教育的另一个意义在于消除民族间隔阂。据陈国钧考察,当时苗夷民受汉人欺诈高压,因此常具戒心,若汉人来到寨中,则会受到他们的防范与远拒。此时,若对于苗夷民以热情相待,直至互相认识,可改变其多善疑惧的心理和态度。在苗夷地区“兴学传教,人为我谋”,实行苗夷“同化”教育,“则三数年后,不难完成民族统一”[7],以实现苗夷族和汉族的融合与共同发展。
二是重视对苗夷地区基层干部和苗夷妇女的教育,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以教育促进生产。该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看到了发展贵州苗夷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而且非常重视对苗夷基层干部和苗夷妇女的教育。吴修勤“怎样训练苗夷族的干部”和陈国钧“怎样训练苗夷族妇女”两篇论文,详尽论述了对两者进行教育的重要性。首先,吴修勤在训练苗夷族干部时说道,要以“人”看待他们,还要以“自家人”看待他们,必须如此,然后方可以谈如何训练。训练的时候要以优待的态度和兑现为原则对待他们,挑选人才的时候不能以普通的目光去找寻,训练的这些干部政府需要及时任命,不可尽开空头支票,训练了却不任用,对于仍保留着“剖符为信”、“一言为定”这样古朴风尚的苗夷地区,很容易造成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等严重后果。[8]陈国钧在深入苗夷区域实地调查的时候,还发现苗夷族身上有许多瑰异的特质,特别是苗夷妇女,他认为苗夷妇女在中国妇女中是最艰苦耐劳,最自重自立,于社会,于国家,是最有贡献的人了,苗夷族在家庭中以妇女为重心,每个妇女都具有经济独立能力,在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中俱有重要的地位,她们身体强健,劳作时无异于男子。因此,应注重苗夷妇女的教育。而正是因为没有“教育的帮助”,所以“苗夷所有知识简单,文化也就难有进步,物质的生活总是很难改善”。[9]
陈、吴等贵州调查时,发现贵州苗夷地区仍是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再加上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农作物产量低下。而在资源丰富地区,苗夷民“多迷信为龙神之地不敢开发,如木材不敢斫伐,矿产不肯开采”,这在一定程度上虽保护了地区生态环境,但是对于民族地区来说,要想扩大生产,提高生活,那么对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条件下,进行适当开发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吴修勤在谈如何训练苗夷干部时,就非常强调实用的观点,如在耕种方面,结合苗夷地区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主张传授苗夷民如何改良耕种,而不是教其使用机器耕种等不符合他们实际的生产方法等。
苗夷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人们从事的职业也比较单一,农忙时下地劳作,闲暇时在家刺绣编织,由此,陈国钧认为:从苗夷族职业的简单便可知其现代文明的落后,而这种落后又恰恰是教育的落后所导致的。从苗夷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教育的落后导致了其文化的落后,而文化的落后又进一步导致了苗夷经济的落后。反过来,经济的落后又制约着苗夷地区教育的发展。如此循环,导致苗夷地区“民族进化迟缓,不逮国内其他民族”。[10]因此,陈、吴等认为,在苗夷地区传播知识,施行教育,介绍新生产方法和生产组织,以提高其生活,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举。
三是紧密结合时代背景,提倡开展爱国救国等针对性教育,提高苗夷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书中作者结合抗战形势,指出推行苗夷教育实乃抗战建国伟业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贵州成了陪都重庆的屏障和西南交通之枢纽,“当兹抗战方殷,后方人力物力,均需大量储备,凡我同胞,亟应不分畛域,共同努力,应能充实国力,以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使命。”[11]陈国钧在贵州期间,不仅仅看到了贵州三百多万苗夷同胞于抗战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其尖锐的指出了若要让这几百万劳动力甘愿为国奋战,则必须在苗夷地区发展教育,以教育力量来引导实为当前之要务。“如果于苗夷区域中广兴教育,严加组织与苗夷同胞得天独厚之体质,不难化獉狉为文明,蔚成国家之劲旅。”[12]他还主张教育之目的,特别是针对成人教育的目的,乃激发民众自动,与汉族“熔冶一炉,陶铸成保卫民族国家之中坚,抵御敌人侵略”。[13]在祖国危急存亡的时刻,希望通过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来唤起苗夷族同胞保家卫国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这种将教育同时代接轨同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结合的认识,时代意义十分突出。
四是主张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抵御外来文化侵袭,掌握教育的主动权。吴修勤在“怎样训练苗夷族的干部”一篇中强调“要巩固这座堡垒,必须建设这三百万民众的心理,然后敌人才不能攻破,这是国防大事。”[14]主张在贵州苗夷族之间实行教育的时候,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训练的内容都应当积极宣传国家大一统思想,大民族意识以及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的伦理道德思想,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崇仰政府的信心。认为在苗夷族社会广兴教育,则能“替他们染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颜色”,[14]49传播中华民族大统一的主流文化,以防外界文化侵略。
该书关于苗夷教育的研究深刻具体,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特别是对有关威宁石门坎的教会教育研究,作者更是发出了犹如“洪水猛兽”似的惊呼,直言其目的乃实现文化侵略。“……直到现在,石门坎教会的教育势力仍极广大。据最近调查,计在黔滇境内有三十七所,川境有十五所,共计五十二所。苗夷子弟培植成功为数甚多,但可惜在教会势力之下,染梁宗教的气味太浓厚,很少国家民族意识的灌输,再者该教会学校学科,系用罗马字母拼为花苗文课本,便利研读,其用意之深且远,足见外人文化侵略是无疑的。”[15]认为教会办学校的目的,并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乃为“宗教而教育”,认为其一方面大批地注射儿童的宗教麻醉剂,他方面又借儿童的力量来传播到各个家庭,“所以苗夷教育在贵州,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亟待改进的地方很多。若再不能切实办理下去,那么我弃人取,一般侵略者必会乘浑水好摸鱼,便大可施其文化侵略的伎俩,单说石门坎教会教育苗民的工作,就有四十年的历史,诚使我们警惕!” “按文字和语言,都是民族同化的要素,大凡灭绝和离间种族者,必先从语文做起,像伯格理特创一种文字来教苗民,也就可知他的用心所在了”。“对这种外人在苗区做的文化侵略的工作,我们亟应设法防止,……亟盼我们贤明当局切实办理苗民教育,以挽回失却了的教育权!”[16]这些见解,从维护国家教育主权,传播爱国主义等正统文化,以及防止民族分化,抵御外来文化“异化”的角度来讲,不失积极意义和价值,值得人们思考。
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对当今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启示
“教育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新声,是改变一个民族的先声”,[17]在对《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考察的过程中,不难发现,陈国钧,吴修勤等学者对于贵州苗夷教育的调查和研究,无不闪烁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经验价值。他们所主张的教育思想对于当前贵州民族教育,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第一,开设民族文化特色课程,发展具有贵州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教育是文化传承的工具,以学校为载体,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是最有效也是最实际的渠道之一。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如神话、传说、歌谣、音乐、舞蹈、刺绣、工艺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载体和灵魂,是孕育民族先进文化的土壤。这些先辈留下来的灿烂历史瑰宝,需要我们后人担当传承、保护和弘扬的重责。 “民族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应在教育结构、专业设置、学制、教材、办学形式等方面,逐步走出一条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路子。”[18]民族学校设计课程时应该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走适应民族地区实际的路子,将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引入课堂,结合少数民族人民喜爱的编织、刺绣、绘画等生产技艺和健康的民族歌舞,开展劳动技术教育和音乐、体育教学,激发少数民族人民的学习兴趣,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第二,大力推进双语教学,重视民族语言的研究和保护。语言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同时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赖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少数民族语言正面临着消失和后继无人的局面,民族地区的年轻一代已大多不会本民族语言。中国知名学者周海中教授指出: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正处于逐渐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保护弱势的民族语言和抢救濒临消失的民族语言。这样既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又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19]《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中,陈国钧关于“贵州苗夷教育的补救办法”中多次提到发展苗夷语言的重要性,低强调要“由教厅延聘语言专家,设立苗夷语言研究会,专做各种苗夷语言之研究。”还建议“组织苗夷调查团成立苗夷民俗研究会,派员到各苗夷地带去作实地的科学调查,其范围不仅限于苗夷的人口、种别、地域、历史、传说、语言、生活、宗教等项”。[20]这些意见和观点高瞻远瞩,意义深长。
第三,大力加强民族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知识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温家宝同志曾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老师,才能有好的教育。要建设一支献身教育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要采取有力措施吸引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来当老师,提高教师队伍特别是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贵州少数民族学校由于地处偏远,教师待遇偏低,教师收入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悬殊,因此大量的优秀教师流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许多教学骨干人才也流向了本地条件好,待遇高的行业和部门,这就无可厚非的导致民族学校,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民族学校,留守的大多是学历低,能力低,工作积极性也低的教师。要解决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问题,首先必须着力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当地师范教育对农村的适应性。其次,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培养。再次,如陈国钧所言,从优支给薪资,改善民族学校教师工资水平,对于穷困地区的学校,给予优惠政策,予以政策上的照顾。
第四、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民族教育发展。民族教育投入是民族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民族教育投入的多寡既是对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说明,也是国家和政府对民族教育重视与否的重要衡量尺标。陈国钧在谈及贵州苗夷教育补救办法时,将教育经费的讨论放在第一和第二条,非常注重民族教育经费的问题。在新的时期,国家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与支持,并确保教育经费及时足额到位。各级政府也应当大大增加教育经费的预算,并努力向社会募集一定的爱心捐款。对于教育经费的使用,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各级各类学校要将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在刀刃上,用在最需要用的地方,不断完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住宿制学校孩子们的伙食和住宿条件等,推动少数民族教育向更高层次方向发展。
[1] 王伯群.贵州苗夷研究丛刊序[M]//陈国钧,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1.
[2][4][6][7][9][11][13][15][20] 陈国钧.贵州省的苗夷教育[M]//陈国钧,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37,44,37,40,38,35,35,39,46-47.
[3] 陈国钧.边民教育之借鉴[M]//陈国钧,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 :291.
[5] 梁瓯第.边疆教育问题的研究[J].教育通讯,1941(8、9期合刊):19.
[8][14] 吴修勤.怎样训练苗夷族的干部[M]//陈国钧,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 : 50-52,49.
[10][12] 陈国钧.边民教育之借鉴[M]//陈国钧,吴泽霖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 :283,283.
[16] 陈国钧.石门坎的苗民教育[M].陈国钧,吴泽霖.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294.
[17] 杨军昌.石门坎教育文化(续)[J].教育文化论坛,2011(3).
[18] 江泽民.[M]//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与宣传手册.宗教文化出版社,1983:23.
[19] 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54237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