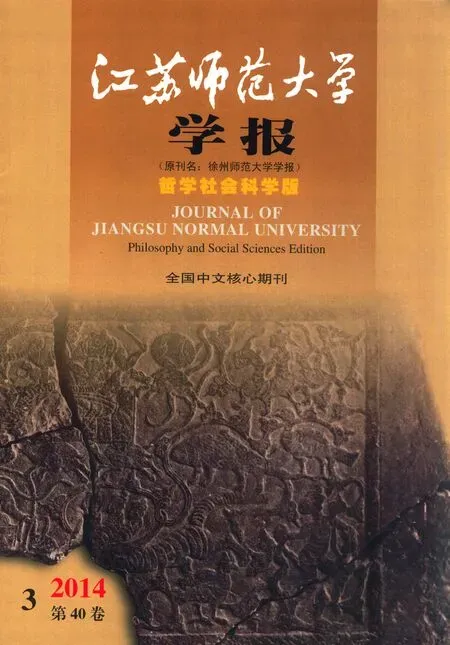查慎行与王渔洋交游及相关诗史问题考辨
2014-04-17李圣华
李圣华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金华 321004)
在“国朝六家”王士禛、朱彝尊、施闰章、宋琬、查慎行、赵执信中,“南查北赵”属于清初新生代诗人的代表,二人皆列名士禛门下。《长生殿》案风波后,赵执信“轶山左门庭”,查慎行与士禛交谊则善始善终。在康熙诗坛,王、查被推许为相“代兴”的人物。然慎行自建一帜,终不依附“神韵”说纛下,而士禛目定的“代兴”人物亦非慎行。从王士禛到查慎行,体现了清诗“正宗”之变,查、王交游关涉着一代诗史的发展演变,也关涉着南北诗学的交流与分野。本文拟探讨查、王之关系,从而进一步考察康熙诗坛演变的趋向,冀稍有助于清诗历史生态的微观剖析与嬗变规律的整体认识。
一、查、王交游始末
王士禛,字子真,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查慎行原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浙江海宁人,生于顺治七年(1650),时渔洋年17岁。顺治十四年(1657),渔洋倡大明湖“秋柳唱和”,诗名远播。翌年成进士,任扬州推官五载,与东南名士相唱和,风华映于一代。康熙十七年(1678),以诗文兼优擢翰林侍讲,未任,转侍读,自此主盟坛坫数十年,成为清王朝认可的诗歌“开国宗臣”[1]。相比渔洋的仕宦显达、才名早播,慎行可谓僻居乡野、声闻不彰了。30岁前,他南行不过钱塘,北行不越苏州。康熙二十二年(1683)《将有南昌之行,示儿建》云:“我年二十九,足不出乡闾。南舟阻钱塘,北辕限姑胥。循循守矩矱,尺寸敢少渝”,“实拟奉成训,终身依墓庐。黾勉同汝叔,食蒿甘荠如。此意难自保,饥寒旋相驱”[2]。所谓“循循守矩矱”,亦自有因。海宁查氏、新城王氏俱明代著名的文学世家,明亡后却选择了不同的家族发展道路:王渔洋、士禄兄弟在祖父象晋教导下刻苦读书以备科举;查慎行与弟嗣瑮则奉祖大纬、父崧继两代遗民之教,不以科举为业。崧继所立家训即是“不令为科举干禄之学,而读书为诗古文”(黄宗羲《查逸远墓志铭》)[3]。慎行19岁始习帖括之文,30岁尚未进学。由于不以科举为业,慎行早具诗词才华,康熙十五年又从学黄宗羲,得其经史之学。尽管学识、才力不下渔洋,终因“足不出乡闾”而声名未远彰。
慎行早年的人生道路与渔洋几有天壤之别,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十八年,慎行因饥寒相驱入贵州巡抚杨雍建幕府。这段从军经历使他获得援例捐监的机会,康熙二十三年夏游学国子监。渔洋时任国子祭酒,与慎行就有了一种师生名分,诗文中谈到慎行,大都用“门人”一称,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慎行入直南书房,始有所改变。对于这段师生之谊,慎行康熙四十三年《送刘雨峰出守真定》忆云:“我初游学来帝京,渔洋夫子官司成。君时实助四门教,相临以分称师生。众中期许良独厚,洒脱不用常格程。过从往往得一醉,叩发谈议交纵横。”[4]
其实,早在晤面数年前,渔洋已从友人陆嘉淑处看到慎行词集一卷。陆嘉淑为慎行岳父,乃浙西词派名家,与弟宏定有“冰轮二陆”之目。康熙十六年北游,携慎行词集乞序于渔洋。康熙二十四年,王渔洋为慎行作《慎旃集序》,首述及之:
老友海昌陆先生辛斋,尝携其爱婿查夏重词一卷见示,且曰:“此子名誉未成,冀先生少假借之,弁以数语。”其时余官曹署,冗俗碌碌,未及为也。及余转官司成,则夏重与其弟德尹后先入成均,余乃以一日之长临之。[5]
渔洋在扬州倡红桥唱和,《衍波词》流传海内,又与诸名家选词评词,俨然一代宗盟,故有嘉淑乞序为慎行延誉之事。康熙十六年,渔洋任户部四川清吏司郎中[6],所见慎行词集,今已不传。渔洋自称未作序的理由是“其时余官曹署,冗俗碌碌,未及为也”,然真实的原因盖为其时以词为少年绮靡之习而欲弃之。慎行详知这段故事,康熙二十三年入都亦携词集一部,转请中表兄朱彝尊评定。此即《余波词》自题所云:“甲子夏,携至京师,就正于竹垞,留案头许加评定。”[7]
列名渔洋门下,慎行与渔洋及王门弟子惠周惕、吴雯、洪昇、查昇、汤右曾、盛符升、卫台瑺、王戬、张云章、朱载震等人唱和甚欢。顺康诗坛盛行题图之风,既为交接之助,亦为标举风流。慎行入都随携《放鸭图小像》,广延名流题咏。渔洋作有《题门人查夏重芦塘放鸭图四首》。康熙二十三年冬,渔洋奉使祭告南海,慎行作长歌送别,并出诗集乞序。《送少詹王阮亭先生祭告南海》云:“公之文章在馆阁,每借名区发雄慨”,“后先人物谅无几,才地彼此恒相待”,“岂徒荣遇际旷典,已见风流压前辈。”[8]明年秋,渔洋还京,即循例乞假归省,匆匆戒道之际不忘撰序之事,《慎旃集序》称慎行为“黄叔度一流”人物,诗文“滂葩奡兀,奔发卓荦,蛟龙翔而虎凤跃,今之诗人或未之能先也”[9]。康熙二十七年(1688),渔洋父丧未免,因太皇太后薨奉旨叩谒梓宫,正月十五日入都,二月二十六日离京,《北征日记》详载京师与慎行兄弟、汤右曾诸门人交往的情况。这是慎行与渔洋分别3年后的第一次晤面。次年十一月,渔洋入都补官,慎行已受《长生殿》案牵累,黜国子生,逾岁随徐乾学离京。这段时间不长,慎行也见到渔洋,还为渔洋长子启涑作《西城别墅十三咏,新城王清远属赋》。康熙三十二年(1693),朝廷不复深究《长生殿》案,慎行秋举顺天乡试。时渔洋在经筵讲官、兵部督捕右侍郎任,慎行复执门生礼。明年,朱彝尊属题《小长芦图》,慎行用渔洋体赋绝句3首,题作《朱竹垞表兄属题小长芦图,用阮亭先生体赋五、六、七言绝句各一首》。康熙三十九年(1700)冬寓京师,渔洋出《倚杖图》邀诸子赋诗,慎行《奉题阮亭先生倚杖图》云:“几时真裹幅巾去,容我来随杖履游。”[10]第二年正月,慎行将南返,与朱载震诸同门饮于渔洋带经堂赋诗。康熙四十一年冬,慎行蒙特恩召直南书房,逾年成进士,授编修。这一际遇令渔洋刮目相看,笔记中屡有载述。慎行对渔洋推尊如故,《赴召集》收录《奉题大司寇新城公荷锄图》、《蚕尾山图再为新城先生赋三首》,前者有“君臣际会唐与虞,文章政事谁不知。东家司寇鲁大儒,品望独与经术俱”之赞[11]。康熙五十年(1711),渔洋殁于家。3年后,慎行游太湖,抵渔洋湾,睹山思人,《重阳日由邓尉坐罛船沿太湖滨抵渔洋湾,登法华岭,与观卿拈韵各赋五章》其三云:“新城老诗翁,于焉恋清景。渔洋曾自号,四海传歌咏”,“俯仰有古今,徘徊惜俄顷。谁为后来者,继蹑最高岭。”[12]因渔洋之逝,往事成陈迹,不胜其悲。
二、王渔洋目定“代兴”另有其人
王渔洋喜弘奖风流,好标榜,任国子祭酒,门人遍天下,其中诗才卓荦者,首推“南查北赵”。《长生殿》案后,赵执信放拓无聊,复不满“神韵”之说,起与渔洋相角。慎行亦不满“神韵”之说,但态度远较执信温和,与渔洋交游善始善终。“南查北赵”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影响,日渐疏远。不过,无论“轶山左门庭”的执信,还是恪守师礼的慎行,都非渔洋生前目定的“代兴”人物。此一话题不仅关涉王、查、赵之关系,亦与康熙诗风嬗变有关,故有必要细论之。
康熙中叶之诗,山左、浙西为盛,“南朱北王”共执牛耳。慎行居乡已闻渔洋之名,不无膜拜之情,迨列名门人,心怀感激。由于亲近渔洋,慎行对山左诗人也多有好感,乐与交接,与田雯、赵执信、谢重辉、颜光敏的交往即是。康熙二十五年冬,执信过访,赋诗订交。慎行《赵秋谷编修见示并门集,辄题其后》云:“依稀潮州韩,髣髴眉山苏。中有青丘子,拍肩大声呼。”[13]执信年17举山东乡试第2名,18岁举会试第六名,殿试二甲,选庶吉士,授编修,英才早著更过渔洋,而为人也恃才傲物。慎行早识其名,因其来订交,喜出望外,将其比作唐人韩愈、宋人苏轼、明人高丘诸大家。“南查北赵”意气相投,欲为京师“酒徒”,不虞名士为世所雠,牵入《长生殿》案,执信罢官,慎行同被吏议,革国子生。慎行赋《送赵秋谷宫坊罢官归益都四首》,又与朱彝尊、魏坤联赋《解珮令·联句送赵秋谷归益都》。不过,“南查北赵”继而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执信被放,纵情诗酒风流;慎行收拾科场梦,回归江湖,3年后改名慎行,重入科场。就驰骋于诗歌疆域而言,二人也有同有异:不依附“神韵”之说,乃其同;一与渔洋相角,一守师礼,即其异。此不论其同,而专说其异。
渔洋才华虽不容质疑,却非出口妙句成章的诗人。每值酒会送别,应景即事之作时不能佳,且限于学力,或流于空疏浮廓。后人嘲笑“一代正宗才力薄”,非无来历。至于所标榜的严羽“妙悟”说,亦难服众口。这些都成为赵执信攻击的理由。如渔洋奉使南海,赋诗辞别姜宸英及门人慎行、盛符升、惠周惕、汤右曾、洪昇等人。《甲子冬,奉使粤东,次芦沟桥,却寄祖道诸子》诗云:
芦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故人感离赠,昨夕共清言。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14]
此诗后来遭到赵执信的嘲笑。《谈龙录》云: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芦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吴门亡友顾小谢(以安)宅,漏言及此。客坐适有入都者,谒司寇,遂以告也,斯则致疏之始耳。[15]
诚如所评,渔洋以才力不大,捉襟见肘,乱发感喟。又如康熙三十三年除夕前大雪,渔洋邀慎行、姜宸英、蒋景祁、宋至、殷誉庆诸子集寓斋,酒酣各赋五言咏古一章。渔洋所作可谓诗才不佳,下字无谓。不过,执信早年还是未敢多提质疑的。慎行亦知士禛才力学力有限,标榜“妙悟”说太过,却未如执信那样直接分庭抗礼。这一方面是因既奉之为师,终身不肯悖于礼。另一方面,慎行虽傲睨世俗,但性格内刚外柔,“慎言慎行”,负性之气不肯尽显于外。
康熙文坛质疑权威风气甚炽,如汪琬斥责钱谦益、侯方域,阎若璩复质疑汪琬;王渔洋嘲笑遗民阎尔梅、吴嘉纪,赵执信则质疑渔洋。这一现象有着复杂的成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文坛出现新老更替局面。慎行对渔洋并非没有质疑,只是态度缓和而已。总体看来,查、王交往是密切的。慎行与执信最初惺惺相惜,后来交往极少。那么,他是否赞同执信与渔洋相角呢?从查、赵交游的前密后疏来看,慎行似更袒护渔洋,以为渔洋诗虽非尽善尽美,却仍不愧一代作者。这种态度与人生道路选择不同一样,也造成“南查北赵”之间的隔膜。
尽管查、王交游善始善终,渔洋也欣赏慎行的才华,但还是未将其视作“代兴”人物。关于谁可“代兴”,渔洋未大张其辞,不过还是有所偏爱,曾将汤右曾、史申义许为“足传己衣钵”。史申义实不足道,汤右曾诗才稍在史氏之上。全祖望推许右曾与慎行、朱彝尊为浙诗三鼎足,《翰林编修初白查先生墓表》云:“浙之诗人,首朱先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汤先生西厓,实鼎足,至今浙中诗派,不出此三家。”[16]难脱因右曾官位而拔高之嫌,右曾实难与查、朱相提并论。
客观地说,在清诗史上足称得上与渔洋相“代兴”的诗人,非慎行莫属。清人刘执玉编选《国朝六家诗钞》,《查慎行小传》说:“《敬业堂》篇什之富,与《带经堂》相埒,名篇络绎,美不胜收,才华魄力,足与阮亭代兴。”当然,这也不是刘执玉的发明,早在慎行生前就已流行这一说法。“南朱北王”逝后,慎行为诗坛宿望。查嗣瑮《五月七日,兄初白七十寿,作诗五章》其二云:“一自论文无秀水(谓表兄竹垞),人言此席属先生。”[17]慎行《残冬》其九云:
海内连年丧老成,南伤秀水(注云:竹垞先生殁于己丑秋)北新城(注云:阮亭先生于去年下世)。读书自要师前辈,知己谁能托后生。此段人情看烂熟,向来士习例相轻。笑他江左衣冠族,誓墓区区为角声。[18]
尽管慎行无意执盟,然后世自有公论。清人法式善《题海宁查怀忠(世官)南庐诗钞后》二首其一云:“一代诗名盛,恢奇敬业堂。翕然合唐宋,卓尔抗朱王(注云:秀水、新城)。”[19]确有见解,可与刘执玉之说相印证。
三、初白诗在王渔洋影响下的变化
王渔洋仕宦显赫,然未能给慎行科举仕途带来帮助。慎行入直南书房,是陈廷敬、张玉书、李光地等人推荐之功。不过,渔洋门人的身份还是为慎行广结诗友提供了便利条件,入国子监也构成他从浙西走向海内诗坛的一个重要开端。慎行与“神韵”说保持了较远的距离,但诗学思想与创作还是受到渔洋的一些影响。
一是酷爱诗酒风流。渔洋风雅自尚,追求名士风度,传诵南北。慎行入都前已闻渔洋高事,迨列名门下,欣踵其风。《长生殿》案发前五年间,慎行参与了大量的京师诗坛酒会。我们可据《敬业堂诗集》、《余波词》列出近200人的唱和名单来,其著者除旧识朱彝尊、查昇、李符、梁佩兰、万斯同、汤右曾外,更多为新交王士禛、赵执信、钱澄之、姜宸英、黄虞稷、田雯、谢重辉、曹贞吉、徐乾学、唐孙华、朱之弼、沈季友、惠周惕、吴雯、魏坤、张云章、王又旦、王源、翁叔元、乔莱、严曾榘、龚翔麟、颜文敏、李澄中、顾贞观等数十人。
康熙中叶,南北诗人聚首京华,在“南朱北王”的推毂下,诗坛酒会盛况空前。慎行至此不啻煤入炉中,与之俱化:招朋呼伴,剧饮狂呼,拈韵斗险争奇,搜肠刮肚。北游非宦非耕,去住两无策,他却另有收获,得诗朋酒侣之乐。康熙二十八年寓槐树斜街,与梁佩兰等数十人常聚于朱彝尊古藤书屋,烂醉狂吟。查、朱等人的京师唱和引起后世诗论家的关注。清人汪师韩即将其与渔洋秋柳唱和、元初月泉吟社相提并论。《冯星阶诗集序》云:
昔元初吴清翁作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入选二百八十人,无不丽句清词,标新竞美。我朝顺治丁酉,渔洋山人赋《秋柳》于北渚亭,海内和者数百家,抱玉握珠,差肩迭迹。其后竹垞老人与魏禹平、查悔余联句之作,一一隽旨清音,工力悉称。[20]
慎行参与酒坛诗会,在一段狂欢后,一场离奇的观剧风波将他抛入流言的漩涡.慎行自悔往事,然终不改诗酒故习。康熙三十四年偕查昇、姜宸英、惠周惕、唐孙华、赵俞、宫鸿历等7人举酒人之会,杨中讷、汤右曾、翁嵩年等人相继加入,“月必有集,集必有诗”(《酒人集》自题)[21],一时盛况传于好事者之口。慎行自编其诗为《酒人集》。慎行热情投入雅集社盟,沉酣于诗酒风流,与渔洋的影响及风气倡导有着一定的关系。诗歌雅集对顺康诗坛的作用尤为显著。渔洋以“秋柳唱和”为端走向诗坛,以“红桥唱和”为基执文坛牛耳。慎行在京师参与并发起“酒人”之会,同样也奠立了他在康熙诗坛的地位。
二是效为馆阁清音。渔洋中岁留意“文治”,“绝世风流润太平”[22]。慎行对此深有体会,《送少詹王阮亭先生祭告南海》即有“公之文章在馆阁”、“已见风流压前辈”之句。由于困顿江湖,他难效渔洋借馆阁清音鼓吹“文治”,20年后受到康熙帝垂青,成为文学侍从,诗因境而变:从寒士江湖之调转而为馆阁清音。如《南书房敬观宸翰恭记》一类作品借赞歌盛事,颂歌盛世;为渔洋题《荷锄图》、《蚕尾山图》,亦是馆阁清音。所作进呈御览,每能得到康熙帝的赞赏,并获得“烟波钓徒”的美称[23]。可以说慎行从渔洋手中接过“风流润太平”的接力棒,馆阁之诗虽不注明拟渔洋,实多效仿的意味。当然,慎行失其寒士故步,复多不自得,数年后回归旧调。
三是参禅赋诗。慎行入直前还曾有一段参禅的经历。康熙四十年属禹之鼎作《初白庵图》,取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之意。盖江湖载酒20余年,行程逾十万里,心力已倦,欲结茅林下,归心禅寂。初白庵虽未筑成,但慎行返里后确实是“洗心皈释典”,所赋诗编为《繙经集》,自题云:“妄念稍萌,遂成障碍。自我致寇,于彼何尤?从此洗心皈释典,未必非天之全我晚境也,戒之哉!”[24]他为友人盛宜山作《瓣香诗集序》,述及盛氏一生“诗格三变”:初为诸生,志不见售,诗以少陵为宗,怫郁沉苦之思形诸唱和;中年厌弃举业,溯江涉湖,诗以发抒盘礴之气,一变而为纵横灏衍;白首归来,究心内典,筑室南湖,诗渐诣平澹[25]。无疑亦是夫子自道。
慎行参禅礼佛,固有心态之变,亦有所取法:一是前人苏轼;二是当世王渔洋。慎行嗜苏诗,每欲躬行东坡诗路。渔洋中岁通达禅事,酷爱读佛典,尤嗜《林间录》,为清初居士禅的代表人物[26]。慎行参禅礼佛,渔洋的作用也甚为明显。《读楞严经二首》其二云:
尘根递缠绕,毕竟同生异。如结既绾成,是一要非二。一成仰方便,六解当以次。观性证三空,解脱亦如是。[27]
慎行皈依佛典,寻求解脱,近于重复渔洋的旧路。渔洋喜以禅证诗,以禅入诗。慎行不尽然,而以禅入诗则无异,《繙经集》富有禅机与顿悟之趣。只不过对慎行这位半生漂泊江湖的寒士而言,想一变而为居士,实为不易。他终不耐“寂寥”,做不到“招呼猿鹤随孤磬,收拾烟霞贮一瓢”(《题永福寺诗僧得川诗卷》)[28],经过短暂的参禅“疗伤”后,重归江湖。
四、查、王之分歧
慎行自辟诗路,不肯寄人篱下,无论“南朱”,还是“北王”,他都无意亦步亦趋。查、王之间思想、诗学、创作分歧差异显著。二人思想分歧,主要源于不同的人生经历、家庭环境、问学旨趣;诗学分歧,集中体现了浙东诗学与“神韵”说的分野,以及南北诗学的地域差异;创作不同,一方面来自江湖寒士与清华名士遭遇、心态各异,另一方面来自南北诗风的对立冲突。以下详作辨析:
其一,尚“风雅之遗”、“归于自然”与主“神韵”、“妙悟”之异。
王渔洋标举“山左门庭”,取法严羽“妙悟”说与“盛唐为高”第一义,提倡“神韵”说,大抵趣在“清远”,味在“妙悟”。“妙悟”说本是远离“风雅之遗”的产物。宋室南迁,作为中原诗学核心的“风雅之遗”说也南移江浙。慎行生于浙西,传黄宗羲之学,远追浙东“风雅之遗”诗学传统,讲求诗歌有本,其教人诗律谓:
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须辨毫发于疑似之间。[29]
郑方坤赞赏此语,《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三《敬业堂诗钞小传》引评云:“诚词苑之良规,学海之宝筏也。”[30]在慎行看来,诗主“意”而不主“辞”,“意”以“厚”为则;诗主“气”而不主“直”,“气”以“雄”为高;诗主“空”而不主“巧”,“空”以“灵”为妙;诗主“脱”而不主“易”,“脱”以“淡”为本色。世人常以“易”为“淡”,以“巧”为“灵”,以“直”为“雄”,以“辞”为“厚”,慎行斥为肤论。他强调“性情”为本,与黄宗羲一样,不满于严羽“妙悟”之说。黄宗羲《张心友诗序》批评严羽论唐“虽归宗李、杜,乃其禅喻,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亦是王、孟家数,于李、杜之海涵地负无与”,反沧浪之论说“张子心友好学深思”,“天假之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莫非唐音。今虽未竟其志,其气象要自不凡”[31]。慎行承之,注重分辨“性情”,从而区分诗家品格。由于主“意”、“气”、“空”、“脱”,慎行所谓诗法,简言之即“归之自然”。其中岁前之诗尚不免雕琢痕迹,而后趋于“天然”,如《秋花》所云“画工那识天然趣,傅粉调朱事写生”[32]。《漫与集》诸集之诗,平易之中法度历然,谓之有所学可也,谓之无所学亦可。
宋元以来,两浙之诗以承“风雅之遗”为本,吴中之诗则并尚才情。渔洋树帜,不肯借鉴江浙“诗统”,转求助于严羽“妙悟”说,力为沧浪护法。赵执信不信渔洋之说,而取法于吴中诗学,举戈相视。慎行承浙东诗学,不采沧浪之说,由此与神韵派各成一队。
其二,昌言“诗不分唐宋”与兼采唐宋之异。
从推尊宋诗来说,慎行与渔洋相近,从兼采唐宋来说,二人亦然。但其间区别也是明显的。慎行尚宋,由“不分唐宋”说来。“不分唐宋”乃黄宗羲、陆嘉淑等两浙诗人所标举的诗学。渔洋尚宋,从厌弃学唐肤熟而标新立异来。慎行推尊宋诗受到渔洋影响,但用意与目的仍显有不同。渔洋后来由两宋而复归于唐,慎行依然坚持“不分唐宋”之说。就尊唐而言,渔洋表面上尊杜,称黄山谷学杜最近,骨子里实好王、孟,而且极不喜白居易。赵执信《谈龙录》云:
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又薄乐天而深恶罗昭谏。余谓昭谏无论已,乐天《秦中吟》、《新乐府》而不薄,是绝《小雅》也。若少陵有听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33]
这并非全是交恶后肆加攻击之辞,而是反映了真实的情况。当然,渔洋疏远杜、白也包含了欲变革遗民诗风的想法,此不赘说。慎行学杜、白,身体力行,终身不易。就学宋而言,渔洋最推许黄山谷。慎行取法更在苏东坡,以30余年之力补注苏诗,诗也得力于东坡为多。
渔洋《慎旃集序》发挥黄宗炎所说“步武分司,追踪剑南”云:
姚江黄晦木先生常题目其诗,比之剑南。余谓以近体论,剑南奇创之才,夏重或逊其雄,夏重绵至之思,剑南亦未之过,当与古人争胜毫厘。若五七言古体,剑南不甚留意,而夏重丽藻络绎,宫商抗坠,往往有陈后山、元遗山风。[34]
渔洋读慎行诗的感觉是近体尚可与陆游并论,五七言古则无从论矣,因比于陈师道、元好问。事实上,慎行早年诗并非“宗陆”,其好“拟宋”大抵在苏轼。渔洋昌言宋诗,所好则在黄庭坚。二人论唐诗亦异,渔洋所好在王、孟,慎行独心许杜、白。那么,渔洋前论是否得到慎行认同呢?但观《瓣香诗集序》所说“一变而为纵横灏衍,有陆放翁、元裕之之余风”[35],即可知他不反对渔洋之说。自然,不反对并不意味“宗陆”。慎行直到暮年仍饶有兴趣地“效放翁体”。《余生集》、《漫与集》出入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及邵雍诸家。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七十三吟》效陆游同题所作。雍正四年(1726)的《二月二日效放翁体》乃《敬业堂诗集》中第一次出现“放翁体”字面,这一年慎行77岁。这类诗确接近“放翁体”,但需要指出,慎行效“放翁体”、“康节体”更多地反映了诗人老矣而兴趣犹盎然,愿意尝试新事物。所以,不必据此论其受渔洋影响而学陆。
其三,沿遗民诗余绪、发为寒士之调与倡立“清诗”、润饰太平之异。
慎行与渔洋中年后对明遗民、遗民诗的看法评价判然有别。慎行父、师辈多遗民,其亲近遗民,有始有终。渔洋任扬州推官,广结秦淮、京江遗民,获得高誉,但随着身份与观念的变化,对遗民愈来愈多不满,如批评吴嘉纪“本色渐失”、“诗格渐落”,力挫阎尔梅的狂放锐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慎行对阎尔梅的狂怪行止与霸戾之诗则充满崇敬之情。康熙三十三年(1694)冬《读白耷山人诗和恺功三首》其二云:“人谓狂生本不狂,漆身吞炭事何常。”其三云:“一卷频浮大白开,即论诗句亦雄才。”[36]与渔洋态度迥异。二人对遗民僧大汕的态度亦类此。大汕为觉浪法嗣,住广州长寿寺。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斥其“妖僧”,极尽丑诋。慎行康熙五十七年(1718)春游广州,《长寿庵坐湛庵禅师方丈听谈石公旧事》云:“津梁谁得限,传法到交南”,“贤嗣真龙象,千钧独力担。”[37]
相较创作而言,慎行沿查崧继、黄宗羲、黄宗炎、钱澄之遗民诗风,发为江湖寒士之调。渔洋早年尚受遗民诗沾薰,入为文学侍从,主动改弦易辙,标榜“清诗”,润饰太平,遂与遗民诗判然而分“朝”、“野”。抑有更可说者,渔洋早处清华,慎行身自寒士,久沦江湖,“寒士自有寒士语”,难与簪绅朝士同。慎行入直南书房前三年,俨然重复渔洋诗歌旧路,但他仍好以寒士之调传写馆阁之声,“野气”终不尽失,未几复归旧调。此亦“胎习之为性”使然(钱澄之《查德尹诗序》)[38]。
此外,查、王学问源流不同,慎行为浙东之学嫡传,学问厚殖,诗歌不沦于虚空。渔洋并非是不学,但学问博杂而不成体系。这种差异也造成二人诗歌的分野:渔洋诗归入“妙悟”、“神韵”,慎行则讲求“性情”与“学问”。
由上可知,查、王之间存在显著的分歧差异。这也可以解释慎行何以终不依附“神韵”之说,而渔洋缘何无意目其为“代兴”之传。
综上所述,查慎行列名渔洋门下,由此获得一个广阔的诗歌交游空间。慎行与渔洋的交谊善始善终,异于赵执信谈龙之讼,而查、赵关系也因此由密入疏。慎行在渔洋影响下,酷嗜诗酒风流,成为京师诗坛酒会的关键人物之一,又一度参禅礼佛。慎行亲睹渔洋“绝世风流润太平”,也为他后来发为馆阁清音埋下伏笔。尽管如此,二人思想、心态、诗学及创作仍存在显著的分歧,慎行终不肯帖服于“神韵”说下,这对浙诗的承传与清诗的兴盛,都有重要的意义。
清初诗坛查、王两大“代兴”人物的交游,诚是清诗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南北诗学的分野,遗民诗的传承与变革,严羽“妙悟”说的接受与批评,宗唐宗宋之争的纷杂变化,以及诗坛盟权的转移变换,都可从二人交游中看到其复杂的历史形态。就诗史流变言,从渔洋到慎行的“代兴”,反映了清诗的“正宗”之变,江湖寒士之调逐渐成为清诗的强劲音符。清中叶诗人之所以弃渔洋而推尊慎行,也具有特殊的诗史内涵。
[1]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
[2][4][5][7][8][9][10][11][12][13][18][21][24][27][28][34][36][37]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周劭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14-115、1753、859、1421、161、1754、753、791、1283-1284、211、1165-1166、520、761、762、771、1753、519、1396 页。
[3][31]黄宗羲:《南雷诗文集》,《黄宗羲全集》第10册,平慧善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368、48-49页。
[6]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14]王士禛:《蚕尾续诗集》卷二,《王士禛全集》第2册,袁世硕主编,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169页。
[15][33]赵执信:《赵执信全集》,赵蔚芝、刘聿鑫校点,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35、537页。
[16]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64-865页。
[17]查嗣瑮:《查浦诗钞》卷十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02页。
[19]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九,清嘉庆十二年王墉刻本。
[20]汪师韩:《上湖诗文编》之《分类文编补钞》卷上,清光绪十二年汪氏遗书本。
[22]李圣华:《从名士风流到文学侍从——王渔洋诗歌“三变”及其文化意蕴》,《甘肃社会学科》,2005年第2期。
[23]陈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谱》,《查慎行年谱》,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页。
[25][35]查慎行:《敬业堂文集》卷中,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本,第10页。
[26]李圣华:《王渔洋的佛门交游及其禅宗思想》,《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9][32]查为仁:《莲坡诗话》,《清诗话》,郭绍虞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482、514 页。
[30]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清代传记丛刊》第24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325-328页。
[38]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五,彭君华校点,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