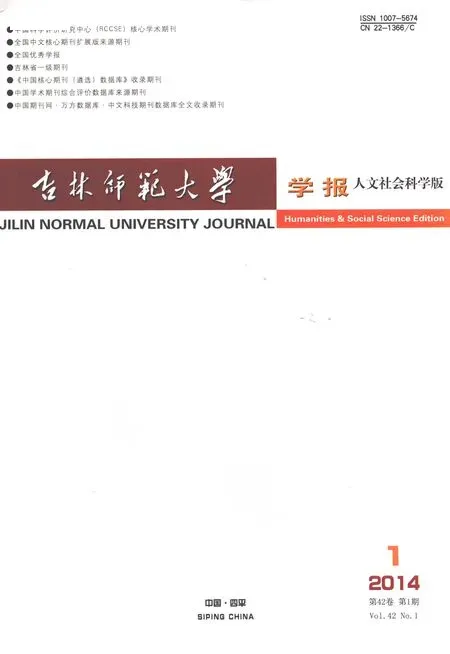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2014-04-17王辉斌
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胡震亨批评唐代乐府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唐音癸签》一书中。胡震亨对唐代乐府诗的批评,方法以“专论类批评”为主。在批评对象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乐府进行了重新定义;二是对唐代雅乐及诗乐关系进行了系统观照;三是对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乐府诗进行了具体品评。认为李白是唐代“乐府第一手”,杜甫则以新乐府见长,并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对二人的乐府诗成就进行了喻比。
胡震亨;《唐音癸签》;乐府批评;新乐府论
胡震亨(公元1569—1642年),初字君鬯,后改字孝辕,号赤城山人,晚年又号遯叟,今浙江海盐人。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代表人物。其一生著述甚丰,与唐代诗学相关者,主要有《李诗通》21 卷、《杜诗通》40 卷、《唐音统签》1033 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作1027卷)等。《唐音统签》共由十“签”组成,第十“签”即最后一“签”为《唐音癸签》,是胡震亨研究唐诗的一份重要成果。《唐音癸签》凡33卷,以搜罗赅备、体大思精而见称,其中的4卷(卷十二至卷十五)《乐通》,专论唐代乐府,更是以前此同类著作之所无。此外,在卷一《体凡》、卷五至卷十一《评汇》,以及九卷(卷十六至卷二十四)《诂笺》、五卷(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九)《谈丛》之中,也多有论及乐府诗者。综勘这些卷次中的“乐府论”,可知胡震亨对于唐代乐府诗的批评,不仅是以“专论类批评”为主,而且所获成就也是相当突出的。所以,本文特以《唐音癸签》为据,并着眼于三个方面,对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进行一次较全面之梳理与观照。
一、具有经典性的新乐府论
据胡震亨之子胡夏客于《李杜诗通》所撰“识语”可知,《唐音统签》为胡震亨“阅十年”而“书成”的一部巨著,其中的《唐音癸签》,因主要是就《唐音统签》中之唐人唐诗而发,故所论“乐”与乐府诗,亦皆为唐代的音乐与乐府诗,且精彩纷陈,创获良多,如对唐代新乐府的具体观照,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新乐府是唐人奉献给乐府文学的一份特殊礼物。据现有的资料可知,新乐府之于李唐一代,肇其始者,乃为深谙音乐之道的王维①关于王维为唐代新乐府创始人的文学史事实,具体参见拙著《王维新考论》第五章第一节,第219-230页。该书由黄山书社2008年出版。,其后,经过元结、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不断的艺术实践,而使之蔚为大观。其中,白居易的《新乐府并序》,则首次从理论的角度对新乐府进行了定义。其云: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篇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
在这篇《并序》里,白居易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新乐府进行了规范:一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二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三是对新乐府的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即 “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即在白居易看来,凡符合这三个方面的条件者,便可称之为新乐府。与白居易关系笃密的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一文中,也对新乐府进行了认识。《序》文有云:
“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誊,尚方宝剑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 《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2]
元稹认为,凡属于“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者,为新题乐府,也即新乐府,并举出了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行》以为例。 元稹的这种认识,由于曾经与白居易、李绅等人进行过讨论,并得到了其赞同,因而乃“遂不复拟赋古题”,即专意于新乐府的创作。
白居易与元稹,既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领袖人物,又都有着十分丰富的新乐府创作经验,因之,其之所言,应是较为符合唐代新乐府之实况的。但是,白居易与元稹所言之新乐府,实际上乃是以“为民、为物、为事”为主的一类乐府诗,也即为拙著《唐后乐府诗》所论述之即事类乐府①关于即事类乐府,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第一章第二节,第10-30页;第二章第五节,第122-135页。该书由黄山书社2010年出版。。元、白的这一新乐府认识,由于主要是建立在“为民、为物、为事”与“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等方面,即重在强调作品的“刺美见事”(思想性),而将其它品类、其它题材的“新题”皆排斥于新乐府之外,因而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正因此,生活于北宋与南宋交替之际的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即于该书卷九十的《新乐府辞序》中,对新乐府进行了如下之重新定义:
“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元微之病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谓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近代唯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乃与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更拟古题。因刘猛、李馀赋乐府诗,咸有新意,乃作《出门》等行十馀篇。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则《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请先蝼蚁。如此之类,皆名乐府。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3]
这一定义的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为郭茂倩本人对新乐府的具体认识,一即对上引白居易、元稹关于新乐府文字的转述。属于郭茂倩自己之认识者,主要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29字,但“唐世之新歌”究竟所指为何,郭茂倩却没有进行交待。若从其对白居易、元稹关于新乐府文字的转述而言,似其之所指,当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与李猛“《出门》等行十馀篇”之类,也即为“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的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之作。说杜甫《悲陈陶》、李猛《出门行》等皆为新乐府,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却不一定就是“唐世之新歌”,这是因为,在现所存见的郭茂倩之前的所有唐宋乐府材料中,均无称杜甫《悲陈陶》、李猛《出门行》等为“唐世之新歌”者。更何况,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之新乐府,也并非全部为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之作,因为其中更多的乃是如王建《送衣曲》、刘禹锡《泰娘歌》、张籍《楚宫行》、李贺《春怀引》等“乐府杂题”,此则表明,郭茂倩之于《新乐府辞序》中对新乐府所下之定义,与其于《乐府诗集》所收录之新乐府的实况,乃是大相抵牾的。虽然,郭茂倩在《新乐府辞序》中也曾言及了“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云云,但《乐府诗集》之11卷“新乐府辞”中,却根本没有“以被声乐”之“歌谣”,这一事实似可表明,唐代是没有这类“歌谣”新乐府的。可见,郭茂倩的这一认识,仅为其关于新乐府的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乐府诗集》之《新乐府辞序》的上述矛盾,表明了郭茂倩所持“唐世之新歌”说,虽然是意在纠正元稹、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认识的缺陷与不足,但却使之存在着一种较其更大的缺陷与不足。所以,对于郭茂倩的这种“唐世之新歌”说,精通唐代诗学的胡震亨显然是有所知晓的,这从《唐音癸签》自始至终不曾言及“唐世新歌”者,即略可获知②胡震亨撰著《唐音癸签》时,曾参考过郭茂倩《乐府诗集》,这从《唐音癸签》之笺注多次引《乐府诗集》之文字,即略可获知,如卷十二《乐通—·鼓吹曲》之注有“郭茂倩云”,卷十三《乐通二·唐曲》之注有“郭茂倩《乐府》载有古辞”等,即皆为其例。而卷十五《乐通四·唐人乐府不尽谱乐》,则于文末直接以“郭茂倩云”的形式,抄引了《新乐府辞序》中的一段文字,而成为胡震亨对郭茂倩“新乐府定义”十分熟悉的一条确证。所以,“胡著”曾参考过“郭著”者,乃为事实。。也正因此,胡震亨即选择了以乐府诗制题立论的新途径,以试图对新乐府进行再定义,因而于《唐音癸签》中针对“什么是新乐府”这一命题,提出了一种有别于白居易、元稹、郭茂倩诸家之说的全新认识,此即卷一《体凡》中的一段经典性文字。其为:
“诸诗内又有诗与乐府之别,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曰歌,亦或曰行,或兼曰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谱之乐者,自有大乐、郊庙之乐章,梨园教坊所歌之绝句、所变之长短填词,以及琴操、琵琶、筝笛、胡笳、拍弹等曲,其体不一 。”[4]
这就是胡震亨针对“什么是新乐府”所给出的一种全新定义。这一定义主要着眼于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制题方式,亦即诗题结构;一为具有歌辞性特点的单音汉字。二者的有机结合,即构成了乐府诗中“无复倚旁”的“新题”。既然是乐府新题,则就必为新乐府。即在胡震亨看来,凡具有这两个要素的乐府“新题”,即为新乐府,如《兵车行》、《泰娘歌》、《春怀引》等,但这些新乐府却并“非必尽谱之于乐”。以胡震亨的这一新乐府定义,核之有唐一代的新乐府之作(诗题明确标有“新乐府”等字样者不在此列),可知其不仅极为正确,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郭茂倩 《乐府诗集》有关新乐府认识上的矛盾。
其实,胡震亨对这一新乐府定义的提出,主要是围绕着两个方面进行的,其一是既不脱离乐府古题的形式而又与之有别;其二是在总揽唐代新乐府之后以立论的。就前者言,汉魏之前或汉魏时期的乐府题①汉魏之前的乐府题,即“前乐府题”,关于“前乐府”的创作与发展概况,可具体参见拙作《“前乐府”及其先秦的创作》一文,载《西华大学学报》2013年2期,第29-33页。,无论是民间乐府抑或文人乐府,大都是由“×××歌”、“×××行”之类结构而成,且一般以“三字题”为主,如托名为虞舜的《南风歌》、无名氏之《董逃行》等,即皆为其例。而胡震亨的“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曰歌,亦或曰行,或兼曰歌行。又有曰引者”云云,即正是藉此而提出。以后者论,唐代的新乐府,其题“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乃比比皆是,如张籍集中明确标为“乐府三十三首”者,除《秋夜长》、《雀飞多》、《寄昌蒲》等9题外,其馀则全部属于如此而为②关于张籍集中的新乐府诗题之结构,具体参见中华书局2011年版《张藉集系年校注》卷七之“目录”,以及校注正文第803-857页。。其他如李绅、元稹、温庭筠等人的新乐府题,亦大抵如此。对此,曾经以“阅十年”之精力而编撰千卷本《唐音统签》的胡震亨,应该说是极为了解的,因之,其在总揽唐人新乐府的这一大前提下,所提出的上述关于新乐府之定义,显然是与当时的创作实况互为扣合的。所以,从总的方面讲,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之“新乐府论”,不仅无比正确,而且还极具经典性,因而值得特别称道③韩国外国语大学梁海燕《王维乐府诗的重新认定》(载《乐府学》总第八辑)一文认为,《唐音癸签·体凡》于“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也”下有“始于杜甫,盛于元、白、王建诸家。元微之尝有云,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为得诗人讽兴之义者,此也。详乐通内”之自注,因而指出:“胡氏所列举的唐人新乐府常见题名,乃基于中唐兴起的创作思潮,并非就整个唐诗史而言。”其实,这种认识乃为错误。这是因为,胡注之所言,并没有“基于中唐兴起的创作思潮”,如其认为新乐府“始于杜甫”者,即为其例。此外,胡震亨于自注中引元稹《乐府古题序》者,其意旨在表明,新乐府是具有“刺美见事”之特点的,所以,其并不是用来证实“中唐兴起的创作思潮”的。而且,胡震亨于所注之中,已明言“详乐通内”,而《唐音癸签·乐通》四卷所论之“乐”,乃全部为有唐一代之各种乐曲与乐器等,而非“中唐兴起”者,即可佐证。所以,“中唐兴起”说之不能成立,乃显而易见。既如是,则该文对“王维乐府诗的重新认定”是否正确,也就藉之可知其大概了。。
二、赅备详细的音乐诗乐论
李唐是一个诗、乐极为繁荣昌盛的国度,因之,歌诗传唱即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所以,自杜祐《通典·乐典》始,唐代的“乐”,即成为了历代史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如王傅《唐会要·雅乐》、郑樵《通志·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以及《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等,即无不如此。而作为著名唐诗批评家的胡震亨,则于《唐音癸签》中以四卷《乐通》的篇幅,亦对其进行了关注。在这四卷《乐通》中,《乐通一》为总论,《乐通二》、《乐通三》为分论,《乐通四》为诗乐论,其既分工明确,又各具特点。
《乐通一》的总论,主要是对 “雅乐调”、“俗乐调”、“十二和”、“二舞”、“庙舞”、“十部伎”、“鼓吹曲”、“大射乐章”、“乡饮酒乐章”、“侲子之唱”、“凯歌”等11种乐,以及“唐初乐曲散佚”进行了述论。二者共12类。这一论述,基本上是以唐廷雅乐为主的,故其所反映的,实际上为胡震亨的一种雅乐观,而“论初唐乐曲散佚”之所言,又可为之佐证。其有云:“此固雅乐曲也,何以亦不录乎?辞之近郑、卫者,既尽为之删,其稍雅者,又得不亟存一二,唐乐章之挂漏独甚,史家固不能辞其责也。”[4]126其中所云 “史家”,所指分别为《旧唐书·音乐志》与《新唐书·礼乐志》的作者。胡震亨通过较详细之考察后认为,“旧史不能考遵前代史例,于乐志中只录郊庙,而无朝会宴射等曲”,而“新志则并郊庙不录”,致使“其辞因日就亡佚”。这样看来,可知《旧唐书·音乐志》与《新唐书·礼乐志》的作者,是确属“固不能辞其责”的。
《乐通二》与《乐通三》,所述论的音乐对象亦为12 类, 具体为:“唐各朝乐”、“唐曲”、“琴曲”、“羯鼓曲”、“琵琶曲”、“筝曲”、“笛曲”、“觱篥曲”、“舞曲”、“散乐”、“四夷乐”、“乐署”。 其中,“唐各朝乐” 为总论,“乐署”为音乐机关,馀则皆为对“曲”与“乐”的分论。在总论方面,“唐各朝乐”共对由唐太宗到唐德宗的七朝皇帝之乐,进行了以史料为依据的罗列与笺释,且极为详备。如于太宗朝所列《神功破阵乐》条,并有笺注云:
“初,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示不忘本。因制舞图,左园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用乐工百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后令魏征、褚亮、虞世南、李百药等更制歌辞,名《七德舞》。永徽中,更名为《神功破阵乐》。”[4]128
这条笺注,犹如一篇短小精悍的 “神功破阵乐史”,将《神功破阵乐》的生成原委、流变概况、表演形式等,均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于各种述论对象的分论,则亦具有此等特点。如对“唐曲”的述论首先是唐以前之“并周、隋”37曲,继之为“含元殿熊罴部十二按所奏雅曲”10曲,“有年代题意可考”者之 “大小曲”179曲,“题义无考”者297曲,四者共计523曲,其中周、隋曲37种,唐曲486种。这486种唐曲,基本上涵盖了有唐一代乐曲之全部。而尤值注意的是,胡震亨在这两卷《乐通》中,不仅详列了523种曲目,而且还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对其出处进行交待。如“有年代题意可考”者之《霓裳羽衣曲》一曲,胡震亨即先后引录了《乐苑》、《逸史》、郑嵎《津阳门诗》注三个材料,用以证实此曲确为唐玄宗所制。在对所引用的材料中,如认为其记载不确或者有疑窦者,即特地指出,并以存疑待之,如《乐通二·凌波曲》的笺注,即属如此。其云:“《太平广记》:‘玄宗东都昼寢,梦凌波池中龙女拜床下,帝为鼓胡琴,拾新旧之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命禁乐习而翻之,奏池上,龙女复见,因置庙岁祀之。’按:此似附会兴庆祀龙池之事者,说未可据,姑存备考。”[4]137凡此,均表明了胡震亨之于《乐通二》、《乐通三》的述论,乃是相当严谨的。
《乐通四》是对“诗乐”的专论,且所论分为10类, 即 “总论”、“词曲”、“律调”、“拍”、“叠”、“遍”、“破”、“犯”、“解”、“唐人乐府不尽谱乐”。 其中,以“总论”、“唐人乐府不尽谱乐”最具代表性。在“总论”部分,胡震亨依次引录了沈亚之、元稹(唐)、吴莱、马端临(元)、蔡居厚(宋)关于论述“诗乐”的文字,旨在强调诗与乐的关系,以及“近时乐家,多为新声”的乐府文学现象。而于“唐人乐府不尽谱乐”之中,在论述诗、乐、乐府之间关系的同时,还曾明确指出,唐人乐府多有“不尽谱乐”者。其云:
“古人诗即是乐。其后诗自诗,乐府自乐府。又其后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诗即是乐,三百篇是也。诗自诗,乐府自乐府,谓如汉人诗,同一五言,而‘行行重行行’为诗,‘青青河畔草’为乐府者是也。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者,如六朝而后,诸家拟作乐府铙歌……等,只是诗,而《吴声》、《子夜》等曲方入乐,方为乐府者是也。至唐人始则摘取诗句谱乐,既则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其词旨之含郁委婉,虽不必尽如杜陵之尽善无疵,然其得诗人诡讽之义则均焉。即未尝谱之于乐,同乎先朝入乐诗曲,然以比之诸填词曲子仅佐颂酒赓色之用者,自复宵壤有殊。”[4]174
这就是胡震亨的诗乐观。在这段文字中,胡震亨所述论的内容,由“古人诗”而“三百篇”,再由“三百篇”而汉人“乐府”,而唐人乐府,并指出杜甫等人的乐府诗,虽然具有“诡讽之义”,但却“未尝谱之于乐”。这实际上是针对唐人的新乐府而言,即认为唐人于新乐府的创作,虽然是“相继有作,风流益盛”,但在“谱之于乐”方面,却并非是全部都可配乐以唱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又其后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两句。前句所言“其后”,是指李唐之后,即认为唐以后的乐府与诗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实质上是说,唐以后的乐府诗并不注重与音乐的关系了。后句所言“乐曲”,则是谓新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词,即这一时期的乐府所指主要为词体艺术。
综上所述,胡震亨之于四卷《乐通》的述论,主要表现出了这样的几个特点:其一是在乐曲的收罗方面赅备详细,用力甚勤。仅就486种唐曲而言,就较崔令钦《教坊记》325种超出了161种,其数量之多,在同类著作中几无可比。而这些曲名,又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一为新乐府名,一为词体名。以前者言,如《扶南曲》(王维)、《宫中行乐词》(李白)、《花游曲》(李贺)等,即皆是。其二为引证材料丰富,所获结论大都可以据信。这一特点在《乐通二》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有年代题意可考者之“大小曲”179种,胡震亨不仅于每种曲几乎均进行了笺注,而且都是依材料以立论的,是名符其实的“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小曲”之179种曲的笺注中,胡震亨共引用了近100起材料(没有标明书名或“×××云”者不在此列),有的还于一条笺注中引了数起,如《胡鞛子》一曲,所引《国史补》、《乐府杂录》、《海录碎事》者,即为其例。其三是充分体现了胡震亨以雅乐为主的诗乐观。对于这一特点,《乐通二》与《乐通四》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乐通二》所收罗、笺注之曲目,几乎全为朝廷雅乐的实况,即足以说明之。
三、切中肯紊的作家乐府论
在《唐音癸签》的有关卷次中,对若干具体诗人的乐府作品进行品评,是胡震亨之于唐代乐府诗进行批评的又一重要内容,这种批评,实际上就是其表现于《唐音癸签》中的“作家乐府论”。据粗略统计,《唐音癸签》共对近20位诗人的乐府诗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品评,其中,以对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王建、张藉等诗人乐府诗的批评,乃最具代表性。而其批评的形式,则主要有两种:一为引他人之评论以进行品评,这类批评主要散见于《评汇》诸卷之中;一即胡震亨本人的评论,这类批评多见于《诂笺》、《丛谈》诸卷中,二者合而为一,即构成了胡震亨对唐人乐府诗的一部专论。为便于认识,兹举《评汇》、《诂笺》诸卷中有关李白、杜甫乐府诗的批评如次,以为例说。
(一)对李白乐府诗的品评
《唐音癸签》对李白乐府诗之品评,《评汇》、《诂笺》诸卷均有,且各具特点,如《评汇五》之“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胡应麟语)、“拟古乐府者,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胡震亨语)等,即皆为其例。又如:
“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出其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构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指;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繇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作略。今人第谓太白天才,不知其留意乐府,自有如许功力在,非草草任笔性悬合者。不可不为拈出。 ”[4]87
文末有“遯叟”之自注,表明此条评语乃出自胡震亨手笔,而非“汇”他人之“评”所致。综观此条评语之所言,可知若非对李白乐府诗了然于胸者,是绝对难以作出如此之评价的,则胡震亨之于李白乐府诗的精熟度,仅此即可窥其一斑。
《诂笺》在《唐音癸签》中共有九卷,即卷十六至卷二十四。在这九卷《诂笺》中,胡震亨论及李白乐府诗者,主要有《越女词》、《梁甫吟》、《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秦女卷衣》、《丁都护歌》、《蜀道难》、《山人劝酒》、《豫章行》等,除《越女词》外,其余全部为旧题乐府(古乐府),这正与李白之于乐府诗的创作实况相契合。胡震亨对李白这些乐府诗的“诂笺”,或言其本事,或笺其字词,或揭其寓意,虽不一而足,但所言却多为中的之论,这与其曾撰《李诗通》21卷乃不无关系。如对《豫章行》的“诂笺”为:
“古《豫章行》,咏白杨生豫章山,秋至为人所伐。太白亦有此辞,中间止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两句。首尾俱作军旅丧败语,并不及白杨片字,读者多为之茫然。今强味之,如所云‘吴兵照雪海’,及‘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闻’,‘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皆永王璘兵败事也。盖白在庐山受璘辟,及璘舟师鄱湖溃败,白坐系浔阳狱,并豫章地,故以白杨之生落于豫章者自况。用志璘之伤败,及己身名坠坏之痛耳。其借题略点白杨,正用笔之妙,巧于拟古,得乐府深意者。 ”[4]230
这既涉及了“古《豫章行》”的本事、本义,更着眼于李白的生平行事,对其《豫章行》之所写进行了重新笺释,认为乃是“用志璘之伤败,及己身名坠坏之痛耳”云云,所言甚是①对于李白《豫章行》之所写,中华书局1979年版王琦笺注本《李太白文集》卷六,不同意胡震亨之此言,而认为“此诗盖为征戍之将士而言者”,乃误。。不独如此,胡震亨还着眼于艺术的角度,对李白《豫章行》进行了“用笔之妙,巧于拟古,得乐府深意”的赞许,实堪称道。其它如对《丁都护歌》、《秦女卷衣》等之笺释,亦大抵如此。
(二)对杜甫乐府诗的品评
杜甫的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共收录了12题24首,其中,旧题乐府5题17首(含《丽人行》),新题乐府7题7首。《唐音癸签》之《诂笺七》,则对杜甫 《丽人行》、《哀江头》、《哀王孙》等作进行了 “诂笺”,且重在对诗中典故与史事的勾勒。如对《丽人行》的“诂笺”为: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啣红巾。’注者作春游景色解,大憒憒!此诗纪杨氏诸姨与国忠同游事,非苟作也。《广雅》:‘杨花入水化为萍。’《尔雅翼》:‘蘋根生水底,不若小浮萍无根漂浮。’国忠实张易之之子,冒姓杨,乃与虢国通,不避雄狐之诮,是无根之杨花落而覆有根之白蘋也。又‘杨白花,飘荡落南家’,为北魏淫词,用之真切于比者。青鸟,西王母使者。飞去啣红巾,则几于感悦矣。咏时事不得不隐晦其词,然意义自明。惜从来无与发覆者。”[4]236
这一“诂笺”,既引录了《广雅》、《尔雅翼》对“杨花”与“白蘋”的注解,又指出“国忠实张易之之子,冒姓杨”,“是无根之杨花落而覆有根之白蘋也”,因而颇能新人耳目。而从最后“惜从来无与发覆者”一句又可知,胡震亨对他的这一“诂笺”乃是相当自信的。而对《哀江头》、《哀王孙》的“诂笺”,一偏于对诗中语词的笺释,一重在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如此”,虽侧重点不同,但“诂笺”的对象大体类似。而此,只是胡震亨对杜甫乐府诗品评的一种类型。
胡震亨对杜甫乐府诗品评的另一种类型,是将杜甫的乐府诗与李白的乐府诗进行比论,以从中总结出各自的规律与特点。这类批评,主要散见于《唐音癸签》的《评汇》诸卷之中,且其几乎皆为胡震亨之所言。如《评汇五》中的一条评语为:
“拟古乐府者,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谁知又有杜少陵出来,嫌模拟古体为赘剩,别制新题,咏见事,以合风人刺美时政之义,尽跳出前人圈子,另换一翻钳鎚,觉在古题中翻弄者仍落古人窠臼,未为好手。‘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两公之谓矣。 ”[4]87
胡震亨认为,李白以“拟古乐府”擅长,是当然的唐代“乐府第一手”;但杜甫则“另制新题,咏见事,以合风人刺美时政之义”,全然“跳出前人圈子,另换一翻钳鎚”,即以创作新乐府为能事。李白与杜甫,一个为拟古乐府的大家,一个为创作新题乐府的里手,二人的乐府诗既各不相同,而又具成就,故而胡震亨乃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喻之。这一比喻,既贴切,又形象,确属“两公之谓矣”。
[1]白居易.新乐府并序[M]//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52.
[2]元稹.乐府古题序[M]//全唐诗:卷四一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0:4604.
[3]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62.
[4]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
[责任编辑:孙艳红]
I206.2
A
1007-5674(2014)01-0035-05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1.007
2013-11-1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1BZW072)
王辉斌(1947—),男,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