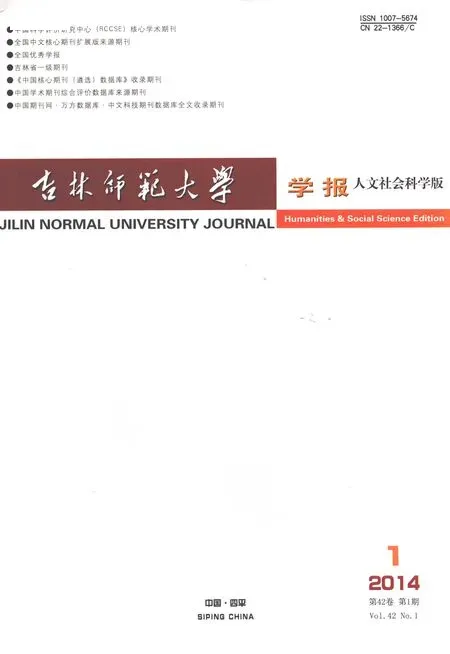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政治军事背景
2014-04-17余恕诚王树森
余恕诚,王树森
(1.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0;2.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合肥230051)
论初盛唐东北边塞诗及其政治军事背景
余恕诚1,王树森2
(1.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0;2.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合肥230051)
初盛唐时期的东北边塞诗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唐太宗为代表;第二阶段以陈子昂为代表;第三阶段以高适为代表。东北边塞诗具有丰富的内容,情感基调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将陈子昂、高适的东北边塞诗与开元、天宝时期的西北边塞诗相对照,会发现前者写边疆负面现象较多,情绪不及西北边塞诗高昂。这种差异,只有统观唐代武后至玄宗后期从国家西陲到东北的总体边疆形势、民族关系态势以及朝廷的应对策略,将相关诗歌置于初盛唐时期总体民族关系态势影响下的各战区实际状况之中,方可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
边塞诗;东北;吐蕃;唐太宗;陈子昂;高适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多发生在长城沿线特别是代北蓟辽等地,这与北方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①对此,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其长篇历史散文《内蒙访古》中曾有过充满诗意的描述,可参看。。与之相应,中国文学对于民族矛盾的反映往往多以发生于东北疆的战事为背景。顺着这种历史趋势而下,甚至可以联系到近现代文学对于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1]唯独在唐代,由于吐蕃勃兴于青藏高原,并在河陇天山一线与唐展开争斗,给有唐三百年的民族关系形势带来深刻影响,使得西疆边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唐代因之产生了总量超过一千首的有关吐蕃诗歌,其中包含了大多数唐代边塞诗名篇。尽管如此,边塞诗表现地域的转移并非一蹴而就,唐诗中书写东北边疆的篇章依然多见,从唐开国君主李世民起,一直到开元、天宝时期的诗人,都有脍炙人口的东北边塞诗作。武后朝陈子昂从武攸宜东征契丹,写有十三首边塞诗;盛唐著名边塞诗人高适一生两次深入东北边防前线,留下了二十多首关系东北边事的边塞诗,此外像祖咏的《望蓟门》、崔颢的《雁门胡人歌》、《古游侠呈军中诸将》等名作也都以开元年间东北边疆形势为背景。只是由于吐蕃因素的存在,正如东北边事不免会与唐王朝在河陇青海所进行的政治军事行动相关联,东北边塞诗有时与西北边塞诗显出反差,也同样需要被纳入唐蕃角力的大背景下加以观照,才能获得较全面的认识。本文即拟依据唐前期边防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吐蕃勃兴对唐王朝边防全局的影响,探讨初盛唐时期东北边塞诗的内容特色及其成因。
一、突厥之败与唐太宗的东北边塞诗
如果将是否有实际的边疆战事背景作为区分一般文人拟乐府与边塞诗的重要标准,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可算是唐代第一位边塞诗人。尽管历来的诗评家,从王世贞到闻一多,对其诗歌成就多有微词,但是唐太宗少随父兄征战四方,开创有唐三百年基业,此后又缔造了贞观之治,基于这样的独特经历与体验,诗歌创作也表现出常人难以比拟的襟怀气度,而最能代表这种襟怀气度的,就是他的边塞诗。现存太宗边塞诗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围绕战胜突厥而创作的诗歌,另一部分则是辽东之役途中所作诗歌。从表现地域上看,太宗的边塞诗西不逾灵夏,而向东则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属于典型的东北边塞诗。
突厥作为漠北强国,威胁中原由来已久,隋唐之际,突厥不仅屡屡直接寇扰边境,甚至制造了像唐高祖武德九年(626)颉利可汗兵临长安城外那样的严重事件,同时更深度介入当时的群雄逐鹿,支持各种割据势力,严重阻碍了唐初的统一事业①在隋唐之际的割据者中,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李轨、高开道、窦建德及刘黑闼等都曾倚突厥为援,甚至连唐高祖太原起兵之时,亦向突厥称臣纳款,突厥因此“成为操纵诸割据者,制造战乱的根源”。(范文澜语)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寅恪等人认为唐太宗统一天下实质上是从当时的亚洲霸主突厥手中夺得,是具有相当道理的。。贞观四年(630),唐朝军队一举俘获颉利可汗,终结了困扰中原数百年的突厥之祸。此后十余年间,唐太宗进一步向西开拓疆域,使唐王朝的统治与声威拓展到中亚地区。作为一位具有强烈历史感的君主,唐太宗清楚自己的武功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在诗咏中多次提及征讨突厥的胜利。贞观二十年秋,太宗巡幸西北,在灵州被西北诸族奉为“天可汗”,他喜而作诗序其事云:“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2]正是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进行自我表彰。这种充满自信的志得意满在另外一些诗中亦屡有表露,如“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幸武功庆善宫》)、“绝域降附天下平”(《两仪殿赋柏梁体》)等。究其创作背景,均缘于当时唐王朝对以突厥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所取得的军事胜利。
位于今天朝鲜半岛 (也包括中国东北辽河以东的部分土地)的高丽、新罗、百济等海东三国,自古就与中原地区有着紧密联系,受汉民族文化影响很深。但从隋文帝起,中原王朝几代君主出于大国自尊的心理,均企图以武力将半岛纳入统治范围内。贞观十九年,太宗亲自统领大军再次征讨高丽。在从贞观十九年早春到初冬的近十个月里,太宗和他的开国臣僚们一路走一路歌,仅太宗本人,现存作于此次出征途中的作品,即有《春日望海》、《于北平作》、《五言诗悼姜确》、《辽城望月》、《五言塞外同赋山夜临秋以临为韵》、《执契静三边》、《宴中山》七首。辽东之诗,是太宗边塞诗的又一重要组成。
太宗征辽诗作,贯穿自出征至班师的全程,描写地域则涵盖了包括蓟北、辽东的环渤海地区,是唐诗史中第一组完整的以作者边疆经历为背景的边塞诗。从艺术上看,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组边塞诗塑造了一位既勇武豪情又仁民爱物的帝王形象。太宗自弱冠之年起驰骋沙场,锻造了他勇武顽强的个性品质。东征高丽,太宗迫切希望获得一种巅峰体验。征辽诗中常常可见喷薄欲出的豪情,如《春日望海》云:“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寥寥十字,就将一位坚定从容的帝王与统帅的恢弘气度传达出来,颇可与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名句相呼应。《辽城望月》诗中有云:“驻跸俯九都,停观妖氛灭。”作此诗时,唐军已经攻下辽东城,从这两句诗可以想见作者在胜利之后登高远眺的喜悦与自信。“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春日望海》)还是在出征途中,太宗即曾遥望沧海,思接古今,脑海里浮现了那些像他一样开疆拓土的前代雄主,他愿意将自己与他们相提并论,希望超越他们。而当敌人终于向自己俯首,他怎能不从心底里迸发出难以抑制的豪情?
展现在这组边塞诗里的唐太宗,也时时流露出仁民爱物的情怀。辽东之役发动时,太宗年近五旬,已不再是当年那位孤胆秦王,而他背后的那些与之一生相随的将领谋臣,也都陆续成为老人。因此对于这个开国团队而言,此役仿佛是对峥嵘岁月的追忆,仿佛是对他们在战火硝烟中所缔结友谊的重温。七首诗中,至少 《春日望海》、《山夜临秋》、《执契静三边》、《宴中山》四首诗作于君臣宴乐的环境中,太宗首唱,群臣赓和。仅以《宴中山》一诗为例,许敬宗作序云:“皇帝廓清辽海,息驾中山,引上樽而广宴,奏夷歌而昭武。于时绮窗流吹,带薰风而入襟;雕梁起尘,杂飞烟而承宇。更深露湛,圣怀兴豫。爰诏在列,咸可赋诗。”核诸太宗自道所谓“回首长安道,方欢宴柏梁”,可见其当时兴致之浓。表面上看,太宗的游宴赋诗,与一般的君臣宴豫并无二致,但如果细按创作的背景、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就会发现如此的君臣相得实在来之不易。岁月无情,战争更是残酷,当远征尚未完全展开之时,岑文本这样的老臣已经病逝,而攻城略地,又使一大批唐朝将士殒命。《五言悼姜确》[3]一诗中,太宗深情追忆了这位从早年即追随自己的将领,高度评价他的韬略与忠心:“未展六骑(奇)术,先亏一篑功”,对姜确在胜利前夜的殉国,表示了真切的惋惜。此诗后云:“凄凉大树下,流悼满深衷。”在这些文臣武将看来,太宗对他们有知遇之恩,他们愿意舍身以报。而太宗本人也能以一片赤诚对待他的臣子,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样历久弥坚的推心置腹,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不多见的②《资治通鉴》记载了多条太宗仁民慈爱的掌故,如太宗与长孙无忌为布衣交,用之为宰相。贞观二年正月无忌罢相,有上表构陷者,太宗不以为疑,以表示之,并向百官公开表示:“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卷192)征辽东时,太宗亲为李思摩吮血(卷197),为契苾何力敷药,掩埋阵亡将士骸骨(卷198),均可为证。。
太宗辽东诗在艺术上的第二点值得称道之处,则是对环渤海地区乃至朝鲜半岛山川风物的描绘。中古以前,由于中原王朝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河中上游,东北地区的自然人文,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并不充分。此前只有曹操的《观沧海》以描写渤海景色而成为名作。在这七首辽东诗中,太宗则首次将环渤海广阔地带的山川景物、节候风光作了有序呈现。《于北平作》写卢龙塞外之景:“遥山丽如绮,长流萦似带。海气百重楼,岩松千丈盖。”《辽城望月》写夏初的辽东月色:“玄兔月初明,澄辉照辽碣。映云光暂隐,隔树花如缀。”《山夜临秋》作于“边城炎气尽,塞外凉风侵”的仲秋时节,当时太宗已经班师,诗中追忆了朝鲜“水静霞中色,山高雨里心。浪帏舒百丈,松盖偃千寻”的三千里江山,也描写了东北地区“连洲经鸟乱,隔岫断猿吟。早花初密菊,晚叶未疏林”的旖旎秋光。《春日望海》一诗,虽然作于和大海尚有一段距离的定州,但诗中却遥想了“浮潮云卷色,穿浪日舒光。照岸花分影,迷烟雁断行”的滨海春色。在同样作于定州的《宴中山》一诗中,太宗云:“昔去兰萦翠,今来桂染芳。云芝浮碎叶,冰镜上朝光。”辽东之行从春到秋,而所作诗歌也将这一地区的春光秋色进行了细致点染,使东北自然风光之美得以在世人面前展示。
唐太宗的边塞诗,无论是对武功征战的追怀记录,还是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总体上表现出一种阔大气象,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太宗本人的性格气质与人生经历等个体因素外,根本上需要从唐初军事胜利特别是打败突厥,解除传统安全威胁的大背景中寻找成因。如前所述,突厥为祸中原数百年,到隋唐之际发展到了顶峰。但是唐太宗即位之后,仅用数年时间便决定性地击败突厥。突厥灭亡,为唐王朝的北疆营造了数十年的安宁局面,使唐在东亚大陆建立起绝对优势,此后唐王朝灭高昌、开西域、定吐谷浑、服南粤,一路高歌猛进,而且基本上都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作为这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的最高领导者,唐太宗自然能从中体验到巨大的成就感,并最终体现在有关边塞诗的创作中。贞观十九年的辽东之役,虽然最后因为朝鲜军民的殊死抵抗而草草收兵,太宗本人也追悔莫及。但战役之所以中止,很大程度上仍是太宗从战略高度出发,主动撤退的结果,特别是战役本身实为一次象征意义远超实际意义的军事行动,是一次对本朝军事实力以及素质、忠诚的盛装检阅与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征讨辽东的目的同样达到。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能创作出具有很高艺术感染力与认识价值的东北边塞诗,他本人也才能成为唐代边塞诗发展进程中的开风气人物。
二、“东拒复西敌”——高宗武后朝的东北边塞诗
唐太宗苦心经营而来的地区政治军事优势到高宗统治前期仍在持续甚至扩大,但是从高宗龙朔年间(661—663)起,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西疆的吐蕃在对外扩张中,逐渐将势力渗透进唐河陇天山一线,唐蕃大战在所难免;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不仅有北突厥复兴,而且奚与契丹等东北部族亦开始寇乱唐东北边境,造成了唐东西边防的全面紧张,吐蕃与突厥并犯边塞的局面贯穿了整个七世纪下半叶①参《册府元龟》卷133“帝王部·褒公第二”条;同书卷323“宰辅部·总兵”条;同书卷655“奉使部·智藏”条。,直到唐玄宗即位之初,仍未得到根本改观。不过总的来看,吐蕃在唐玄宗开元十年(722)之前对唐王朝所造成的威胁仍不及东北疆的突厥、奚与契丹严重。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人,在已经开始注意西疆吐蕃之患的同时,仍然将最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东北。高宗武后朝的边塞诗,便折射了当时唐王朝东西疆形势同时紧张的现实,其中反映东北边事的东北边塞诗,仍占有主体地位。
高宗武后两朝,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东北边境再次出现动荡,突厥骨咄禄、默啜频频寇扰,造成长城以北全线紧张;原本已经归顺的奚与契丹乘机重新投靠突厥并屡屡犯边。形势迫使唐王朝仍将主要兵力投置东北边塞设防。初唐著名诗人沈佺期的名作《独不见》,就反映出当时的东北边疆形势: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按,此诗是初唐最著名的一首七律。《文苑英华》题作《古意》,《全唐诗》题作《古意呈乔补阙知之》,陶敏等即依 《全唐诗》题系此诗作于武后垂拱元年(685)左右。[4]但乔知之本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从军的地点在河西张掖及居延海一带,与诗歌中所写到的辽阳、白狼河等地相隔甚远②按,白狼河即今大凌河,据严耕望所考,此地在营州之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当防御契丹进攻之要塞。参严耕望著:《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卷,第1752页。,因此必然有需要弥合之处③按,据《资治通鉴》卷206"(武后神功元年(697)六月)左司郎中冯翊乔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条《考异》所引卢藏用《陈氏别传》、赵儋《陈子昂旌德碑》等文所述,万岁通天元年(696),乔知之以左补阙职从建安王武攸宜北征契丹,陈子昂诗中多有述及。对此,罗庸在其《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中提出质疑,认为乔氏以左司郎中而非左补阙职受戮,时或当在天授二年(691)云云(第36-39页)。但是细按罗氏所言,并未提出过硬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考异》之说。而假如《考异》之说成立,也就是说,陈子昂两次北征均与乔知之同僚,且乔均居左补阙职,那么这首《古意呈乔补阙知之》,或可被系于万岁通天元年前后。。而从中间二联,特别是“九月”、“十年”等时间名词与“辽阳”、“白狼河”等地理名词中,至少可以读出,在沈佺期生活的时代,对东北部族的防御仍然牵系着唐王朝相当比重的国防力量,并且旷日持久,否则,就难以理解这位“卢家少妇”的良人何以要征戍辽阳十年不归。在沈佺期的诗中,像“辽海”、“黄龙戍”等明确指向东北的地名并不鲜见④在《关山月》诗中,沈佺期说:“汉月生辽海,朣胧出半晖。合昏玄莬郡,中夜白登围”;《杂诗三首·其三》中,诗人说:“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这几处地名都位于东北。,这些都足以表明,唐王朝针对东北部族所展开的政治军事行为依然吸引着全社会关注的目光。
尽管如此,沈佺期同时也有“西流入羌郡,东下向秦川”(《陇头水》)的诗句,虽然诗中并未直接出现征战之词,但显示出陇西的羌族气息已经引起诗人的注意⑤吐蕃是由羌族建立的国家,范文澜说:“羌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唐时吐蕃国勃兴,分立的诸国合并成为统一的大国,尤其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更光辉的标志。”(载《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编,第2册,第446-447页。)因此沈佺期诗中出现“羌郡”一词,表明河陇地区的吐蕃因素开始出现并引起注意。。实际上从高宗龙朔年间起,唐与吐蕃就已经从始交阶段的接触试探,逐渐走向争胜夺利,特别是吐蕃向天山一带的扩张影响了唐在西域的利益,使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咸亨元年(671),唐蕃在青海爆发了著名的大非川之役。诗人骆宾王随军出塞①按,骆宾王从军西域的经历,由清人陈熙晋首揭,近来杜晓勤等人在《从阿史那忠墓志考骆宾王从军西域史实》(文载《文献》2008年第3期)一文以地下史料补充完善了陈说,认为咸亨元年骆宾王出塞实为“随阿史那忠西行远征,对西域诸蕃部进行‘安抚’、‘劳问’”,是唐为了配合同时在青海一带展开的由薛仁贵等领导的抗击吐蕃军事行动而采取的协同措施。,沿途创作《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等十首诗,是唐诗史上第一组描写西部边疆风光的边塞行旅诗。只是由于诗人彼时过多停留在个人愁苦之中,因此才并未于诗中留下唐蕃初战时的珍贵民族关系信息。咸亨元年之后,唐蕃之间冲突渐多,随着这种唐王朝同时应对来自东、西两个方向边疆危机的局面继续向前发展,诗歌在这段时间也随之出现了将东北、西疆之患一并纳入描写范围的独特现象。如初唐崔湜的《塞垣行》(一作崔融诗)开头八句:
疾风卷溟海,万里扬砂砾。仰望不见天,昏昏竟朝夕。是时军两进,东拒复西敌。蔽山张旗鼓,间道潜锋镝。
第五句“东拒复西敌”其实是对于高宗武后时期唐王朝边防格局十分具有象征性的揭示。而同样被认为是崔湜所作的《大漠行》(一作胡皓诗),则更加切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边疆态势,此诗前十句云:
单于犯蓟壖,骠骑略萧边。南山木叶飞下地。北海蓬根乱上天。科斗连营太原道,鱼丽合阵武威川。三军遥倚仗,万里相驰逐。旌旆悠悠静瀚源,鼙鼓喧喧动卢谷。
其中出现的“蓟壖”、“武威川”近十组地理名词基本上可被归纳为东、西两个方向,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以突厥、奚、契丹为代表的东北边患与以吐蕃为代表的西疆边患同时出现的重要表征。这首诗的后面还出现“右西极”与“左北平”对举现象,在高宗武后朝的许多边塞诗中都有表现,在传统的观念中,一般认为这只是一种概括描写,然而如果进一步追究,为什么像这样的东西兼举的现象只在七世纪下半叶至八世纪初这几十年的诗歌中才集中出现?只要明了当时唐王朝在边防上呈现出东西两线作战的态势,就会理解诗歌中所出现的这种特殊现象实际上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军事根源。
作为初唐百年最重要的诗人,陈子昂的个人经历与创作,似乎更能反映出高宗武后朝的边疆形势及其影响下的东北边塞诗创作概况。陈子昂的边塞诗创作,最主要的还是以他两次从军北部边塞的经历,特别是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从梁王东征为背景的。早在垂拱二年,陈子昂从乔知之北征,期间所作 《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等文中,诗人已经对唐王朝的北疆边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分析。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原先归附的东北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谋叛,先下营州,数月间榆关之外悉为攻陷,到本年十月,契丹兵锋直指冀、瀛诸州,史称“河北震动”②《资治通鉴》卷205,“(万岁通天元年十月)孙万荣收合余众”条。,陈子昂即于此时进入武攸宜军幕。这次契丹之役,唐王朝进行得十分被动,虽然有武三思、武攸宜两位武氏宗亲前后指挥,仍一败涂地。连王孝杰这样纵横西北的名将,竟然在此处遭致败没③《资治通鉴》卷206:“神功元年(697)春,三月,戊申,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陈子昂既以参谋之职佐任边幕,面对战场上的失败,更希望能提供建议,然而刚愎自用的武攸宜对于陈子昂的建言献策却予以拒绝④《新唐书·陈子昂传》云:“次渔阳,前军败,举军震恐。攸宜轻易,无将略。子昂谏曰:(云云),攸宜以其儒者,谢不纳。居数日,复进计,攸宜怒,徙署军曹。子昂知不合,不复言。”。这当然让诗人感到怅惘、愤懑,作于此间的《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六首》等诗,诗人频频表露出岁月空度,面对边境危机而报国无门的遗憾:“而我独蹭蹬,语默道犹屯。征戍在辽阳,蹉跎草再黄”(《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这种遗憾苦闷的心境,到了《登幽州台歌》则郁结到了极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寥寥四句,纵有解读不尽的丰富内容,但是诗人内心郁结的根源,却是他对东北边事无所起色的苦闷与担忧。
契丹之役的失败,固然让人叹息,但是如果以更宏阔的眼光看问题,这次失败乃至于高宗武后时期唐方在应对突厥等东北部族时屡屡受挫局面的形成,除了具体的人事因素 (如唐王朝内部的军政腐败)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吐蕃已经崛起于唐西疆,突厥骨咄禄部也在西北扰乱,以唐王朝的实力,难以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东拒复西敌”的局面必然造成唐王朝在边疆上的被动。对此唐内部的有识之士早已有预见⑤《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仪凤三年九月),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瓘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因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万岁通天元年东征契丹的失败,恰恰验证了这种预见,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试摘引关于陈子昂参加武攸宜军幕前后《资治通鉴》中有关唐王朝西疆边防情况的记载:
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
(正月)丙午,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击突厥。
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
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
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
(九月)丁巳,突厥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
以上记载,表明此二年西北边境应对吐蕃、突厥的战争,实较东北战事更加频繁,因此唐王朝不能专力对付东北,军事进展显然会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陈子昂基于个人失意和对东北战局的忧虑,诗中缺少明亮的色彩与乐观的情绪,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绥靖政策主导下的东北边塞与玄宗朝东北边塞诗
盛唐诗人崔颢的名作《雁门胡人歌》云: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
此诗作于诗人开元后期入河东军幕期间,描写了一幅既生动热烈又和平安宁的边疆风情画,其中包含着一种喷薄欲出的侠气。这种侠气在崔颢的其他边塞诗中也屡有表露,如同样作于军幕的《古游侠军中诸将》,前八句云: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刻画出一位“英姿飒爽,有风云之气”(《唐贤三味集笺注》)的“游侠士”形象。在崔颢的这些诗篇中,其观察的焦点往往集中在那些生活于边疆的个体(“雁门胡人”与“少年”)身上,而且全篇往往令人振奋激越甚至充满着桀骜倜傥之风概。之所以如此,除了诗人自身的性格气质外,与当时的时代环境特别是开元前期东北边防形势同样有着很深的关联,这就是诗人所说的——“闻道辽西无斗战”。
作为地处东亚大陆中心的王朝,唐需要同时应对多个方向的军事威胁,这种局面从高宗后期开始,就在不断发展着,也让唐腹背受敌,不堪其扰。从当时的周边民族形势来看,北部的突厥虽然在其首领默啜、骨咄禄的前后统领下,一度气势汹汹,但内部毕竟分崩离析,强弩之末已属难免;东北的奚与契丹此时毕竟仍未积聚起与唐抗衡的足够实力;西域等地民族众多、本身缺乏统一领导,同样也难以产生较大威胁;唯独西方的吐蕃,正处新起之时,从松赞干布起,几任赞普均雄心勃勃,又有强臣主持军政,汲汲于对外扩张,对以关陇地区作为核心统治区的唐王朝造成威胁最大。因此从武后后期开始,唐已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应对吐蕃进攻。为此,唐逐渐对突厥与契丹等族采取绥靖政策以安定东北边疆形势。公元707年前后,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又置烽燧一千八百余所,史称“自是突厥不得度山(阴山,笔者按)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旧唐书·张仁愿传》)突厥后来的确再难有大的作为,唐玄宗开元五年(717),突厥默啜被唐将郝灵荃斩杀,其后一蹶不振,作为一支独立的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突厥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突厥的衰败,使东北部族又陆续向唐归附,为了防止东北再生变故,唐玄宗以和亲等策一意安抚,对此,在英国学者崔瑞德所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曾有过很好的评述。[5]正是由于边防策略的改变,玄宗即位之后的几年间,东北局面曾经一度好转。开元九年,兰池州胡酋康待宾被斩,塞北形势进一步安定,玄宗喜而作《平胡诗并序》、《旋师喜捷》等诗相庆,引起裴漼、韩休等一干朝臣奉和。[6]开元十年、十一年,张说、王晙先后赴朔方巡边,唐玄宗与群臣均作诗相送,诗中对于历经艰辛而取得的边防胜利成果,予以了真挚讴歌。
开元十年以后长城以北直至辽东前线这一轮乂安居面的重获,并不是短暂的。由于突厥的衰亡、东北的归顺,整个长城以北,从辽东到渭北泾原,都没有大的集中性战事发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开元末。尽管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唐王朝仍维持着相当的常备军,但是边防军更主要的职责还是对边疆进行控制,并不需要频频征战,所以尽管祖咏笔下的蓟北前线仍是“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望蓟门》)的一派严整肃穆的阵势,但背后也折射出刀枪入库、久无大战的实情。
高适于开元十九年秋北上蓟门,当时的东北前线在唐玄宗保守防御策略的引导下,已经多年无大战①高适《营州歌》中“虏酒千钟不醉人”句即是这种边防态势的生动写照,可与崔颢《雁门胡人歌》对读。。对于这种局面,诗人并不认同,诗人认为唐王朝在东北边疆上所采取的防御策略过于保守,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除契丹等东北部族给边疆带来的祸乱。最能体现高适主张的就是其《塞上》一诗,诗云:
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边尘涨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
此诗作于高适东出卢龙塞时,他通过对边防前线的实际察访,发现驻守于此地的唐朝军队力量并不弱小,但是面对边尘北涨、虏骑南侵的形势,却并不能有效制止。“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二句,是诗人经过思考后,对之所以形成当下局面的原因所得出的结论。所谓“和亲”,是指开元五年唐玄宗以永乐公主下嫁契丹首领李失活等事,而所谓“转斗”,实际上就是节节抵抗、消极防御的意思,在诗人看来,都不是“长策”、“远图”,只有像汉代名将那样“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边疆危机,才是真正的上策。“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诗人愿意为之竭尽智力,而当他的志愿得不到边镇主帅的认同时,则从心底感到了失意和苍凉。
随着在蓟北等地体验得愈加深入,诗人对于当时边镇的很多现象也愈加不解。譬如《蓟门五首》其三:
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
诗人认为,国家的军力本来完全可以开拓穷荒,扫除边患,为什么要一意取悦讨好胡族,以至不惜以牺牲自己士兵的生活待遇为代价,将大量财帛用于贿赂“降胡”,赎买和平呢?诗人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极度苦闷,最后甚至索性露出使性之辞:
随波混清浊,与物同丑丽。……倏若异鹏抟,吾当学蝉蜕。
——《赠别王十七管记》
高适首次北上,对于边镇各种所谓阴暗面、腐败面的暴露批判,无疑是深刻而尖锐的,但是像这样的边疆腐败,并不只是存在于东北,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为什么高适对于东北边镇的腐败予以强烈抨击,而此后佐河西哥舒翰幕期间,却不着一词?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不过东北边镇应对契丹等族的被动局面,与河西军幕征讨吐蕃的高歌猛进大相径庭,无疑是造成诗人关注焦点转移 (甚至有意选择)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动机,当开元二十年信安王李祎大举兴兵抗击契丹并大获全胜时,诗人再无暴露批判之心思,转而热情讴歌唐朝军队的巨大胜利,赞扬主帅的赫赫战功。在《信安王幕府诗》中,诗人云:
帝思麟阁像,臣献柏梁篇。振玉登辽甸,摐金历蓟壖。度河飞羽檄,横海泛楼船。北伐声逾迈,东征务以专。讲戎喧涿野,料敌静居延。军势持三略,兵戎自九天。朝瞻授钺去,时听偃戈旋。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云端临碣石,波际隐朝鲜。夜壁冲高斗,寒空驻彩旃。倚弓玄兔月,饮马白狼川。庶物随交泰,苍生解倒悬。四郊增气象,万里绝风烟。关塞鸿勋著,京华甲第全。落梅横吹后,春色凯歌前。
从皇帝选将,写到誓师出征,再到完胜回朝,京都受赐,将整个抗敌入侵的过程全景式地展现出来,毫不吝啬地使用大量谀颂之词,与此前诗人所创作的边塞诗情感基调相隔天壤,根本上就是由于诗人从信安王出师的盛大场面中,看到了建功立业的重大希望。这种希望使他扫却了先前所体验到的所有阴霾。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开元二十年信安王李祎的东征确实大获全胜①《资治通鉴》卷213:“(开元二十年二月)乙巳,(李)祎等大破奚、契丹,俘获甚众。”,然而,统观整个玄宗时期,特别是开元年间的边防形势,东北战场总体上的被动局面,并未就此得到根本改观。高适的名作《燕歌行》,主要就是写开元二十六年前后东北部族对唐王朝东北边境严重侵扰,以及唐朝军队抵御外族入侵虽英勇顽强却损失惨重的沉痛现实②按,此诗主旨向来聚讼纷纭,主要有刺张守珪隐败冒功说、追述张守珪瓜州空城计说、讽安禄山说等,参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89页。尤其是诗乃讽刺张守珪隐败冒功的说法,一直十分盛行,实际上这一说法究难成立,笔者将另文讨论。。
问题在于,为什么唐朝军队会遭遇如此重创?过去的研究,单单抓住“美人帐下犹歌舞”一句,将失败完全归因于东北边镇的军政腐败。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类似的腐败并不只存在于东北,仅仅以此来追究,并不能真正揭示出问题的根源。实际上,东北战场之所以遭遇惨败,还是应该从唐边防全局特别是西疆吐蕃的倔强中来寻找成因。[7]如前所述,自唐高宗后期以来,唐蕃矛盾逐渐上升,几经曲折,到了玄宗即位之后,吐蕃已成为唐王朝最大边患,心高气傲的唐玄宗也将解除吐蕃之患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为了击退吐蕃,就不能不将边防的重心放在西北,大的方针政策之外,具体的兵力、财物与人员的调配,都要优先考虑西北,开元年间给吐蕃进攻造成巨大阻碍的唐朝名将王忠嗣,一度竟然一身佩四将印,到了天宝初年,唐玄宗甚至把全国镇兵的60%都部署于西部边境,用于防御和反攻吐蕃。这样就难免会造成东北边防力量的被减弱。《燕歌行》中“胡骑凭陵杂风雨”等描写,反映出外族实力的强盛与进攻的凶猛,更反映出在东北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所以尽管我军士气并不低 (“男儿本自重横行”),且素质很好(“死节从来岂顾勋”),但本地的防御力量毕竟不足。诗中有“校尉羽书飞瀚海”之句,历来未有确解,但据当时唐王朝的用兵情况看,应该说的是东北边镇需要从驻扎于三受降城等地的朔方军请求支援③对此,笔者将另文申述考证。。然而,从朔方到幽蓟,东西何啻千里?面对东北突如其来的战争,援军想要在短时间内驰援,的确十分困难。更重要的是当时西线兵力正与吐蕃进行鏖战,因此更难抽出足够兵力。“力尽关山未解围”,之所以遭遇惨败,本质上是由于东北本地军民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而造成的,“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两句,所反映的正是当时的兵败场景。对于边疆失败,高适自然痛心,自然要暴露感慨,这诚然是诗人的可贵之处。然而诗人囿于时地,未必即能做到从全局上考虑问题。实际上,只要充分注意到开元后期唐与吐蕃在西疆所展开的战事,就会明了东北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难免的。兹不妨再摘录《资治通鉴》中有关开元二十五年、二十六年西疆的军事态势,以供参照:
开元二十五年(737)
(二月)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
开元二十六年
三月,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鄯州都督,知陇右留后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为威戎军。
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萧炅为河西节度使总留后事,鄯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仍毁所立赤岭碑。
七月,杜希望将鄯州之众夺吐蕃河桥,筑盐泉城于河左。
九月,吐蕃大发兵救安戎城,(王)昱众大败,死者数千人。昱脱身走,粮仗军资皆弃之。
从上引诸则材料可见,开元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唐蕃在西部争斗不止,而且朝廷从河西、陇右到剑南,分道经略吐蕃,试图以全线进攻之势将其逼退。在这种情况下,对东北军事策应不够及时,以致将士被围,长期困守孤城,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说正是基于唐王朝在西北布置重兵,汲汲于反攻吐蕃,并一度处于优势,而在东北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8]的总体边防格局,同样是开元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王维出使河西,唱出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使至塞上》)、“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出塞作》)的嘹亮歌声,而高适则只能感叹“孤城落日斗兵稀”、“力尽关山未解围”的东北军事失败。东西两边,悬差如此,其实只要追讨当时的边防实际,就并不足怪。
如果说唐王朝在当时的边疆事务处理上确有失误,那么这种失误应该在于,唐王朝特别是玄宗本人可能过于夸大了吐蕃的危害性,特别是开元中期之后,吐蕃自知与唐结怨失大于得,而唐方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对于吐蕃的防御或反攻要适可而止,有所节制。因此在双方有条件也有可能再次调整唐蕃关系、再次实现边境和平的背景下,唐玄宗仍然不愿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处理唐蕃关系,反而一意孤行,对吐蕃穷追猛打,不仅严重损害了唐蕃友好的大局,也使唐王朝对于东北边事的处置受到损失,到后来甚至不得不依靠安禄山这样有东北地域与民族背景的蕃将来维持①《旧唐书·安禄山传》云安禄山乃“营州柳城胡也”,《新唐书·史思明传》:“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与安禄山共乡里。”,从而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由此看来,《燕歌行》诗中所描写的东北军事失败,以及《蓟门五首》等诗所揭露出的边镇军政腐败问题,之所以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唐王朝全力应对吐蕃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离开这一点,孤立地看待玄宗时期的东北边疆形势以及产生于其中的东北边塞诗,所得出的结论,与实际情形难免会有出入。这或许也是阅读高适等人东北边塞诗时,所需要有的“同情之理解”(陈寅恪语)吧。
[1]常彬,杨义.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朝鲜叙事[J].中国社会科学,2010(2):185-199.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陈尚君.全唐诗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662.
[4]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298.
[5]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97.
[6]岑仲勉.突厥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8:417.
[7]王树森,余恕诚.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J].民族文学研究,2011(5):71-77.
[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327.
[责任编辑:王金茹]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Northeast Frontier-styl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Their Political and Military Background
YU Shu-cheng1,WANG Shu-sen2
(Chinese Poetry Reserch Center,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 China;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Anhui Province,Hefei,Anhui 230051,China)
The northeast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The representative poet of the first stage is Tang Taizong;the second stage is represented by Chen Ziang;the third stage is represented by Gao Shi.The northeast frontier poems are rich in content,and the emotional keynote presented phase changes.especially take Chen Ziang,and Gao Shi's northeast frontier poems to contrast with the Northwest Frontier frontier Poems of Kaiyuan-Tianbao period,we will find the former writing more negative emotions tha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fortress poem.This difference,only with the overall frontier situation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western and eastern,ethnic relations situation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take the poe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ach of the war situation,can get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m.
Frontier-style Poetry;northeast China;Tu-bo;Tang-taizong;Chen-ziang;Gao-Shi
I206.2
A
1007-5674(2014)01-0022-07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1.005
2013-12-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编号:11BZW039)
余恕诚(1939—),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唐代诗歌;王树森(1986—),男,安徽合肥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唐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