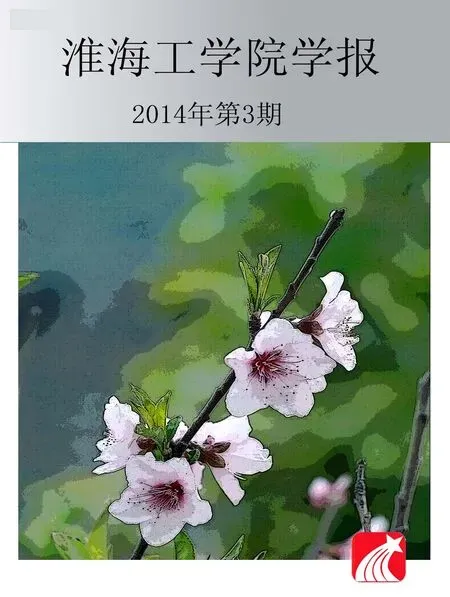皇帝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权力的博弈
——读《叫魂》*
2014-04-17沈江茜胡晓晨
沈江茜,胡晓晨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叫魂”事件升级的原因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史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1]1流行于整个中国乡土社会的“叫魂”深根于民间风俗文化,并不是1768年特有的现象,然而为什么会在乾隆年间从江南发端后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升级成事件,引发全国性的清剿呢?孔飞力教授在收集和考察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找到了其蔓延的原因。从中国民众传统的宇宙观来看,人们相信身体和灵魂可以分离,而通过一些法术的力量可以从头发中摄人魂魄,这种意识恐慌一直深深地存在于民众的信仰里;从经济上来看,繁荣盛世的背后实际隐藏着人口过度增长、物价上涨以及环境恶化的威胁,人们对能否通过辛勤劳动来改善他们的境况产生怀疑,对社会、陌生群体充满了敌意和焦虑;从政治上看,谋反与汉化是清朝统治者尤为重视的两大内容,头发问题一直是满、汉之间冲突的焦点,“留头不留发”早在清初就成为了一种表明归顺的象征,因而乾隆皇帝有理由相信这一事件与谋反存在关联,加之他对现行官僚体制的不满和对满族日益汉化的抱怨,故而十分重视和关注“叫魂”事件。
二、从“叫魂”事件处理过程看皇帝与官僚的博弈
“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底层老百姓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言与真实,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2]普通民众都忙于寻求方法进行自我保护,以对抗不可预知的妖术。位居九五之尊的乾隆皇帝同样寝食难安,他过于敏感地将这一事件与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阴谋相挂钩,紧密关注叫魂案件进展,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和督促地方官员进行清剿,力图尽快弄清和擒获叫魂恐惧的幕后元凶。而处于皇帝和民众之间的官僚阶层更是焦头烂额,不得不在两者之间穷于应付。
官僚满腹经纶,对叫魂妖术断然难以相信,却又担心民众恐慌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危及地方治安,使得乌纱帽不保,因而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运作,他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采取消极的缓和措施,以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围绕着这一事件的处理,掌握专制权力的皇帝和运用常规权力的官僚之间展开了一场博弈,这场博弈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展开的。
一方面,官僚阶层极力控制信息的传递,试图运用常规权力处理事件,并以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抵制皇帝的专制权力。在“叫魂”事件发生的前两个月,没有一个省级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妖术”案件,他们的应对之道大致相同,没有人小题大做,把它当成紧急事件向皇帝奏报。他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制止流言谣传,安抚恐慌情绪,惩治兴风作浪、无事生非的行为。当乾隆皇帝要求各省报告情况并采取行动时,除了山东巡抚富尼汉主动奏报叫魂案件情况外,其他诸省官员基本上都在用各种方式消极怠工,控制信息的上传。
江西巡抚吴绍诗在乾隆皇帝下旨后,接二连三地向乾隆皇帝奏报他是如何精心在江西全境布下了一张严密的警戒网、如何卖力地查缉“妖党”行踪、如何费心地寻找可疑人物,然而最终结果却是没有发现一起叫魂案,也没有产生任何关于审查案犯的文字和材料。据此不难推测,这一切只是吴绍诗的装模作样而已,他压根就不打算查办这个案子,也没打算将当地的真正情况告知给乾隆,仅是做足了场面,忙而不动。湖广总督定长得知几个叫魂案疑犯在湖南被抓后,立刻从武昌赶到长沙,与当地众多官员一起对案件进行审理,最终发现此案并未涉及“叫魂”,于是联名将审理结果奏报给乾隆皇帝。通常来说,定长没有必要跋涉六百多里从总督府到湖南亲自审讯案犯,更没有必要协同其他高官一同审理,其目的就在于结成稳固的同盟,统一上奏口径,摆脱个人责任。南京布政使建议皇帝整顿保甲以清查在南京地区的每一个人,两江总督高晋则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对僧道进行重新登记,他们力图将来自皇帝的紧急的、非常规要求导入日常的、习惯的轨道,将缉拿疑犯变成日常公务,回到官僚阶层的常规权力中来。
另一方面,皇帝建立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强化专制权力,达到严密控制官僚机构之目的。“皇帝用成文法规约束官僚,以确保他们在行政常规权力中办事,然而皇帝自身权力也容易被常规化。但是这套制度对官僚进行约束,同时皇帝也受到制约,即他也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不可为所欲为。官僚正好可利用由法规赋予他们的行使权力范围的便利,为自己营造一座避难堡垒。”[3]换句话说,如果官僚在行政常规权力中按程序、制度办好了分内之事,就不会受到来自皇帝的任意惩罚。书中也有提到,在每三年一次的官僚考核中,“官官相护”使得这种制度化的考核成为了一种摆设,因而乾隆皇帝为了打破常规权力的束缚,对信息控制进行争夺,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他建立了专属自己的情报信息系统,加强对官僚的监督和掌控,沿用雍正时期的密折制度,且将其由公开转为隐蔽;利用“粘杆处”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先后六次下江南“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同时他也注重挖掘人才,加强对官僚的甄别和遴选,培养自己的心腹嫡系,完善陛见制。“叫魂”案件的出现更是为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可以合理整肃官僚阶层的机会,通过将“叫魂”与谋反阴谋相联系,使得普通事件升级成最为严重的政治罪,借此充分利用专制权力冲击整个官僚体系,企图解决官僚体制存在的固有弊端,重新建立关系网络,规范官场风纪。他还利用这一次难得的机会与官僚阶层摊牌,“他抛却了君臣之间温情而又虚伪的外衣,毫不忌讳地用最严厉的辞藻来斥责那些在他看来饱受江南浮靡文化蛊惑的各级官僚”[4]。他在朱批中毫不掩饰他的焦躁、不满和猜疑,责备江苏按察使吴坛“汝实有负朕之信任,不知恩之物”,斥责湖广总督定长“以汝伎俩恶术,不过又皆审处完事。汝安守汝总督养廉耳?不知耻无用之物,奈何?”如此这般措辞在朱批中几乎随处可见。乾隆皇帝认为正是由于官僚阶层本身的腐化以及对君主的忘恩负义,他们才会对叫魂案件姑息纵容,对君主指令置若罔闻,行动不利,最终导致缉捕“妖党”无果。面临来自乾隆皇帝的巨大压力,各级各地官员不得不纷纷行动起来以表忠心和能力。
三、“叫魂”事件结局呈现出的博弈结果
“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术案子能够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1]346这样一个令人惶恐不安、震惊朝野上下的案件竟然以一种闹剧的形式收场,不免令人啼笑皆非。然而,即便如此,乾隆仍不忘维护其皇帝尊严,将错误推到官僚阶层的身上,并对一大批官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惩戒,或降职、或革职、或遭到弹劾。但这场皇帝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博弈,仍是以皇帝的失败告终的,因为皇帝虽然惩罚了一批官员,但整个官僚制度运转中存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即信息渠道闭塞、不畅通,“天高皇帝远”,皇帝难以摆脱受蒙蔽的处境,在信息获取中处于弱势;常规的弹劾考核制度模式化、样板化,加之官吏间的相互袒护,使其缺乏实质意义,流于形式,如同摆设;官吏为了规避风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容易产生惰性心理,敷衍塞责。
不管皇帝建立了怎样繁多巧妙的信息传递系统和秘密通讯渠道,只要信息的传递者仍是存在于传统制度下的这些官吏,就无可避免的受到官僚阶层本身的影响。“传统制度的特质决定了即使贵为皇帝,主要也只能依靠行政系统来监控行政系统。历史证明,几乎所有被派出负有监督地方责任的官员和机构,最后都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地方官或者机构”[5],因而皇帝对于信息的控制往往就难以实现。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于清朝政府之中,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
参考文献:
[1]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2] 张益刚,武传忠.“叫魂”背后的思考:精神控制的危机与应对——从《叫魂》看清政府的社会控制[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4-86.
[3] 谢海涛.评《叫魂》一书中的“官僚君主制”[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3):133-134.
[4] 陈艳.盛世下的信任危机——据《叫魂》一书所提供的材料来看[J].法制与社会,2007(6):656.
[5] 张鸣.叫魂的多余话[J].读书,2000(6):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