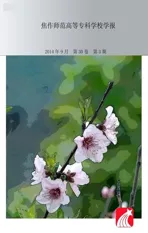河南武陟董永传说考
2014-04-17唐霞
唐 霞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覃怀文化研究所,河南 焦作454000)
董永传说是我国历史悠久、广为传播的民间传说, 唐宋以来,博兴、孝感、丹阳、东台、通州、蒲州、河间等地都声称有董永遗迹。20世纪50年代随着黄梅戏《天仙配》的上演,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更是名扬天下。2006年5月河南省武陟县与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湖北省孝感市等四个地区的董永传说经国务院批准同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而,董永传说的口头遗产在我国早已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民间传说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其分布状况是不平衡的,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传说内容,这些传说多与当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风俗文化相联系,反映了民众的认识和情感。武陟董永传说的基本母题直接落实于当地的地方风物和文化遗址,该地区在口头传承流变过程中逐步成为富有特点的中心地带之一。
一、董永传说的历史演变
董永行孝的故事在我国流传已久。山东省嘉祥县城南的武氏墓群石刻的壁画最早记载了董永行孝的故事。武氏墓群石刻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武梁祠。东汉末年,嘉祥武氏世代为官。桓帝建和元年(147),其后世子孙在武氏墓前建立祠堂。后历经沧桑变幻,洪水漫淤,现祠堂不在,余下石阙、石狮、墓碑、画像。武梁祠董永行孝的石刻壁画中右侧一老者手持鸠杖坐于独轮车之上,上有“永父”二字,左侧是董永在田里劳作,旁边刻有“董永,千乘人”,董永的上方左边有一头象,右边有一只鸟。[1]在武梁祠的画像中,仅仅展现了董永行孝的故事,并没有“卖身葬父”、“遇仙”、“送子”等情节的展现。因为该画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关于董永行孝故事的记载,而且是金石佐证,所以多为学界所认同。
曹魏时,曹植在乐府诗《灵芝篇》中也提及了董永的孝行:“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2]纪永贵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口头文化遗产——董永遇仙传说研究》中将曹植诗中董永的孝行归纳为三:借贷养父、佣作偿债、卖身葬父。[1]除了董永的孝行和武梁祠画像的内容一脉相承之外,曹植笔下还出现了“神女”这一人物形象。至东晋干宝《搜神记》所载,与曹植《灵芝篇》相比,故事情节更加丰富曲折: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3]卷一
后世董永传说的基本情节在《搜神记》中都已经具备,但是董永和织女之间还没有恩爱缠绵的感情纠葛,只是为董永助织赎身。织女在帮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与之告别。这也充分说明了孝感文化和遇仙文化是董永传说发生的逻辑前提。至此,董永遇仙传说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孝”与“仙”都已经具备,情节模式基本定型。
晋到唐的董永遇仙传说材料几乎是空白,可能是因为在《搜神记》成书的东晋时期,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该传说的巨大影响抑制了董永传说的传播。
唐宋时期,文人的诗文集、笔记及类书也转录董永的故事,但都是围绕孝感、遇仙的模式,并没有发展创新。而这一时期出现的《董永变文》、《董永遇仙传》等话本的讲唱内容和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受追求娱乐和消遣的听众所左右。话本除了主题上依然保留“孝感”和“遇仙”两个基本的情节单元之外,还增加了“送子”、“寻母”等情节,这些情节的展开极大地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展开性。
至明清时期,多地的地方曲艺、戏曲都搬演过董永的故事。由于戏曲传播手段和戏曲从业人员的观念影响,情节有所增减,主题亦有推衍,但多是细部的修剪、损益和置换。虽然在情节模式上没有再获得新的拓展空间,但是由于传说中包含的戏曲要素以及该剧由“行孝”向董永与七仙女之间“情感”的倾斜极大地满足了民众的精神追求,民间对董永传说仍充满热情。
关于董永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因在文献中缺乏实据,所以多有争论,各地也多称当地有董永遗迹。目前学界多认为董永的原型为《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卷十七)中所载的高昌侯董永,因为高昌侯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姓名相同,时间上与武梁祠壁画以及曹植、干宝的记载并不矛盾,而且从地点上看也一致,都是千乘人。
总之,董永传说应该是最早源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高昌侯董永,然后在几个地点落地生根,由百姓口耳相传,演绎成包含特定的行孝、遇仙情节的故事,逐步扩展成许多大同小异的口述版本。至唐宋时期,经过民间艺人的再创作,经过文人笔记、地方史志的文本记述的再传播,后来,各地的地方戏曲、曲艺更是多搬演此故事,逐步形成如今广泛传播的丰富的口头遗产。
以董永传说口头遗产目前的分布状态来看,除河南武陟外,主要集中在江苏东台、金坛、丹阳,山东滨州,湖北孝感,山西万荣等地。
江苏东台市称董永是江苏西溪古镇人。清嘉庆二十一年《东台县志》(卷二十二)《人物志》记载董永是西溪镇人,但其文字与干宝的《搜神记》相同,卷二十二还引清人刘积兰《彭城堂笔记》云:“广陵董永妇,王戚甾川人。”[4]并解释说:西汉甾川国造反,有一贫女七妹随父逃难到东台西溪,见董永卖身葬父,很为同情,就嫁给董永为妻,因家贫无食,七妹把藏在怀中的一张“蚕子”孵化饲养,三年后广为传开,七妹操劳过度死去,后人附会为天仙下凡。当地还保存有许多遗迹,如七姑娘采桑的“桑园”、“桑家沟”,董永卖工的“傅家舍”以及西溪十八里河口的古槐树,西溪北面的“缫丝井”等。 东台的董永故事传说呈现多而杂的特点,关于董永的传说少,而七仙女的传说则很多,而且关于七仙女、傅员外的身份都有多种迥然不同的说法。
山东滨州市博兴地区流传董永为千乘(今山东博兴陈户镇)县人,他孝顺父亲,父死后卖身葬父。守孝三年后到付家为奴*董永传说中,关于董永卖身为奴的富户姓氏,有“傅”、“付”不同的版本,此处仅与引文保持一致。。付家小姐爱上董永,被其父赶出家门,两人在麻大湖边的老槐树下定情。婚后二人男耕女织,还清了卖身的钱。付员外也被感动。因为付家小姐生得花容月貌,又心灵手巧,人们将其称为仙女。[5]
湖北孝感及其附近的安陆地区流传的董永故事和遗迹也十分丰富。相传董永为东汉时期千乘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和父亲一起至安陆(今属湖北)王母湖。传说的主体情节也包括卖身葬父、仙女下凡与其婚配,助其偿债,及槐荫送子等。为了纪念董永的孝行,此地改名为孝感。
山西万荣地区流传当地的皇甫乡小淮村是董永传说的发生地。清光绪版的《山西通志》有“魏董永”的记载。相传董永早年丧母,与父相依为命,为安葬父亲,到槐树院佣工挣钱,田家窑的田仙姑娘,为董永的至孝感动,嫁给董永。当地现存有《董氏家乘》、董永墓、“董永故里”石匾等相关遗迹,当地还有结婚时置办“合婚布”的习俗,相传此俗为纪念董永夫妇,象征夫妻恩爱,吉祥如意。
董永传说的多地流传、不断附会的现象是传说故事常有的特点。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中指出:“当地各村,不同的人所叙述着的传说,已经经过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加工,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说法,能够概括全盘,统于一尊。”[6]可见任何一个传说的口头传播过程都显现出将传说人物从远处拉向受众身边的特征。
二、武陟的董永传说及其地域特色
(一)武陟的董永传说
武陟流传的董永传说情节丰富生动,与早期曹植、干宝笔下简单的记载已有了不同的风貌。
清道光九年(1829)《武陟县志》(卷十九)《古迹》记载:
董永墓,相传孝子董永即武陟人,故有其墓,恐亦乡曲之谈也。[7]
老槐荫,在县治西北,相传孝子董永与仙女相识于此。[7]
虽然县志上对董永是武陟人的说法也并不肯定,但武陟民间多相传董永是武陟县小董村人,小董村董氏宗祠号为“良史堂”,明代时改为北岳庙。董永系史官董狐之后,生于西汉永始二年(前14)二月初三,其父董秀以打铁为生。董永幼年丧母,事父至孝,父亲去世后毅然卖身葬父,到傅村傅员外家当推磨工。[8]
由于董永纯朴善良,引起了天宫的七仙女的爱慕。七仙女不顾森严的天规,瞒着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下凡来到人间,在大槐树下遇到去傅员外家的董永,于是就请老槐树为媒,和董永结为夫妇。为了给董永赎身,七仙女答应在三日内织成一百匹黄绫。聪慧能干的七仙女在众姐妹的帮助下,一夜之间织就百匹黄绫。从此,二人度过了一段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不料,刚刚过了百日,玉帝就发现了七仙女私自下凡,遂派天兵天将将七仙女强行捉回天庭。第二年,董永如约抱回了自己的儿子“琢儿”。
关于全国各地多有董永遗迹的现象,武陟民间是这样解释的:由于董永之子“琢儿”和董卓同音,为了避免灭门之灾,董永后裔大部分举家南迁。他们分别辗转迁徙到湖北安陆(今孝感)、湖南永州、江苏丹阳和安徽等地。这些董氏族人安居下来后,不忘根本,纷纷在当地立董永衣冠冢作为祖坟,对外自称“良史董家”。留下的一小部分董氏族人后来在明成祖朱棣“三洗怀庆府”时,为求自保,有的举家外逃,有的被迫改姓(孙或傅)。此后,小董村没有了董姓人家。当地有“不见董家人,只见董家坟”之说。
除此之外,武陟当地还流传有董永幼年、董永和七仙女相亲相爱、董永路、落仙台、董永整理草药为百姓治病、董永整理民间药方被封为“药王”等等传说,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二)与当地风物特产的结合
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多数都经过了历史的概括、虚构,成为一个极具魅力的艺术典型。一代又一代的传播者往往借一点历史因缘,将不同时代的东西概括、集中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这实际上也是民众对历史人物期望的反映。这样,传说中的人物更典型、更感人,也更真实可信。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典型化的手法应用是不自觉的。
目前,小董村尚有“汉孝子董公董永之墓”墓碑;大凡村有槐荫寺;下樊村有落仙台;傅村有傅员外家后花园的石狮、石马,及董永在傅家当“推磨长工”时使用的石碾、石磨等;小董村至傅村、西大院村之间的路百姓也称之为“董永路”……传说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紧密结合,民众在讲述董永传说的时候,常常辅以实地、实物的展示和解说,使人们像相信正史一样相信董永传说的真实性。
除了各种实物之外,武陟小董村还在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形成了两个庙会,据说二月初三是董永的生日,而十一月初十是董永的受封之日。每逢这两个庙会时节,当地的群众都来祭拜董永,规模盛大,其影响涉及到周边地区而至今不衰。
此外,武陟的各种特产,民间也相传多是董永发明或最早发现的。例如传说董永和七仙女生活在一起之后,常到焦作的太行山区采集草药,发现了“四大怀药”,并用之济世救人;董永偶然救了被王莽追赶的刘秀,并利用家中现有的食材为刘秀作了一锅咸粥,刘秀食之赞不绝口,流传下来就是武陟的地方名吃——油茶;还有董永和七仙女为医治生病的刘秀,用绿豆磨成浆,再加入清热解毒的药物,制成凉粉等。
这些相关地名、景物的遗存以及民间庙会、地方特产都是董永传说在武陟流传的“佐证”,是传说粘附于地方风物的“可信”印证,这些印证,有着久远的口头传承的历史,也是武陟董永传说口头遗产认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七仙女形象的世俗化
在董永遇仙传说的发展过程中,在曹植笔下,七仙女最初称作神女,她的地位崇高、美丽神秘、不染俗尘,与董永之间没有恩爱缠绵的情感纠葛。但在武陟董永传说中七仙女的来历、社会关系有着当地独特的解释体系,七仙女几乎成为了当地妇女的一员。
首先,关于七仙女的来历,除了相传七仙女是天宫玉皇大帝之女外,武陟民间相传,七仙女的原型就是张七姐。张七姐原是南方人,父亲张老田是农民起义军绿林军的将领。绿林军失败后,张七姐逃到北方,在武陟爱上孝子董永,二人在大凡村的槐荫树下私定终身。七姐拿出其父劫富济贫的贡品黄绫替董永赎身,托言说是众姐妹一夜织成。[8]还有一种说法是张七姐的父亲张老田是现在武陟县三阳乡下封村落仙台人,娶妻王婉容。第七个女儿起名张七鲜。张七鲜天生聪明,尤善纺织,能在丝绸上织出五彩缤纷的花鸟虫鱼、人物走兽,栩栩如生。周围的妇女们看过后都夸她不是凡人,像是天上的仙女。张七鲜后来与董永成亲,被人们尊称为张七姐,后来被神化为七仙女。[8]
无论是哪种说法,七仙女的身份来历已经完全卸去神秘的面纱,作为民间女子的世俗身份逐渐得到确认。她熟知武陟当地的各种礼俗、生活习惯,发明了各种小吃,她的形象和行为与凡间女子已经没有任何区别。
汉代孝观念受到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逐步神秘化、政治化,成为董永行孝遇仙故事发生的重要社会背景。董永既不求仙学道,也不孤苦求娶,他能得到织女青睐的唯一原因就是“行孝”。织女下凡只是对董永孝行的奖励,二人并没有生情。在后期董永遇仙传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由孝感向情感发展。武陟董永遇仙传说中,七仙女虽然仍保留了其“仙女”的外衣,但是由于受当地民众的审美趣味、生活理想的影响,已经充分地世俗化、地方化,七仙女的性格、语言、思想、行为都向世俗风格靠近,更符合当地生活本身的形态,情节发展合乎生活逻辑,同时把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活素材加以剪裁、集中,通过偶然、巧合等引起故事的转变,即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即给人以真实感,又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四)大团圆结局的形成
在武陟流传的董永遇仙传说中除了“孝感”、“遇仙”、“送子”、“寻母”等基本的情节单元之外,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董永和七仙女美好的大团圆结局。如流传张七鲜(七仙女)在傅村傅员外家打工百日后,二人一同返回到大凡的大槐树下,被父亲张老田派兵将抓回。张七鲜生下儿子之后,母亲王婉荣将孩子派武陟人齐林送回,“齐林”谐音“麒麟”,故又有“麒麟送子”的说法。三年后,董永背着儿子北上太行山寻妻,终于感动了张老田和王婉容,一家人得以团聚,从此夫妻二人在民间行医,还常常上太行山采集草药,探望父母。武陟,古为王莽与刘秀作战之地,当地多有王莽撵刘秀的传说,民间更是将二者融合。据说董永和张七鲜还营救过刘秀,给他治病疗伤,并为其指点迷津。由于董永和七仙女多次搭救刘秀,因此刘秀登基之后,封董永为孝廉。
董永传说中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有其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原因,与我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密切联系。这一思维方式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古人不是把宇宙视为外在于人的对立物,而是泯灭物我的界限;不是以整体的切割、肢解为目标,而是以多样统一为归宿,把人与宇宙看成是互相包容、和谐统一的整体。在“法天为吉”的信仰力量的驱动下,尚圆习俗风行海内。[10]“圆满”不仅仅是潜在民俗心理,也是一种强大的艺术精神,千百年来,人们认为董永至孝、七仙女美丽善良,理应得到完满的归宿。
这种大团圆的喜剧性的结局,在我国古典戏曲及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比如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白蛇传》,人们就借助宗教这一超自然的力量(如“祭塔”、“佛圆”)使白娘子摆脱永镇塔底的悲惨命运,赋予整个故事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深刻反映了我国民众的尚圆之俗。[10]董永与七仙女的美好团圆结局也正是这一艺术精神的积淀。
三、武陟董永传说形成的原因
(一)“孝文化”背景的影响
董永因行孝而遇仙是早期这一故事的核心情节,其因行孝而遇仙的故事结构必须在孝的神秘化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孝”最初的含义尊宗敬祖,生儿育女,施孝(尽孝)的方式主要是在宗庙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神祖考妣等逝去的祖先。除了祭祀祖先, “孝”还表现为把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生生不息,即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春秋战国时期孝义开始向“善事父母”的层面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孔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孔子关于孝的论断主要停留在家庭伦理层面,主张言人事而远鬼神,强调通过“孝”与“礼”、“孝”与“悌”的结合,维系社会和家庭的稳定与和谐。而汉代以“孝”治天下则有其明确的政治倾向。董永民间故事最初只是汉代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事父至孝的孝子故事,但是历史却选择了董永作为社会孝观念宣传的典范,一直流传至今。在流传过程中,董永故事虽然由 “孝” 到“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孝文化的影响在其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却仍不容忽视。
包括武陟县在内的焦作地区是黄河文化的中心地带,也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其中的孝文化世代相传。孝文化在焦作地区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民间流传最广的还是民歌和民间故事。如丁兰刻木是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在焦作地区亦有流传。一说焦作修武县方庄镇丁村是丁兰的故里,至今村东尚有丁兰墓;二说沁阳水北关村是丁兰故里,尚有丁兰墓、丁兰故里碑。此外,二十四孝故事中的郭巨相传是东汉时期温县人(今属焦作市),当地至今流传有“郭巨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的民谣。还有像扼虎救父的杨香是晋朝沁阳崇义人,亦流传有“虎掀父翻真危急,女与虎斗不顾身,顷刻之间就解脱,奇闻奇事真惊人”的民谣。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山涛也是出了名的孝子。山涛事母至孝,“会遭母丧,涛年逾耳顺,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武陟县还流传着民歌《王祥卧冰》:
九州八府数洛阳,洛阳有个大王庄。大王庄有个王员外,他有个儿子叫王祥。王祥他母得了病,一心想喝鲤鱼汤。十冬腊月冬雪寒,哪来鲤鱼煎鱼汤?王祥来到河岸上,慌慌张张脱衣裳。全身衣服都脱净,只身躺在冰凌上。冰凌暖开去逮鱼,逮了鲤鱼熬鱼汤。[11]
焦作地区深厚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孝文化成为董永传说在武陟当地广为流传、备受推崇的重要文化背景之一,体现出当地人民对于“孝”的重视以及尊老、敬老的传统。
(二)地方戏曲文化的推波助澜
在民间文学史上,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凡是一些著名的、深受民众欢迎的叙事文学作品,都会凭借多种文艺形式传播。同样,董永故事的传播也并非是一个完全独立封闭的系统,它和戏曲、曲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之前,董永故事的口头传播形态已经基本定型,主体情节已经具备,形成了基本的结构样式,但明清以来,各地的曲艺艺人、观众共同参与,逐渐增添许多的细节。
焦作地区戏曲文化资源丰富,在中国舞蹈史与中国戏曲史上具备双重划时代意义的唐代民间歌舞戏《踏摇娘》即出自此地。20世纪,焦作地区先后出土了宋金元时期的杂剧砖雕,说明宋金元时期此地的戏曲活动已经非常频繁。[12]武陟是千年古县,戏曲是当地民众非常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从1948年到1958年,(武陟县)共成立了100个剧团,加上解放前成立的48个剧团(戏班),共有148个剧团”[13]。戏曲和口头传播活动具有双向互补的特点,有时从民间故事转化为戏曲,有时则由戏曲到民间故事,艺术手段不断变换,叙事内容却大体相同,而且互相启发。董永传说在武陟地区流传之后,除了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到处传讲之外,必定也通过焦作地区丰富的戏曲文化传播。在武陟地区流传的怀梆《织黄绫》、云话《槐荫记》都记载了董永的故事,可以说当地丰富的戏曲文化成为武陟董永传说广为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纪永贵.中国口头文化遗产——董永遇仙传说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4:31.
[2] 黄震云,孙娟.汉代神话史[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32.
[3] [东晋]干宝.搜神记[M].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清]周右.东台县志[M].清嘉庆二十一年刊本.
[5] 董永传说[M].滨州年鉴,2008:38.
[6] [日]柳田国南.传说论[M].连湘,译.上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13.
[7] [清]王荣陛.武陟县志[M].清道光九年刊本.
[8] 王波.焦作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普及宣传手册[Z](内部资料).2010:36.
[9] 孙巨才.董永故里的七仙女节[N].焦作日报,2010-08-16.
[10]唐霞.试析白蛇传故事的民俗文化内涵[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92-94.
[11]王瑞平.中原孝文化及其影响研究[J].商丘师范学校学报,2009(4):47-51.
[12]王建设.静物遗响——豫西北地区戏曲文物考略[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7-11.
[13]王光先.武陟县戏曲志[Z](内部资料).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