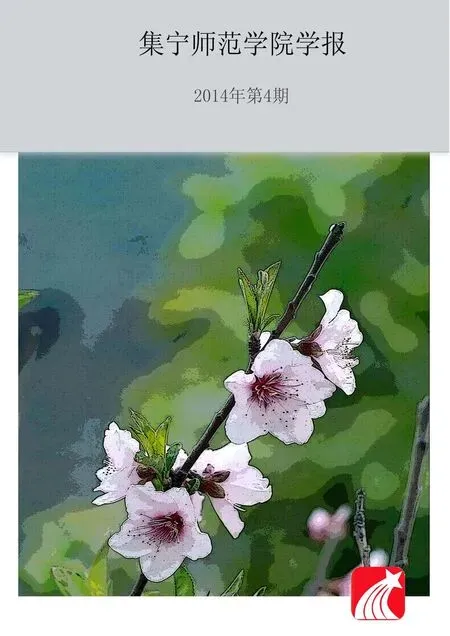白川静《诗经》研究举隅——以“水占”为核心
2014-04-17代珍
代珍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日本学者白川静受葛兰言社会人类学角度及闻一多民俗学角度研究《诗经》的启发,借鉴本国民俗学研究,尤其是《万叶集》民俗研究的方法,形成自己对《诗经》的民俗学阐释。
一、白川静《诗经》研究基本观点
(一)古代歌谣的咒语性
白川静的诗经民俗学研究以中国古代的文字作为民俗语汇,从古文字的构造中探究中国古代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为古代民俗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日本人把“告”字看成是神的宣告,我国《说文解字》对“告”未加训义,只说明字形“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大意是牛要诉说什么,便用角上的横木来拱人。段玉裁将《说文》的“会意说”改为“形声说”,白川静对此有所质疑。他认为“牛”与“告”声音不合,而且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字形来看,“告”的上部并不是“牛”,大概像是在树枝上系东西的形状,而下部的字形是“U里面加一横”,如果是系在树枝上的东西,那就不应该是“口”。由于日本人将“告”可以看作挂在神树上的致神呈文,《万叶集》中又有类似的描写,“深山有神树,枝上木棉生,采棉洁酒器,掘地置酒盆,青丝穿玉珠,悬珠竹上存”(《万叶集》卷三,三七九)。那么据此,白川静提出“U里面加一横”是装入祈祷文的“祝告之器”之说。白川静从“告”字的构字探究中认为中国古代同日本古代一样存在“言灵的思想”(古人关于语言具有神秘力量的观念),并且明显地保存在它的文字构造之中。同理,白川静又从字形构造解释 “歌”“谣”。“歌”的原义是“苛责”,即“呵声”。由于我们看不见鬼神,必须要用激情表达,再加上特殊的抑扬顿挫,并带有奇异的韵律传达给他们,所以“歌”是向神灵祈祷,要求实现愿望的强烈感情。“谣”古书作“上肉下言”,即徒歌的意思。取肉供神以表示祈祷,所以是祈祷的言语。所以原始歌谣的形态就是运用当时最优雅的修辞,求得高度的咒术灵验。在此基础上,白川静结合对《万叶集》的研究,认为原始歌谣原属撼动神明,祈祷神灵的语言媒介,是在人与神的对话中,人类所发现的显示最高咒术灵验的赞歌。此外,中国和日本的古代文化也给白川静这一说法提供了依据。日本是一个信奉“神”的国度,日本人称“神”为“迦微”,认为神不为人的感性所知,依附于人、自然物所出现,给予它们神异的力量。在中国先秦以前,原始的巫术思想也很浓厚,人们相信人神能自由交流,媒介是咒术灵验的咒语(咒语是一种被认为对鬼神或自然物有感应或禁令的神秘语言,用以祈福消灾)。中国古文献中有记载中国先秦·秦汉时代,诅咒行为一般用“祝”、“诅”等字表示,祝愿和诅咒本来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从善的方面说是 “祝福”,从恶的方面说是 “诅咒”。不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日本,神灵存在的信仰的确能够反映出原始歌谣作为咒语的可能,这也为白川静的观点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二)古代歌谣“咒语性”之表现
白川静认为古代歌谣的本质是咒歌性质,那么,从此种意义看,《万叶集》的初期作品以及《诗经》里的歌谣都产生于相似的咒语世界,具有咒语的性质。歌谣的咒语性质必定会支配着这些歌谣,并且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白川静曾说:“我想对历来在《诗经》修辞学上称为‘兴’的发想法加以民俗学式的解释。我认为,具有预祝、预占等意义的事实和行为,由于作为发想加以表现,因而把被认为具有这种机能的修辞法称为 ‘兴’是合适的。这不仅是修辞上的问题,而且更深地植根于古代人的自然观、原始宗教观之上,可以说一切民俗之源流均在这种发想形式之中。”①从白川静的这段话中,我们得知“兴的发想”即是原始歌谣咒语性质的表现,即“兴”在诗歌中具有发想的机能,表达预祝、预占的意味。这也解释了我们之所以对《诗经》中一些“兴”的语句无法理解,或认为它们与下文没有关系或直接关系的原因,我们不理解先民的思想、生活习俗以及这种发想背后所隐藏的民俗现象。
依据神灵存在思想,《诗经》与《万叶集》中的“草木鱼鸟”并不是孤立的呈现,而是有其蕴含的。中国古人所谓“问语草木”,即是相信草木、山川都是有神灵栖宿的,蕴含充满灵性的自然的神秘力量,这些都可以看做原始信仰。所以白川静认为中国传统学者所谓的“兴”“比”所借用的花草、林木、鸟兽、鱼虫等带有咒语的性质,能感应人的心灵精魂。因而《诗经》的“兴”也解释成人与神灵交流而发的吟唱,《诗经》所描述的世界是万物有灵的巫术世界,《诗经》诗篇中的草木意象也是一种表现某种固定意义的固定表达。如“南有乔木”,是向栖宿神树之神的召唤;“采草”“采伐”是向神祈祷成就的预祝的表达方式;“见彼南山”意味着祝颂的寿歌。《万叶集》初期的羁旅歌及其后的自然写景歌,在本质上几乎都是这样的咒歌,《诗经》中具有这种发想与表现的歌谣也颇多。《诗经》与《万叶集》中有关采草、祝颂、恋爱等内容的诗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古代祭神、预祝方式以及对歌风俗等民俗现象,都应是通过兴的发想加以表现的。正是这种万物有灵观和有关神的种种观念、巫术等构成古代民俗的核心,而《诗经》中“兴”的民俗学阐释以诗歌的形式反映民俗,也是这一“言灵的思想”的延伸。
二、《诗经》“水占”风俗研究
白川静以日本古代民俗为参照,探究《诗经》“兴的发想”所反映出的中国古代的民俗现象,是其研究《诗经》的主旨。基于以上研究成果,白川静参照《万叶集》中描写水占的歌谣以及西村真次《万叶集之文化史研究》中“水占”土俗研究等史料,运用兴的发想探究《诗经》中《扬之水》三篇所反映的民俗现象颇能体现出白川静 《诗经》民俗学研究的方法。
(一)《万叶集》之“水占”
白川静通过日本的民俗史料记载了解到日本所流行的水占有“木屑”、“木积”和“水绳”等方式,但他欲从《万叶集》中找到相关记载。
若得为渔栅,归依宇治人,
相思如木屑,流过竟如尘。
——《万叶集》卷七,一一三七
诗歌中出现了“木屑”与“水流”两个词语,会使人在头脑中将其进行联系,加之日本或许有这种“木屑水占”的风俗记载,所以白川静会认为这大概是描写这一风俗的,但他尚不确定,或许这些不是为水占而漂流的,只是把相思比作木屑罢了。
今晚绕石河,念妹别时多,
凭水占凶吉,清流是此波。
——《万叶集》卷十七,四 二八
这首诗歌可能是白川静认为日本有水占风俗的最有力的依据。此外,《万叶集》中有三首歌颂《柘枝仙媛》的故事,大概是有人拾到漂流的柘桑枝,随后柘枝化作美女,二人共结良缘,其中一首:
柘枝今夕至,流水送仙姿,
未有修桥者,谁能取柘枝。
——《万叶集》卷三,三八六
白川静认为“柘枝传说”大概与这种水占风俗有渊源。柘枝传说大概是讲吉野人味稻在吉野仙境捕鱼时,漂流而来的柘枝化为仙女与味稻私通的故事,这在《怀风藻》纪男人、藤原史、丹墀广成等所作《游吉野川》中有所记载。白川静发现《诗经·周南·汝坟》中描写有人在汝水的堤岸上摘折小树枝,献给河水,祈求逢见心上人的现象与《万叶集》中歌颂“柘枝仙媛”的诗歌很相似,这也引起了白川静对《诗经》中类似表达的关注。
(二)《扬之水》三篇之“水占”
联系《万叶集》中所描写的日本水占风俗以及《诗经》中的类似表达,白川静对《诗经》中《扬之水》三篇从民俗学角度加以全新阐释。以下是这三首歌谣:
《王风·扬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予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予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予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
《郑风·扬之水》
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唯予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迋女。
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
《唐风·扬之水》
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扬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绣,从子于鹄。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依据日本风俗研究以及白川静本人对《万叶集》等的研究发现,日本有采伐薪枝,让其顺水流去,进行水占的风俗。基于这种认识,白川静结合《扬之水》三篇诗歌的感情基调,运用兴的发想法即歌谣的咒语性质(在这里即是“水流束薪”的预占),认为《扬之水》表现出了与日本流放柴和绳等进行“水占”的相似的风俗。我们先对这一“水占”风俗做一下界定:它是在神前供祭时,折一嫩枝,付之东流,由其流动情状而卜。也就是说从山柴在水上漂流是否受岩石的阻碍来占测吉凶和成败,顺着山里川流而下的柴薪被看做是神的赠品,会带来幸福;受到阻碍“不流”,则是不幸的象征。白川静在解读《王风·扬之水》时,“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予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联想到“不流束薪”是日本“水占”中的厄运,而且整首诗歌流露出一种悲哀的情绪,所以他说“这些防人大约是在征戍地进行水占的吧,而这首诗恐怕是作为军歌以安慰他们孤独的心灵的。”②在对《郑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唯予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迋女”的解读中,白川静认为“这也是以水占失败为发想的。咏唱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寂寥情绪,而其孤独恐怕是离别的结果吧。”③关于唐风《扬之水》“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白川静由“白石凿凿”看出预祝的结果是由投入溪流的束薪顺着激扬的流水漂然而下,川底的白石闪烁可见,这是一种吉占。此外,在这首诗中“既见君子”与“未见君子”相对,诗歌中已经见到君子,主人公心情是欢愉的,所以整首诗歌表示由于预祝得以相逢的喜悦。
(三)白川静“水占”研究特点
分析白川静《扬之水》三篇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水占”研究的特点:1.参照《万叶集》与日本史料记载的日本水占民俗,尤其是对比《万叶集》,从《诗经》中找到与此相似的表达,将其归为一类的表述,说明同一现象的存在;2.运用兴的发想法,同时结合诗歌所表达的感情基调认为《扬之水》三篇是具有咒语意味的表达。“兴”即是兴式的祝颂语,作为“兴”的“扬之水,不流束薪”“扬之水,白石凿凿”所反映的是先民的预祝、预占行为,而这一行为通过兴的发想表现出来,这在他看来也许更接近《诗经》的价值所在;3.认为《诗经》与《万叶集》均产生在信仰神灵存在的时代背景下,是具有咒语性质的古代歌谣,反映相似的时代民俗文化。
依据白川静水占研究的特点,在《诗经》的其他篇章里可以找出类似的表达或得到相似的解释,如《菁菁者莪》:“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杨木舟顺水流时而上下起伏,究竟是“下”代表厄运,还是“浮”代表好运,在诗篇中我们找不到答案,但是“既见君子我心则休”的欢愉心情似乎能够看出这是一种好的预占。又如《瞻彼洛矣》“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禄福如茨。”洛水水声洋洋,畅流无阻,预示一种好的迹象——君子来此,带来诸多福禄。《诗经》中也有提到观泉水占卜的现象,如《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榖。”《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也许《诗经》时代的先民存在这样一种观泉水清浊或流向而占卜的民俗,而这与《万叶集》中“凭水占凶吉,清流是此波”的表达十分相似。《诗经》中还出现与《万叶集》所描写的类似的自然现象以及摘草、采薪等行为,而这些“樵薪”“采摘”和水占或许具有同样的意义,出现在《诗经》中多是祭祀、祈求平安,具有预祝的意味,这也是白川静将《诗经》与《万叶集》对比研究的依据与意义所在。
三、白川静《诗经》研究之认识
白川静曾说过:“《诗经》学困难之处不在训诂,而在《诗》篇的理解。欲了解古代歌谣之构思动机与修辞意义非有相当的方法不可。”④他所采用的“相当的方法”即是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诗经》,有别于传统研究的构思与方法,对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我们要给予正确的认识。首先,从民俗学角度看,白川静致力于从《诗经》“兴的发想”中发掘先民的民俗现象,较我国早期学者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诗经》全面而深入,但是针对《诗经》中反映的具体民俗现象,研究依据多显不足。如水占民俗,虽然在日本有此种风俗,西方也有针对物体的漂浮或下沉决定幸运和厄运的占卜,但是从中国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我们无法确定《诗经》时代是否有白川静所说的折枝付之流水,观其是否在水中受阻占卜的民俗。其次,白川静的《诗经》民俗研究植根于日本本土文化,以日本民俗为参考,将《诗经》与《万叶集》进行对比研究,此种方法多少摆脱不了国家地域文化的影响,对异国异文化特性的研究有所欠缺。白川静也承认《诗经》与《万叶集》虽有类似的构思基础,但是其历史条件仍各具特色。《诗经》中的国风多社会诗,阶级意识已很明显;但《万叶集》里就没有反映这种阶级意识,也没有产生社会政治诗,所以《诗经》与《万叶集》所呈现的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第三,民俗研究其实就是研究文化传承,白川静认为文化传承有两大支柱即宗教方面的东西和社会方面的东西。但是正如《中国古代民俗》的译者杜正胜先生所提出的“在本书中他对古代民俗只着重从宗教方面进行研究,而对社会方面的这个支柱则很少接触,这就不能全面的反映出《诗经》所要反映的现实以及表达的思想。”所以,我们不禁要质疑,难道《诗经》中的“兴”都是表现预祝意味的吗?白川静之所以没有从社会方面阐释,是因为“《万叶集》是日本最早期的创作诗,充分呈露个人世界内心沉潜的一面,日本文学自古就欠缺社会性,没有社会诗性质的倾向。”⑤正因为《万叶集》中没有社会阶级意识以及社会政治诗,所以白川静在研究《诗经》时也没有注意其社会性,但这对《诗经》产生于贵族阶级社会的历史背景就缺乏探讨,也就造成《诗经》民俗研究的纰漏。最后,关于《万叶集》与《诗经》的关系问题,研究《万叶集》的人一般认为其受《诗经》的影响颇多,白川静本人也同意这种观点,但他同时又强调,《万叶集 》中四千多首和歌的作者中具有中国古代文学修养的人员比例很小,大部分作品与中国文学没有关系。这也体现出《万叶集》作为日本古老歌谣既有借鉴性又有独自的特性。那么《万叶集》所反映出的民俗现象究竟是日本本土所生,还是借鉴《诗经》之后的异化,我们就无从得知。白川静运用日本学者对《万叶集》的研究成果,或许有各种文献依据,但是没有提供确切的中国民俗依据,这使得他的这些说法有些牵强。正如王晓平所评价的那样:“他用《万叶集》为代表的日本古代和歌来解读《国风》既有发人未发之论,也有误彼为此之说。”⑥
从解读诗歌的方法上来看,清代的方玉润主张研《诗经》要“寻文按义”,“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阵开阖变化,复乃细求字句研练之法”。⑦我们从字句研练上来细数几家对《扬之水》三篇中开头几句的解读,以此对比白川静的“兴”的发想,也许从中会发现一些问题。《诗集传》解释《扬之水》三篇中的“扬”:“扬,悠扬也,水缓流之貌。”⑧方玉润在注释此三篇时,皆从此说。《毛诗序》释义《唐风·扬之水》:“《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⑨《诗集传》称“扬之水,白石凿凿”为“比”,“言水缓若而石巉岩,以比晋衰而沃盛。”“白石粼粼,“粼粼,水清石见之貌。”⑩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征引了诸家观点,也多从以上说法,如刘氏敞曰:“非扬之水,不能使白石凿凿,非召公微弱,不能驱百姓归沃,沃以强盛。”“严氏粲云:‘时沃有篡宗国之谋,而潘父阴主之,将为内应,而昭公不知。此诗正发潘父之谋,其忠告于昭公者,可谓切至。’”姚际恒言:“扬之水,水之浅而缓者。”“白石凿凿”“喻隐谋之张露也。”方玉润同意以水喻昭公,以石喻恒叔的解释。方玉润对《郑风·扬之水》的解读“此诗不过兄弟相疑,始因谗间,继乃悔悟,不觉愈加亲爱,遂相劝勉:以为根本之间不可自残,譬彼弱水难流束薪。”可见他是将“扬之水,不流束楚”这一句看做“比”。综合以上诸家说法均认为“扬之水”是“水流缓慢”的意思,“不流束楚”“白石凿凿”“白石粼粼”都是“比”的手法的运用,只有《诗集传》称《王风·扬之水》中每章的一二节为“兴”。以上是我国宋以后对《扬之水》三篇的训诂,虽多喻政治事件,但是在字义解读上暗含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注重诗歌反映的社会现实意义。按照上述对《扬之水》三篇的释义来观照白川静的研究,就会发现两者的解释有出入。白川静认为“扬”是“激扬”的意思,而且三首诗的开头几句都是“兴”的表达手法。今人周振甫在《诗经译注》中解释这三篇时,打破前人注解,称“扬”为“激扬”,“扬之水”即为“激扬的流水”,与白川静的解读相同。如果按“激扬”翻译,抛却诗歌承载的现实意义,那么,激扬的水流定会把束薪冲走,不至于被岩石阻挡,所以与“不流束楚”的表达似乎略有矛盾,所以白川静将其称为“兴的发想”,暗含民俗现象似乎略微妥当。从这种分歧可以看出两点,其一,《诗经》民俗学研究关照的是“兴”所承载的宗教现象,对于诗歌所反映的现实寓意则不给予解释,这也是白川静对《诗经》社会方面缺乏探讨的体现。其二,对《诗经》的释义解读,既是各家研究存在矛盾的地方又是出现新见解的契机。如闻一多《诗新台鸿字说》运用训诂学,引《说文》、《尔雅》等古籍,考察“鸿”字,得出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白川静的此种解读也是试图从新的角度探究《诗经》,这也印证白川静所说的训诂是一项创造工作。所以不论是我国古人、近人、今人的《诗经》研究,还是国外的《诗经》学研究,能自圆其说者,都是企图对《诗经》进行创造性和多面性的研究。
另外,关于白川静“兴”的发想,还存在一些疑问。诸如“兴”究竟有没有这种意思?把这种发想法称为“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尚待解释。白川静曾说 “兴的发想法也可以称为咒的发想法。如果歌谣的原有性质是咒语式的东西,那么兴的发想法恰好与其原有性质相适应。”如此看来,白川静关于“兴的发想法”似乎还只是一种试图解释《诗经》的个人说法。其实,关于“兴”的解释,自古以来,颇多讨论。闻一多曾说“兴”,闹了几千年也没有人解释清楚,这是研究《诗经》的重点和困难之处。他在《说鱼》一文中,谈“鱼”字在《诗经》中作为“兴”的用法时,说“兴”就是隐语,具有“隐藏”意义。笔者认为赵霈霖的说法多有可取之处。他认为从总的根源上看,“兴”的起源植根于原始宗教生活的土壤中,之后演变为个别的具体的原始形象,所谓“原始兴象”是被神化了,是具有一定观念内涵的物象被引入诗歌中的结果。再后来就成为了一般的规范化的艺术形式的“兴”(丧失观念内容而逐渐演化成的抽象的形式)。“在积淀和演化的过程中,习惯性联想中的宗教内容不断减弱直至消失,艺术的审美因素则相应的不断增长直至发展成为‘兴’的本质。”但是“兴”的宗教内容结束而审美因素的形式化开始确立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又不得而知。可见,国内、国外学者对于“兴”都不能全面确切的解释说明,也许时间的距离使得它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谜。
白川静曾指出葛兰言以东南亚遗存的歌谣作为推论的比较资料对诗篇的理解虽多错误,但以一位外国人身份提示中国古代歌谣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其观点是极具启发性的。的确如此,虽然白川静的《诗经》研究方法尚存在一些缺陷,但是他欲恢复美丽的古代歌谣集的生命,对古代歌谣的本质进行探讨,使诗不至于失落在猜谜式解释学上的探索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诗经》是一部蕴含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原型意义的著作,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学总集,更是周代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的艺术表现,属于先秦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是先秦汉语的代表,所以白川静先生从文字学、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诗经》意义颇大。如果说闻一多先生对《诗经》民俗学研究的开创“深具锐眼,洞灼内奥”,那么白川静即是在对古代歌谣的构思动机和表现手法上沿着闻一多的道路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
注释:
④⑤白川静著,杜正胜译,《诗经的世界》,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社2009版年,分别引自第304页,第305—306页。
⑥王晓平,《论白川静诗经学》,《诗经研究丛刊》,2002年,第265页。
⑧⑩〔南宋〕朱熹注,《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分别引自第29页,第46页。
⑨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