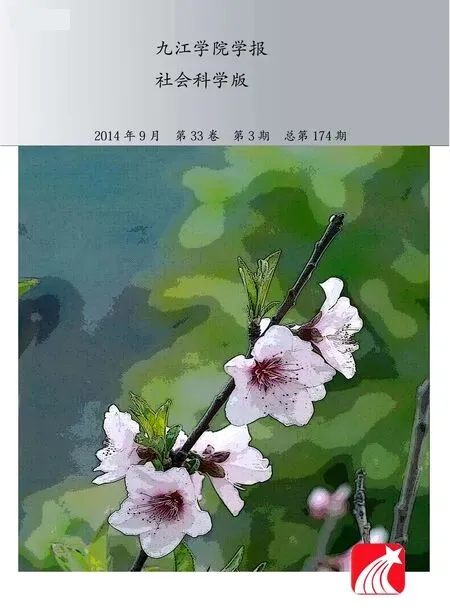从书斋命名看士大夫对陶渊明的接受*
2014-04-17滑红彬刘佳佳
滑红彬 刘佳佳
(九江学院图书馆 江西九江 332005)
从书斋命名看士大夫对陶渊明的接受*
滑红彬 刘佳佳
(九江学院图书馆 江西九江 332005)
陶渊明业已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对传统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书斋命名的角度揭示士大夫对陶渊明的认同和接受,论述陶渊明对书斋文化的影响及其文化意义。
陶渊明 斋号 书斋文化 接受史
陶渊明不仅以文学著称,他的形象和思想业已浸染到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陶渊明作为士大夫的精神归宿,对书斋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士大夫来说,书斋不单是藏书、读书、著书的具体处所,更是寄托怀抱、安顿心灵的一方天地。可以说,斋号是士大夫心灵的独白,不仅能表露其情趣志向,甚而透显出其心灵最深处埋藏的情愫,因此,士大夫对于陶渊明的认同和接受往往能够通过斋号得到体现。
一、对陶渊明清高人格的仰慕
陶渊明清峻高洁的人格魅力千百年来一直都赢得后世的仰慕,萧统称赞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并认为陶作有强烈的净化人格的魅力:“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1]受陶渊明人格魅力之熏染者代不乏人,有的士大夫更是以陶名斋,托物言志,以示对陶渊明的仰慕和追随。
元代文学家虞集“早岁与弟槃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2]
明代归有光亦步武虞集,以陶庵名其书斋。归有光《陶庵记》云:“已而观陶子之集,则其平淡冲和,潇洒脱落,悠然势分之外,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百世之下,讽咏其词,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进于孔氏之门。而世之论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间,谓为大节,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夫穷苦迫于外,饥寒憯于肤,而性情不挠,则于晋、宋间,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并诸邵子之间。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予又今之穷者,扁其室曰陶庵云。”[3]归有光读陶集而心生敬仰,喜陶效陶,正是被陶渊明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萧统言陶集“有助于风教”可谓真实不虚。
以陶名斋者还有很多,仅在清代,以“陶庵”命名者就有陈星、金世章、曹续祖、李浃、倪馥等,以“陶庐”命名者有法式善、王树枏、金武祥等,还有李钟麟“陶轩”、张诠“陶圃”、罗信南“陶龛”、蒋耕堂“慕陶庐”等等。
在众多以陶名斋的士人中,有几位藏书家需要格外注目。顾湄,字伊人,江苏太仓人,其藏书楼名曰“陶庐”。钱谦益《陶庐记》:“顾子伊人得宋刻苏长公书《陶渊明集》,藏弆斋中,晨夕吟讽,名其处曰‘陶庐’。”[4]周春字芚兮,号松霭,海宁人,其藏书楼迭称礼陶斋、宝陶斋、梦陶斋。黄丕烈题跋记载:“汤注陶诗,宋刻真本,松霭与宋刻《礼书》并储一室,颜之曰‘礼陶斋’。其书秘不示人,欲以殉葬。贾人吴东白谈及周公先去《礼书》,改颜其室曰‘宝陶斋’,今又售去,改颜其室曰‘梦陶斋’。并闻他估云,周去书之日,泣数行下。”[5]而黄丕烈本人亦有藏书楼曰“陶陶室”。黄丕烈,字绍武,号荛圃,江苏吴县人,著名藏书家。王芑孙《黄荛圃陶陶室记》云:“同年黄荛圃,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诗》,继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不胜喜,名其居曰‘陶陶室’。”顾湄、周春、黄丕烈诸人对于《陶渊明集》的这种喜爱固然是出于重宋版书的缘故,但宋版书亦夥,而独拳拳于此者,乃是为陶渊明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正如王芑孙所说:“今者托趣于陶陶,非独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盖荛圃宜为县而不为,略似陶公;其力耕校者,又大致仿佛,故因以自寓焉!”[6]
二、对陶渊明回归主题的共鸣
中国士大夫总是在用舍行藏之间徘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出了士大夫普遍的境遇和内心世界。当士大夫在仕途上遭遇坎坷后,便会想到归隐,回归出仕之前的状态,也就自然而然地对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生活方式产生共鸣。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不仅仅是生活意义上的远离尘嚣、躬耕田园,还包含回归自我、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的哲理意味,因此,陶渊明能够成为失意士大夫追寻人生价值、求得内心平衡的精神支柱。
《归去来兮辞》是集中表现陶渊明回归主题的名篇,特别是经过苏轼的追和之后,更是得到普遍的认同,也成为文人学士为书斋命名的典故渊薮,用以寄托胸襟。
苏轼早年在政治上奋发进取,勇于建言,后遭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对于陶渊明有了深刻的认同,将陶渊明作为自己贬谪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东坡志林》卷一:“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轩,以‘容安’名之。”[7]黄仲元亦云:“坡老和翁四言、五言,风味大略相似,及和翁辞,自许为翁后身,毕竟道著翁意落在何处。后来坡以寄傲为轩。翁千载人,坡亦百世士也。”[8]“容安”、“寄傲”均典出《归去来兮辞》之“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苏轼以此名轩,是对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共鸣,也是自我胸襟的发抒,对后人,特别是对两宋党争中被贬谪者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苏门弟子晁无咎在绍圣年间屡遭贬谪,备尝党争之苦,并从崇宁二年(1103)蛰伏故里八年之久。闲居中,他于东皋经营田园,摭《归去来兮辞》中语以名其居,有“松菊堂”、“舒啸轩”、“临赋亭”、“遐观楼”、“寄傲庵”之称,并自号归来子,希冀以此保持心理上的平衡,求得心灵慰藉。
至大观元年(1107),又有赵挺之在党争中失势身亡,其子赵明诚因官秩被夺,遂偕妻李清照屏居乡里十年,聚书校雠,把玩金石。李清照父家及夫家均在党争中得罪罹祸,因此她以“归来”名其书堂,并自号易安居士,显示出她对陶渊明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的认同,甘心悠游岁月,老于书林,以排遣党争带来的沉重情累。
此外,唐庚“寄傲斋”、张祁“归去来堂”等也都是借陶来排遣“朋党之争”中畏祸的情累,自我镇定,追求个体自由与生命价值。对于宦海浮沉的士大夫来说,陶渊明不仅仅是清峻人格的文化符号,更是文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是在逆境中保持自我的精神支柱。
后世以《归去来兮辞》命名书斋者亦复不少,如元代危公镇“寄傲轩”、刘仲泽“审安斋”、明代文嘉“归来堂”、叶树廉“归来草堂”、清代戴漉巾“归来居”、陈醇“归来草堂”、沈赤然“寄傲轩”等等。但与宋代党争旋涡中的士人不同,他们没有身负“朋党之恶”的畏祸情累,更多的是发抒远离尘嚣、回归自我的清雅之念。
三、对陶渊明固穷安贫的认同
固穷安贫是指一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道德原则。陶渊明“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能够抵制利禄的诱惑,在贫困中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并能在贫穷中体味人生,获得心理的平静和精神的高洁,成为千古传诵的楷模。同时,陶渊明将固穷和安贫的思想化为诗文,开创了诗歌中大量描写固穷安贫主题的先例。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陶渊明都成为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清代文学家姚鼐的书斋名“惜抱轩”,典出陶渊明《饮酒》:“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意谓守志勿移,不为穷达动摇其心。
倡导“诗届革命”的黄遵宪,著有《人镜庐诗草》。“人境庐”取典于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黄遵宪学博才高,然而屡困场屋,久试不第。其书斋原名“在勤堂”,黄遵宪改称为“人境庐”,表明他对陶渊明固穷安贫的认同。
近代大学者黄侃执教南京中央大学,筑“量守庐”,读书其中。“量守”取自陶渊明《咏贫士》“量力守故辙,岂不饥与寒”之句,意谓量力而守法度。章太炎《量守庐记》:“寡得以自多,妄下笔以自伐;持之鲜故,言之不足以通大理;雷同为怪,以炫于横舍之间,以窃明星之号,此非吾季刚所不能也。……夫季刚之不为,则诚不欲以此乱真诬善,且逮于充塞仁义而不救也。”[9]可见黄侃要以“量力守故辙”表明其不趋时、不求新的严谨学风和固穷安贫的学术追求。
陶渊明《归园田居》诗有“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之句,“守拙”意谓保持自身淳朴之本性,而不同流合污。陶渊明“守拙”之说对后世影响甚大,以此名斋者甚多,几乎成为认同陶渊明固穷安贫思想的代名词。在清代,“守拙斋”、“守拙轩”、“守拙堂”、“守拙山房”、“守拙庐”等多达数十家,如吴昌硕之书斋即名“守拙斋”。吴昌硕曾做安东令月余,故制“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印,另有“喜陶之印”等,他对于陶渊明当别有兴会。
四、对陶渊明生活旨趣的向往
陶诗的美在于自然,他的诗与生活融为一体,随其所见,指点成诗,率真自然,具有一种特别感人的力量。正如袁行霈所说:“他似乎无意写诗,只是从生活中领悟到一点道理,产生了一种感情,蕴涵在心灵深处,一旦受到外力的诱发(如一片风景,一节古书,一件时事),便采取了诗的形式,像泉水一样流溢出来。”[10]因此,生活中的细微感受和寻常片段,一经陶诗道出,便产生一种独特的韵致,为后世文人所称赏和向往。
陶渊明“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11],并将读书生活的乐趣写入诗中,“孟夏草木长”一诗是他写读书之乐的名篇,令后世文人向往不已。诗中“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物我情融,最见陶渊明特有之意境,甚得后人共鸣。清代崇恩有“吾亦爱吾庐”,藏图书碑帖甚富。张曾裕、吕世宜、吴鳌、陈纶等人也均以“爱吾庐”作为书斋名。另外,清代汪日桂之藏书楼名“欣托斋”,亦源于此句。
诗中“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之句写耕读生活,自然淡雅,亦深得后人追随。清代华长卿即以“时还读我书屋”名其书斋,此外尚有曾对颜“还读我书室”、钟元赞“还读我书斋”、葛奎“还读书斋”、韩崶“还读斋”、周孝壎“还读庐”、陈宝箴“还读楼”等,不一而足。
《赠羊长史》中“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句亦涉及读书生活,表达其怀古之情。清人周亮工即以“赖古堂”为书斋名,周亮工又号“陶庵”,并刻“学陶”印,对陶渊明景仰之至。
“停云”、“东轩”也是陶渊明创造的独特意向。“停云”隐喻思念亲友,辛弃疾在铅山有“停云堂”;文徵明名其居所曰“停云馆”,并刻有“停云”“停云生”印。清代李家瑞书斋名“停云阁”。“东轩”在陶诗中数见,《饮酒》即曰:“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因此东轩成为高洁闲适、遗世自得的象征,如清代藏书家郁礼有“东啸轩”、查善和有“东轩”等等。凡是这些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经陶渊明笔触点染,就给人以极平淡又极生趣的意境,言浅意永,发人深思。
明代张奇龄创“涉园”以藏书,卷帙甚富,其林泉之胜,甲于东南,后传至其裔孙张元济,绵延三百年。张元济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出版家、文献学家,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主持影印《四部丛刊》,嘉惠学林。“涉园”本于陶渊明《归去来辞》“日涉园以成趣”之句,以示淡泊自洁、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近代藏书家陶湘之藏书楼亦名“涉园”。
以陶名斋与和陶诗、集陶诗一样,都是借文人雅事表达士大夫对清高人格的向往,对保持个体自然性情的追求。和陶诗、集陶诗是在文学创作上表达其对陶渊明的接受,而以陶名斋则是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对陶渊明的认同,它们从不同地维度诠释着陶渊明对传统文化产生的既广且深的影响。
[1]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496.
[2](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6.4181.
[3](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426.
[4](清)钱谦益.钱牧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1009.
[5](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185.
[6]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 1982.53.
[7](宋)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 1981.79.
[8]李修生.全元文(八)[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365.
[9]程千帆、唐文.量守庐记学记[M].北京:三联书店, 2006.5.
[10]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61.
[11]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466.
(责任编辑秦川)
本文系九江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九江藏书文化研究”(编号2013SK28)的成果之一。
2014-05-16
滑红彬(1983- ),男,九江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藏书文化。
I 207.2
A
1673-4580(2014)03-0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