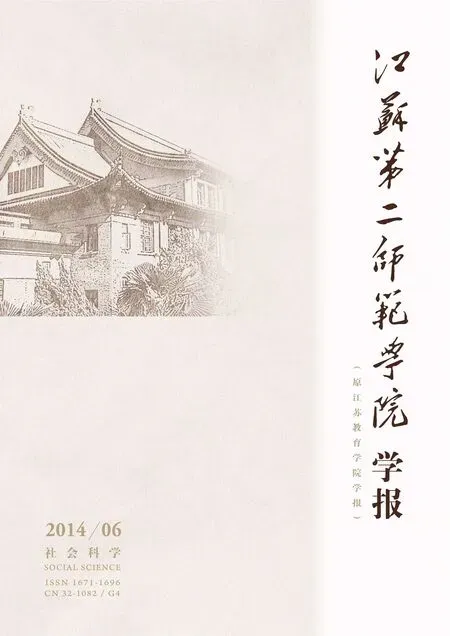参考文献著录若干问题探讨
2014-04-17曹小春
曹小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学海》编辑部,江苏南京 210013)
关于参考文献标注著录,在国家标准方面,仅有主要针对文后参考文献著录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下简称《著录规则》)。在学术探讨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关于文后著录的数量可观,关于文内标注的极少;二是关于科技论文的较多,关于社科论文的较少;三是关于中文的较多,针对西文的较少;四是讨论不全面,有一些遗漏。在工作实际方面,不同刊种、不同刊期、不同论文都可能不尽相同,比较混乱。而且,关于参考文献标注著录,无论是国家标准,还是学术探讨,抑或工作实际,都存在着不够妥当的地方。本文拟对我国目前参考文献的文后著录、文内标注和正文责任者提及的国家标准、学术探讨和工作实际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文字和符号所用语言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对文后参考文献的文字著录,明确提出原则上要用文献本身的。但对于文后参考文献著录中所用符号,以及文内标注和正文提及责任者①《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05)指出:倘若正文中已提及著者姓名,则在其后的“()”内只须著录出版年。显然,正文提及责任者与参考文献著录关系密切,所以这里将它与文后著录和文内标注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所用文字和符号均没有提出规则,尽管如此,在该《著录规则》的字里行间以及举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其规定的规则是:文后著录和文内标注所用符号按英文的,文内标注所用文字用文献本身的。实际操作和科学研究中,人们普遍认可上述几项规则。由于正文提及责任者的格式在国家标准中完全不涉及,因此所用文字和符号在实际工作中较为混乱。
笔者认为,既然是中文著作的文献著录问题,那么,不仅其中的中文文内标注、参考文献著录、正文提及就都应该按照中文的习惯,外文文内标注、参考文献著录、正文提及也应该尽可能按照中文的习惯。国家标准规定对欧美责任者在文内标注和文后著录时一律先姓后名就符合这一精神。②虽然欧美责任者的名字翻译成汉语有符合中文规则和容易记忆的好处,因而多数港台期刊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期刊也是翻译的,而且尽可能翻译成像中国人的名字,即第一个字用中国存在的姓氏,后面用一个或两个在汉语中有明确含义(特别是褒义)的字,但是,由于音译不容易准确,而且同一名字可能会产生多个翻译,形成混乱,因此笔者还是倾向于用原语言,如实在要进行翻译,要尽量避免用有明确含义的汉语的字词,以免误导读者。当然,外文的题名(包括书名、刊名、报纸名、专利题名、科技报告名、标准文献名、学位论文名、析出的文献名等)应按著录信息源所载的内容著录。
这里不存在读者不能理解著录中的中文的文字和符号的问题。也不存在不“接轨”的问题,因为只要著录项目与著录格接轨,用中文的标点符号和其他标识不会使人不理解,如也通西文的读者会自然而然地将此处中文中的顿号看作等同于西文中的逗号。
按照上面的讨论,在符号方面,目前国家标准的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的文后著录方法是不妥的,工作实际中的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的正文责任者提及方法有些人也是使用错误的。在文字方面,外文文献的文后著录和文内标注方法(著者-出版年制下)也是不妥的。
例1:当前:余敏.出版集体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179-193.应改为:余敏:出版集体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179-193.
例2:当前:PEEBLES P Z,Jr.Probability,random variable,and random signal principles[M]. 4thed. New York:McGraw Hill,2001.应改为:PEEBLES P Z,Jr:Probability,random variable,and random signal principles[M],4 版.New York:McGraw Hill,2001.
例3:当前:张扬,李红,王刚(2008)论述了……应改为:张扬、李红、王刚(2008)论述了……
例4:当前:WEINSTEIN L,SWERTZ M N,SODEMAN W A(1999)研究了……应改为:WEINSTEIN L、SWERTZ M N、SODEMAN W A(1999)研究了……
例5:当前:(Crane et al,1972)应改为:(Crane等,1972)
二、关于标注著录与文中引用的关系
一般认为文中只要有引用,就应该有相应的文内标注,文后也应该列出参考文献,也就是所谓引用一定要有出处。其实这是可以商榷的。例如,在中国学者中,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出自毛泽东之口,那么是不是在文中引用时就一定要标注并且在参考文献表中如是著录:“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再如,对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话,是不是可以就仅仅指出是马克思说的,而不在文中标注这样在文后著录:“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显然,如果这样做,是浪费作者或编者的时间精力和纸张。所以,对于公知的引用可以不标注和著录。其实,对于不太重要的引用也可以不标注和著录(这一点较难举例说明)。
三、关于参考文献项位置
国家标准、学术探讨和工作实际中,都是将注释置于每页的页脚,而将所有参考文献统一置于文后。的确,将参考文献项和注释项分列在不同的地方,可以避免二者混搅在一起。但这样做,阅读起来不够方便,一是在此文有很多页码的情况下翻动纸张看参考文献表耗费较多时间,就是在阅读电子版本时拉动word、pdf或web文档的滚动条也耗费较多时间;二是在采用顺序编码制下,参考文献的文内标注也采用上标形式([]),与注释的标注形式(○)很相似,容易混淆。笔者认为,“注释”的含义和“参考文献”的含义有交叉,因此可以采用《中国社会科学》的做法,将参考文献和注释合并置于每页的页脚,这样可以解决原有做法阅读不便的问题,也无其他不妥。
四、关于参考文献标注体系
《著录规则》规定,在文后著录和文内标注时都可以采用顺序编码制或著者-出版年制。相比较顺序编码制,著者-出版年制的主要好处是阅读正文时可以直接了解责任者和文献发表的时间,但著者、出版年夹在正文中毕竟对阅读有些影响,更重要的是,当作者较多时如被要求文内标注与文后著录、正文提及一致,就显得太复杂了;而如果它们不一致,显然也不好。目前是不一致的,下面以对责任者的处理为例说明之。
表1中,2个以及3个责任者的情况有:文内标注与正文提及、文后著录不一致,文内标注与文后著录也不一致。对于西文文献的欧美责任者的处理还有中文和西文之间的不协调问题。4个及以上责任者的情况为:除上述问题外,文内标注的“et al”与正文提及的“et al”、文后著录的“et al”含义不同。
如果像前面说的那样,将参考文献和注释合并置于每页页脚,由于每页的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数量有限,所以只需要当文内出现要进行注释和参考文献标注时,按它们出现的顺序合并进行统一编码,然后在页脚加以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著录。在这种情况下,顺序编码制能够很好地实现和著录的目的,著者-出版年制可以不再保留。现在大多数科技期刊都采用顺序编码制也是因为考虑到著者-出版年制缺陷较多。
五、关于国家标准
《著录规则》颁布已经多年,总的说来,科技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较多,其他主办单位的学术期刊大多不执行。那么,为什么很多期刊不执行?一个原因就是上面多次提到的此标准不够完善,特别是对社会科学期刊适用性不强。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只是一个推荐性标准。
我国的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前者是必须执行的,后者是鼓励机构和个人自愿采用的。《著录规则》属于后者,也就是说,机构和个人可以不执行它。事实上,参考文献标注著录问题纯粹是一个学术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较复杂的学术问题,国家完全可以放任从事学术研究的个人和团体在实践过程中逐渐自然形成一些规范,不仅不制订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也不制订。就欧美国家来说,它们就不存在这一方面的国家标准。也许有人会问,不是有ISO 690《文献工作文后参考文献内容、形式与结构》和ISO 690-2《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第2部分:电子文献部分》两项国际标准吗?必须注意到,国际标准的制订者是民间机构,而国家标准的制订者是权力机关。即使此国家标准是推荐性的,它也与学术环境应尽可能宽松的理念不太符合。现在有些学者将现有工作实际与《著录规则》进行比对,寻找不符合之处,然后提出如何使之吻合的解决之道,似乎就是误认为它具有强制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