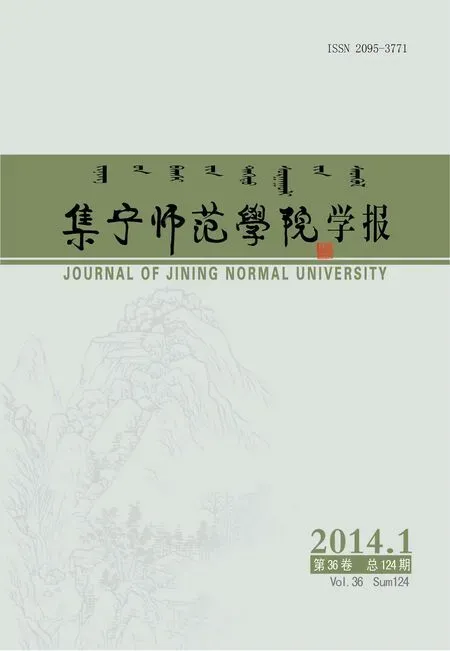救助动物,实现自我价值
——论欧茨笔下女性的生态责任
2014-04-17杨建玫
杨建玫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0)
救助动物,实现自我价值
——论欧茨笔下女性的生态责任
杨建玫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0)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在小说中关注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及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在她的笔下,许多女性通过救助动物的行动与男性权威相抗衡,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直接反抗男权社会,并通过承担生态责任实现了自我价值。欧茨以此批判男权思想,关注遭受男权思想压迫的女性和自然,展现了她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
女性;救助动物;自我价值;生态责任
生态女权主义批评家常把(粗暴地)对待动物及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同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压迫联系起来,强调女性、自然界和动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女性把拯救动物、关怀其生命与女性自身的解放视为统一的任务(Buell,708)。在欧茨的笔下,《我们是穆尔维尼一家》(We Were the Mulvaneys,以下简称为《我》,1996)中的玛丽安和《中年》(Middle Age,2001)里的卡米拉承担起生态责任,将自身的命运与动物的命运联接到一起。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美学术界对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Joyce Carol Oates,1938—)的研究方兴未艾,聚焦于欧茨的一些揭示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探讨暴力、女性实现自我等主题的获奖小说。①然而,为什么她笔下女性的命运与动物的命运能联接在一起?中美研究现状表明研究者还未全面、系统地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和《中年》,探讨欧茨笔下女人与动物关系的实质。
一 救助动物
有动物为伴的生活充满乐趣。人们通常会因动物的丢失、患病或受伤感到担心,会对动物的生长和发展感到满意,会为动物的死亡感到悲伤。动物构成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喜剧和悲剧(Burgess-Jackson,245—246)。在《我》中,多年来,玛丽安深受父亲迈克尔男权思想的束缚,她的坎坷生活促使她投身于动物救助的工作中。
由于玛丽安家里养有狗、猫、狗、马等动物,所以她从小就特别喜爱动物,尤其对她的忠实朋友玛芬和小马莫莉情有独钟。人类与宠物之间的良好关系有益于人类的精神健康,因为他有关怀的对象(Bustad,190)。在被人强暴、遭受了人生巨大的痛苦打击之后,玛丽安最想见的就是玛芬和莫莉。在与它们无声的精神交流中,她的注意力转移了,精神痛苦减轻了,得到一种心灵安慰,这充分显示出她与动物之间的深情厚谊。
激进的生态女权主义学者从批判男权思想入手来分析生态问题,强调应当通过关怀伦理这一直接的政治行动解放女性和自然(Merchant,191)。玛丽安的命运变化源自于她救治玛芬的行动。玛芬生病后,玛丽安带它到一个动物庇护中心求医,在等待玛芬被救治的过程中,她看到这个中心有许多被人遗弃的老弱病残动物。受工作人员的感染,她也动起手来救助动物,她想到,“如果人类不保护各个物种的话,许多像鸟、爬行动物、两栖动物的物种对于人类而言可能都是未知的”(Oates,414)。玛丽安的这种思想反映了美国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强调的把“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思想(Holmes Rolston III,48)。当玛芬被送回到她手里后,她决定留在这里,从事动物救助工作。
玛丽安由关心自己的宠物发展到关爱所有的动物,并成为动物庇护中心的一名专职动物保护工作者。她在这里一干就是四年,认为自己的工作十分有意义。人们对于宠物的首要责任在于为它们提供所需,其中一个责任就是保证动物在生病之后得到医治(Burgess-Jackson,266)。玛丽安救助玛芬的行为体现了她对动物的责任感,她将爱转移到更多动物的身上,为自己能为动物保护工作尽一份微薄之力而深感欣慰。
玛丽安不但在这个中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工作,还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与这个中心的创办者怀斯特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他们志同道合,共同从事动物救助的工作。弗里丹提出,新女性健康自我的核心是“把握人类身份的两个根基:爱情和工作”(《第二阶段》,256),玛丽安达到了这一标准,她既在这个“动物保护中心”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也找到了知心爱人,做了母亲,成为一名拥有健康自我的新女性。在从事救助动物的工作之后,玛丽安摆脱了男权控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获得了独立的自我身份。她不仅给予动物关爱,还获得了经济的独立与心灵的充实。她为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而自豪,为能够帮助动物减轻痛苦而欣慰。
与玛丽安相似,《中年》里的卡米拉也是在饱受了丈夫莱昂内尔的压迫之后逐渐参与救助动物的工作。虽然莱昂内尔在公众的眼里是一位温文尔雅、事业有成、看似爱护家人的正人君子,但本质上,他既是一位不尊重妻子的大男子主义者,也是一位排斥动物的物种歧视者。与莱昂内尔的婚姻危机使卡米拉情绪低落,而好友亚当的离世更使她一度陷入悲痛之中。收养了亚当的狗阿波罗之后,卡米拉逐渐开始了动物救助的工作。从此,她与狗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救助受伤和被弃狗的过程中,卡米拉发现了生活的意义,她的思想发生转变。卡米拉不仅花费昂贵的医疗费请求医生救治“影子”,还给当地走失动物庇护中心捐了款。从此,她成为动物庇护中心的志愿者,开始关注流浪狗,这一抉择为卡米拉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希望之窗。她以坚强的态度应对婚姻危机,将全部身心都扑到了动物救助的工作中,她终于从亚当死亡和丈夫不忠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然而,当莱昂内尔重新回到家以后,卡米拉又面临着再次遭受他的压迫和被限制在家养狗的困境,这使得她不得不在莱昂内尔与狗之间做出选择。是莱昂内尔压迫卡米拉和她的狗,破坏了她与狗之间和谐、快乐的生活。
二 实现自我价值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中,女性与自然共同遭受压迫和支配的命运建构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转引自Armbruster,102)。如今,曾经消极被动的卡米拉再也不会因为丈夫的无理要求放弃自己的追求,她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不会为了自私的丈夫放弃它们。卡米拉的选择证明:“破坏了自然的和谐的男权意识形态通过压迫女性表现出来,而消解男权意识形态是女权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共同目标”(Ruether,106)。卡米拉选择养狗是对莱昂内尔男权思想的挑战,充分显示出她要保持独立自我的女权主义立场。因此,卡米拉成为这场婚姻危机的胜利者,她的反抗行为显示出她的深刻变化:她以自己的行动消解了丈夫对她的压迫和支配,从转变成为一位女权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
弗里丹认为,女人对家庭主妇这一形象直接予以“否认”,并不意味着她必须在婚姻和事业之间做出抉择,女性应当把婚姻与“事业”的终生目的结合起来(《女性的奥秘》,356)。弗里丹的这一观点在卡米拉拒绝为了丈夫放弃狗的选择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卡米拉并非要放弃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她是想要保留经历了深刻的身心转化之后才得到的工作和自由,希望在维持与莱昂内尔的婚姻、继续扮演家庭主妇角色的同时也能够保持自我,从事喜爱的工作。然而,莱昂内尔阻止她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使她和她的狗都遭受到男权压迫和支配,但卡米拉最终选择与狗相伴。
莱昂内尔对狗的排斥导致了他的可悲下场。他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消极,对于自己生命的意义深感困惑不解,陷入了精神困境。那天,当发现游泳池里有狗屎时,莱昂内尔挥舞着手杖朝着卡米拉大吼,举起手杖朝卡米拉的肩膀打去。这时,几只狗扑上去撕咬他,他与狗混战在一起,最后被活活咬死。莱昂内尔是一位典型的歧视其他物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虽然他还未获得机会虐待卡米拉的狗,但是他从内心厌恶它们,无法容忍它们在家里的存在。他打心眼里排斥狗,一贯对它们骂骂咧咧,他死在狗的爪下是罪有应得。莱昂内尔的悲剧在于他自视为君王,他不但歧视其他物种,还不尊重妻子。他既具有人类沙文主义思想,又具有性别歧视思想,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莱昂内尔的悲剧是欧茨为人类中心主义者谱写的一曲悲歌,他的下场印证了澳大利亚动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观点:“对动物的残忍会导致对人的残忍,因而人类应当善待动物。”(辛格,224)。欧茨以此告诫人们:不能善待动物、不能容忍动物存在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人们不应当歧视其他物种,应当给予动物一定的生存权。
卡米拉通过救助狗的工作终于获得了身心解放。在成为一位积极、热心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同时,卡米拉摆脱了丈夫对她的思想束缚,通过参与动物救助的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也就是说,她借助自然之力——狗——来反抗男权压迫,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得了解放。
《我》和《中年》通过玛丽安和卡米拉保护动物、关爱动物生命的行为,表达了女性生态责任的主题。玛丽安和卡米拉最初受男权压迫,养动物是为了与之相伴,然而,在与它们有了深厚感情之后,她们逐渐对动物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充满了关怀之情。她们逐渐由最初只关心自己的宠物发展到关注动物救助的工作,并最终投身于其中。她们将动物看作与自己有平等关系的独立主体,通过动物救助的工作,她们既实现了自我价值,也使动物获得了关爱。她们的经历证实了科拉德和康楚奇的观点:“女性被压迫、受虐待的经历能够使她们对自然遭受的压迫和支配更加敏感,她们会奋起拯救自然。”(Collard与Contrucci,138)她们与动物的联系以一种新的方式被展现出来,动物在建构其主体身份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成为两部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她们自愿参与这一工作的行为也反映了美国当代“草根”派动物保护主义者自发地投身于动物保护运动的特点。
在欧茨的小说中,女性人物通过与自然联系对男权社会进行反抗。柯琳、阿比盖尔反对食肉和狐火邦女孩及玛丽安反对折磨动物的言行都是基于对动物的关怀,体现了女性的关怀伦理,消解了男性权威;柯琳和奥古斯回归自然界,重塑了自我,成为生活的主人,获得了独立的女性自我身份;卡米拉和玛丽安承担了生态责任,她们直接参与到救助动物的工作中,实现了自我价值,不但使自身获得了解放,也通过给予动物关怀的行动促进了自然的解放。
三 欧茨关注女性与动物的语境
长期以来,欧茨关注动物,关注女性的命运,这源自于她的个人经历、社会和文学语境,与她长期与动物为伴的生活、梭罗的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她童年时期经历的受伤害事件和美国当代生态女权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
“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关系在于作为个体的观察者对它们的友好情感,或者甚至是爱”(Raglon&Scholtmeijer,131)。欧茨是一名坚定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对动物情有独钟,动物成为她小说创作的一个焦点。童年时生活在养有各种动物的农场里,幼小的欧茨有机会与动物近距离接触。在以后的岁月里,她长期喂养动物,对动物充满了爱心。在她家四周僻静的树林里,欧茨可以经常看到鸟、鹿和青蛙,鸟儿也是欧茨尤其厚爱的小生命。在她的日记里,动物时常跃然纸上,动物给欧茨的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次接受访谈时,当记者问及她最想写什么时,欧茨回答说是动物和农场。由此可以理解欧茨在许多小说中塑造动物形象的原因,它们凸显出她内心的动物情结和她对动物的深切关爱。
梭罗的自然保护主义思想也对欧茨的动物保护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欧茨曾谈到,她在大学时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梭罗的 《瓦尔登湖》(Walden)。梭罗对动物充满了关爱。他谴责人类对动物的肆意杀戮,对动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强调人需要与其他动物建立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受此影响,欧茨在部分作品中也塑造了许多像梭罗一样采取行动保护动物、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人物。
欧茨在创作中始终关注女性的命运,这源自于她童年时代的一次受伤害经历。在她十岁时一次上课前,一群野蛮的乡村男孩子将她逼到教室的角落,对她推推搡搡,她感到极度恐惧,极力抗争,却招来了他们的哄笑。这种事情对于女孩子而言是一场噩梦,也对欧茨的心理造成了很大伤害。甚至到她60多岁时,她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一事件使欧茨的内心产生了很强的无助感和疏离感,以至于受男性伤害的女性成为她创作中始终关注的焦点。同她本人一样,这些女性试图从童年的恐怖事件中逃脱出来,躲藏到一个人的世界中。这些受伤害的女性形象反映出她作品的自我指涉性特点。
由于欧茨具有关爱自然、关注女性命运的思想基础,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生态女权主义运动发生之时,她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一运动的核心是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对自然的支配联系起来,来分析生态问题,并在反对男性压迫的斗争中寻求解放女性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欧茨受此影响,在许多作品中揭示出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语境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揭露并批判性别歧视,表现出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
欧茨在小说中关注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及其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她塑造了许多通过自然与男性权威相抗衡的女性形象,她们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直接反抗男权社会,实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胜利。欧茨以此批判了男权思想,展现了她关注遭受男权压迫的女性和自然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
欧茨在小说中探讨了20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生态语境下的性别问题。她不但仍然关注自然,还将关注点扩展到生态语境下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使女性和自然都成为她的道德关怀对象。欧茨对遭受男权压迫的女性和自然的关注既反映了她在小说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特征,也显示出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因此,欧茨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是她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一部分。
注释:
①参看Grant,Mary Kathryn.The Tragic Vision of Joyce Carol Oates,Durham (North Carolina:Duke University Press,1978).
[1]Armbruster,Karla.‘Buffalo Gals,Won’t You Come Out Tonight’:A Call for Boundary-Crossing in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A].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C]. Eds.Greta Gaard and Patrick D.
[2]Murph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97-122.
[3]Burgess-Jackson,Keith.Doing Right by our Animal Companions[A].Animal Rights.Ed.Clare Palmer[C].Hampshire,England:Ashagate,2008.245-271.
[4]Bustad,LeoK.Animals,AgingandtheAged[M].Minneapolis,Minn:UniversityofMinneapolisPress,1980.
[5]Collard,Andree and Joyce Contrucci.Rape of the Wild[M].London:The Women’s Press,1988.
[6]Merchant,Carolyn.RadicalEcology:TheSearchforaLivableWorld[M].NewYork:Routledge,1992.
[7]Oates,Joyce Carol.We Were the Mulvaneys[M].New York:Dutton,1996.
[8]Ruether,Rosernary Radford.New Woman/New Earth: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M]. New York:Seabury,1975.
[9]贝蒂·弗里丹著,程锡麟译.女性的奥秘[M].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05.
[10]贝蒂·弗里丹著,小意译.第二阶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1]罗尔斯顿·霍尔姆斯,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2]欧茨、乔伊斯·卡罗尔著,李尧译.中年:浪漫之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本刊声明
作者所呈交的论文必须是作者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对在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作者必须在论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文中不得涉及国家规定的保密性内容。如因作者不慎而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作者本人承担。
本刊不接受一稿多投,因作者一稿多投引起的纠纷,由作者本人承担,本刊概不负责。
《集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Saving Animals to Achieve Self-Value——On Women’s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under Oates’s Pen
YANG Jian-mei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Law,Insf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Zhengzhou 450000,Henan)
Joyce Carol Oates,a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ha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inn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and about women’s rebellion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Under her pen,many women challenge men’s authority through saving animals;in other words,this means that they have achieved self-value through shouldering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She criticizes the patriarchal thinking by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women,the latter of which has been oppressed by the patriarchal thinking,thus representing her eco-feminist thinking.
women;saving animals;self-value;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I3/7
A
2095-3771(2014)01-0030-05
2013-11-08
杨建玫(1970—),女,汉族,河南省安阳市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基金名称: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美国作家欧茨的生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3-GH-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