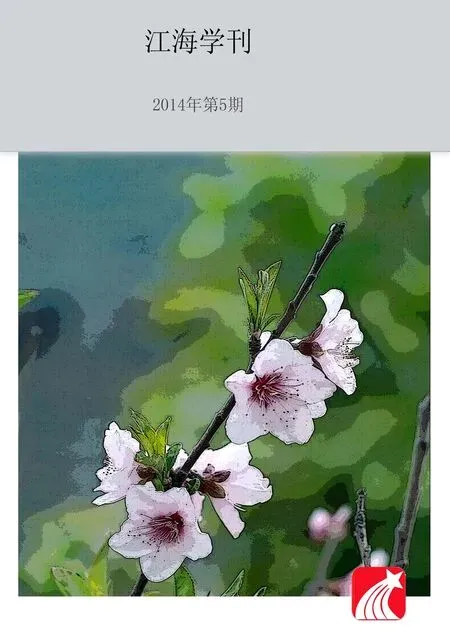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如何“以俄为镜”*
2014-04-17郑忆石
郑忆石
20世纪后期,互为邻居的俄罗斯与中国先后发生了无论方向、方式上,还是速度、目标上都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转型。①这一转型带给两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后果,一方是作为俄罗斯前身的超级大国苏联在分崩离析中其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败落;其二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对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推进。
哲学是社会现实的映照。21世纪的当代俄罗斯哲学,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阴晴不定、涨落起伏的多变历程后,无论在研究的内容、主题,还是思路、方法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在总体上呈现出复兴、多元、开放的新态势。伴随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30多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得到国家支持而获得长足发展并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又因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面临着范式创新和中国化等诸多问题。
作为曾经的“先生”和现在的“邻居”,中国和俄罗斯无论在历史发展中抑或现实国情上的相似性,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代俄罗斯哲学如何被边缘化的教训,挖掘其问题转换究竟有何深层机理,探索其未来会走向何方等问题,以便为处于转型中的当下中国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于是,如何“以俄为镜”?便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何以遭遇“滑铁卢”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需要“以俄为镜”?这有必要简单回顾20世纪后半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命运及其缘由。
从十月革命至国家解体,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遭遇,可谓从天堂到地狱。历史为苏联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行为的理论指导提供了契机,使其得以在国家政权的极力扶持下,从不同领域展开研究并获得理论发展的体系化、系统化,但同时又埋下了最终解体的隐患。之所以如此,与它长期受制于领袖意志和政策导向,缺乏学术的民主与自由直接相关。“70年来,俄国的人文科学(包括哲学)长期被用于为国内决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人服务,许多人文科学被强求一律地按‘唯一正确的学说’发展已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②,以致“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更替,政治路线甚至政策的每一变化,往往都会影响到哲学的发展”③。
在这种氛围下,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注定具有难以消除的弊端: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浓厚的“依附性”使其打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烙印;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过度的“入世化”使其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在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高度的“越位化”使其带有明显的救世主义痕迹;在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上,明显的“封闭性”使其表现出鲜明的保守主义特征。因此,尽管在斯大林时期,苏联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甚至以宪法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并通过大量出版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建立起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④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按理说,这种由国家、宪法规定的形式所强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当在苏联人的精神世界中确立起坚不可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目标。然而,正是由于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过严、过死、过于集中的管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政治化的定位,造成了思想停滞、理论僵化、主流意识形态严重脱离时代、民众及现实的状况,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感。以致一旦斯大林去世,理论禁区一经打开,苏联理论界便极易由反斯大林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走向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极端。
这股最初由赫鲁晓夫刮起的“解冻”之风,首先在理论界得到了呼应。而理论界思想镣铐一经打开,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则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猛烈冲击着苏共长期秉承的意识形态。于是,斯大林逝世后的近40年时间内,苏联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状态:社会层面上,报纸杂志不断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整个舆论导向也在嘲笑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人们力图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但国家层面上,苏共仍一如既往地强调意识形态控制,以致赫鲁晓夫后来以不无矛盾的心态承认,“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⑤,但又不得不沿用那套已经过时,但看起来却尚有作用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办法。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面对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普遍感到“索然无味”的现实,苏共“除了重新编写《苏共党史》、大量印行马恩列著作及勃列日涅夫著作外,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⑥。被严重政治化、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的苏联哲学,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既不能解释苏联面临的各类实际问题,又不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性介入,更没有达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变社会、塑造新人的目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们心目中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丧失生命力、说服力、感染力便是自然的。
事实上,自苏联政局速变⑦以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便开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苏联解体前,由戈尔巴乔夫实行的以“公开性、多元论、民主化”为引导的政治改革,由自由派掀起的全面否定马列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的潮流⑧,进一步引发了社会范围内的虚无主义思潮:历史领域的虚无主义,将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历史,描绘成失误与悲剧交织的历史;文学领域的虚无主义,将举凡颂扬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作品,统统当作挖苦、讽刺、嘲弄、戏谑的对象;道德领域的虚无主义,将所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都当作狭隘经验予以消解和抛弃,并重新祭起70多年前被摒弃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大旗;精神领域的虚无主义,将摧毁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作为走出精神迷途的唯一正确路径⑨。这一切,在推动理论界“百家争鸣”的同时,也引发了哲学界的理论分野⑩和思想混乱。
苏联解体后,失去国家政权支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迅速解体,还与当时俄罗斯社会的现实直接相关。
经济基础的改变,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地位的丧失。苏联剧变之初的俄罗斯民主派,在确定以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后,在总结以往改革教训中改变了口头革命、纸上谈兵式的模式,直接采取行动从而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成为急于在意识形态上推倒重来的国家主政者们的首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俄罗斯社会全面转向私有制时,经济基础的改变自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政治制度的改变,导致了强有力政治核心力量的消失。寻求理论支撑的各派政治势力,在纷乱忙碌的政治争斗、动荡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自然将多元理念作为其理论选择,从而抛弃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由此,失去了社会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出路便似乎只剩下退出当代俄罗斯哲学的历史舞台这样一条路了。
社会心理的转变,促使从官方到民众都选择了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成了严重的禁锢。禁锢的恶果让俄罗斯人一方面认为被严重政治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不适应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需要,一方面又受涌动多年的自由化、民主化、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冲击,在来势猛烈的西方哲学文化价值观中,似乎看到了解救俄罗斯的希望和福音。于是,从官方到民众,都以为只要尽快引进西方哲学文化,就可以立马在思想观念上摆脱社会的精神危机。于是,期望通过尽快摧毁传统意识形态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以便社会形成向西方价值观转变的不可逆转之势,自然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心理。
终于,随着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随着铺天盖地的激进思潮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现,随着甚嚣尘上的攻击浪潮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冲击,随着狂飙突进的西方哲学文化、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席卷与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迅速遁迹乃至“烟消云散”。
21 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复兴中的警示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衰落”⑪后,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呈现出全面复兴的景观,并具有下述基本特点:
一是价值取向更为多元。在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中,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等当代西方思潮仍然畅行无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都能够从中觅迹;救世主义、静修主义、神秘主义等俄罗斯传统宗教思想都仍然不乏新的生长点。而力图将自由、民主等人类普世价值与俄罗斯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相融合,则是俄罗斯哲学研究致力的方向和重心。
二是研究内容更为多样。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历经20多年的重建,已经在达成主导思想“多元共识”的基础上,具有更为多样的研究内容,除了回归欧亚主义,除了重塑“新俄罗斯思想”,除了在复兴宗教哲学中继续提升其地位、影响,除了在热捧西方哲学中继续扩展其研究领域⑫,除了对90年代的诸多研究领域,如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人的哲学、教育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等研究的内容深化,还拓展到东方哲学、全球学、哲学人类学等,除了对研究包括哲学基本理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哲学史(西方的、俄罗斯的)、各哲学分支学科(伦理学、价值论、逻辑学、美学、科技哲学等)在内的哲学理论,还有对斯大林哲学、苏联哲学、列宁主义、第二国际思想家的重新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文本的重新解读。
三是研究活动更为活跃。无论是举办的哲学会议⑬,还是出版的哲学刊物⑭,较之90年代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俄罗斯哲学系的增加、哲学课时数的增长中看出来。与苏联时期只在六所著名大学⑮设有哲学系相比,如今,仅在俄罗斯,就有10多所大学设有哲学系⑯。与苏联剧变后俄罗斯大量削减哲学课程相较,如今俄罗斯的课程设置,虽然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急剧减少了与之相关的课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理论),但整个哲学课程却是不减反增⑰。哲学系与哲学课时数的增加,虽然并不直接说明哲学研究的状况,却也从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哲学研究的活跃与多元化的氛围。
四是评价更为理性客观。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已经具有了更为宽容的气度和更为开阔的眼界,既不因宗教哲学家、苏联时期有独立见解的哲学家及其哲学著作曾经的落魄和如今的得势而盲目推崇、人为拔高;也未因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的霸权和如今的失势而一味拒斥、人为贬低。这一点,我们既可从学界对俄罗斯过去百年的哲学人物、著作的评价态度中看到⑱,也可从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界对于斯大林体制、列宁主义等的评价中得知。与俄罗斯社会和一般学界那般好走极端的众说纷纭不同,俄罗斯哲学界对于斯大林体制、列宁主义等的评价,采取了一种相对客观和中性的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价,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辩护士曾固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反对者也经常抱有的意识形态成见和政治干扰”⑲。
“自由、民主、多元”的研究理念对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研究而言,其作用无疑是双重的:既促使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复兴”,并推动其向更为自由、多元的方向发展;又不可避免地继续消解本已脆弱的“国家意识”,并以此抹去了民众重铸“强国梦”的自信。有鉴于此,俄罗斯的当政者们(先是1996年的叶利钦,后是新千年前夜的普京)才一直要求学者们在基于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社会心理、价值共识的基础上,研究并确定适应俄罗斯社会变化的新“民族思想”,提出一方面要继续坚持精神自由、思想多元、政治自由,否定在俄罗斯恢复和建立任何由官方赞同和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承认出于国家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的迫切需要,要求一个在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中,信奉统一的价值观。
这种新的价值观,虽然强调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俄罗斯传统价值观、20世纪经过历史检验的价值观的“结合”,并力图将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融入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以形成新的价值观念。但是,它同时又十分强调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对于俄罗斯社会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并把为祖国和民族的历史与成就而自豪的“爱国主义”,视为新俄罗斯社会稳定的理论旗帜和人民创造力的源泉;把基于俄罗斯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特征而决定其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个伟大国家,以及研究和运用先进技术、保障人民高水平生活、树立国际形象的“强国意识”,视为新俄罗斯经济繁荣的思想支柱和国策核心;将民主、法制、个人自由、政治自由,与恢复国家权力的并行不悖的“国家观念”,视为新俄罗斯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发展目标;将那种重视国家、社会、集体的传统习惯,强调社会需要共同信仰、全民需要共同奋斗目标的“社会团结”,视为新俄罗斯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民心凝聚的社会基石和重要力量。
可见,普京的“新俄罗斯思想”,核心点和关键词仍然是“国家”。爱国主义、社会团结也好,强调传统观念也罢,在成为俄罗斯复兴“强国梦”精神源泉的同时,都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宣扬着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可见,普京的“新俄罗斯思想”,在表明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将更多地向传统“回归”的同时,也反映出俄罗斯并没有抛弃统一的意识形态或国家观念,只不过,这些新的意识形态或国家观念,穿上了“爱国主义、传统文化”的外衣。
尽管哲学家与政治家思考问题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哲学作为时代发展、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折射,要发挥其“解释世界”⑳的功能,就不可能彻底摆脱“国家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纠缠。尽管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开放、自由、民主的社会环境,但开放不等于放弃主流价值,更不能由此沦落为某些社会势力利用、威胁和危害社会稳定、甚至制造社会混乱、酿成社会危机的工具。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俄罗斯哲学曾经饱受其害,进入新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仍在勉力消除这一给俄罗斯哲学带来严重伤害的危险因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迄今为止,俄罗斯哲学中泛滥的各种思潮,对一些早有定论的理论的任意曲解,对传统文化的随意界说,表明了当哲学研究中的“自由、民主、多元”一旦走向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多元主义,其对哲学研究本身的伤害,并不亚于教条主义。因为究其本质,它不过是一种变形的教条主义,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已。
无疑,“开放、自由、民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发展的前提。但是,如何在“开放、自由、民主”中避免像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那样,走向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元引导的歧途,避免落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陷阱,是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如何“以俄为镜”中,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以俄为镜”
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了解我们的邻居俄罗斯在20多年社会转型中的经验教训一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样需要了解俄罗斯在20多年中,其社会意识是如何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变化的:即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是如何在叶利钦执政的八年里,破除了高度垄断的斯大林政治体制,结束了集权垄断、党政合一,建立以总统设置、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特征的政治体制,实现了多元化、自由化。与之相应的,是西方哲学、宗教哲学如何在90年代的哲学解体中,迅速成为哲学中的时尚,又如何随着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受阻而迅速衰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去意识形态化、多元化、自由化中被边缘化、被抛弃的?在21世纪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又如何通过国家权力的调整,意识形态逐渐与中央集权的新趋势相一致,而强调“新俄罗斯思想”㉑的?如何认识这一似乎具有集中统一色彩的治国理念,这一貌似“一元”的思想观念所强调的实质?㉒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在多元化、自由化的社会氛围中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虽然重新被人们关注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仍然被排斥在主流意识之外。而“新俄罗斯思想”本身,也表明了俄罗斯对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矛盾心态:既具有明显的权威主义色彩,又强调了民主化、多元化对俄罗斯社会的重要性。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在迫使我们思考如何才能坚守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阵地的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以俄为镜”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当务之急,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
(一)路径选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引领
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已经走上了分散、分化、多元、开放之路。然而,作为体系化的世界观,哲学无法摆脱政治“纠缠”的客观现实,这决定了它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又决定了它面对社会的伦理道德、精神意识的问题,负有重建主流意识形态或主体价值体系的使命。因此,吸取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两极化”的教训,需要我们既保持思想的独立行走、精神的自由思考,又要为社会的健康文明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撑和精神指导。
与之相应,当我们赞叹当代俄罗斯哲学的“开放”时,又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开放”的走向,是仅将西方的哲学与文化视为唯一坦途,或只以传统哲学为唯一根基㉓,则难免陷入新的理论误区。因此,如何通过思考当代俄罗斯哲学对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的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西方先进文化的吸取三者之间的有效结合,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需要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二)方法选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论
路径的选择离不开正确的方法。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能否通过“以俄为镜”担当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之责与社会之责,还在于能否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具体言之:
1.坚持历史生成与逻辑生成的结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俄为镜”的目标所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在”与“未来”。但“现在”由过去走来。因此,“描绘现在”需要“回溯过去”,以便在知晓当代俄罗斯哲学今天何以如此的原因同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引以为鉴的历史素材。“现在”又是通向未来之桥。因此,“描绘现在”又需“洞悉未来”,以便在看清当代俄罗斯哲学未来发展动向的同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定理论导向提供精神支撑。有鉴于此,必须将当代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演进历程,置于其生成的思想源流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在追溯当代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形成的理论脉络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俄罗斯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历史,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厘清各自的演进历程,在对两者的比较分析中,获得清晰的理论前提。由此,“出入历史”与“出入理论”,在历史生成与逻辑生成的互动中,展开对当代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比分析,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以俄为镜”的基本方法。
2.坚持哲学比较与社会现实的互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俄为镜”的价值诉求,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推进,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引领。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俄为镜”之路,要求比较两国哲学何以“似曾相识”又“独自徘徊”的过去、现在、未来,并在这种比较中寻求其学理原因。然而,理论源自现实,哲学折射时代,学理分析只有紧扣实践,才能避免泛泛而论。因此,在将两国哲学何以“似曾相识”又“独自徘徊”的学理原因与社会根源相契合的探讨中,需要我们既“走入哲学”又“走出哲学”。具体而言,就是在对两国哲学各自面临的问题、以何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哲学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和程度、对当代俄罗斯哲学何以有着如此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现实境遇的原因等等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寻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其使命的最佳途径。由此,在“源于哲学”(以哲学为轴心)与“高于哲学”(在回到社会生活的“问题”中反思哲学理论)的互动中,展开对当代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比分析,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以俄为镜”的又一基本方法。
3.理论阐释与价值评价的融合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俄为镜”的未来走向,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提供学理支持。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俄为镜”之路,需要围绕30多年来两国哲学发展的现状,在运用历史追溯与逻辑归纳、走入哲学与走出哲学、具体分析与整体比较相结合等方法来看清自己的未来。但“点燃过去”是为了“照亮未来”;“出入哲学”是为了服务当下;“微观与宏观”的透视是为了寻求意义价值所在。而意义与价值,又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应有与现有的统一。因此,如何通过客观的理论阐释进行比较,透过比较看清俄罗斯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实现了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又在这种发展中达到自身发展目的;如何在对两国哲学做出这种历史还原的纵深分析和现实展现的横向比较中,以同样客观的态度,分析比较两国哲学各自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在尽可能避免好坏是非的极端评价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自己在世界哲学格局中的现实地位与未来走向的关键。因此,“客观描述”㉔与“主观评价”㉕的融合,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以俄为镜”的方法之三。
①在方向上,有放弃还是坚持社会主义之别;在方式上,有剧变还是改革之别;在速度上,有激进还是渐进之别;在目标上,则有趋向西方认同目标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观西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之别。
②[俄]B.A.沃龙佐夫:《俄罗斯科学改革中的重中之重》,《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通报》1998年第1期,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③贾泽林等编:《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④在中学、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规定高校学生必修包括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学习的人数达到千万。
⑤[苏]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⑥周尚文:《苏共在党建中的疏失及其教训》,《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⑦标志之一是主要领导人走马灯似的快速更替: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接替勃烈日列夫,1984年2月契尔年科接替安德罗波夫,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
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苏联“所有的职业演说家的演说,都是从痛斥苏联的过去开始,而以赞扬西方结束”。([俄]B.利西奇金、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⑨参见杨金华《虚无主义思潮与意识形态危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⑩为数众多的反马克思主义极端激进派,他们以“反正统”自居,以“无知者无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大量耸人听闻之论攻击马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为数甚少的传统正统派,他们坚决反对激进派的所作所为,以维护“传统、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为数较多的中间温和派,他们既反对极端派也不赞同正统派,主张以批判分析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
⑪作为对苏联哲学的反弹,这一时期只有宗教哲学、西方哲学尚有生机。即便如此,与整个社会的乱象相一致,哲学在总体上是衰败的。
⑫当代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都可以在当代俄罗斯哲学界觅得研究踪影,如当代西方风头正盛的分析哲学、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等,在俄罗斯都获得了充分的研究。
⑬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哲学会议的举办次数十分有限,即便是最多的1995年,也只有18次;参会人员有限,即便是最为壮观的1997年“全俄第一次哲学大会”,也只有1098名与会者。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会议举办次数增加,仅在2000年,全俄罗斯的哲学会议就达92次之多;会议规模扩大,如2005年召开的全俄第四次哲学大会,设立分会场25个,讨论题目25个,与会者5000人,提交论文3000余篇,
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哲学刊物的出版,虽然增长但仍然数量有限,即便是最多的1998年,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仅出版了106本哲学专著(参见李尚德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不仅书籍、杂志等出版物数量大为提升,而且出版物质量有所提高。(参见B.A.列克托尔斯基《纪念〈哲学问题〉创刊60周年》,《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3期)。
⑮如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明斯克大学、哈尔科夫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⑯如国立莫斯科大学、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国立莫斯科文化艺术大学、莫斯科人文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国立俄罗斯师范大学、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国立俄罗斯社会大学、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以及一些理工科院校,等等。
⑰即普遍地由过去的每周4学时增至6学时,由每学期80学时增至120学时。
⑱上世纪末,俄罗斯哲学界做过对百年来哲学人物和著作评价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学界公认的30位著名哲学家中,有16名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多为宗教哲学家,并在20世纪20年代被镇压或被驱除出境;有14名马克思主义者,但其中大多为苏联时期受排斥遭打击的对象。在30位的排名序列中,宗教哲学家排在最前面,其中别尔加耶夫列第1位,其余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分列其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列宁为第12位,普列汉诺夫为第18位。在苏联时期的哲学家中,科普宁、凯德诺夫、弗罗洛夫等位列20名之后。(参见李尚德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页)
⑲[俄]B.M.梅茹耶夫:《我理解的马克思》,林艳梅、张静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⑳经过教条化苏联哲学惨痛经历的俄罗斯哲学家们,已经放弃了对哲学具有“改造世界”功能的认可。
㉑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参见《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0页)
㉒对此,普京认为,它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普京还根据俄罗斯的特定条件,指出它绝非斯大林时期的类似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统天下的“一元”,而是与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同时反对建立极权制度相适应的“可控民主”之表现形态。(陆南泉等主编:《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上),序二,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㉓例如,今日俄罗斯学界的“西化派”与“传统派”各自的主张。
㉔对两国哲学三十余年发展现状的描写阐述。
㉕在对中俄哲学各自三十余年发展历程的“客观描述”中做出应有评价;以“国家意识”、“全球意识”、“文化意识”、“自我意识”为核心对俄罗斯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整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