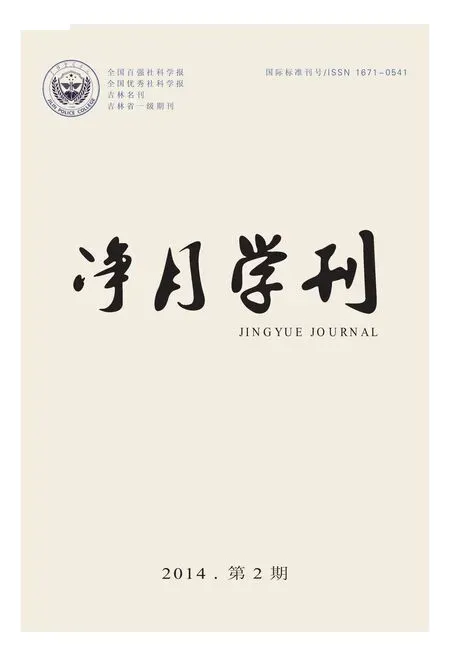论扒窃行为的独立构罪
——以“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背景
2014-04-16花岳亮
花岳亮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63)
论扒窃行为的独立构罪
——以“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背景
花岳亮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63)
最高院、最高检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之后,对 《刑法修正案 (八)》新增的几种盗窃类型做出了具体的条文解释,为进一步准确适用盗窃罪奠定了法律基础。解读2013年新司解条文,扒窃行为能够独立构罪,突破了盗窃罪传统数额犯的藩篱,但2013年新司解中对扒窃的解释在整个盗窃罪体系中仍旧存在着定位不清晰与界限模糊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扒窃相关问题的厘清,希冀对实践中具体适用扒窃入罪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盗窃罪;司法解释
我国于2011年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了大幅度修正。为适用好新盗窃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指导实务部门打击盗窃犯罪。其中就扒窃入罪自草案提出以来一直为理论和实务界所争议,“两高”最新《解释》对扒窃进一步明确化,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新司解的背景下对扒窃做好解读。
一、《解释》中扒窃的理解
(一)明确扒窃独立构罪
扒窃是否入罪的问题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而尘埃落定,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刑法》第264条盗窃罪中新增盗窃类型的理解。在原有以数额为标准的一般盗窃和多次盗窃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新内容。对于新增盗窃类型,学界有着不同理解。其中争议最大的是针对《刑法修正案(八)》新规定的“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到底是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两种行为类型还是应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和“携带凶器扒窃”。《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不少学者撰文从多角度将“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理解为后者。
随着“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的发布实施,对“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理解上的争议已烟消云散。从两高新司解第3条可看出,该条对《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分别用一款的条文来说明。新司解对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分别加以解释,可见“两高”已明确扒窃应当独立成罪,而不是理解成携带凶器扒窃,扒窃也不需和“携带凶器”绑定而受其限制。因此,扒窃独立成罪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为此就扒窃需借助《解释》的具体规定来理解。
(二)解析扒窃构罪要素
《解释》第3条第4款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理解扒窃,可据司解条文从三个方面来认定。
1.扒窃的空间地点。“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是对扒窃行为发生的空间地点的具体规定。这一规定符合日常生活对扒窃行为的理解,并未超出一般人的观念范畴。扒窃是第2次草审过程中匆忙添加上去,必须对其发生的空间地点明文规定,首先要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基础,其次需对《刑法》语言进行提炼以契合条文,再次需将扒窃行为明显区别开其他特殊类型的盗窃。限定了扒窃的空间地点,就能明确在户内是没有发生扒窃的可能,也就不会产生“入户盗窃”与扒窃适用上的冲突。当然也将扒窃与以数额为入罪标准的一般盗窃犯罪区别开,对盗窃罪的适用有重要意义。
2.扒窃的行为对象。扒窃作为盗窃罪中一种特殊类型化行为,其行为对象当然地理解为财物,但作为盗窃罪的行为对象——财物,在理论界内存在着争议。“财物”的理解范围有一定的宽泛度,但是一般盗窃中对“财物”存在的争议在扒窃的行为对象中基本不会有。因为扒窃行为的特殊性,其作用的行为对象也必然有其特殊化。其行为对象应限定于具有价值和管理可能性的有体物,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有体物都可以成为扒窃的行为对象,比如说有体物中的不动产不会成为扒窃的行为对象。像无体物、财产性利益、虚拟财产等不具有实物性,行为人无法通过扒窃的方式取得,理应将其排除在扒窃行为对象之外。扒窃行为当场短时间取得的性质决定了其行为对象范围必须小于一般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其行为对象应该有前述的限制。
3.扒窃的对象限定。普通的盗窃行为只要一般意义上秘密取得,达到构罪数额的财物就成立盗窃罪,而新司解对扒窃的行为对象做了明确限制,必须限定为“他人随身携带”。有“随身携带”的限定,扒窃的行为对象就被大幅度缩小。正如前述,其行为对象应该限定为有体物,再增加“随身携带”的限定语,行为对象就进一步明确化,对于“随身携带”的具体理解将在下文中详加阐述。随身携带性作为界定扒窃入刑的关键要素,一方面有利于精确地认定扒窃行为以区别于其他特殊盗窃类型,另一方面更便于在实务中准确地规制扒窃行为。
(三)扒窃独立成罪的重要性
首先,“两高”《解释》将扒窃行为作为盗窃罪的一种新类型予以法定化,奠定了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条文基础。明文规定扒窃独立成罪能迅速平息理论界关于“携带凶器扒窃”的争议,指明了理论研究的方向,避免了研究资源的浪费。
其次,对于与一般传统盗窃行为以及新增盗窃类型相区分,进一步细化盗窃行为的制裁法网,使盗窃行为入刑更加细致化。明确扒窃入刑一改笼统定罪的传统,让《刑法》制裁更有针对性,依据不同的行为方式确立不同的入刑标准,符合刑罚个别化的要求。
再次,扒窃独立成罪有利于实务中正确地认定扒窃行为,降低扒窃的入罪门槛儿,有利于严厉打击社会上严重的扒窃现象,扭转社会上的不和谐现象。
二、扒窃解读中的困境突围
随着扒窃罪行法定化,《解释》对扒窃的定义虽然消解了“扒窃”与“携带凶器扒窃”的争端,但是在对新司解关于扒窃的解读中,发现细究之下仍存在解读中的疑惑,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都会面临一定的困境。为此,需对《解释》的扒窃做更深入的解读,以期在扒窃解读的困境中突围。
(一)“公共场所”的概括化
“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应当认定为 ‘扒窃’”,《解释》中界定了扒窃的空间地点,以此一方面符合一般人的观念,另一方面限缩定性扒窃的空间,以划清与其他盗窃新类型的界限。但是何为“公共场所”?日常生活中界定的公共场所,能否直接应用于司解?法律用语是否应高于日常生活用语?认定扒窃行为的公共场所能否类比于其他罪名中的公共场所?这些疑问随着《解释》的出台相伴而生。
《刑法》总则第五章并未对“公共场所”一词做明文规定,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场所管理条例》,根据场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将公共场所分为公共娱乐场所、公共交通场所、游览场所和商品交易市场四种类型,包括七个方面。该条例采用列举的方式无法囊括所有的公共场所,条例的规定也无法直接适用于《刑法》,不能为《刑法》所直接采纳。
此外,《刑法》分则中包含“公共场所”的罪名有第130条的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第291条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等。第291条对“公共场所”以罗列+兜底的方式界定,细究之下该条文也未明确“公共场所”的具体内容。
之所以要明确“公共场所”的具体内容,是因为一方面要与入户盗窃分开,至于“入户”在抢劫罪司解中已明确规定,可作为“入户”的判断依据。那么除去“户”所包含的内容,其余相应场所还是不能直接划归到公共场所的概念下。这就必然在“户”与“公共场所”之间存在一个真空地带,在这一真空地带采用等同于扒窃手段的方式盗窃是定性为扒窃还是认定为一般盗窃,就产生了疑问。针对这一情况应谨慎对待,因为扒窃这一单一行为的入刑降低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儿。是否将这一真空领域纳入“公共场所”之中即是否将行为人规制于《刑法》之下的关键点。
基于《刑法》谦抑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考量,在目前对“公共场所”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应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中界定的“公共场所”为基础,结合《公共场所管理条例》的规定,严格限制规定公共场所的范围,将以往部分学者认定的建筑工地、高校教室以及机关单位的办公场所排除在公共场所的范围之外。将这些场所发生的盗窃认定为一般盗窃,避免简单地认定为扒窃,避免轻易对盗窃行为人动用《刑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新司解对“公共场所”的概括化规定,从而更好地适用条文来规制扒窃。
(二)“盗窃”的重复化
“两高”《解释》对扒窃的定义中“……上盗窃他人……”动词词语采用的仍旧是“盗窃”一词,以盗窃来定义扒窃,此种解释有重复定义的嫌疑。既然扒窃是盗窃罪的一种特殊的构罪行为,那么扒窃就应是盗窃的下位概念,然而新司解又以盗窃来定义扒窃,这种以上位概念来定义下位概念的归纳方法违背逻辑,不符合基本的思维逻辑过程。根据该定义,可说明行为人在公共场所盗窃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时是扒窃,构成盗窃罪。在对扒窃行为人的行为进行描述时,已用“盗窃”一词,跳跃扒窃这一层级,就直接说扒窃行为人在“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时构成盗窃罪。从这一论证行为人构罪的思维过程,可看出扒窃行为人是“盗窃”而被认定为盗窃罪。这种属概念是属概念,而缺乏种差的定义方式明显违背基本的定义原理,其中存在的逻辑矛盾冲突不言自明。
《解释》中出现这样的逻辑瑕疵有着其自身的历史缘由。“扒窃”一词以前仅限于侦查学和犯罪学使用,中国政法大学的徐久生教授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对扒窃定义为:“‘扒窃’一词不是法律用语,而是公安机关特别是一线民警在工作总结时常用的词汇,是指在公共交通上,或在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行为人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从他人身上获取财物的行为。”作为非法律术语的扒窃一词,将其纳入《刑法》的语言体系中,自然缺乏法律用语的明确性和精练性,需要法律明确其具体内涵,划定适用范围圈。
以盗窃来定义扒窃并将其纳入盗窃罪的条文中,这是一个回到原点的怪圈。既然《解释》已做出规定,那么我们暂时需在该条文之中理解适用扒窃。盗窃作为一类罪名规定在分则的《财产犯罪》一章中,有着该行为的特殊性和入罪的必要性,就是行为的秘密窃取的性质。那么以“盗窃”一词做谓语来解释“扒窃”,在认定扒窃行为时,也必须强调行为的秘密窃取性质。秘密窃取性质是相对于被害人而言,否则在被害人明知的情形下,该行为就会符合抢夺罪或者抢劫罪的犯罪构成,不再属于盗窃的规制范畴。
尽管以“盗窃”来定义“扒窃”存在逻辑上的悖论,但还是要以体系解释来正确界定扒窃行为。抛开逻辑上的矛盾之处,扒窃行为被写在盗窃罪名之内,其自身就需符合秘密窃取的要求,不得背离这一基本要求。当然能将定义中的“盗窃”改成窃取更佳,也就避免了逻辑上的不周延。
(三)“随身携带”的笼统化
《解释》规定“……他人随身携带的……”认定为扒窃。“随身携带”看似日常生活用语,但被纳入《刑法》条文后就需对其细致地探讨。有论者将“随身携带”理解为受害人贴身携带的财物;有论者将其解读为既然是“扒”,就应是与他人紧密联系并受他人实际控制的物品;还有论者将之解释为他人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的财物。汇总这些观点,简单说来就是财物在物理距离上与被扒窃的被害人的远近,这一物理距离到底可延伸到多大的范围却无定数。当然不能删繁就简地以物理距离的远近来简单化认定“随身携带”。
首先涵盖在“随身携带”的语境之下的贴身携带毋庸置疑,这也是对其的当然解释。贴身携带一般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对被扒窃财物的位置要求。位于被扒窃的受害者脖子上的项链、手腕上的手表、口袋里的财物、肩上背的财物、手里提的财物都是贴身携带之物,一旦行为人窃取这些财物就符合了扒窃定义中“随身携带”的规定。对于贴身携带当然属于“随身携带”在理论上一致认可。
然后是解读成“近身携带”,大部分论者也认可这一解读。仅将“随身携带”局限于贴身携带,无疑会极大地缩小扒窃的适用范围,不能准确做到对每一种犯罪行为有效地定罪量刑,处以刑罚,达到预防的目的。如何准备界定近身携带,应将贴身携带的财物限定在他人事实支配领域内的财物,对于表面上处在他人支配领域之外,但存在可以推知由他人事实上支配的状态时,比如他人门前停放的自行车,用于食堂占座的水杯、手提电脑等,对于后者可以推知的情形,不能够认定为贴身携带,因为这完全等同于在无人的房间窃取财物这种一般盗窃。此时财物所有人不存在现实地支配,更具体地说就是财物所有人没有现实地握有财物,短时间内不可能及时地对自己的财物进行现实的支配。扒窃之“扒”在于行为人短时间内迅速窃取他人财物,行为人完成扒窃后,盗窃罪即告既遂。即使此时他人及时发觉财物丢失,对扒窃行为人来说其扒窃行为已经完成。因此,扒窃的迅捷性必然对应着财物所有人在被行为人扒窃这短暂的时间内对扒窃行为处于无知与不知的状态,否则也就不是扒窃行为。
近身携带的财物应该解读为在被扒窃者的事实支配领域内的财物,并且被扒窃者要对该财物现实地握有或者监视,处于被扒窃者随时可掌握之中。只有这样规定近身携带,才能将一般意义上的财物占有区别开,圈定扒窃行为自己的行为对象。将“随身携带”解读成贴身携带和近身携带,有利于正确地认定扒窃行为的行为对象,合理地划定扒窃行为的规制范围,一方面保证《刑法》的谦抑性,另一方面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扒窃构罪的具体适用
界定了扒窃行为的构罪要素,分析出经过新司解定义后扒窃行为的原则性之处,找到破围之术,对实践中具体适用扒窃来认定盗窃罪,就需跳出扒窃行为自身,来分析清楚与其他类似的或重合处或相似处或联结处,从而更准确地适用法律条文来定罪量刑。
(一)扒窃的去行政化
扒窃行为被纳入盗窃罪肇始于1997年最高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司解要求在一年内三次以上扒窃的才构罪,对于扒窃一次的行为还不足以将其摆在《刑法》的天平上。那么对于一次或者间隔性的两次扒窃行为如何处理,则由《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规制。《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骗……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实践中相当部分的扒窃行为被认定为这里的“盗窃”而受到行政处理。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以及“两高”最新司解实施后,针对扒窃可以单独成罪的规定,存在如何处理针对扒窃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与界限问题。既然《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司解都已将扒窃独立入罪,此时在《处罚法》中的盗窃就无须再涵盖扒窃,而是将扒窃全部交由《刑法》来规制,以此来分清行政法与刑罚在规制扒窃上的含糊界限,避免在具体适用中的过度自由裁量权,以保障当事人权益。对于存在重刑主义的忧虑可借鉴前述的论证,再将扒窃纳入《刑法》的视域中,在具体认定其性质时结合《刑法》第13条的但书就完全可以解决指责者存在的重刑主义倾向。将扒窃完全从行政处罚当中剥离出来,归入《刑法》的归责体系中,对解决行政与刑事在处理扒窃交集问题上的矛盾,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扒窃的去数额化
《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扒窃的……”首先可以解读“扒窃”是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相并列的盗窃罪规制情形。传统盗窃罪一直以来被认定是典型数额犯,即使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新增加了几种类型后,还有学者坚持认为盗窃罪是数额犯。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后,对盗窃罪是否原来的纯粹数额犯争议的焦点在于扒窃构罪原则上是否还需以数额作为入罪要素。
诸多学者不认可扒窃行为独立成罪时不需数额加以限定,其中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是扒窃入罪是在修正案二次讨论时才临时加进去的,其论证合理性不够充分,将置于盗窃罪中作为入罪的类型之一,就应受盗窃罪是数额犯的限制;二是最主要的理由,如果《刑法》只是规制单纯的扒窃行为,脱离数额的限定,那么实践中只要有扒窃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扒窃取得受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无论是否具有价值,无一例外加以《刑法》制裁,这完全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体现了重刑主义,不利于保障权益。
针对上述坚持扒窃以数额为标准的观点,在《刑法修正案(八)》审议过程中出现任何一种审议要求都是符合审议的规则流程,以此作为否认扒窃行为入罪去数额化的理由未免牵强。再有就是以实践中只要扒窃就入罪的情形作为反驳理由也不具有合理性。抛却数额对扒窃行为入罪的限定就会引发刑罚不合理的现象的臆想也是没有根据的。坚持认定行为人一旦扒窃并从被扒窃者处取得财物就入罪,完全符合条文规定,恪守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另外,在扒窃的财物价值相当细微乃至微不足道时,入罪将违背定罪量刑的均衡原则之时,可引用第13条的但书来加以限制,将行为人隔离在《刑法》的阈限之外。通过但书来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遵循了法治的理念,同样起到保障权益的作用。公安部1993年颁布的《关于修改盗窃案件立案统计办法的通知》中规定,已将扒窃犯罪的立案标准提到“不论盗窃财物数额多少,均立为刑事案件”的高度,从历史角度看,扒窃也无须数额就构罪。因此,仅以扒窃行为入罪易致无罪重罚、轻罪重罚的现象为由,不足以要求扒窃入罪需以数额为限定入罪条件。
从新司解中可找到支撑扒窃构罪无须数额为限的理由。新司解第6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3项至第8项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数额达到本解释第1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50%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中对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这两种情形与数额联结来认定“其他严重情节”,可理解为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是需以数额加以限定来认定构罪,或者至少说该两种情形之下是可以和数额相联系来确立构罪的。那么为何没有将扒窃与数额联结来认定严重情节,就恰恰说明司解遵循了《刑法修正案(八)》立法的原意来进行司法解释,而立法原意就是扒窃行为可以单独构罪而不需数额再作为构罪要素。
因此,在认定扒窃的构罪要素时只考虑扒窃这一行为是否成立,其他任何要素都无须纳入考虑范围。扒窃的去数额化在实践中必须切实贯彻好这一规定,严格依照法条的内容来定罪量刑,而不允许在扒窃行为入罪上有过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三)扒窃的类型固定化
1.与“数额较大”的分离
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是将盗窃罪圈定在数额犯这一类域中的“功臣”,然而随着新的类型的加入,为了清晰地界定各自间的区别,盗窃罪已经突破数额犯的藩篱。为此,正如前述,扒窃已经完全与数额要素分离,数额不再是认定扒窃的前置要素。
2.与“多次盗窃”的脱离
1997年的最高院司解将一年内3次以上扒窃定为多次盗窃,在2013年新司解实施后,扒窃从多次盗窃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构罪条件。新司解对“多次盗窃”的界定,“两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其中“盗窃”一词的理解成为关键。在盗窃罪中的“盗窃”看,其包含数额较大的普通盗窃、入户盗窃以及扒窃,但新司解第3条第1款中的“盗窃”是否有扒窃之意?这里的“盗窃”只是指代有数额要求的普通盗窃,而不能够宽泛解释为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因为扒窃按前文所述,只要行为完成就能独立入罪,而不会存在两年内扒窃未成达到3次,其危害性明显,而用“多次盗窃”来规制。扒窃因为其行为的特殊性和行为完成的即时性,只能以扒窃获得他人的财物才认定构罪,所以只有扒窃并得他人财物才可认定为扒窃,对于扒窃的准备阶段的预备行为都不能认定为扒窃行为,也就不会存在准备扒窃却未得财物两年内累计到3次而认定为“多次盗窃”并定盗窃罪。扒窃应以新司解为条文、为基础,摒弃1997年司解将扒窃纳入“多次盗窃”的规定,将扒窃作为独立的构罪类型加以固定化。
3.与“入户盗窃”的不兼容
至于扒窃和“入户盗窃”的分立是显而易见的,《刑法修正案(八)》将二者并列规定于同一条文之内,此次“两高”新司解又将扒窃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发生的盗窃他人携带的财物的行为。因此,由“户”和“公共场所”的各自相对立不兼容的含义可见扒窃和入户盗窃之间只能相互独立,各自独立构罪,而不会发生两者之间的交叉竞合问题。
4.与“携带凶器盗窃”的离析
新司解发布实施之前存在着是否将“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与携带凶器扒窃的争议。新司解发布后,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分别独立构罪,两者之间的争议不存在了。
那么,看似解开了缠绕在两者之间的纠结点,但是面临的新问题是,如果行为人是携带着凶器进行扒窃之时,此种情形下应该构成盗窃罪是确定无疑的,但定性之后如何具体量刑却问题显现。此时,携带凶器盗窃已能够独立入罪,扒窃也是如此,当二者复合到一个行为之中,问题随之产生。既然《刑法修正案(八)》已将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独立成罪,那么当携带凶器扒窃时,不能简单地把携带凶器盗窃中“盗窃”再宽泛地解释为包括构成盗窃罪的各种情形,就是不能把扒窃包含在携带凶器盗窃的“盗窃”之中。否则就会把携带凶器扒窃解释成携带凶器盗窃,使新司解已界定清楚的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再次混淆。
携带凶器扒窃的,应该认定为既符合携带凶器盗窃的构成,又符合扒窃的构成。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分别属于盗窃罪规定类型,二者都是基本犯罪情节,并非加重的犯罪情节,这两种类型均构成盗窃罪,而并非分别构成独立的罪名,并不符合想象竞合犯构成要求。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同种数罪并不分别处罚,为此针对携带凶器扒窃的,就只能适用盗窃罪的基本的量刑情节。并且在适用基本的量刑情节之时,不能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强调只能在基本的量刑情节之内,绝对不允许超出量刑幅度的上限。至于携带凶器扒窃具有盗窃罪的两个基本的情节时,可以接近基本量刑幅度上限进行量刑,以示《刑法》对携带凶器扒窃的社会危害性的否定。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肖中华.侵犯财产罪办案一本通[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
[3]柯汉民等.盗窃罪证据运用及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4]陈家林.论刑法中的扒窃——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与解读[J].法律科学,2011,(4).
[5]时方.对扒窃行为的理解及司法适用的探讨[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6]李竟芬.“扒窃人刑”中若干争议的消解[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2).
[7]陈平.对扒窃入罪的理性思考[J].政法论坛,2011,(15).
[8]许光.试析扒窃入罪的条件与司法认定[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
[9]李翔.新型盗窃罪的司法适用路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5).
[10]周啸天.携带凶器盗窃的刑法解析[J].法律科学,2011,(4).
[11]付立庆.让立法远离浪漫主义的迷雾[N].法制日报,2011-03-30.
(责任编辑:孙秀娟)
D924.11
A
1671-0541(2014)02-0106-06
2013-11-25
花岳亮(1989-),男,江苏南通人,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刑法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