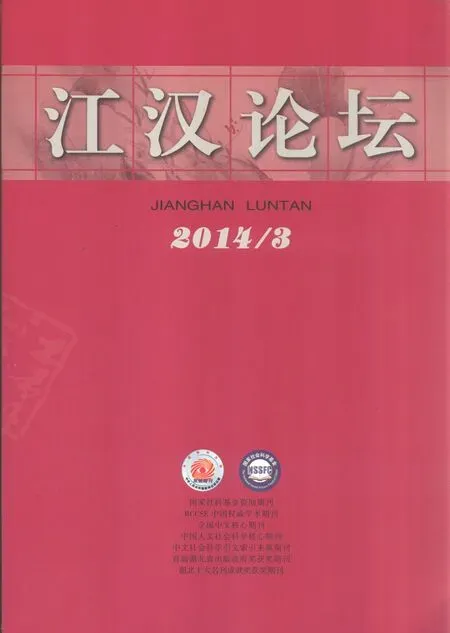集体谈判中政府侵权现象研究
2014-04-16艾琳
艾 琳
近年来,劳动关系矛盾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不但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也决定着社会的平衡。但不同利益主体的表达能力和维权能力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建立起一个利益表达机制方能达到动态平衡的市场关系、社会关系。集体谈判制度的确立无疑便是一种重要的利益表达机制。
政府介入劳动关系主要是运用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是通过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行使来实现的。在集体谈判中,政府并不代表或者直接融入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任何一方,而是居于劳动者和雇主双方之上,以“裁决者”和“公正者”的身份主持社会公正,这种公正也是以保护劳动者为宗旨的劳动法的立法依据。在这种立法依据上,政府的作用就是强化一部分人的权利并限制一部分人的权利,追求法律的“实质的平等”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相对于劳动者是促进劳动者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相对于雇主则是劳动者权利保障的权利主体,是一个特殊的法律关系主体。
一、政府在集体谈判中的侵权现象
综观我国集体谈判制度的运行现状,不难发现,由于政府在自身功能定位和施政目标设置上的原因,造成了许多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
(一)政绩导向下的政府越位
我国的集体谈判是一种由政府主导、官方工会发动、企业工会代理、地方党政机构配合的自上而下的功能形态和推进模式,它有别于以劳动者的诉求为起点、工会作为代表、政府监督协调的自下而上的运作体制和制度安排。在自上而下的集体谈判中,政府始终以主动参与、主导实施的姿态提供行政强制力的支撑,本应是谈判主角的劳资关系双方却不能成为推进集体谈判的主体力量。有学者认为,集体谈判在中国的引进是一个官僚化的过程,它是由地方党政机构推动的,而不是对劳资关系的主动回应,企业经营中的工资和雇佣条件都包含在了当地政府颁布的指导框架中。②这个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谈判推行过程包括制发文件、分派任务、限期达标等,政府部门和工会将研究提出并经上报批准的集体谈判“内容”和“要求”传达到企业,作为企业劳资双方讨论协商的核心要求和主要参考。因此,在集体谈判的过程中少有工人参与,也较少有真正的谈判过程,集体谈判多流于形式。③例如,2010年8月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10]32号)第二条明确规定:从2010年到2012年,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实行集体合同制度。诚然,在行政层面通过量化的指标推行集体谈判制度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数字的增长可以部分证明进步的存在。但是如果在推进集体谈判制度的出发点上不能体现对谈判主体地位的尊重,不能还原集体谈判的本质要求,在推进集体谈判的过程中,不能够加强对谈判过程及手段运用的指导,政府就难免出于政绩的考量,把完成集体合同覆盖率指标当作集体谈判的目的。以这种方式完成的集体谈判,实际就会演变为“政府下达任务—工会提出要约—企业配合应约—政府部门检查推进”的要约工作链。
同时,我国《集体合同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工会或职工代表提出的集体协商要求的,按照《工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工会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依法处理。该法明确地把对集体谈判义务主体侵权的救济责任全归于政府。毫无疑问,在劳动纠纷的处理中,政府的行政救济确实是一种十分直接且可行的介入方式,但不应该成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方式。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行为的目的应该是把劳资双方都纳入到一定的法律制度框架之内,尊重劳资双方的主体地位,以劳资双方契约自治方式和制度化形态来化解、处置劳资矛盾。由此可见,在我国的集体谈判实践中,政府同时身兼运动员、裁判员两个角色。
(二)管制导向下的政府缺位
政府介入劳动关系,要通过一系列的劳动标准立法,维持社会基本的公平与稳定④,才能起到均衡和制约的作用。政府不能通过立法来保持劳资关系双方力量的对等均衡,不能通过立法来约束劳资关系双方的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缺位。例如,旨在强化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劳动合同法》对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是暂且不作规定,或者只作原则性表述,带来了集体谈判实践中大量依据不充分、不明确情形的存在。一般而言,引发劳资冲突特别是劳动者集体行动的普遍原因是工人权利受损,在劳资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政府更有责任通过公权力的介入来实现劳资双方力量的相对平衡。亚当·斯密指出:工人在经济上的维持能力总比不上老板,因此,工人的联合或工人协会往往更具有暴力性和侵犯性。⑤这种因能力上的缺失而造成的实际危险,政府是要有所预防、消解和补偿的,如果劳动者的权利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引发涉及范围更广、更为激烈的劳资冲突将不可避免。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共同进步的状况下,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可以也应当形成利益制衡的格局,使有着不同利益和主张的群体能够共生共存。劳资双方为实现合作互利,需要法律制度进行保障;劳动者为追求自身合理权利的抗争,也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
此外,政府在劳动者权益受损时的行政救济也同样存在着缺位现象。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末,全国劳动监察机构共有3291个,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配备专职保障监察员2.3万人,同期全国就业人口总数为79163万人;到2012年末,全国劳动监察机构仍为3291个,配备专职劳动监察员2.5万人,全国同期就业人口总数为76704万人。⑥笔者计算,2010年,专职监察员与就业人员数量比约为1:34419,2012年数量比约为1:30681,虽然比例有所提高,但劳动监察的力量仍十分薄弱,劳动监察的效果可想而知。劳动执法力量不足也反映了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视不足。执法者自身缺乏权利受侵害的切肤之痛、检查人员配备数量不足是集体谈判权行权艰难的另一个方面原因,更关键的是如果不改变“市场转型期的中国劳动政策变迁的基本取向是服务于企业效率和国家经济发展”⑦的格局,那么,政府缺位的现象就不可避免。
(三)利益导向下的政府错位
长期以来,政府习惯于以行政手段调整和控制劳资关系,但是这种方式因与雇主主导的劳资关系现实相悖,已经被证明是难以有效发挥应有作用的。政府一方面出于职责的要求,应对集体谈判义务主体的侵权行为进行强力干预;另一方面出于招商引资、加快发展的政绩需要,又有意无意地暗许或者放纵雇主不履行诚实谈判义务,放弃了对有失公平、公正的劳资关系进行严格校正的责任。因此,在看到失衡的分配制度是诱致我国劳资矛盾的直接性变量的同时,还要认识到既往经济发展模式下“亲资本、疏劳工”理念对集体谈判制度建立和实施的负向作用。正是因为“权力与市场的 ‘非法婚姻’,即权力与市场结合到一起,形成了权贵经济”⑧,为了“营商环境”而无视劳动者的利益,这是极其严重的公权错位,其本质是政府放弃了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责任和使命。
以轰动一时的黄埔冠星精密表链厂劳资纠纷为例,上千名工人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罢工行动,最后启动集体谈判事态才得以平息。回顾整个事件过程,政府错位的现象无处不在。比如当劳动者提出集体谈判要约时,厂方反对工人诉求的凭据竟是地方政府“维稳小组”的通告。可见,在现实中政府有着解释法律的权力,当地政府的表态就是法律,而对法律的不同解读,反而使劳资双方本可通过集体谈判解决的矛盾陷入了僵局。当工人采取罢工手段时,政府则运用行政强制力迫使工人复工。当工人被问及“在劳资冲突中,你们希望政府做什么”时,工人的回答是:“我们希望政府公正。不用向着工人,只要别向着老板就行了!”工人质朴的回答恰恰表明了本应在集体谈判中受到政府保护的劳动者在政府错位情况下的无奈与期盼。
二、政府侵权对集体谈判制度的负面效应
政府在集体谈判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必然带来集体谈判的形式化、表面化,并进一步造成集体谈判制度的空洞化、虚拟化,具体讲就是有集体协商无集体谈判、有集体合同缺集体认同。
(一)有集体协商无集体谈判
我国工会既具有行政属性又具有社团属性,社团属性是其表,行政属性是其里,从这一点讲,双重代理的工会就是政府的有机构成或者职能延伸。在推进集体谈判制度过程中,政府越俎代庖,宏观上政府确定集体合同的签订数量和覆盖率,微观上从发出要约到签订合同都有政府的身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选择性地施行,运用行政强制力要求企业与职工签订格式化的集体合同;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通常会识趣地配合政府的工作,很少会与政府不合作。这种默契下政府或者政府通过工会与雇主就既定内容进行协商,企业给了政府“面子”,政府照顾了企业“里子”,企业职工是有组织参加的旁观者,却不能通过代表自己的工会以权利主体的身份参与其中并表达意见,更遑论与雇主的谈判博弈了。不论是出于对劳动者的尊重还是对于社会民主制度的需要,企业职工的自决权都是重要的,它要求雇员对关系到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与参与权。⑨政府过度介入劳资矛盾、干预集体谈判的结果就是劳动者难以实现本应具有的发言权、参与权,加剧了劳动者对法律的漠视和对权力的崇拜。既然权大于法,劳动者遇到劳动争议时自然就不愿也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想到的首先是寻求政府的权力公道。对劳动者在集体谈判中主体权利的“过度代表”和“包办代替”不仅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以此所构建的有协商无集体谈判的集体谈判制度无疑也是在作茧自缚。将集体谈判表述为集体合同,实质是对集体谈判的否定,既在表明劳资矛盾的非对抗性,也暗含着对集体谈判的控制与操纵。
(二)有集体合同缺集体认同
2010年7月,全国总工会召开的第十五届四次执委会议要求“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两个普遍”的要求无疑对扩大工会组建率和集体合同覆盖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集体合同的覆盖率稳步提高的同时,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劳资矛盾愈发尖锐,持续高涨的劳资冲突向大规模、高频率的方向发展,集体谈判的社会“减压阀”作用没有实现。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推进集体协商的出发点是完成考核指标,有别于集体谈判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协商与谈判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决策过程,而是一个咨询过程,它强调在劳工关系中的合作而不是敌对关系。协商与谈判不同,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双方能否达成一致,而在协商中,决策的最终力量总在管理者手中。”⑩用基本利益一致的“协商”替代存在一定对抗性的“谈判”,提高了集体合同的原则性、通用性,但集体合同的内容也会更加一般化、空泛化和简单化。统一规范格式和文字表述的集体合同,表达内容和方式完全法条化,从工作待遇到工作环境都是老套的最低标准,不断增加和细化的指标是出于考核的需要而非针对解决特定企业职工的具体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签订集体合同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是没有太大实质意义的,对企业而言无非是陪着政府完成了“表演”程序,还免去了诚实履行集体谈判的义务。很显然,缺乏对劳动者权益真正关怀的以完成考核达标为主要目的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集体“失语”了,本是权利主体的劳动者成为了政府与企业协商成果的承受者,完成了集体合同签字确认的“画押”。政府对劳动者权利的全面代理,蚀化了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利,在这个形式大于内容的链条中,本应最有发言权的劳动者成了帮助完成集体协商套路演出的第三方。
三、对集体谈判中政府侵权的救济
第一,劳资冲突的有效解决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法律制度。当前政府普遍采取的救急式的短期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促成劳资矛盾解决长效机制的建立,也不利于建立各方认同、自愿参与的集体谈判机制。这就需要完善集体谈判制度立法、工会法立法,特别是要正视罢工权的立法。在国际劳动法律体系中,罢工权是重要构成部分,它不是一项单独的权利,而是实现集体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之所以在集体谈判中既被排斥又不得不依赖政府这一特殊主体,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罢工权保障。一般情况下,罢工权只有在雇主拒绝正当要约和谈判破裂时才会启动,是在资强劳弱的劳动关系中制约雇主不诚实谈判和不承认谈判的最重要且唯一的手段,在劳动者没有这种权利作为谈判的资本发起要约、平等对话时,只能任由政府这一“大家长”为其提供保护,而这种保护的代价就是虚化的集体谈判和空泛的集体合同。同时,在我国一元工会的主导下,工会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明显缺失,向政府负责的工会无法真正成为劳动者的代言人,所以,想实现罢工权的立法,加强对工会法立法的完善和改进也是立法救济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行政救济是针对集体谈判中特殊主体侵权的最可行最直接的救济,其本质在于敦促政府归位。在集体谈判中,因政府瑕疵行政行为导致劳动者集体谈判权受损的,应该对其违法或不当行为进行消灭或者变更。对因政府越位而越权代理的集体合同应宣告无效,重新启动集体谈判。对已进入实质进程的集体谈判应在以下四方面主动作为:一是在谈判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政府要适时地进行调解、斡旋,促使谈判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二是强化行为管控。当参与谈判的任何一方不信守谈判信用,过度偏离了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或者在谈判之外做出单方面的施压行为时,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提出适当的强制性要求,促使其遵守谈判规则。三是指导谈判范畴。为了促成集体谈判有效结果的取得,需要劳动者、工会能够尽快提出明确的利益诉求,也需要雇主代表在回应这些诉求时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为此,政府可以结合各方面的情况提出禁止谈判事项、规定讨价还价幅度等,以控制的方式对集体谈判有所规制。四是在集体谈判结束之后,政府还应敦促劳资双方切实履行义务,使达成的集体合同得以履行并对履行中可能出现的理解偏差和纠纷作出及时的处理。
第三,司法救济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救济虽然具有巨大的公信力,但存在着成本高、周期长的不足,其“不告不理”的被动性,使其在集体劳动争议中很难发挥作用,如果每个劳动者都按照完备的法律程序进行争议处理,必将耗费大量的法律资源和社会资源。司法救济可作为底线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在政府实施了侵权损害,又没有通过行政救济矫正瑕疵时,应启动行政诉讼救济。根据集体谈判权力主体的特殊性,建议由工会或劳动者授权的律师代表,对在集体合同的签订程序中、在集体谈判的进行中存在官商勾结、官商合谋的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审理并作出裁判。而在这一救济中,更要侧重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通过诉讼进行救济的关键是举证,在集体劳动关系中,政府作为特殊主体,占有大量的资源优势和劳动者无法触及的技术操作规程,劳动者无能力提供证据证明其侵权的实质,这就需要行政机关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性,这样才能使权利相对人得到真正的救济。
注释:
① 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② Simon Clarke,Chang-Hee Lee and Qi Li,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04,42(2),p.236.
③ 赵炜:《基于西方文献对集体协商制度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
④ 李琪:《产业关系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楠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3页。
⑥ 数据引自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⑦ 岳经纶、庄文嘉:《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劳动监察体制:基于治理视角的一项整体性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5期。
⑧ 孙立平:《“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⑨ 约翰·巴德:《人性化的雇佣关系——效率、公平与发言权之间的平衡》,马振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⑩ 约翰·P·温德姆勒:《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集体谈判》,何平译,中国劳动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