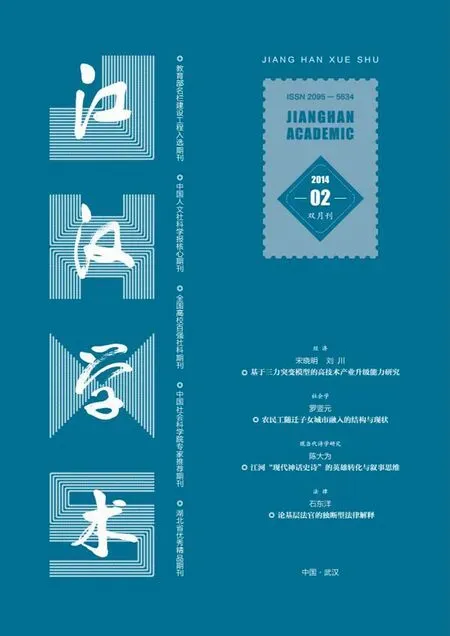对我国媒体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反思与重构
2014-04-16李廷军
李廷军
(江汉大学 教育学院, 武汉 430056)
20世纪初,欧洲、北美洲、大洋洲以及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种新型教育——媒体素养教育。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媒体素养教育的适应性也不同,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选择和确定的媒体素养教育的目标也存在差异。这些都隐含一定的价值取向,不同媒体素养教育价值取向也代表了媒体素养教育者对各自国家媒介与公众等环节关系的不同反思。因此,明确媒体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有助于认识我国媒体素养教育的核心和本质。
自1990年代末以来,媒体素养教育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至今已十年有余,并俨然成为学界的一个显性话题。在中国当前语境中,非本土媒体素养教育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面临的最大困境无疑是过于严格的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沿袭。因此,抛弃传统“纯粹”保护主义取向,超越媒体素养教育的困境,建构一种“超越保护主义”的媒体素养教育,还有待于学者们给予足够重视并作进一步研究。
一、“纯粹”保护主义:我国媒体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现状反思
1.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的政治保护压力
政治制度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其阶级统治而采取的统治方式、方法的总和,它包括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以及为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1]。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我国相去甚远,其政治制度多为多党轮流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经济上,西方国家基本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因此,大多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最初直接来源于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其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政治保护主义。“从上个世纪70 年代以来,诸如‘反对性别政治’和‘种族政治’等‘身份政治’内容和‘意识形态’内容被加入了这种政治保护主义的范畴。相应地,大众媒体要为男性至上主义或种族主义负主要责任。而通过媒体素养教育过程中的媒介分析,这种有关大众媒体的性别偏执、种族偏执和意识形态偏执可以得到克服或矫正。”[2]其实,这种基于政治保护的媒体素养教育亦被许多其他西方国家顺理成章地看作是一种消除错误信仰、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其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受众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挑战社会上偏颇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政治保护主义是某些国家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主要动机和行动,推行起来也颇为不易,因为其明显有违现代意义上的媒体素养教育的初衷。
我国有着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政治、历史、文化和教育背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全体国民对新闻媒体不能有丝毫怀疑,有关媒体教育几乎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少涉及政治体制和媒体制度改革,因此,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无暇顾及这场由国外引入、由民间学者发起的媒体素养教育运动。在世纪之交,我国即使勉强引入和开展了媒体素养教育,也是如履薄冰,时刻担心触碰雷区。对此,有学者尖锐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下,从事媒介素养教育会承担更大的风险,……我们的学生已经接受了多年的政治教育,媒介素养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社会教化?……我们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是否应该强调沉默,强调聆听他人的技能?……我们推动个人、社会运动组织、社区活动中有效使用媒介,但所有的这些实践相对于日益强大的、依赖于市场、在中国还包括国家政权的媒介组织,是否太微弱了?……”[3]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广大媒体教育工作者们思考。
事实上,在现有媒体制度和政治体制下,我国公民已习惯了疏于对媒体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进行思考,从而对媒体的商业化倾向和政治教化倾向缺乏认识。可以说,我国的媒体使用者是很好的媒体信息接受者,但并不是很好的分析者、辨别者、评判者和利用者,由此导致媒体素养普遍不高。据一项权威研究发现,“在目前中国,无论是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思考、还是对媒介生产的积极介入,均处于偏弱水平,其影响因素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值得深入探究”[4]。这是因为,中国媒体素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主要资助来自政府,这样更便于官方对该教育项目的控制,避免越轨行为。同时,“尽管媒介素养强调政治参与,但在中国,可供人们选择的参政行为有限,职责性、公民性、制度性的参与,与绝大多数人无缘,即使那些最激进的行动者也不例外”[5]218。因此,无论是作为一场社会运动,还是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在我国开展媒体素养教育即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会面临种种压力。
(二)文化层面:精英思维倾向颇为严重
媒体素养教育起源于英国,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当时社会精英出于对大众媒体的本能抵制而采取的一种文化保护。当前,我国与媒体教育有关的、相对重视技能的“信息技术教育”(teaching with media)早已进入中小学课程体系,但真正与媒体教育相关的、侧重于文化的“媒体素养教育”(teaching about media)却迟迟未能正式进入该课程体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媒体素养教育重技能、轻文化的倾向和仍处于起步阶段的事实。即使涉及到文化考量,媒体素养教育也是采取一种精英文化取向、主流文化取向和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精英思维。
媒体素养本质上是个文化问题。所谓文化,关涉的是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它们才是媒体素养的核心和媒体素养教育的永恒主题。同时,媒体素养教育理应针对社会普通公众,但是众多学者仍然立足于精英教育来确立媒体素养教育的目标。若以这种文化取向和思维看待其他非主流文化,则不难发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众文化几乎已经成了‘自由’和‘个性’的代名词,它意味着反叛权威、精英和摆脱传统的束缚,拒斥诸如真、善、美、圣等终极价值或人类永恒的崇高目标对人的感性世界的制约,它依靠追求时髦和不断更新来寻找自身的价值”[6]。若将这种“文革式”的思维和观点运用于媒体素养教育,必然会产生严重后果。我们不仅应该主动地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等主流文化,也应该以包容的态度去关注、甄别、引导和欣赏诸如摇滚文化、大话文化、涂鸦文化、恶搞文化、博客文化、微博文化、山寨文化以及草根文化等形形色色有价值的亚文化风景。
(三)价值层面:“妖魔化”媒体倾向依然存在
英国媒体素养教育学者巴扎尔格特在回顾英国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时,曾批评早期“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是“灾难的开端”,因为“责难媒体”的媒体素养教育连带地产生了“否定”媒体的误解。而“否定”媒体的思维在所有国家媒体素养教育理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7]受英国媒体素养教育运动的启发,美国的媒体素养教育运动也一直伴随着“道德恐慌”和对媒体信息、媒体受众等概念的简单化理解。大卫·帕金翰对此评价道:“美国的媒体素养研究经费经常来自于精神健康领域的资金,这意味着这些问题主要被视作是病理学上的问题。”[8]由此可见,受众在道德失范的媒体信息面前是多么无能为力,他们迫切需要基于道德保护、文化保护、健康保护以及政治保护的媒体素养教育。
目前,我国的大众媒体也一度出现了“去政治化”倾向,几乎都在如何“经营”媒体上做文章——因为有一些媒体因为追逐利益而越来越低劣化。于是,“我国学校和社会对青少年媒体接触行为的关注,仍集中在对媒介负面影响的抵御和防范上。部分高校开学时为防学生过度迷网而禁止新生带电脑入学,以及一些中小学禁止学生带手机上学的做法,都说明了社会和学校对青少年的日常媒介行为的焦虑心态”[9]。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家长、老师,甚至教育机构片面认识、夸大了媒体的负面影响,他们对大众媒体,特别是对基于网络的众多新媒体采取了“抵制”、“否定”甚至“妖魔化”的价值判断。与此相对应的是,由这种取向出发的媒体素养教育往往局限于对青少年媒体行为的片面约束、抵制和保护。事实上,我国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和媒体管理部门还简单停留在媒体受众是媒体被动的受害者,他们会被媒体的强大效果一击即倒的传统观念上,因而会更倾向于“媒体罪恶观”的教育,即在媒体素养教育中,充斥着拒绝式、对立式和预防注射式的思考,以及只靠常识的思考,从而使媒体与媒体受众处于互为对立的角色。这和西方早期“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所采取的“抵制”取向几乎如出一辙。
实际上,媒体素养是一个包涵多重维度、多重要素、相互交融的复杂能力结构和素质结构,要求我们要有多重批评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有机结合起来去把握和判断。而且,媒体素养教育作为一项价值性很强的教育活动,有关文化、审美、道德等标准的价值尺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忽视这些价值标准的存在,必然很难企及媒体文本的价值真谛,也难企及媒体素养教育本身的价值真谛。当前我国的媒体素养教育所表现出的“抵制”媒体、“妖魔化”媒体的取向,无疑过于简单、机械、浅薄和粗暴,从而在价值判断时往往陷入了诸如“好与坏”、“正面与负面”以及“留与弃”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
(四)教育层面:灌输式教学尤为普遍
在引进西方媒体素养教育理念之初,卜卫就曾警告说,“在媒体素养教育中,教师不应以自己的体验代替学生的体验,不能以自己的判断代替学生的判断”[10]。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我国一贯主张媒体舆论和思想的引导,在教育上,始终还是师道尊严,以灌输训解为要,耳提面命为豪,在这样的状况下,媒体素养教育的话语很容易消融于固有的劝说指导传统中,成为家长、教师调教孩子的又一个上好理由。……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又增加了一个对学生进行灌输式教育的机会,离提高学生素质的根本目的相差甚远”[11]。而且,不少教授媒体素养课程的教师仍然相信他们可以教给学生“正确价值观”、“正确知识”和“精英品味”以及相应的能力。因此,大多数文章或教材局限于教授“知识”,但缺少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反省:这些知识是谁建构的?为谁建构的?为了达到何种目的?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个人的批判自主权和赋权没有被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如果主流或传统的教育学没有任何改变的空间,比如,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改革,那么在这种情景下,仅仅靠媒介素养教育来挑战教育制度可能收效甚微”[5]202。
西方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过程不断提醒人们,媒体素养教育的对象在接受媒体素养教育之前并非对媒体一无所知。在我国,正如陆晔教授指出,“尽管从未冠以媒体素养之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众传播媒体的喉舌功能,普通民众对媒体文本的解读、认知、理解,一直是他们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领域。除了有组织地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进行学习之外,公众在新闻使用上,业已形成相当深刻的领悟力。无论知识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对‘文以载道’历史传统都有着来自民间的深厚理解,因此寻找媒体文本的‘弦外之音’,多年来从来就是公众媒体使用的目的之一”[12]。事实上,我国媒体使用者在媒体化生存过程中,也早已积累了基于切身感受的、丰富的媒体体验和媒体素养,虽然这种媒体素养带有某种自发性和朴素性。介于此,用灌输式的说教去替代学生关于媒体识读的“批判性自主”体验,恐怕只能适得其反。
二、“超越”保护主义:我国媒体素养教育价值取向的理论重构
(一)不再需要“保护”吗?
首先,无论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文化霸权的抵制,还是对我国媒体市场化运作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应对,抑或是对不良意识形态的消除和对“身份政治”的矫正,媒体素养教育都是一种调适人和媒体之间不谐关系的相对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是我们对社会和媒体中出现问题的积极思考和主动作答,即存在一定的保护色彩。显然,面对媒体的负面影响,面对人与媒体关系的种种不适,完全放手、放任自流的态度和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譬如,在Web2.0的世界里,“很多‘业余者’用他们的电脑在网络上发布各种各样的东西:漫无边际的政治评论,不得体的家庭录像,令人尴尬的业余音乐,隐晦难懂的诗词、评论、散文和小说。……在博客里,人们恬不知耻地公开了自己的私人经历、性生活、人生渴求、生活所缺甚至重新活一次的想法”[13]。在这样一个世界,人人都应该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正确处理好自己与媒体的关系,以免使自己在这样一个精英消解、草根为王的时代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其次,我国的媒体素养教育,应该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弘扬和保护。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虽不免有其糟粕,但终以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和精深博大、兼容并蓄的亲和力,在当代彰显出超越时代及地域的文化熏陶和保护价值。然而,深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下我国一边是网络恶搞的盛行,一边却是书籍阅读率的一再下降和“浅阅读”现象的日渐普遍。据悉,“我国民众每年人均阅读图书仅有4.5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以色列的64本”[14]。而且,“很多人根本无法忍受一星期或几天不看电视的日子,却可以对几个月不读书泰然处之”[15]。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提倡传统文化教育、提倡“文学文化”教育,提倡“对包括《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文学巨著,无论是原拍、戏说,还是翻拍,不看最好,少看次之,而要多读、多读、再多读”[16],对于我国媒体素养教育的开展和社会民众媒体素养的提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再次,我国当前的大众文化,虽然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也越来越受到诸如“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媒体文化的威胁,发展环境并不容乐观。而且,在新媒体环境和参与式文化中,诸如对个人隐私、知识产权、文化的侵犯和信息安全的失范、信息犯罪、信息污染等弊端也导致了媒体道德观念的紊乱和沦丧。因此,我国的媒体素养教育,本能地有着文化保护、道德保护和政治保护等历史使命。当然,这种保护,并不是对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非主流文化赶尽杀绝,而是有褒有贬,有打有压,有收有放,是一种理性而有序的保护。
(二)媒体“赋权”的涵义与价值
一般来说,“赋权(Empowerment)”广泛涉及“公民参与”、“协同合作”和“社群意识”等概念,具有多层次性(个人、团体、组织及社区)、多面向性(人际、社会、行为、组织及社区)、草根性(涉及由下而上的改变)和动态性(是一段进程而非处于一个稳定状态)等典型特征[17],对现代公民教育和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卜卫认为,“赋权是指一个过程,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批判地运用存在于他们直接经验之外的知识和方法,目的是加深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赋权的核心问题是寻找那些可以消除社会不公正和减少权力不平等的方法”[18]10。她进一步强调,“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应该包含个人的层面,即发展对媒体的批判性自主权,以及社会层面的,即提高发声的能力,这最终将有利于发展一个更为民主的社会”[18]12。事实上,作为“超越保护主义”媒体素养教育的核心价值取向,“赋权”在我国还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1.“赋权”的超越“保护”指向
英国大卫·帕金翰博士认为,“赋权”是与“绝对保护”相对的一个概念,是“超越保护主义”媒体素养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他还认为,教育者对大众媒体的态度应该变“堵”为“导”,应以青少年为中心,尊重他们既有的媒体知识和媒体体验,引领青少年根据自身利益对媒体信息做出明智选择,尤其是要鼓励、“赋权”青少年参与媒体制作,以增进他们对传播的本质和新媒体技术的认识。因此,这种新的媒体素养教育已不再是一种被动的保护主义策略,而是一种培养青少年对大众媒体进行批判分析的对话过程。[19]事实上,20世纪末媒体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新媒体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媒体生态和人们的媒体观念。这时的参与式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相应地,媒体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必须有所改变,先前被动的保护主义取向已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种主动“探索”、“赋权”取向,即从被动的“防御性保护”逐步走向主动的、赋权式的“进攻性保护”,即所谓的“超越保护主义”。
2.“赋权”的“参与”指向
媒体素养教育所强调的“赋权”,“不仅是对媒介的回应,也是对主流教育学的回应。这其中潜藏着自下而上的对媒介生产机制、媒介社会功能的反思和对一般意义上知识生产的精英立场的反思。媒介参与式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组成部分,旨在促进公平的社会表达和多样化的信息流动,因此所有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的对价值观、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的操控都值得警惕”[5]477-478。因此,开展媒体素养教育,“如果以赋权为目标,以参与者的文化经验为基础反省主流文化并发展改变社会的行动,那么,就一定要采用参与式方法,而不是以往的灌输式教育”[18]21。事实上,“参与”式方法的实质,与提倡网络面前人人平等的互联网精神有着天然的契合。受教者运用各类媒介的“参与”行动是在演练如何“参与”公共空间的民主生活,就是让受教者在“参与”中学习如何利用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
3.“赋权”的“批判性自主”指向
美国教育理论家亨利·A·吉鲁克斯认为,“赋权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和行动的能力。这个概念具有双重指向,既是对个人而言,又是对社会而言。个人的自由和天赋能力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但个人能力又必须与民主紧密相连,这是因为社会改善一定是个人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激进教育家把学校看作是社会形式,这些形式应当培养人们具有思考、行动、成为主体和能够理解其思想所承担义务的限制的能力。……而当今主流的教育哲学想要的却是教育人们去适应那些社会形式,而不是批判地质疑它们。”[20]由此可见,“赋权”具有研讨、协商、对话和行动的特征,它不能容忍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其目标显然不是培养简单的批判技能,而是建立人的批判自主权,以促成个人的解放。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保罗·弗莱雷就曾指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具有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公民,也就是塑造能够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动的政治主体。媒体素养对批判性的要求决定了媒体素养教育既是批判性自主思维的养成教育,又是积极的行动教育,因此,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更为开放的、更为民主的教育。当前,针对我国媒体素养教育中的“灌输”倾向,我们不仅应该强调媒体素养教育理论的批判性自主思维,更应该在实践上强调“赋权”的批判性自主行动。这种思维和行动是媒体素养教育需要“赋权”最重要的理由,同时也是现代媒体素养教育最根本的特征。针对当前诸如“媒介有多坏,受众有多傻,现在就看精英如何出来教育他们别上当受骗”的种种议论,有学者告诫我们,媒体素养教育“本质上是反对媒介和文化对人的操控,但不能从一种操控转到另外一种操控;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个人解放的过程,不能造成新的文化压迫”[5]203。由此可见,媒体素养教育的目标不仅应该包含个人层面,即发展对媒体的批判性自主权;还应该包含其社会层面,即提高个人在媒体上的发声能力。
三、结 语
平心而论,我国这十多年来的媒体素养教育研究和实践探索是十分艰苦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伴随这些探索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社会目前正在进行着一次巨大的工业化、城市化变革,这场以‘时间迁徙’和‘空间迁徙’的方式同时进行着的变革,把西方国家持续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进程压缩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内完成。与此对应的是,短短的十多年之内,西方媒体素养教育流变过程中历时态的多种价值取向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共时态地涌入研究者的视野,由于对有关媒体素养理念、目标、实践形态和社会意义等各维度,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尚缺乏较为一致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起点,从保护主义的道德防范立场,到对媒体市场化商业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对公民社会的认同,到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从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到哀叹大众文化泛滥的悲观主义……这些,比Hobbs概括的美国围绕媒体素养的七大争论,要更加莫衷一是”[12]。
但是,媒体素养教育遵循自由、平等、民主等基本价值观,对于我国每一位生活在当代的公民,尤其是青少年,接受“媒体启蒙”已经成为其成长过程中的必要和必需。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媒体素养教育的中国特色,否则就根本没必要开展、也无法开展。或者说,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我们总不能等到我国的政治体制、媒体制度以及文化建设较成熟时才开展媒体素养教育,而应该在条件还不太成熟时积极创造条件启动之。当前,不管何种纷争,有一点已然达成了共识:应抛弃传统的“纯粹”保护主义取向的媒体素养教育,代之而起的是,建构和开展一种“超越保护主义”的媒体素养教育。
以“赋权”作为媒体素养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借助媒体启发人们摆脱蒙昧的操作意义,能够启蒙受教者个人的权利意识,引导他们以批判思维解构媒介,从而理解自身的社会处境,学会利用媒介维护自身利益,积极主动地争取个人的自由幸福以及社会的民主公正。这正是培养现代公民的一条正途。正如卜卫所说“‘赋权’其实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最重要的理由,同时也是现代媒介素养教育的最根本的特征。”“赋权”取向体现了“超越保护主义”媒体素养教育从集权到分权再到赋权的权力转移的发展过程:媒体使用权及参与权从成人、教师的手中逐渐下放,最后再由新媒体直接分散、赋权给媒体使用者;权力的转移也反映了传播活动从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教育活动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的转移。这种转移,在网络时代往往又会产生文化民主化的结果:创作者与观众、生产者与消费者、专家与业余者之间的传统区隔一时轰然坍塌。这样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媒体素养教育的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张永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2] Buckingham.D.Media Education in the UK: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1).
[3] 陆晔,卜卫,李月莲,等.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7).
[4] 周葆华,陆晔.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 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J].新闻大学,2008(4).
[5] 陆晔.媒介素养:理念、认知、参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6] 王艳,张彭松.大众文化及其本质[J].理论界,2006(2).
[7] 邱伟.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困境[J].东南传播,2007(1).
[8] Buckingham D.Children Talking Television:The Making of Television Literacy[M].London: Falmer press,1993:10-11.
[9] 高校禁止新生带电脑入学,80后不能没有网?[EB/OL].(2007-10-14).[2013-09-08].http://q.sohu.com/forum/10/topic/349791.
[10] 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J].现代传播, 1997(1).
[11] 仇加勉.超越保护主义:文化反哺视角的媒介素养教育[J].现代传播,2007(4).
[12] 陆晔.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J].今传媒,2008(2).
[13] 安德鲁·基恩.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网民的狂欢[M].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1.
[14] 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布[EB/OL].(2010-04-28).[2013-05-14].http://www.gmw.cn/content/2010-04/28/ content_1105804.htm.
[15] 高德胜.道德教育的时代遭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43.
[16] 王旭明.建议少看多读《红楼梦》[EB/OL] .(2010-09-03).[2013-08-12].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02f740100lvza. html.
[17] Dalton James H,Maurice J Elias,Abraham Wandersman.Community psychology: linking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M].London:Thomson Learning,2007.
[18] 彭少健.2008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19] 秦学智.帕金翰“超越保护主义”媒体教育观点解读[J].比较教育研究,2006(8).
[20] 亨利·A·吉罗克斯.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M].刘惠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