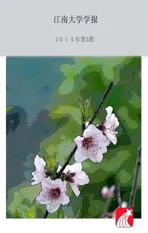论孝与仁
2014-04-14李景林
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北京100875)
一、小序
孝和仁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二者的关系,可见《论语·学而》篇有子的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的主要内容是对亲人尤其是父母的“爱”和“敬”的情感。有敬、悌的意义实质上已包含在其中。当然,在孝里面有爱,在悌里面也有爱,但是从概念的显性特征来讲,孝的着重点在“爱”,悌的着重点在“敬”。孝悌,体现了敬和爱两个方面。
孝悌“为仁之本”。何晏《集解》解释说:“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也。”朱子《集注》解释说:“本,犹根也。”意思是说,孝悌是仁的基础或根本。在孔子那个时代,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里面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孝悌。《孝经》首章开宗明义,亦引孔子的话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德的根本,是教化的开端。仁是全德之名,是德的总称。这里讲“孝”为“德之本”,与《论语》讲仁以孝悌为本,意思是相通的。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孝悌这种情感,对人来说是一切情感里边切近,又最真挚的情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这一点,是永远无法割舍的。对人来讲,孝悌的情感是人最为自然真挚的情感,因而是人的德性成就的真实基础。
儒家讲孝悌为仁之本,但孝并不等于仁。孝相对于父母而言,悌相对于兄长而言,因此孝悌作为一种情感,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仁”不局限于孝悌,但为仁成德,却必须以孝悌为前提。儒家讲孝悌为仁之本,是着眼于孝悌作为情感之真实、真诚对于人成德的根本性意义,并不是把仁局限于“孝悌”。所以,一方面,仁德的成就要以孝悌为前提;另一方面,孝悌一定要推扩达于仁德,其所本有的道德意义才能得到实现。
二、孝养与爱敬
从文字上讲,孝的本义是善事父母。《说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是一个会意字。金文中“孝”的字体构形,上部为一老人的形象。“孝”字从老从子,意谓“子承老”,即子辈奉养老人。“孝”字既可用为动词,指子善事父母,对父母的孝顺;同时,也可用为名词,意指人的一种美德和德性。
关于孝的意义,我们先来看《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无违”,并不是简单地说不要违背父母,其意义要在不违“礼”。《孝经·广要道章》说:“礼者,敬而已矣。”唐玄宗注:“敬者,礼之本也。”礼的意义在于“敬”。“无违”或不违礼,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敬”的精神。我们要注意,这个“敬”字,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指对父母的尊敬,敬事父母的行为是“孝”;另一方面也表明,“敬”是孝作为德的一个内在的原则。又《论语·为政》篇记孔子答“子游问孝”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里强调的也是“敬”。孝必须以“养”为前提,没有“养”,孝当然无从谈起,但是这只是一个基础。对于犬马,对于宠物,人同样能有养,如果不能敬,养父母与养犬马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孟子说得更直截:“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孟子·尽心上》)对父母仅有衣食之养,而无爱敬之情,实无异于把他当作畜牲来畜养。这里,凸显了“敬”对于“孝”的根本性意义。
又《为政》篇:“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什么是“色难”?《礼记·祭义》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这句话,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色难”的意义。即言孝子奉养父母,所表现出的和气、愉色、婉容,是由内心的深爱达于容色,这不是能够做作得出来的。侍奉父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父母年老,脾气可能不太好。孝子内心对父母有深爱,这种深爱,由中心见于容色,才能做得到这一点。这就叫“色难”。这样以对父母内心的爱敬之情为根据的奉养,才能称作“孝”,具有“孝”的道德价值。我们请个保姆,在饮食起居的照料上可能做得比我们自己还好,但这并不就是“孝”。这里所凸显的,是“孝”德对于父母长辈之“爱”的一面。
《论语·学而》篇说:“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何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礼记·坊记》:“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郑玄注:“弛犹弃忘也,孝子不藏记父母之过。”有些人总是唠唠叨叨,表说父母不好的地方,这实际上是对父母的不敬。孝子不藏记父母之过,而总是赞扬他好的地方。《诗经》里面有“追孝”①《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匪棘其欲,遹追来孝。”之说,意思是要追念并承继父母、前辈的孝德。对于父母前辈,要继承的是他好的、善的、美的方面而不记过恶,由此而形成一个好的家族传统。此即所谓“无改于父之道”。
孝子对父母的这种爱、敬之心,会表现在孝行的方方面面。比如《里仁》篇:“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有错,当然要谏诤。《孝经》说:“父有争子,则身不?于不义。”(《孝经·广场名章》)父母做错事,如不劝谏,就可能陷其于不义,这不是真爱父母。但对父母的谏诤,要讲究方式。“几谏”,要委婉地对父母提出意见。如父母不从,就再找其他的机会。孝子对父母有真爱,会表现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孟子》有一个说法,叫做“父子之间不责善”:“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责善”,就是板起面孔直接指责、责备对方的错误。“责善则离”,“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是说,板起面孔的指责,会伤害父子的感情。这个“几谏”的方式方法,也体现了对父母真切的爱敬之情。
又如《里仁》篇:“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不远游”,古代也很难完全做到,在现代社会,就更难做到。所以孔子退一步,讲“游必有方”。“有方”,就是让父母知道你在哪里,在做什么,状况如何,免得老人牵挂。过去信息不发达,做到“游必有方”也不容易。现在这一点就很容易做到。又《里仁》篇:“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知父母之年,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很多人连父母的生日都不知道,这是不应该的。知父母之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为什么?父母高寿,八十、九十岁还健在,是我们做子女的福分。孟子讲“君子有三乐”,第一乐就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但是增加一岁,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因而“一则以惧”。此言孝子深爱父母之心、之情,极细微而亲切,本身就有一种感动人心的教化意义。孔子所讲的道理,特别切合人心,切近人情。
综上所论,“孝”作为一种德,其主要的内容表现为对父母的奉养和爱、敬之情。《礼记·祭义》:“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尊亲”包括对父母的敬和爱。“弗辱”,是说孝子处世,不能做有辱父母令名之事,其实质仍在于“尊亲”。“能养”则其下者。这里讲“孝”的三个层次,养为基础,如果没有奉养,孝就无从谈起。但仅仅是奉养,尚不足以尽孝之义。“孝”必须以“能养”为前提,但其本质的内涵则是爱和敬。
三、敬与敬畏
其实,儒家所言“孝”的意义,不限于此。儒家孝的观念,不仅是对在世父母长辈而言的,而且包括生命成始成终的意义在内。为什么要孝?人的生命,根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根源于父母的父母。由此返本复始,人的生命,可以说是本原于天地。所以,进一步说,儒家的孝道思想,还包涵着一种通过“慎终追远”以追寻人的生命本原的形上学意义。
《礼记·中庸》说:“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荀子·礼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礼记·祭统》亦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生为生命之始,死为生命之终。这里所言“孝”,就涉及到生命之成始成终的意义。上文引孔子论“孝”也讲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讲丧礼,追远讲祭礼。①何晏:《论语集解》“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可知,孝道不仅局限于对父母、亲人的爱敬和奉养,更要由生命之成始成终,通过追思生命的本原(“追远”),以实现人的德性成就。
《孝经·圣治章》说:“父子之道天性也。”又《三才章》:“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在儒家看来,父子之情,父慈子孝,出于天性,而非人为。从这个意义说,父慈子孝,乃天经地义;孝道作为人(民)行之法则,亦本原于天道。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继嗣不断,由此亦可以看作孝的意义的一种表现。所以,祭祀皇考先妣,并能奉祀不断,既为“孝”之意义的彰显,亦包涵有一种追思生命本原的超越性意义。
现实中每个人地位不同,所处境遇亦不同,因此,孝行在现实上亦有不同层次的表现。《孝经》自第二章以下分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位或五个层次的“孝”②《孝经》《天子章第二》、《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分别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就指出了这一点。同时,孝道又是贯通于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原则。《庶人章》说,“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上述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个位次的孝德的表现中,天子之孝实贯通此五位而为“孝”的意义之最高表现。《孝经·圣治章》:“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严父”,严即敬、敬畏。此仍以“敬”为孝之本质内涵。这个“敬”的意义,在天子之“孝”上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孝经·圣治章》“严父莫大于配天”,是从祭祀的角度论“孝”之“敬”的意义。《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这是说,人因其所处社会等级的差异,亦有不同的祭祀对象,而只有天子有祭天之权。古代天子祭天,可以其先祖配享。《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报本反始,是古人制祭的原则。万物本原于天,人本原于先祖。天子祭天,以其先祖配享,意谓其先祖之德可以配天。这一点,既表现了祭祀“大报本反始”的精神,同时,亦最充分地体现了孝道的最高意义,由此亦贯通并构成为上述五位孝德的意义基础。
《大戴礼记·礼三本》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三者偏亡,无安之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这个“本”,义即本原或根据。“性”读为生,亦即生命。人的生命,本原于父母先祖,所以先祖是族类之本,天地是宇宙万有一切生命的本原。人是文化的存在,君与师,则是文明创制之原。西方人的上帝信仰,是个人直接对越上帝。中国人则讲敬天法祖。从这段“礼三本”的论述可知,儒家建立超越性价值基础的方式,乃是由法祖而敬天。这与西方宗教实现其超越性终极关怀的途径和方式,是有很大差别的。
如前所述,“孝”的核心在“爱”和“敬”。这爱敬之情,由此“法祖而敬天”的途径,乃具有了一种内在的宗教性和形上学的意义。一方面,它把天之作为生命本原的意义通过“慎终追远”的序列建立起来。这个“礼三本”,当然是从社会整体的礼文创制而言的,而天子祭天以祖配的最高意义,乃贯通在天子以至于庶人之祭祀的整个序列中,使之获得了超越性的意义。由此,人对父之“敬”的意义,乃转变为对“孝道”作为一种道德法则之具有形上意义的“敬畏”。《孝经·圣治章》所谓“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就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种形上学超越性的敬畏,同时又因于亲亲之“爱”的一面,而具有可以亲切体证、实有诸己的落实。
四、“仁”与行仁之方
孔子首先提出了一个仁学的思想系统,在孔子仁学思想中,仁是一个关于为人之本和理想人格的概念,同时又是全德之名。
《礼记·中庸》篇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就是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的规定。《论语·卫灵公》篇:“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水火,为人的日常生活所依凭者,然过多则会伤及人的生命。而仁则是人的精神生命之所依归之处,所以说“吾未见蹈仁而死者”。
《里仁》篇记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不远人,每个人都有能力能做到仁。一个人,其他的事,不见得有能力做到。像功名利禄、寿命长短、功利事功效果之事,皆非人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决定者,儒家把这些统称作“命”;但是,行“仁”,选择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仁人,却是人唯一可以不借助于外力,自己能够自作决定的事情。所以唯有“仁”,才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为人之本质所在。
儒家把事功功利效果之事归诸“命”,并不是说它与人完全无关。《孟子·尽心上》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命有“正命”和“非正命”之别。人行其所当行,所得到的结果,那个“命”,就是“正命”。相反,一个人不行正道,或者作奸犯科,被关进监狱,死在里边,那就是“非正命”。人在现实中的价值抉择,赋予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以正面和负面的价值,此即孟子所说的“正命”或“非正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君子有命,小人因为“无义”,所以“无命”。因为他得到的不是“正命”。《礼记·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儌幸。”孟子更讲“修身”以“立命”①《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人选择居仁由义,便赋予了你的行为及其结果以“正命”,这个“命”,是人的价值抉择所“立”起来的。人行其所当行,得其所应得,这既是天命的实现,亦是人的人格的完成。孔子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孔子论仁,认为仁是人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之作为人的本质所在。以后孟子的性善论,其根据即在于此。
仁又是一个标志理想人格的概念。《里仁》篇孔子云:“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易·乾文言传》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成名”,即成就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之名。君子之为君子,实以“仁”为其“体”(体仁),君子之德,亦须经由始终如一、不间断地行仁来达成。所以,仁,是标明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者,是一个理想人格的概念。
不仅如此,不同层次的道德人格亦皆以践仁行仁而得以成就。《论语·述而》:“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伯夷、叔齐的“贤人”之德,既由“求仁得仁”之途径而成就,故亦包涵于“仁”德的概念中。《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忠恕为仁之方,推己及人,成己成物,达致天下,至于其极为“圣”。可见,行仁而至乎其极者乃为圣。理想的圣人之境亦由推极践仁的功夫而致。故孔子乃以“仁”这一概念表征其人格之理想。
同时,仁又为全德之名或统括诸德的一个总体。孟子说:“仁,人心也”。朱子《仁说》以仁标“心之德”:“语心之德……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陈淳《北溪字义》也说:“仁者乃心之德……仁所以长众善而专一心之全德者,何故?盖人心所具之天理全体都是仁……举其全体而言,则谓之仁,而义礼智皆包在其中。”仁为“心之德”,这个“德”,是性质或本质义。心总体言之是仁,分说则有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规定。仁统括仁义礼智,概括了仁义礼智的全体。所以,仁统括诸德,而为诸德之总名。
孔子讲“仁”,并未对仁下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孔子所说的仁,就是道。“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形而上者,本来不可说。所以,孔子所教人者,唯行仁之“方”,即我们怎么样达到仁。这个行仁之方,就是“忠恕”之道。通过“忠恕”这个行仁之方,我们才能对“仁”的本真内涵有所了解。
《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用“忠恕”来概括“夫子之道”,大体不差,但并不完全准确。《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违”就是离开。忠恕离道不远。忠恕是行仁之方,当然离道不远,通过忠恕可以把“道”实现和呈现出来,但却不能把忠恕等同于道。《中庸》这个说法,把仁与忠恕之道的关系表述得很准确。
《论语》讲忠恕,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论语·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颜渊2》:“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论语·雍也》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概括地讲,忠恕行仁,就是要从人最切己的欲望、要求出发,推己及人,由内向外最后达到人与我、物与我一体贯通的境界,它所表现的就是“仁”。所以“忠恕”就是为仁之方或达到仁的方法和途径。当然,它不仅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实现仁的一种工夫。
忠恕这一概念,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强调情感的真实。忠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忠恕两个字,亦可以分开来讲。朱子释忠恕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③见朱子《论语集注·里仁·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章》。忠者中心,恕者如心。尽己、推己,要在一个“己”字。尽己之忠,强调的是为人的真诚;推己之恕,强调的是要以真诚之心处事待人。为仁之方,是从人最切己的意愿出发推己及人。要达到仁,实现仁德,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情感、意愿表现出来要非常真诚。
第二,这个忠恕,突出了一种差异性的原则。“忠恕”,涉及到外与内、人与己、物与我的差异与沟通的关系。忠恕行仁,就是要从切己的意愿出发,通过推己及人的践履工夫,达到内外、人己、物我之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忠恕是一个“沟通原则”。但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乃以肯定我与人、人与人、人与物的差异为前提。所以,忠恕所达到的沟通,是在差异实现前提下的沟通。西方人讲普世伦理,肯定孔子忠恕之道之作为普世性伦理原则的意义。瑞士神学家孔汉斯一方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原理的普世性价值,同时,又试图对它作出一种“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所谓“积极表达”[2]。这种对忠恕之道的理解,所表现的是西方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与儒家的思想是根本不相应的。
忠恕之道这两个特点,表现了“仁”德的根本精神。忠恕,是由己出发,推己及人。《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儒家讲忠恕,历来强调的都是对自己的要求,而非对他人、他物的要求。孔子此语,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己”的要求,就是“诚”或“忠”。“推”,即今人所谓将心比心或“换位思维”。这推己及人的过程,同时即是一个不断消解人对私己的偏执,从而保证人我、人物各在其自身的限度内有所成就的过程。人以此接人处事应物,则无往而不“通”。这一忠恕的原则,所达成的是个性差异实现或限制性前提下的沟通,它所体现的,乃是一种价值平等的精神。反之,对忠恕作“积极表达”,主张“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则会忽视人我、人物间的实存性差异,以己之意欲和价值强加于人、物,从而造成人我、人物间的隔阂与冲突。[3]
总之,忠恕讲的是己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是成己和成物、自成和成人、内与外的关系。通过推己及人的践履工夫,达于内外、人己、物我之动态合一,就是德。最高的德,就是仁。忠恕是行的工夫,其所成就的,就是人我、外内一体相通的境界。此一境界所实现和呈显的,就是“仁”。而仁这种“通”的精神,则是以因任人、物存在之平等性实现为前提的。
五、孝与仁的关系
忠恕行仁,是推己及人,达于人己内外的一体相通。这个推己及人的前提,是人的真实情感。在现实中,人最真挚的情感莫过于“亲亲”之情。《论语》讲孝悌“为仁之本”,孔子讲“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礼记·祭义》),就指出了这一点。
不过,《论语》讲忠恕行仁之道,尚未直接把忠恕与孝道相联系。孔子后学论人的德性成就,更注重孝道。由曾子到思孟学派的发展,其言忠恕,特别凸显出以“亲亲”之情作为忠恕行仁之发端的意义。
曾子以忠恕来概括孔子的一贯之道,曾子又以其孝德孝行显名于后世。所以,曾子论忠恕行仁之道,乃以“孝”为前提。《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篇:“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又《曾子立孝》篇:“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这两条材料,皆言忠恕与孝的关系。“忠”,以诚敬为本。如前所述,“孝”德之义,不仅在“养”之效,而要在“敬”之情。因此,曾子以“忠”为“孝之本”,而以孝为“忠”之用。“立孝”篇“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以下所言,即忠恕之道;而这个忠恕之道,则是以孝悌亲情为前提,而以忠敬为其精神之依归。
《礼记·中庸》引孔子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道不远人,即由忠恕而见。忠恕之行,乃以切己之情为出发点。人之生,本于夫妇之道,《中庸》第十二章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因此,忠恕之行,其切近处,乃必自亲亲孝道始。《中庸》第十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子曰:‘父母其顺矣乎!’”此章乃引《诗经》以明此义。又《中庸》第二十章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此章记孔子答哀公问政,其所论乃由远至近、由外至内的归结,其实仍言忠恕。由治道而归结为孝亲。亲亲之推扩,则本乎“忠”,亦即诚敬之心。
孟子论忠恕行仁之方,亦沿袭了这一思路。不过,孟子更突出了“仁”对于“孝”德之价值实现和完成的意义。《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里,孟子据孩童皆有亲亲敬长的孝悌之情,来说明人具有先天的“良知”、“良能”。此亦孟子证成其性善说的一个根据。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讲“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并非说“亲亲”现成地就是“仁”,“敬长”现成地就是“义”。“无他,达之天下也”,乃指出,我们之所以可以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仅仅在于,亲亲敬长之情,可以并必须推扩至于天下,达至人我、内外的一体相通,实现为一种普遍的爱和敬,其作为“仁”和“义”的本有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天下”,指人类社会而言,孟子又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个“仁民而爱物”,更赋予由孝道亲亲推扩而实现“仁”的忠恕之道以宇宙论的意义。在中国古人生命伦理义的宇宙观念中,万物皆有生命。“爱物”这个在今人不易理解的观念,对于儒家却是天经地义的。
综上可见,孝道与仁德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孝悌为仁之本;同时,孝悌亦必经由忠恕的途径推扩而至于“仁”,才能实现其所本有的道德价值。下面,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方面再做进一步的申论。
儒家之所以要讲“孝悌”“为仁之本”,是因为,亲亲之情是人最真挚的情感;由乎亲亲,仁德之成就才能有真实的基础。如前文所述,儒家讲忠恕行仁之方,强调差异实现前提下的通性。由此,仁作为一种普遍的“爱”,亦非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其内在地包涵有等差性的规定。《孟子·滕文公下》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孝经·圣治章》则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在孟子看来,杨朱的“为我”和墨家的“兼爱”,是抽象的两个极端。“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是偏执在我或己的一端,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墨家偏执于“兼爱”一端,则这“爱’成为与个体实存和人的情感生活无关的抽象原则。这两者都会破坏人的伦理秩序,导致一种“禽兽”亦即非伦理的状态。墨家要先爱利他人之父母,“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这种所谓的爱和敬,必是出于某种外在目的的人为的造作,它不自然,不真实,不合乎人性,不能为人的内心生活所亲切体证,所以叫做“悖德”、“悖礼”。
儒家所言仁,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但它并非一种与个体实存无关的抽象的普遍性。其忠恕行仁之方,乃循着由己及亲,由亲及人、由人及物这样一种成己成物的途径来达成“仁民爱物”的超越境界。在儒家的伦理体系中,“亲亲”实构成为人的自爱与普遍人类之爱的中介或桥梁。《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篇说:“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皆自爱或“爱其身”,但这个自爱本身即包涵着一种超出自身而指向于他者的超越性意义。孝子“爱其身”,不会随便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为什么?人的生命原出自父母及其族类,人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同时即包涵着对作为自身生命本原的父母及其先祖的敬重。因此,“亲亲”乃被看作人类超越其自爱而达于普遍性人类之爱的一个开端。
《礼记·哀公问》引孔子的话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又记孔子答哀公问“何谓成身”说:“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孟子·离娄上》也说:“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这几条材料,准确地地表达了儒家对人的自我实现、孝亲与普遍性人类之爱之间内在统一性的理解。这个“成身”的“身”,不能仅仅理解为当代哲学家所谓的“身体性”。“成身”犹今所谓自我的实现。对这个自我的实现,儒家有其独特的理解。在儒家看来,人的自我的实现(“成身”、“成其身”),是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基础。但是,个体的自我,并非如今人所理解的那种原子式的个体或抽象的私己性。“不过乎物”,就是应事接物,皆能“时措之宜”而与物无不通。“成身”,必经由由己及人、及亲以至于仁民爱物、天人相通的境界,才能最终得到实现。在儒家道德学说体系中,孝的观念和亲亲的情感,具有一种连结个体与普遍、自爱与爱人爱物的中介性功能,它既使儒家的仁爱原则获得了一种差异互通的精神,同时,亦使人类性的普世博爱精神和形上的价值原则,能够落实于人的个体实存和情感生活,从而具有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和切合于世道人心的真实性。
过去我们批评儒家的人性论是抽象的人性论,其实并非如此。实质上,文革中把孝道批判为封建道德,把人仅仅理解为一种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的“总和”;讲什么“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才是抽象的人性论。儒家所理解的人,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存在。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伦理原则,才能够合乎世道人心,具有真实性和现实的意义。
按照孔子的说法,孝子必“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做到“爱人”“安土”“乐天”,乃能“成其身”。这便涉及到孝与仁关系的第二个方面。
孝的概念内涵,首先是相对于父母家族而言的,因而亦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如果不通过一种推扩的途径和工夫历程拓展其意义,这孝德就会具有某种排他性,在实行上也会产生问题。孔子的后学注重孝道,甚至把“孝”的概念加以泛化,如曾子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孝”似乎可以统括忠、敬、信、勇等德目。但其实,由于“孝”德本身在对象上的局限性,它在现实性上常常与其它德性有不能协调之处。如我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就表明了这一点。
儒家处理这一问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就德行工夫上讲,强调必须经过忠恕的途径推扩以达于“仁”,以此为根据,孝德的本有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孟子·梁惠王上》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以爱敬自己父母之心,推及于爱敬他人之父母;以慈爱己子之心,推及于慈爱他人之子,由此“推恩”至于家国天下,此即忠恕之道。这里特别强调“推恩”:“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这里的“恩”,指人的亲亲之情。人固有亲亲之情,这当然已是具有某种超越人的当身性意义的“爱”。但这爱的对象,是父母子女,同时又有局限性。如不能“善推其所为”,则这亲亲之情就会限于一种偏蔽,而成为一种排他的偏私之爱,则亲亲由此亦失其所本有的“孝”“慈”的意义。以推恩的方式解除这种爱的偏蔽,乃能成就一种普遍性的博爱,由此奠基,吾人的亲亲之爱,才能成就和实现其为“孝”(也包含“慈”)德的应有价值。
二是就现实性来讲,儒家特别强调内与外的区分。《礼记·丧服四制》说:
“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所谓“门内之治”,指对家族事务的处理;“门外之治”,指对社会事务的处理。“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是讲处理家族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其治法和原则应有所不同。
这里是分两层来讲内与外的关系。第一层是讲事父和事君,家族伦理和社会伦理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孝经·士章》作“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二者所说,意思大体相同,不过《孝经》讲得更清楚。孝子之事父母,皆有爱与敬两方面的情感。但对父,偏重于“敬”;对母,则偏重在“爱”。“资”者取义。社会生活的原则,要在“尊尊”之义,对待上级,有取于事父之“敬”;家族生活的原则,要在“亲亲”之恩,侍奉母亲,则有取于事父之“爱”。父实兼具尊尊之义与亲亲之恩二者于一身,从中可以看到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内在关联性。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是讲,治理家族与治理社会所使用的方法和原则要有区别。处理家族内部事务,也包涵“义”或责任义务原则,但其显性的或主导性的原则是“恩”或亲亲,所以说是“恩揜义”;处理社会性公共事务的方法和原则,当然也不能没有“恩”或感情的因素,但其主导性的原则应是“义”或责任义务,这就叫做“门外之治义断恩”。这种对“内”“外”或公私两个领域关系的理解和处理,合情合理,充分显示了儒家高超的哲学和政治智慧。有人批评儒家公德和私德、公领域和私领域不分,这个说法是对儒家的一种曲解。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孝与仁两个概念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现代中国社会逐渐由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变为生人社会,社会公私领域的边界亦变得愈益清晰。在这种生存境遇下,一方面,我们特别需要在伦理道德领域中理解和重建儒家的道德精神;同时,亦要注意克服后儒把“孝”作泛化理解的倾向,更好地开发和发扬儒家“门外之治义断恩”这一方面的哲学智慧,着力于社会公共秩序的建构。这两方面的结合,对中国当代价值体系的重建,是有重要意义的。
[1]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6,115-116.
[2]刘述先.世界伦理与文化差异[M]//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08-109.
[3]李景林.忠恕之道不可作积极表述论[J].清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