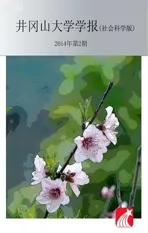唐五代工匠研究述评
2014-04-14彭丽华
彭丽华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8)
唐五代工匠研究述评
彭丽华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8)
学界对于唐五代的工匠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根据传世典籍主要关注于官府工匠的管理、身份地位、类别及家庭规模等方面的研究;第二阶段是依据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探讨工匠尤其是民间工匠的身份、地位、类别、技术级别、待遇、称谓、生活等多方面的研究;第三个阶段则是依托《天圣令》,对唐、宋、日本古代工匠进行比较研究。
唐;五代;工匠;《天圣令》
工匠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之一。四民这种基于社会行业与分工的分类法,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甚至更晚。工匠虽然名列四民,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具有贱民的性质,尤其是官府工匠,子承父业,职业世袭,禁止入仕为吏为官,每岁力役比普通农民多一倍乃至更多,服役年龄较农民为早等等。但工匠的这种近于贱民的身份,在从贵族政治转向君主独裁政治、贵族地位衰落、民众地位上升的唐宋时期,[1]逐渐得以改变,这种改变在唐代又体现得尤其明显,奠定了他们在之后千余年的身份。因此,研究唐代工匠不仅仅有利于深化唐代经济史的认识,也对理解唐代社会结构颇有裨益,更对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有着深刻的意义。
由于传统典籍的取材视角与撰写体例,以及长期以来儒家文化对技艺匠术的鄙视,结果不管是士人还是朝廷都缺乏具体了解工匠及其技艺、生活的兴趣,导致传统典籍有关工匠的记载少之又少,尽管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但却零散而琐碎,因而唐五代工匠的研究实为高难领域,但学界前贤还是作出了突出的成就。笔者就目力所及有关唐五代工匠研究成果作一梳理,稍作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期抛砖引玉,促进唐代工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鞠清远先生的《唐宋官私工业》[2]可视为涉及官府及私人作坊工匠身份及其管理的最早著述,作者指出唐宋官府工业劳动者在征集方法上有着征役与招募的区别,为方便征役,唐代官府强迫工匠平时以团、火为组织,上番服役或纳资折役。该著作通过对唐史典籍有关工匠资料的梳理,还对唐代工匠的人格、类别、数目、休假、工资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并对唐宋时代私人作坊中的招募工匠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唐代招募工匠多以计日酬值,而宋代已出现计日酬值、计件出雇、包工等多种雇佣方式。鞠清远先生《唐宋官私工业》从唐宋比较研究的视角论及的唐代工匠,虽然论述简略,不少地方甚至点到为止,但其谋篇布局的整体结构基本奠定了二十世纪研究唐代工匠的框架。与鞠清远先生有关工匠研究的广度相比,唐长孺先生半个世纪以前所著《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3](P29-92)则是从深度着手,该文毫
无疑问是研究唐代工匠及管理最重要的成果。在这篇文章里,唐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长达几百年的官府手工业者身份、地位的演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深入考察了魏晋时期的“百工”、北朝的“伎作户”、南朝的“番役制度”,认为工匠服役经历了从长期到轮番再到纳资代役的变化,与服役时间缩短乃至纳资代役同时,是工匠身份的变化,过去手工工匠所特有的“百工”、“伎作”等表示卑微身份的名称已不复存在,表明工匠逐渐摆脱了卑贱的身份,但他们仍然是农奴化的手工业者。而和雇匠与纳资代役的出现与普遍,是唐代工匠区别于以往的明显特征。
唐先生对于工匠身份与地位演变的研究,成为后来学者讨论唐代工匠问题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李剑农在《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4]专列一节,通过考察作坊及官府工业形态的变化,论证了手工业者地位的变化。作者认为延至唐代,尽管官府番匠依然受到官府控制,但每岁仅有二十日不能自由,番匠役期与一般番役相等,并可输钱代役取得劳作之自由。从应役之匠户变为输纳资课之匠户,表明唐代番匠之地位较北魏时之工匠已近于解放;张泽咸《唐代工商业》[5](P206-215)也单列一节论述工匠身份及其组织,认为百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并非“良民”,工匠世袭其业,身份近似奴隶,往往聚族而居。官工业工匠在战国至秦汉时期被朝廷严格控制,其衣着、食用乃至生产事业都有着特殊规定。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南朝与北朝相继出现了工匠的番役制与雇佣制,一直到唐代,他们在法令上真正取得了与一般农民等同的良民身份;张泽咸在《唐代阶级结构研究》[6]一书中还提到部分番匠拥有土地,这表明他们的身份与小农无异,更有极少部分工匠因为占有大片土地而跻身为地主阶级。魏明孔《浅论唐代官府工匠的身份变化》[7]从官工匠的职业不易改变进入仕途较其他劳动者为难,受唐政府的控制程度较其他编户齐民为严,受剥削程度较其他生产者要重三方面比较了官工匠与其他劳动者的地位差异,并着重论述了工匠地位在李唐一代的变化。文章认为唐前期,官府工匠是以丁奴、官奴、户奴等称谓出现,较一般农民及私工匠为低,但在开元天宝之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府工匠的身份有了明显的改变,集中体现在大部分的官府工匠由和雇而来,力役的征发反而退居次要位置并愈到后来愈不重要,而工匠参与中央大型工程的营建可获得报酬,以此来论证唐中后期工匠地位较之唐前期的提升。魏明孔在其另一部著作《隋唐手工业研究》[8]的第三章《隋唐手工业者身份的变化》里,通过阐述官府工匠由征集为主到以和雇为主、民间工匠负担形式从隋及唐初期的服役变为中唐以后和雇及纳资代役,及比较官府工匠、民间工匠和农业个体小生产者的身份,来论述隋唐手工业生产者身份的变化,其结论是中唐以后官府工匠与个体民间工匠乃至个体小农业生产者之间在身份上已无严格区别,唐后期工匠所承担的徭役期限,与个体小生产者趋于一致,反映了工匠身份提高的社会现实。上述结论亦见宁可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9]。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10]考察了手工业者的婚配特点,认为手工业者婚配原则是同类为婚,这既是法律规定,也是手工业者为保证技艺不外传的主动防御措施。工匠与士人、士族通婚非常困难,但与普通农民及与自己地位相近的商人联姻则日渐平常,表明唐代工匠地位依然不高。综上可知,唐代工匠尤其是官府工匠的身份与地位较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与贱民阶层的淡化、消亡过程是紧密相连的。
工匠类别是研究唐代工匠的第二个关注点。工匠类别有多种分法,通常是按照手工业分属官府或私营的层级结构分为在官府作坊及私属作场的工匠,如前引唐长孺、张泽咸先生等文,或直接称之为官府工匠与民间私营手工业者或民间工匠。较民间私营手工业作坊工匠来说,官府工匠由于传世典籍中相关资料较多且更为系统而受到研究者更多的重视。前引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一文认为,在唐代官府作坊劳作的工匠,沿袭了过去的番役制与征发制,还出现了两种新的制度,即纳资代役制及和雇制。并不是所有在官府服役的工匠都可以纳资代役,只有非巧手工匠在官府不须征役时才可纳资,巧手工匠则常被留用。官府和雇而来的工匠又有长上匠、明资匠之分,长上匠可能是留用的短番匠,他们经常在职,并有固定报酬。而明资匠则完全出于雇佣,与长上匠相比,他们可能是短期雇佣。和雇而来的长上、明资匠都有定额,人数不多,人数最多
的是那些来自农民或以手工业为副业的农民群体。在前引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一书里进一步总结说:唐代官工匠除了使用低贱的刑徒、官奴婢而外,还有平民身份的短番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长上匠与明资匠技艺水平较高,和雇匠通常是没有专长的体力劳动者。官府工匠仍然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并另有户籍。巧匠们通常要服现役,很少能纳资代役。中唐以后,由于集中在城市的工匠人数增多,官府把城居工匠与商人统称为“坊郭户”。在同一作坊劳动的“同作人”之间既存在着分工的不同,也有着技术上的差异,师傅与学徒、都料匠与一般工匠,彼此间还有等级的不同,从而在分配与待遇上也存在着甚大的差异。李鸿宾则在《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11]中,对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即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区分。李鸿宾另有《唐代和雇及对官私手工业的影响》[12]一文,对有关工匠和雇制度的发展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的影响及边地外族的骚扰,中央政府能够役使的丁民工匠大为减少,促使了工匠和雇制度的发展。和雇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唐代官府对工匠的人身控制,也导致了官府手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及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崛起,并呈现出工匠世代为业、地域聚业、行会活动的新特点。
此外,官府对工匠的管理特点、工匠的家庭规模也是唐代工匠研究的一个着力点。这主要是魏明孔先生的贡献,他长期从事隋唐手工业研究,对手工业的主要承担者工匠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魏明孔《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类型及其管理体制的特点》[13]认为唐代官府管理工匠有明确工匠职责、实行工匠征集与培训制度、在大型工程中实行工头负责制等特点。关于唐代工匠的家庭规模,魏先生撰有《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14],该文通过比较隋唐时期手工业生产者与农民的家庭规模,认为由于工匠为了保证技艺不外传、工匠之间不同的工种等原因,导致个体手工业工匠的家庭类型相对比较复杂,大致有核心家庭、单身或夫妻的手工业家庭、联合家庭、特殊环境下出现的松散家族手工业联合体、家族和作坊合二为一的生产和生活组织等五种情况,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唐代工匠及其管理的理解。
二
敦煌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与出版,促进了唐代工匠研究的深入发展。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研究视角的转变,即从长期以来的官府工匠转向了民间工匠。
就吐鲁番出土文书来说,在这一领域内的突出成果是冻国栋先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前期的工匠》[15](P305-324),在充分解读吐鲁番文书有关工匠史料的基础上,对民间手工业者的类别、身份待遇等作了细致的探讨,作者详细分析了文书中出现的木匠、缝匠、韦匠、铁匠等人的名籍,根据匠人名单推测唐代应有“匠籍”以管理并征发各色工匠,并对不常见的画匠、杀猪匠、韦匠、笇匠、连甲匠、装潢匠、景匠作了考证与解释。文章还指出,唐代官私工匠的组织形式与府兵类似,以州县为团,官府征发工匠时直接下帖于团头,由团头督率团内匠人应时入作,说明唐代民间私营手工业工匠与官府工匠一样受到官府的控制与强制性征发,甚至工匠的家属包括妻子在内也难逃官府的征发。该文还注意到昭武九姓胡人工匠也被纳入唐代边州的工匠系统。工匠上役未必从事本行业的劳作,而可能根据实际需要被官府配作各种杂役。另外,西州地区的工匠还是市场上各种手工业商品的重要生产者。关尾史郎《唐西州“某头”考》[16](P548-556)注意到吐鲁番出土文书有关唐贞观时期的“匠头”,认为“匠头”是从匠中选拔出来的,作为领导人或负责人的匠头,不是官而是平民的身份。朱雷先生《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17]虽重在高昌时期,文中的“作人”也不全指工匠,但也稍涉及唐代,他认为当时承担各种匠役的作人可分为三类:一是作为高昌政权征发的各种服役者,二是寺院中的各种雇佣者,三是如奴婢一般被买卖、继承,但却又如部曲一般拥有一定的财产与自由,并主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殊群体。作者指出这批相当数量的“作人”,在高昌被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平定之后,其名称就再也不见。几年后,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加,李鸿宾在此基础上作《唐代作人考释》[18]一文,他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及传世史籍的记载,认为唐代依然存在作人,且与高昌作人存在密切的关系,即高昌是唐代作人制度的一个来源。而且,唐代作人的地位较之高昌时期在提高。
杨际平先生《敦煌吐鲁番出土雇工契研究》[19]探讨了唐五代雇工问题,作者通过对25件吐鲁番雇工契、34件敦煌雇工契的分析与研究,认为在当地农业、畜牧业、工商业三个行类中,农业雇工最多,畜牧业次之,工商业最少。苏玉敏《西域的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20],除了采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外,还注意到新疆石窟及寺院中的碑铭、壁画、账册及题记等资料的运用,重点探讨了营造窟寺的工匠来源及其待遇。刘子凡《唐前期的西州民间工匠——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21]从西州民间工匠的生业、组织、赋役、兵役与杂任等几个方面就唐代西州地区的民间工匠进行了讨论。这是一篇结合传世典籍、吐鲁番出土文书及新发现的资料《天圣令》的相关记载,力图对唐代前期西州民间工匠的整体面貌进行研究的学位论文。
由于敦煌文献所涉时间跨度较长,朝代延伸至五代乃至宋初,因此利用敦煌文献进行相关研究也常常不以朝代为限,而多以敦煌地区为研究范围。学者们关于工匠的研究,也不例外。至今为止,有关敦煌工匠的研究,最为集中的是对出土文书中常见的“都料”、“博士”、“都师”、匠、师、院生、生等称谓进行考释、划定级别等方面的研究。姜伯勤先生《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22]可谓是最早利用敦煌文书涉及到唐末及归义军时期工匠研究的成果,该文对“行”中各种级别的工匠进行了分析,提出“都料”的技术不同于一般工匠,是拥有高超技艺的上层工匠。姜先生在《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23]中再次论及“都料”、各色“博士”、“院生”的身份,通过对都料与行、作坊与院生的关系及寺院中雇佣而来的匠人的研究,论证了寺户制度的衰弱。认为行首——知某行都料、某师——博士、某匠——子弟、徒工构成了敦煌“行”这种手工业组织中工匠的等第阶梯。
与姜伯勤在研究寺户制度时涉及工匠相比,郑炳林先生《唐五代敦煌手工研究》[24]则是一篇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工匠的专论,从工匠的称谓、种类及都料所指等方面讨论了晚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的发展背景及贸易情况。文章指出,敦煌文书中的博士、匠、师、先生都是工匠的称谓,之所以称呼多样,是因为工匠内部根据行业、技艺的高低而划分细致。院生、生是伎术院的学生,较师、先生的地位要低。都料、都匠都是都料匠的称呼,是手工业行业中的首领,领导一般工匠从事某种产品的制作和出售,在需要多种工匠合作的行业,如建筑业,还出现了跨行业的都料,这种都料不仅是行业首领,也是承建工程的代表、主要的设计者与建造者,并指挥具体施工,实质上是工程总指挥。敦煌石、画、塑、铁、泻、固路、泥、金银、桑、纸、洗绁、染布、褐袋、缝皮、靴匠等工匠的细致种类划分,表明了手工业的发展水平。郑炳林提到博士是工匠的别种称谓,这基本延续了郝春文先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25]一文的观点,郝文指出“博士”还包括自由身份的雇匠及为寺院服役并对寺院具有依附关系的工匠。这与姜伯勤的观点有着部分的相同。但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26]一书中对“博士”的解释有异,认为“博士”是指有技艺的人。马德《敦煌工匠史料》[27]则认为“博士是具有过硬的专业技术、可以从事高难度技术劳动并可独立完成所承担的每一项工程施工任务的工匠。这一级别的工匠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博士”这一称谓,可谓是学者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工匠的热点话题。
此外,学界对“都师”一词的具体所指也有争论。马德《敦煌工匠史料》认为“都师”是敦煌工匠技术级别的一种,与都料、都匠一样,都是同行业工匠的组织者和同行业工程的组织、规划者。郑炳林与邢艳红合作撰成的《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文书所见都师考》[28]通过爬梳、比较敦煌文献有关“都师”的各种记载,对这一名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得出了不同于马德的观点,认为“都师”不是指拥有某一类技术的工匠,而是寺院里仓库保管员和僧众伙食管理者。
尽管多有学者在某一问题上与马德先生持有不同的观点,但马德的《敦煌工匠史料》一书毫无疑问是学界至今为止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工匠问题最全面的成果。该书分研究篇与史料篇两部分。在研究篇中,从工匠的种类、技术级别、身份、生活及工匠与石窟营造、壁画所见工匠劳作图像等角度对敦煌文献所见的工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较全面地展示了敦煌工匠的面貌。在史料篇中,分上、下、后三篇,上篇为工匠职业类别,下篇为工匠技术级别。后篇为工匠遗迹,并附篇工匠名录。在上篇中,作者分门别类地把同一类工匠的史料汇集一处,有石、铁、木、索(索子)、褐袋、罗筋、瓮、帽
子、皮·鞋靴、皱文、染布、毡、桑、金银、玉、泥(托壁)、灰、鞍、弓·箭、胡禄、画、塑、纸、笔匠及打窟人等二十五种工匠。在下篇中,则分都料、博士、师(先生)、匠、工(人、生)五等。该书资料翔实条理清晰,是一本对后人了解敦煌工匠史料大有裨益的著作。
综上可知,由于出土文献的关系,学界有关唐、五代工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工匠的身份、种类、级别、称呼、待遇、生活等方面。这与依靠传世典籍更多地着力于官府工匠的研究相比,扩大了工匠群体的研究范围。比较官府与民间工匠的研究角度,可以发现学界都关注到了两者的身份、类别、待遇等方面,而民间工匠的生活、称呼、技术级别等方面是官府工匠未能或较少涉及的。这种研究区别,并非由于取材或是研究视角的不同,更多地是由于现存资料的限制。其实,时至今日,依靠传世史料并借助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五代工匠进行研究已经难以突破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从这些年来的唐、五代工匠研究现状便可推知。因此,唐、五代工匠的进一步研究有必要另辟他径。
三
1999年戴建国先生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天圣令》,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课题整理组的整理与复原,将残留十卷的《天圣令》呈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些令文中,涉及到不少有关工匠的资料,尤其是《营缮令》与《赋役令》,更是集中了相当一批数量的“丁匠”资料。由于《天圣令》的编撰方式比较特殊,它依据某部《唐令》修纂,先将《唐令》中可用于北宋当时社会的令文,经修改后作为先行法列在每篇令的前半,再将舍弃不用的《唐令》照抄在每篇令的后半①黄正建:《〈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前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这样一来,《天圣令》就包括“不行唐令”与“在行宋令”在内。又由于日本《养老令》是参照唐令修订而成,因此,借助于《天圣令》有助于开展唐宋、日工匠的比较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讲,《天圣令》可谓是促进唐代甚至宋代、日本古代工匠研究的绝好材料,其重要性不亚于当初吐鲁番、敦煌出土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一直以来,由于在出土的具体文书资料和传世典籍所载的制度规定之间,还缺少一些必要的史料环节,导致具体事务的运作难以一一复原。而唐代令文对国家政务各个方面的规定是具体而详备的,至少在唐前期,各级官员都是按照令文的规定来处理政务。《唐六典》载,“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用以“设范立制”的令,完全按照国家政务的类别,规定了各类政务的处理规定和裁决机制[29]。因此,《天圣令》的整理及据此复原的唐令,还为过去工匠研究所不具备的事务运行提供了可能。
《营缮令》是对营缮事务的相关规定,营缮事务的承担者毫无疑问包括工匠在内。《赋役令》则对力役的征发与调配进行规定。就工匠问题来说,牛来颖先生在《〈天圣令·赋役令〉丁匠条释读举例——兼与〈营缮令〉比较》[30]中提到《营缮令》与《赋役令》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进行了规定。这也要求在运用《天圣令》研究工匠问题时,不宜局限于某一篇令,而应结合多篇令文。与对工匠单个群体进行规定相比,《赋役令》中更为常见的是与“丁匠”相关的令文。牛来颖认为“丁匠”是唐律中的“丁夫杂匠”,无需区分服役人员的年龄、身份、技术,“丁匠是对承担正役、杂徭、色役等人的概称。但渡边信一郎有不同看法,他在《唐代前期賦役制度の再檢討——雜徭を中心に》[31]一文中便注意到天圣《赋役令》中没有对杂徭的规定。
除了“丁匠”的释义外,学界还有不少文章利用新出资料涉及到工匠的众多方面。彭丽华《唐代营缮事务管理体制研究》[32]采用了《天圣令》的相关资料来研究唐代营缮事务人力调配问题;前引刘子凡《唐代西州民间工匠研究》也运用了复原唐《赋役令》的相关令文来探讨西州民间工匠的赋役及上役等问题;刘燕俪《唐代的力役规范——以〈天圣令·赋役令〉为中心》[33]一文,以《赋役令》有关丁匠的18条令文,分析了丁匠的预算征发、服役丁匠在途、上役丁匠的有关管理规范等问题;前引牛来颖先生《〈天圣令·赋役令〉丁匠条释读举例——兼与〈营缮令〉比较》一文,对《赋役令》、《营缮令》中的服役主体、“功”临时性役功及服役工匠
的“除程”与给粮,在京营造的“巡行官”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日本学界,大津透先生2009年11月13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报告文章《天圣令与日本律令制研究》中关注了“四民”问题,认为唐、日在士、农、工、商的划分上存在不同,唐代有匠籍,但对于日本古代是否有专门的工匠这个问题尚不清楚,在日本一般是由所谓的“归化人”来承担一些技术工种。十川阳一《八世紀の木工寮と木工支配》[34](P714),虽是研究日本八世纪时期木工支配的文章,但也引用了《天圣令》,并简单论及唐代的工匠管理。他另有《律令制下の技術勞動力——日唐にぉけゐ徵發規定をぁぐつて》[35]一文,是基于对根据宋令复原的唐令与日本养老令的对比研究,作者指出,在天圣《营缮令》与养老《营缮令》里可以找到对应关系的令文中,唯有宋14条与养老令第7条文意迥异,通过比较唐、日令及梳理相关史料,认为唐、日两国征发技术劳动者的制度是不同的。这是基于唐、日《营缮令》单条令文的比较研究,专注于唐、日工匠(即作者所谓技术劳动力)的征发制度,是一篇目光独到颇有巧思的佳作。
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充分挖掘《天圣令》、《养老令》及据此复原的唐令所含括的工匠信息,结合唐宋的时代变迁与唐、日工匠管理、身份等方面的不同,转换研究视角,把拥有专门手工技艺的“工匠”与从事农业并同样承担国家力役的“丁”视为一个整体,放入唐宋或唐日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将能够促进唐五代工匠研究的纵深发展,这也应该成为未来研究唐代工匠的一个重要方向。
[1]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A].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2.
[2]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M].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
[3]唐长儒.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C].北京:三联书店,1959.
[4]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张泽咸.唐代工商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7]魏明孔.浅论唐代府工匠的身份变化[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4).
[8]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9]宁可.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10]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J].人文杂志,1997(3).
[11]李鸿宾.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J].文史,1997(1).
[12]李鸿滨.唐代和雇及对官私手工业的影响[J].人文杂志,1997(3).
[13]魏明孔.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类型及其管理体制的特点[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2).
[14]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1).
[15]冻国栋.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唐代前期的工匠[A].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16]关尾史郎.唐西州“某头”考[A].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17]朱雷.麴氏高吕时期的“作人”[A].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18]李鸿宾.唐代作人考释[J].河北学刊,1989(2).
[19]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雇工契研究[A].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0]苏玉敏.西域的供养人、工匠与窟寺营造[J].西域研究,2007(4).
[21]刘子凡.唐前期的西州民间工匠——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2]姜伯勤.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J].中国史研究,1979(2).
[23]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4]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手工研究[J].敦煌学辑刊,1996(1).
[25]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2).
[26]蒋礼鸿.蒋礼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7]马德.敦煌工匠史料[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28]郑炳林,邢艳红.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文书所见都师考[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3).
[29]刘后滨.《天圣令》与唐宋史研究问题空间的拓展[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09-04.
[30]牛来颖.《天圣令·赋役令》丁匠条释读举例——兼与《营缮令》比较[A].唐史论丛(第13辑)[C].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31]渡边信一郎.唐代前期賦役制度の再檢討——雜徭を中心に[J].唐代史研究,2008(11).
[32]彭丽华.唐代营缮事务管理体制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33]刘燕俪.唐代的力役规范——以《天圣令·赋役令》为中心[A].新史料·新观点·新视角——《天圣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9.
[34]十川阳一.八世纪の木工寮と木工支配[J].日本历史,2007(11).
[35]十川阳一.律令制下の技術勞動力——日唐における徵發規定をあぐつて[J].史學雜誌,2008(12).
A Review of Studies of the Artisans in Tang Dynasty and Five-Dynasty-Period
PENG Li-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8,China)
China's studies of the artisans in Tang Dynasty and Five-Dynasty Period fall into three phases. In the first stage,scholars survey ancient classics to study the government-hired artisans'identity and status, categories,family scales and their management;in the second stage,researchers examine the documents excavated in Turpan and Dunhuang to explore the identity,status,categories,technical levels,treatments, titles and lives of the artisans,esp.civil artisans;in the third stage,the scrutinize Tian Sheng Ling to compare the artisans in Tang,Song Dynasties and ancient Japan.
Tang Dynasty;Five-Dynasty Period;artisans;Tian Sheng Ling
K24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2.021
1674-8107(2014)02-0124-07
(责任编辑:吴凡明)
2013-12-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天圣营缮令》与唐代营缮事务管理体制研究”(项目编号:11YJC770044)。
彭丽华(1983-),女,江西吉水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政治制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