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屠场外的残酷战争(上)
2014-04-12乔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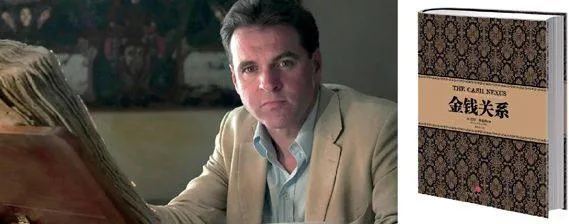




导语
在本刊第10期里,我们刊登了《一战断想》,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解读了一战的经验和教训。本期,我们请乔良将军从金融和资本的角度诠释一战。
这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战争。
尽管马克思早于一战前半个世纪,就在他不朽的《资本论》中,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但欧洲那些冥顽不化的君主们,依旧不肯正视帝国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不相适应”的现实,却又对自由资本主义升级为垄断资本主义后的大工业生产对资源欲壑难填的胃口和日益尖锐的劳资冲突导致的社会阶级矛盾,充满担心和恐惧。
为了摆脱他们根本就不曾理解原因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欧洲同僚们—奥匈帝国的老皇帝约瑟夫、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决策者们,以1914年6月28日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为契机,几乎不约而同地为各自的国家选择了战争脱困之路。
大错既已铸成,相应的错误就会接踵而至。既然帝国的决策者们无法理解在帝国母体内孕育生长并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一次“借腹生子”,帝国的专制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同体异质,互相排斥,他们当然也就对被资本所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战争方式的改变一无所知。而这最终导致欧洲的帝国一哄而上,打了一场耗时四年多,大约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阵亡,2000多万人受伤,耗资2700亿美元,受战祸波及人口15亿,结果却是千金散尽,王冠落地,帝王们自己埋葬自己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惟一的例外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当时真正理解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方式与天性,完全将自己的国家体制与其融为一体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用纯粹资本的方式去理解这场战争,将之视作一次超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生产、运输、贸易、债务、贷款、融资,除了在战争背景下,一切都与和平时期没有两样,所以,这种资本主义的清醒使美国笑到最后,成了一战(包括20年后的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最终的胜利者,应该说毫不奇怪。
战端未启 结局已定
中国人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方人说“打仗就是打后勤”,这两句话异曲同工,引申为现代理念,即打仗就是拼国力。什么是国力?从硬件角度讲,就是获取和控制资源与资本并将其转变为生产力的能力。这种由资源和资本所体现的国家实力,是对战争时长和规模的硬约束:有多少钱(资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资源(人力、物力和生产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决于交战方的战争融资能力,后者则决定了交战方的战争持续能力。这意味着战场上的胜负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所能获得的战争资源和资本能力所左右。这也意味着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懂得:打仗只能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显然,一战交战国的首脑和决策者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而作为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尤其愚蠢。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对战争的胜利更多地取决于战场之外双方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生产能力、税收财政、贸易水平、信用创造以及盟友状况等等要素,却给予了惊人的忽视。
以德国为例,如果德皇威廉与其号称“世界上最出色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当时已经形成的同盟国与协约国双方的真实实力对比有一个清醒的了解,也就不会把对战争胜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断上:
《战争的悲悯》一书在描述德皇和他的军官们时这样写到,“他们笃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国和俄国将得到喘息的机会,组建坚不可摧的力量。”这意味着,那时再动手,对德国人来说,可能就为时已晚。而资源的短缺、流动性的紧张,长时期为准备战争而形成的军备压力,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认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缓解大规模军备、财政收入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出路。”
在这样朝野上下一派轻言战争的气氛中,难得德国人还在战争开始之前,竟然在自己想象力所及的最大范围内,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费用,做出了预算:
“估计战争的费用约700亿马克,当时的财政部长赫尔费里希对此充满信心。”他们完全不曾料到,开战以后,“帝国的战争开支将达到平均每年为300亿马克,每天约为8400万马克。”更不会料到,战争结束后的1920年,德国公债总额将高达2200亿马克。
那么,即使按德国人估算的700亿马克这个数字,这笔战争的成本将如何收回?对此,德国人自信得近乎异想天开:“德国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赢得胜利,只要每年税收足以偿还内债利息,将来取胜后,赔款就是净利润。”
或许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所感染,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军总参谋部,根据著名的“ 施里芬计划”为蓝本制订的作战计划,同样令人惊讶地轻率,充满了投机色彩。一俟开战,德军将牢记施里芬的遗训:“袖拂英吉利海峡”,以六个星期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向,攻打俄国。这个一厢情愿的计划,意在既避免两线作战,又各个击破对手。但是,真正的战争与战争计划往往是两副面孔,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德国人失算了,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半。最后支付战争赔款的,不是对手,而是德国人自己。赔偿数额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仍然高达1320亿马克,足以让战败的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这个数字远远地超过了被榨干的德国国民经济的支付能力。”
其实,设想一下,德国的决策者们在决定开战前,对如下数字略加过目的话,还会轻启战端么?
总人口:同盟国约1.44亿,协约国约6.65亿;可投入战争人数:同盟国约2500万,协约国3000~4000万;全球制造业产量占比:同盟国19%,协约国28%;工业潜力:同盟国与协约国相比为1:1.5。这些数字对比,还没有算上美国。
假如在如此再清晰不过的对比下,还能定下开战的决心,除了疯子,还会有谁这么干?据说,德皇威廉二世因战败而退位后,为时太晚地读罢《孙子兵法》后长叹:“如果早几年读到此书,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我想,他被深深震撼的,一定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注定不可能获胜的德国
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一书中,以一种残酷的、诗意的口吻写道:“一战的决定性因素除了鲜血的流淌,还有资本的流动,二者的意义同等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鲜血和资本,都是它的两种血液,也是国家进行战争的两种能力。前者是国家的战争资源
动员能力:鲜血—人力资源是一切战争资源中的头号资源;后者是指国家的战争融资能力:资本—发钞、税收、举债,是国家支撑战争的重要手段。
在长达四年多的世界大战中,“战争的双方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已过度消耗的国家财政和物力,只为了在战役中获得暂时胜利的一方,必将在那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吞食失败的苦果。它们已弹尽粮绝,它们的劳动力数量—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数量—大幅度锐减,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它们供给士兵和平民的食物储备所剩无几;它们已在国内外债台高筑,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这意味着,在“鲜血和资本”两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注定在战争中也处于劣势,并且几乎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
尽管在一战之前,德国的经济已经取得了傲人的业绩—它的钢产量在1913年就超过了英国,它的国家收入已把自己的宿敌法国远远地甩在身后;它的电气工业总产值在1893~1913年间增长了整整28倍;并且在1913年这一年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足以抵消大英帝国的全部优势。此时,英国正在享受其遍布全世界的殖民地带来的丰厚利润,原有的工业体系足以支撑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工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并不能弥补德国金融业这块致命的短板。这使德国与金融霸主英国相比,在战争融资方面,一开始就处于了下风口。
金融战几乎是与一战呼啸的炮弹同时甚至更早些打响的。1914年7月底,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英格兰银行先下手为强,将贴现率从3%提高到10%,吸引资金回流英伦诸岛。柏林当时还没有统一的贴现中心,资金立刻出现了恐慌。”仅此一举,经验老到的英国人就让德意志帝国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一个月减少存款20%。
面对此举,经验不足、实力亦不够的德国人的应对方式可谓“简单而粗暴”:先是回应以“马克与黄金脱钩,停止兑付黄金;”随后又将3个月国债纳入货币体系,这等于事实上的增发货币。而在金本位时代宣布自己的货币与黄金脱钩,“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贷款途径。”与德军在战争前期的表现相比,德国人在金融战中,毫无可圈可点之处,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但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都逐渐丧失。
到这一年的9月,帝国已经不得不每半年发行一次“战争债券”。直到4年后战争结束,战争债券已累积发行993亿马克,比战争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但随着战争支出与借债规模的同步放大,尽管此时德国的黄金储备已达870吨,在美、俄、法之后居世界第4位,但这仍不足以支撑其信用使公众继续有意愿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
与此同时,德国向国外举债的水平也大幅下滑。相应的,德国债券比英法债券的价格也低出了10%左右。这一差价反映出德国债券在购债人心目中明显的风险,德国不得不提高利息,以拉大德国债券与英法债券的利差,来吸引债权人的青睐,但这仍然甚至愈加无法挽回
德国人在战争融资方面的颓势。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外债规模总额尽管也达到了80亿金马克之巨,但相比英国人从美国那里借到的170亿美元的资金来说,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17年,这一年,协约国从美国拿到的授信额度是23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人仅仅获得了可怜的2700万马克的海外借款。
战争融资能力的每况愈下,严重地制约了德国的战争能力,使其在战争初中期获得部分优势和胜利,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而一点点丧失殆尽。
尽管直到此时德皇威廉二世仍一口咬定:“最先破产完蛋的肯定是俄国人”,但德国被战争损耗得难以为继的定力,已经逃不过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世界级金融寡头的锐眼。他在私信中谈道:“德国政府很拮据。”并且他对德国向国外资本市场兜售债券印象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资本家对某一投资国的向背取舍,是资本流向的晴雨表,从而也就是战争最后胜负的风向标。
但德国人的厄运并不仅限于战争融资领域。英国人对德国展开的金融战是全面的,几乎不留死角。自日德兰海战,英国皇家舰队对德意志帝国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就变成了协约国对德国及同盟国贸易战的一部分。英国人甚至连美国对中立国的贸易船只也不放过,统统予以截留,迫使美国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只与协约国做生意。
从而使“协约国(在贸易方面)的优势继续领先于同盟国;使后者无法从已经变成敌方的中立国进口物资。毫无疑问,英国海军对德国海上贸易展开的打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崩溃局面,”“到1915年,德国的进口水平已降到战前的55%。”
对德国人来说,协约国更狠毒的一招,是“德国人持有的9.8~13.7亿英镑的海外投资,被英、法、俄包括后来加入的美国将其中至少60%进行了查处和没收。德国航运领域受到的打击尤为剧烈,通过击沉和充公,德国承受人丧失了629艘商船,总吨位达230万英吨。德国人通过兜售外国证券筹措了高达1.47亿英镑的资金。为了给支付赤字付账,德国不得不销售高达4800万英镑的纯金,并从外国供应商那里进行短期私人借贷。”
战争打到这一步,就已经不是败象初露,而是败象尽显了。但直到战争结束,德皇威廉二世也没有弄明白—不是你的工业化程度,也不是你的生产能力,而是你的战争融资能力决定你的战争胜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融资能力,就是战争能力。手中能弄到多少钱,将决定打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多强烈度的战争,这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铁律。
(未完待续)
摘编自《国防参考》
2014年第17期
责任编辑:安翠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