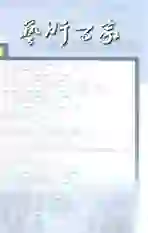姚华与康有为书法观念之比较
2014-04-10徐传法
徐传法
摘 要:晚清时期,碑学之风,盛极一时。康有为在日渐凸显的碑学理论的影响下,提出了“尊魏卑唐”、“尊碑抑帖”等书学观念。姚华作为同时代的一代通才,书法影响重极一时,成为当时的书法重镇,其书学观念是尊碑不抑帖,与康有为有诸多相合相悖之处。姚、康二人书法观念的对比,揭示了在西学东渐等新思潮的影响下,清季至民国时期书法观念由“尚碑”风气逐渐向“碑帖结合”的转变趋势。
关键词:书法艺术;姚华;康有为;书法观念;尊魏碑;碑学;帖学;书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进入清代中叶,随着金石书迹的发现日益增多,书家的审美视野也逐渐开阔,形成了尚碑的艺术倾向,书法随即进入了以碑派为主流的时期。在碑派书法进程中,以阮元、包世臣、[JP2]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些书家,在书法理论上起到了先导作用,他们先后崇尚汉碑、北碑,痴迷于碑刻书法所表现的金石气,追求用笔的厚重、苍茫、浑穆、朴拙。在这些颇有影响书家的助推下,似乎形成了碑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事实上,帖学并没有像片面鼓吹碑学的书家所期望的那样消沉,帖学一脉虽然受到碑学思想异化影响,然碑派审美改变帖学的程度是有限的。至清末,一些书家逐渐走出“碑学笼罩”的阴影,对碑帖之分重新审视,慢慢回归到碑帖结合的路子上来,姚华就是其中的一位。[JP]姚华(1876-1930年),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筑(今贵阳)人。人称弗堂先生,自署莲华盦。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精于文字、声韵、金石之学,又工词曲、诗文与书画。1904年中进士,后赴日留学,1907年学成归国,执教于清华、民国等各大学。晚年左臂致残,以卖[JP2]书画自给。姚华一生著述甚丰,除《弗堂类稿》31卷外,尚有《〈说文〉三例表》、《金石系》、《古盲词》等文稿;近几年出版了《书适》、《姚茫父书画集》、《姚华诗选》等遗作。姚华作为清末重要书家,并没有完全承袭时代碑学之风,而是自辟蹊径,以“一出之于己”的治学风格,在师承与取法上均有不同于时风的书学观念和价值判断。同时期的康有为(1858-1927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提出“尊碑”之说,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深远影响。姚华作为同时代的一代通才,书法影响重极一时,成为当时的书法重镇,其书学观念是尊碑不抑帖,与康有为有诸多相合相悖之处,值得关注。
一、尊魏碑的差异姚华在《弗堂类稿》序跋丙丁中,对大量碑刻(包括汉碑、北碑、隋碑、唐碑等)作了题跋,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这些跋文中,不论是对碑版的考证,还是碑刻的风格流派分析,不乏溢美之词,均为有感而发,显示了其“尊碑”的书学倾向。这与康有为的某些观点趋同,或者说姚华部分地受到了康氏的碑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对阮元、包世臣评论北碑的态度上尤为一致。阮元《南北书派论》,专以法帖属南,以碑属北。姚华对此看法颇不相同,他在研究了书体演变、书风流变的规律后指出:“北人简牍,未见流传,南人亦或以草势之情运入今隶,如《瘗鹤铭》及萧梁诸阙往往可见。前人多称南帖北碑,其实北人亦未尝无帖,南帖与北碑亦无甚异。如以《瘗鹤铭》及萧梁诸阙为律,求之东西魏、北周、北齐造像石刻中,亦未尝无笔势,故碑帖可分,而南北不必分也。”①
这一观点与康有为如出一辙:“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强方朴之遗……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北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 ②由此看,姚华的“碑帖可分,而南北不必分”的观点同康氏是一致的。细究其来龙去脉,就会发现即便是结论相同,但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研究问题的途径仍有很大差异,姚华多是从书体流变、书风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北碑,按照自身的治学套路来寻根求源,绝不是毫无主张的人云亦云。如品评《龙藏寺碑》和《杨大眼》两碑刻时,提出了较为新奇的观点,即从野、史角度论之:“得佳拓(《龙藏寺碑》,笔者注)则精神益真,意态如喜。北碑不外野、史两科,此其史者也。《杨大眼》之类,其野者也。若郑道昭诸石,则隶势篆笔,北书南法可谓彬彬矣。”③ 姚华以为北碑可分为史、野两类,就史、野的分类标准,没有明确论及;从其论述看,他是以碑刻面貌为依据的,而碑刻水平的高下,体现在笔和刀运用上。他以为,到摹刻《龙藏寺碑》的隋末唐初时期,笔与刀已两技亦进,“刀随笔妙之趣”,刀味体现在笔意之中,不再那样凌厉峻拔,就像郑道昭的《云峰山》一样,含有篆意,从而显得文质彬彬,姚华视这一类碑刻为史。同样这两块碑刻,康有为的评论却大异其趣,他将《杨大眼》视为峻健丰伟之宗,把《龙藏寺碑》归为以《敬显俊》为宗的静穆茂密一类。在《碑品第十七》中把《龙藏寺碑》仅列为精品上,《杨大眼》列为能品上,更低一等。康有为的品评标准自有他的道理,但不免也有偏颇之处,随后就有学者为此提出了不同看法。④从对同一碑刻的品评上可以看出,二人同是尊魏,但是他们研究学术的目的、方法、看问题的角度,都是不尽相同的。姚华“平生对出土新碑,犹深置疑”,⑤多是从学术上,对碑刻辨伪考证。康有为“尊碑”的目的在于“抑帖”,进而弘扬他的变法思想,与其政治倾向息息相关。而姚华的“尊碑”,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不带有任何的功利色彩,更多的是为己之学。更为重要的是,姚华于碑帖金石,广搜博取,对历朝历代凡有研究价值的所有碑刻皆“夙极究心”。而康有为“所言碑者,只有魏碑,则南、齐、隋各碑可以不备”⑥,更不要说唐碑了。
二、尊唐和卑唐[HT5”SS]如果说在“尊魏”上姚、康二人还有共同语言的话,那么在对待唐碑上的看法却是各持己见乃至背道而驰。姚华在《弗堂类稿》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唐碑,但从他对诸多碑刻的跋语中,亦能感觉到其对唐碑的钟情。看以下几段文字:题《旧拓王徵君口授铭》:“垂拱中刻,故势兼欧虞,便似东魏诸石,疏阔处已开颜平原,遒鍊处更启柳诚悬。凡在蜕化之迹,多有可味,如此得此旧拓,更耐把玩。”题《陆先妃碑》:“予作书,以汉隶分之势为隶楷,往往似学六朝。而隶楷又素习唐法,根抵于欧颜,变化于褚柳。以为我法,及观《陆妃碑》,抑何类我法之渊源耶!唐法无不宗祖,欧虞褚薛北海季海变矣。然诚悬多见欧虞之势,而笔法不过袭褚颜之旧,而轻重增省之故,其法异派而一涂,无足异也。”题《西平王碑》:“(此碑)是诚悬书之面目,未成者,故时仍欧虞之势。有开张处则颇似平原,唐宋之变,中枢于颜柳,此碑又颜柳之变之中枢也。大抵柳书传世,最盛莫如《玄秘塔》,此则骨未甚张,气未甚遒。”姚华如此崇尚唐碑,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唐法无不宗祖。认为唐碑风气由汉及魏,一脉相承而来,源流相续之迹,显而易见,这正好复合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书学主张,第二,隋唐以来刻工精进。刻工与书家相得益彰,有的书家本身就是刻工,这与魏晋时期书、刻分离现象不同。“中唐碑刻,笔迹宛然,北海之流,且以书家而兼石师,刻笔之精,自得奥窔。”⑦如此一来,书、刻合一,二者皆不失毫发,所以在姚华看来隋唐碑刻大都形神俱佳。第三,字态体势宽博。由初唐的虞世南到颜真卿,字势开张,剔除了狭长的意味,这符合姚华写字要“横平竖直,结字方正”的审美情趣。姚华对颜真卿的崇尚更是无以复加,他以为:“颜书是学人中枢,学颜则四通八达,皆可适也,惟学人浅,不知变通,往往中其气习。东坡、松雪乃善学颜者,玄宰已逊一筹矣。”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四十以来,一是斥弃自写胸臆,手腕渐能运用,更复镕铸诸家。颇觉中唐以降,皆宜收纳,初盛终不可及,无怪童年之一无所得也。” ⑧ 他的这一说法在其门生那里得到印证,他的学生郑天挺在《莲华盦书画集》序中说:“先生作书兼综晋唐篆隶,而一出之于己。二十年前规模米黄,二十年后肆力于颜,写《麻姑仙记小字本》逾千过,既精《说文》好金石,尝杂其锋势于行楷。”⑨可见姚华对于颜体是下了很大功力的,从其作品面目上,亦能感受到颜书的风神。与姚华的尊唐不同,康有为是极力贬斥唐碑:“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绪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亡尽,然浇醇朴散,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米元章讥鲁公书:‘丑怪恶札,未免太过。然出牙布爪,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唐人讲解结构,自贤于宋、明,然以古为师,以魏、晋绳之,则卑薄已甚。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⑩endprint
从表面上看,康有为似乎纠正了米芾“丑怪恶札”这一评论的偏激,从而让人觉得自己对唐人“无复古人渊永浑厚之意”评价的合理性,其实,康有为的评价仍然带有相当的主观色彩。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康有为“卑唐”的理由刚好与姚华“尊唐”的理由相反,首先“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其次,学唐碑者无人名家。“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者无人名家。”再者,唐人书专讲结构,古意已漓。康有为为了自圆其说,已将唐碑归入帖学阵营,这样就达到了抑帖的目的。当然康有为意欲创新变法的思想值得首肯,但过犹不及。很显然,从唐代的书法成就来看,康氏这个论断,不无过刻之处。至于批评唐人过于注重结构,无疑也显示了康有为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从尊碑的些许差异,到对待唐碑旗帜鲜明的两种态度,充分表明了姚、康二人不同的书学主张:信而好古与变法创新。
三、信而好古与变法创新姚华在题跋《陆先妃碑》时有这样一段话:“秦之斯、邈,似自创作矣。然斯、邈亦必有其濡染,千载而下,物证难寻,少见多怪,相炫以为创作。予信世事无创其来也,皆以渐,故创作者浅人之语也。仲尼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后之学者三复斯言。”B11“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以看作是姚华的学书主张,面对上千年的秦篆汉隶、北碑唐刻,他总是老老实实地向前人学习,从不轻言创作。他认为哪怕是一个时代,其“风气转变,不能突然而来,亦不能戛然而止,来踪去迹一一寻得。”在他看来,即使是李斯的小篆、程邈的隶书也是时代风气成就的,他们都有师法的对象,只不过是“千载而下,物证难寻”,不能说是自身的创作。即便集大成的元之赵、明之董,“亦只在变化之间生息。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美自足,以移我则濡染之矣。如是又焉有创造?若果欲创造而悉斥濡染,除是聋瞽,否则古人之遗迹,日充于耳目,何处而避之?此濡染之所由来也。”这里姚华反复强调了继承的重要性。接下来,姚华为颜真卿和宋四家都找到了师承关系:“颜书晚年酷似夏承(《颜家庙碑》),而其他外扩中空,亦取材汉碑而成,此所谓千流同出一源。能会到圆融处,直无法可说。至如有宋诸家,亦何尝不于此中寻讨,然变化可矣,创造则不足也。”在姚华看来,尚性情意态的宋四家,也是“信而好古”的例证,蔡襄自不必说,唯前人侍从,亦步亦趋。“苏出于颜,更兼姿媚,黄则似出六朝,昔人以为自《鹤铭》而变者,苏黄并称,黄应在苏上。米博览兼收,可为薛李之变相,亦文皇之流也。”并进一步指出,他们的“信古”,仍然做得不够彻底,只是前人的变相。若真要写出性情,自出机杼,“宋四家书亦当于碑刻求之,方见真相。”B12所以他们的书作只是在“好而信古”的基础上,做了些变化,创造性是不足的。再有一例,他在跋赵松雪之子赵仲穆《〈醉翁亭记〉行书卷》记:“笔圆从篆,体阔由分,此松雪家法也。仲穆名子,故能不失规矩,惟已属守成,终乏开拓气象耳。”由此可见,姚华的“信而好古”,目的并不是“述而不作”,而是为了更好的创造。守成不是他的最终追求,他同样讲求“开拓气象”,只是他创造的标准相当高。他主张:“固不必事事复古,惟变而不失古法,斯可谓善学古者矣。”颇有见地,此语可作为“信而好古”的最好诠释。同时他还以为创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创造的根基是熔铸诸家,然后才能自辟蹊径,成一家风貌。康有为则不同,他鲜明地提出了“变”的思想,即强调以“变”来求得事物的进步。其《广艺舟双楫》即贯穿了这种思想。在第一章他就明确指出:“变者,天也。”一方面表现了其抛弃陋习、另辟蹊径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多有激越偏颇之词与变古立异之说。如同样是对宋四家的品评,康有为在这种立论的支撑下,则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古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法,专注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独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盛守旧之证也。今世邓石如、包慎伯、赵撝叔变六朝体,亦开新党也;阮文达决其必盛,有见夫!”B13在康有为看来,苏黄不仅仅是“创造不足,变化可矣”的继承者,而是专注意态的“新党”,他们的成功就在于能“大变唐法”。由此可见姚、康二人对于“创造”的态度与标准上是格格不入的,姚华认为应沿着先“信古”、再适可变化,然后出新意的路子行进,学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康有为则是变法的思想主宰着他的头脑。他还进一步阐述:“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可见康有为的求变不是纯粹书法意义上的变法,而是以书喻时事。他指明了变法的取向——“尊碑”,为达到尊碑的目的,康有为不遗余力地历数魏碑十美,并以为“后世所有之体格,魏碑无不具备,遂取一家,皆足成体。”极力鼓吹魏碑。同时,我们也看到,“康有为的‘变,并非破旧立新,而是主张复古。他认为上古、秦汉、魏晋的书法才是美的,而唐以后则每况愈下。他不承认唐代书家变古法是一种创新,反而指责‘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B14所以康有为的变法创新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他顺应了时代风气变化,应当说对书法理论建设与实践指导都是有深远意义的。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姚华虽然稍偏重于“碑学”,但他无意于排斥帖学,而计较书法的碑、帖分野,而是以深厚的学养、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和审视书法,信而好古而有多有创见;客观上打破了“惟碑是尚”的书法风气的禁锢,开启了后人对晚清碑学思潮的反思、批判的先河,使得这一时期的书学观念由单纯的尚碑逐渐走向碑帖结合的路子上来,形成了书法审美的多元化,为后来书法观念的更新与重建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 贵州省贵阳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姚华评介》,1986年版,第178页。
②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宝南第九》,《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804页。
③ 姚华《弗堂类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3页。
④ 黄绍箕在《广艺舟双楫评语》中提出与康氏不同的看法:“《龙藏寺碑》虽晚出,而当别为一宗。新出《刘碑造像》,字多极完密,与《敬显俊》逼似,圆密不及,而中有质朴严重之意,又似过之,可以为辅矣。”见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⑤ 同①,第132页。
⑥ 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⑦ 姚华《书适》,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37页。
⑧ 同③,第48页。
⑨ 同①,第23页。
⑩ 同②,第812页。
B11 同③,第53页。
B12 同①,第193页。
B13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卑唐第十二》,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814页。
B14 同⑥,第7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