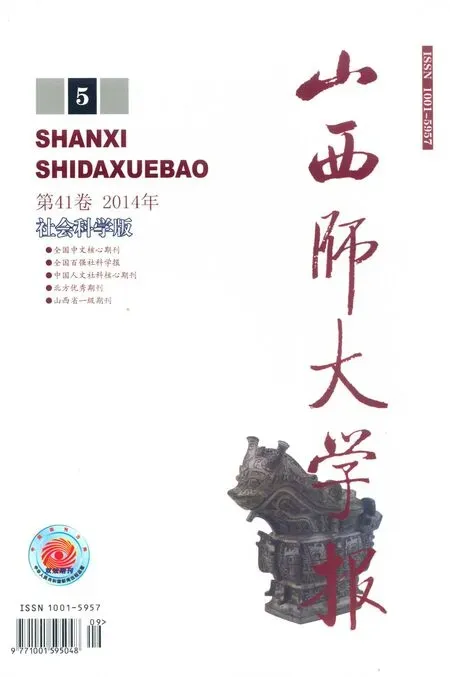贝蒂·弗里丹女性主义思想转型原因析论
2014-04-10肖克
肖 克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长春 130117)
在当代西方社会,女性主义①女性主义(feminism)与女权运动(feminist movement)是指一个硬币的两面,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的指导思想,女权运动是女性主义的实践,因此这两个概念在本文有时是互通的。已经成为最活跃的政治思潮之一,相比其他政治思潮,女性主义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更加密切,更加“界限分明”,更加重视将理念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与政治政策。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重镇,美国的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权运动无疑起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提到美国女权运动,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的一个名字就是弗里丹。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21—2006年)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领军人物,被前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为“美国最响亮的声音之一”。弗里丹1966年与人合作创立了旨在促进妇女权益的全国妇女组织(NWO),并担任该组织首任主席。她终生不懈地通过写作与社会活动,为扩大妇女权益、争取两性平等而呼吁奔走,被称为美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弗里丹的思想经历了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不仅仅是弗里丹个人关于女性主义与女权运动思想的改变,更是整个美国女性主义思潮与女权运动发生变化的缩影。因此只有从西方社会主导政治思潮的变化(宏观层面)、当时社会政治的具体状态(中观层面)与女权运动实际状况(微观层面)等多角度进行分析,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弗里丹思想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弗里丹女性主义思想的转变: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
正是弗里丹在1963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女性的奥秘》点燃了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导火索,成千上万的美国妇女受此书影响,走入职场,进而推动了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纽约时报》书评认为该书“永久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该书虽然首版只印了3000册,后来却迅速以精装本60万、平装本200万的销量,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圣经。随后,弗里丹又出版了以作于20世纪60—70年代文章为主的论文集《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为美国女权运动推波助澜。然而,弗里丹的女性主义思想前后并不一致,在1981年出版的《第二阶段》这一女权主义重要著作中,她的思想相比20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具体来说,相对于《女性的奥秘》的观点,弗里丹的思想在《第二阶段》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显著改变:
(一)女性主义的定义和女权运动的目标发生了变化。所谓“女性的奥秘”意指美国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渲染的、与妇女现实生活不符的安逸舒适的“幸福家庭主妇”形象,实质是男性视角下对女性形象的定义。“女性奥秘论告诉人们,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它告诉人们,纵观其历史,西方文化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低估了这种女性特征的价值”[1]35。在《女性的奥秘》中,弗里丹着力于对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社会角色的批判,认为这种身份与角色的定位是强加于女性的所谓“女性的奥秘”,正是由于男性所设定的这一女性模式期待导致了长期以来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她认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限制了女性人格的发展,她们没有参加家庭之外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果其智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她鼓励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争取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一切女性权利,目标是彻底揭露“女性的奥秘”的谎言,争取彻底的男女平等。“在第一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参与,融入主流,获得权力,发出声音,进入政党,参与政治过程,介入职场、商业领域”[2]13。总之,弗里丹认为性别之间的生理差异不构成任何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得以区别对待的理由,因此一种基于性别平等的包括观念上平等在内的“同样的平等”是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追求的目标。
在1976年出版的《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一书中,弗里丹的论点基本上与《女性的奥秘》的论点相同,她通过一系列写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论文表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尽管女权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距离目标仍很遥远,需要加速进行。[3]1—15后来,在一篇作于1998年的该书新的前言中,弗里丹又对这种想法进行了反思。
然而,在《第二阶段》一书中,弗里丹的思想发生了几乎180度的大转变,将女性主义的目标从追求“同样的平等”转变为追求“在差异中的平等”[4]116。弗里丹认为,女性主义到了应该发动“第二阶段”,即“女性的再发现”和“家庭的再发现”阶段了,应该由以前强调男性与女性的绝对平等到强调女性自身特点;由追求男性与女性社会身份的完全等同到强调女性自身认同。在“第一阶段”,女性主义的战场主要是家庭之外的社会,而第二阶段家庭才是主战场;第一阶段的结果是使得妇女看起来就像“带着文胸的男人”,第二阶段要充分发掘女性独特之处;第一阶段,女性充满了自信,对女权运动的方向深信不疑,第二阶段,女性需要“了解女性力量的局限,以及超越这些局限,产生一种新力量的可能性”[2]157。
(二)女权运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第一阶段,女性主义与女权运动的主体无疑是女性自身,她们常常悲壮孤立但又充满自信的与男性主导的世界作战,作战对象包括弗洛伊德的性唯我论谬论。[1]114—144对女性来说,男性主导的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男性是她们苦难和不平等的根源,是她们反抗的对象。然而,在《第二阶段》,情况发生了变化。弗里丹指出实际上男性也是性别不平等主义的受害者。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男性主义要求男性“假装自己优秀、冷酷、男人气,逼迫自己一人扛起负担整个家庭的责任,在冷酷的经济世界里艰难前进”[2]95。性别模式固化与性别气质疏离之后的结果却给表面上的强势者男性也带来巨大伤害:“越这样,他越感觉到威胁和敌对。”[2]95与处于弱势的女性不同,男性是表面上的强者,因此虚幻的骄傲与内心的虚弱不允许他们去反抗,弗里丹称之为“沉默的美国男性运动”。弗里丹高呼,现在是男性抛弃这种想法,加入女权运动第二阶段的时候了,不仅为了女性,也是为了男性。“在这场改变了所有人生活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男性和女性的需要交汇了。……这是始于追求平等的女权运动的第二阶段的另一半:男性的解放。男人,似乎现在和女性一样,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2]123女性主义的第二阶段,只有男性的加入才完美。
(三)女权运动的开展方式与手段发生了变化,由破坏现状到与男性一起共塑未来,由对抗到合作。在第一阶段,女性主义者为了改变现状,她们成立了很多女性主义组织,她们演讲、抗议、游行,并在受教育权、堕胎权上和家庭中男女分工等议题上争取全社会的支持。总之,她们认为男性能做到的,女性也能做到,给予男人的也应该给予女人。她们力图成为社会的强者,成为“女强人”,然而这种“女强人”仍然是男性标准的强者,正如“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把头发剪得短短的,下身穿灯笼裤,尽力使自己看起来像男人”[1]93。女性主义的发展驱除了笼罩在女性之上的社会压迫迷雾,但是新的权力神话又以新的语言为女性布下新的符咒。于是,女权运动出现了奇特的景观:一方面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破坏,另一方面是女性在第一阶段以“政治平等”为核心的目标基本实现后,她们并没有胜利者的感觉,她们仍然感到不自由,而且往往比第一阶段还迷惑。从效果来说,弗里丹对第一阶段的女性主义并不满意,“在第一阶段,女权运动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性政治上,从针对男人的个人卧室战斗,到反对强奸或色情作品,以‘找回夜晚’。针对男人的性别战争是出于愤怒而导致的无关的、弄巧成拙的行为。它根本改变不了我们的生活”。[2]203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应该改变将男性作为她们敌人和一切痛苦来源的态度,改变那种反体制的“革命者”形象,而重新认识自身,思考女性的作用,主动融入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在内部将这种社会改变成女性们希望它变成的那个样子,尽管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她们也许现在还说不清楚。因此,弗里丹号召大家重新审视那些以前被明显低估了的“女性的领域”,比如照顾儿童等家务活动,号召女性“回归家庭”,在和男性合作的同时以性别为基础进行社会分工。这些“女性的领域”不仅维护了家庭价值等珍贵的传统,而且女性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更可能积累力量,这种力量同样也是政治能量和意识聚集,更会加强女性身份的自我认同和女性权利的实现。
二、西方主流政治思潮的大背景:弗里丹思想转型的宏观因素——论争
女性主义往往缺少自身的理论基础,需要将其他理论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因而依据其所根据的理论而分为多种流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其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西方主流的女性主义思潮,也正是弗里丹被归属于的流派。自然,她思想的转型也脱离不开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这个大背景。
自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论以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一直都是西方主导性的政治思潮,其间尽管发生了许多对自由主义主导地位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与其说是对自由主义的颠覆,毋宁说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因为从宏观着眼,这些挑战都发生在自由主义大传统的范围内。依据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权利而非权力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最原始的因素。在逻辑上,人类不是被分配而是以生命的名义天然地拥有地球上的一切资源,具有无须论证的道德公设。这一公设是人类正义的逻辑前提,一旦放弃,社会伦理系统就将崩塌。按照约翰·格雷的观点,自由主义传统中各种变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关于人与社会的确定概念具有独特的现代性。”[5]2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起源于对人性的一个基本看法:人的独特性在于理性,理性意味着个人自治和自我实现。既然自由主义赞同个人权利优先,那么一个公正的社会就应该允许个人运用他的理性能力自治,实现自我。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18世纪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9世纪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贝蒂·弗里丹。她们坚持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具有理性,女性应当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如果说性别理性有差异,那也是因为教育机会不均等和社会习俗偏见的结果,只要教育机会均等,女性在理解力方面会等同于男性,两性之间的心智差异将最终消除。她们反对强调性别的差异,更强调两性间的相似性。既然个人权利优先,那么就要尊重女性的权利;因为作为具有平等人格的女性也是人,有权运用她的理性自治。伴随着初期女性主义的社会运动就是从18世纪一直延伸到20世纪的以争取选举权为核心的女权运动。
然而,自由主义并没有垄断女性主义的话语权。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生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和女权运动嫁接之后纷纷提出各自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从经济角度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有的认为女性不平等的肇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有的认为女性解放的第一步应该是颠覆父权制,改变女性“他者”的处境,观念的解放才是最大的解放;有的将妇女与自然等同,认为女性应该挖掘自身性别特征优势,变被动为主动。比较自由主义而言,以上这些理论的女性主义思想往往对现实的批判更激烈,更具有颠覆性,因此很快就从自由主义那里抢占了女性主义的理论阵地。
面对这些来自外部的女性主义理论的论争与攻击,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识到整合自身理论、获得更大范围认同的重要性,它希望妇女的解放,但妇女的解放如果是以资本主义制度被取代为代价,以现有全部秩序的解构为结果,那么女权运动的发展前景便使很多人退缩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妥协和重构,拉近了和同属自由主义大传统阵营的保守主义等理论的距离。
表面上看,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经常发生冲突,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两大意识形态,事实上,表面上的矛盾掩盖了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保守自由的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修正、一种限制,因为对传统与秩序的保守有可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致自由,而对自由的捍卫也往往要采取保守的形式。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政治哲学和政治运动,首先形成于欧洲,是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产生的。保守主义的奠基者是埃德蒙·伯克,他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提出了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伯克指出,自由与法律秩序、伦理原则、个人尊严之间有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孤立地强调自由只会导致少数人的特权和自由的毁灭。历史,即我们长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做某种事情的习惯,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近代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奥克肖特更好地表达了保守主义的思想特征,在他看来,传统就是定义现在的决定性要素,而政治的任务就是“寻求暗示”,寻求“传统”的暗示,寻求现在已经存在的而我们还未能认知的本质。传统意味着连续性,追寻传统不是追寻某种理想,更非追求任何抽象原则,而是追求传统的隐含性及其限度。而追求传统中的连贯性的暗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认识我们自己,传统就是“文明本身”,追求之后要求我们所做的就是作出调整与改变。[6]105因此,在对待包括女性问题在内的一切政治问题时,我们不能采取完全和传统断裂的方式,改变必须循序渐进,否则容易引起“理性的误用”,造成灾难性后果。
其他理论流派对弗里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打压,随着女权运动第一阶段目标的基本达成,许多女性已经成为她们以前所极力攻击的制度的一部分,因为她们与现存制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这些都使得弗里丹重新考虑女性主义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在《第二阶段》一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明显的保守气息。“自由”、“信心”、“破除”这些在《女性的奥秘》中经常可见的词汇纷纷被诸如“两性合作”、“回归家庭”、“儿童看护”等保守主义所喜欢的表述所取代。比如,在谈到住房问题时,弗里丹说:“在对个人隐私的需要与对某种形式的家庭和共享空间的需要这两极之间存在一种第二阶段的全新的流动性平衡和压力。”[2]78“全新的流动性平衡”一词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努力与更好融入现有体制之间的努力的非矛盾性,第二阶段女性主义的立论基础也从启蒙理性向传统价值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在弗里丹看来绝不是倒退,而是向一个更高阶段的前进。
三、美国政治光谱整体右移:弗里丹思想转型的中观因素——悖论
弗里丹思想的转变并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变化,也是美国政治光谱整体右移的充分反映。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价值取向更加保守,这构成了弗里丹思想转型的中观层面因素。
众所周知,从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实行凯恩斯主义新政开始,新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大行其道。20世纪60年代,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美国的自由主义政策走向高峰。自由主义政策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强,在社会领域却是价值放任大行其道。这一时代的年轻人蔑视传统和权威,放纵情欲,积极参与“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以“垮掉的一代”文学、摇滚乐、性开放与毒品为代表的“反文化运动”式的自由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另外,二战后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带来了不同于基督教传统的价值观。加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加重政府的负担,造成效率的降低和国力的衰退,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中处于守势。所有这些都表明,新自由主义已经走进了困境。
对待这场自由主义的危机,自由主义阵营分裂了。一些人把“伟大社会”计划的失败归咎于政府投入的不足,甚至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提出怀疑。这些人支持、鼓动甚至亲自参与1960年代的社会政治运动,后来成了所谓的“新左派”。与新左派相反,另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从不同的方向来反思自由主义,他们坚定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坚决反对新左派的攻击,把社会动荡看作是对民主及自由的威胁。这一派人后来就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标志着新保守主义已经在美国思想界取得优势,美国政治光谱整体右移。
女性主义自然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光谱整体右移的大趋势。以弗里丹《女性的奥秘》为标志之一的1960年代女权运动也在很大程度借助了当时价值放任的大潮。启蒙运动所秉持的天赋人权、个体自由等观念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就是公众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性与家庭等议题的态度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变,以至于美国人以压倒性的意见欢迎给女性提供更多的社会机会。民调显示,在1970年到1980年间,美国社会中要求强化女性地位者的比例从42%提高到了64%,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一个不满足于做家务的女性应该走出家庭去发展自身的兴趣,即使她的丈夫反对。[7]100在这段时期,女权运动看起来完全是为了实现启蒙运动在美国未竟的事业,女性主义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一部分,甚至一些人强调,女性主义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部分。
然而,对女性解放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对女权运动的支持,也不意味着同意女性离开家庭而成为劳动力市场主要的一分子。美国女权运动政治学的悖论是:“尽管整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支持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女权主义却使得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失去选票。”[8]105而制造这种悖论的正是以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为代表的势力。
保守主义者是通过将个人自由这个女性主义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基础,与家庭价值对立化,迫使女性主义一定程度上转型的。在1960年代,保守主义的策略是把女性主义当作敌人;在1980年代,保守主义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了女性主义的盟友,只是此时的女性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经历了60—70年代的大溃败之后,保守派利用了公众对美国现状,尤其是社会道德问题的焦虑感而力图东山再起。公众认为选举法、法律对毒品和色情的纵容,甚至女权主义本身,都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而在1980年代的美国,随着人们对华尔街律师的厌恶、对大财阀们的鄙视、对高犯罪率的担心,“自由主义”这个词日益含有更多的贬义色彩,保守派们不遗余力要把人们的愤怒不满导向自由主义。面对女性主义,保守派打出了家庭牌,他们提出问题:如果女性都走出家庭,那么我们的儿童怎么办?更进一步,他们通过哀叹儿童色情、青少年犯罪和垃圾电视节目,暗示女权运动要为此负责。通过保守派的宣传,很多美国人常常自问:目前单亲家庭增多、很多儿童得不到很好照顾、同性恋流行的情形是否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有人直接发出感叹:“父亲们总是很少去照顾孩子,现在母亲也这样了。”[9]21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待女权运动非常重视的《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和《平等权利修正案》上均持反对立场的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轻松战胜民主党人而当选总统,并在1984年再次以压倒性多数赢得连任。这段被弗里丹称之为“冷漠的时期”[2]11,引发了她关于美国女权运动的进一步思考,使得弗里丹在《第二阶段》中号召女性回归家庭,从具有浓厚启蒙运动气质的第一阶段向更具有实际可能性与更广大受众的第二阶段推进。弗里丹不得不承认:“我们为之斗争的平等没法居住,不能使用,斗争情况也不是那么令人愉快。”[2]25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得克服第一阶段的‘否认’情绪……这样我们才能以‘承认’的态度来爱和生活,‘选择’要孩子。”[2]26
四、美国女权运动内部的矛盾:弗里丹思想转型的微观因素——分裂
正是女性主义在面对其他理论的竞争时不得不与保守主义妥协,并对保守主义产生一种张力;另外,如上文所言,保守主义也对女性主义产生一种拉力。在张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女性主义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这并不是弗里丹思想转型的全部原因。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女权运动阵营内部也产生了分裂,这是造成弗里丹思想转型的微观层面因素。
纵观人类的历史,性别间的矛盾尽管有时会很突出,但从一个较长时期看来,性别战争从来不是最主要的斗争,性别矛盾也绝不是最主要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基础上的经济矛盾。
其实从一开始,美国女性主义的兴起就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因素导致的。迫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经济压力,一些妇女发现自己不得不走出家门,寻找一些工作以赚得微薄收入,贴补家用。二战后,战争给生活带来的破环感使得女性感到有必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加之战后美国经济的大发展,女性出去工作的趋势加强了,机会也增多了。战后初期,美国人更加重视家庭生活,结婚率在1950年代始终居高不下,到1950年代末,70%的女性在24岁之前结婚,而1940年仅有42%,1980年代则是50%。1950年代的离婚率也比这个世纪的其他任何十年都低。[10]178—179“在大萧条的挣扎以及战争的牺牲和离乱之后,没有什么比寻找‘安全和充实感’更合理的了”。[8]100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随着女性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她们逐渐产生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与飞速发展的战后经济相结合,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发现如果她们不去工作,不仅维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自身的价值也不会实现。另外,技术进步也对女性意识的觉醒起到促进作用:吸尘器和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普及使得女性不必像以前那样终日忙于家务,她们有更多时间来思考,来受教育,当然更有时间和权利去工作。
从1960年代开始,女性像潮水一样涌向职场。但从一开始,工作的女性之间就存在裂痕。一部分女性受过良好的与男性几乎一样的教育,她们自然会获得较好的工作职位和较高的收入(虽然相比较男性同事,她们的收入仍然偏少)。另一方面则是数目庞大的受过很少教育的女性,对她们来说,最现实的态度就是市场提供什么工作她们就做什么工作。尽管这两部分女性都对女性意识产生觉醒,都有许多人加入女权运动的第一阶段,但很快,起点的不同导致了她们之间在收入、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甚至比男性内部的差距还要大。由于市场涌入了大量没有经验和技能的女性,工资开始大幅下降,使得女性去工作以赚得更多收入的初衷更难实现。而且女性进入职场,使得原本在收入链条下部的很多男性失去了工作,导致性别关系更加紧张。逐渐地,有知识的女性开始认为没有知识的女性拖了女权运动的后腿,而没有知识的女性则认为有知识的女性背叛了女权运动。总之,她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经济利益差异超越性别的一致,而成为她们最重要的身份归属。
这场裂痕在堕胎问题上反映得最清楚。卢克在其著作《堕胎和母亲身份的政治学》中区分了在堕胎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她认为,支持妇女堕胎权的一方“拥有充分的资源;她们受过很高的教育,有一份工作,在职场上有最新的(和持续的)工作经验”[8]104。而反对堕胎的女性往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获得职业技能,因为她们结婚了。而且她们结婚是因为她们的价值表明这会是最让她们满意的生活”[8]104。
正是女性主义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女性主义自身,使得女性在考虑社会政治议题时往往不能像第一阶段那样单纯从性别方面考虑问题。弗里丹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第二阶段》中,弗里丹明确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现实?那些被选入议会、市政厅的女性,或者已经攀升到白宫与类似内阁工作的女性,她们的今天是女权运动的结果,但是,……她们却充当了男性政治机器的代理人,试图让我们妥协,让我们收起女权主义的锋芒。”[2]12弗里丹给出的答案显然经过了深入思考;“女权主义单纯从女性角度而言,已经发展到了最大限度。……女权运动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2]13在第二阶段,女性需要的是“克服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两极对立,以及女人和男人间的对立,得到女权主义许诺的完整性”[2]26。
综上所述,弗里丹关于女性主义思想的前后不一致并非她对美国女权运动的“背叛”,相反,这恰恰是她对女性主义重新思考的结果,更反映了当时整个美国社会各种思潮的博弈与交锋。无论何种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而非一时的哗众取宠,就得根据社会现实逐渐调整自己,在这方面,弗里丹做得非常优秀。弗里丹以其远见卓识将女性主义的基础和结构打牢,力图建造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这也许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1] (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程锡麟,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
[2] (美)贝蒂·弗里丹.第二阶段[M].小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 Betty Friedan.It changed my life: writings on the women's movement. New Yorker: Random House, 1976.
[4] 张立平.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述评[J].美国研究,1999,(2).
[5] John Gray. Liberalism.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6] Michael J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1.
[7] Daniel Yankelovich.New Rules. New York: Bantam Press, 1982.
[8] (美)约瑟夫·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M].赵晓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9] Alan Wolfe. The Day-Care Dilemma: A Scandinavian Perspective. The Public Interest, 1989, (Spring).
[10] Steven Mintz, Susan Kellogg. Domestic Revolution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