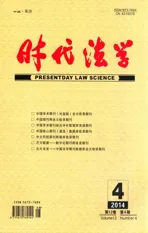国际金融“软法”获得遵守的动因分析*
2014-04-10张庆麟王桂林
张庆麟,王桂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国际金融“软法”获得遵守的动因分析*
张庆麟,王桂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国际金融软法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表现形式、调整范围、效力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传统国际法的特征。在国际金融法获得遵守的动因分析中,理性主义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模式。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构建主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关注私人主体在遵守中的作用和动因是对过于理论化和抽象化的传统国家动因分析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另外,软法制定过程中的广泛代表性和规则的合理性也是促进国家和个人遵守的必要前提。
国际金融软法;遵守动因;理性主义;构建主义
在国际金融领域,相比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等其他领域存在着更多的“软法”,这种不同于传统国际法的规范如何能从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甚至形成类似于或强于国际法的效果,是本文主要分析的问题。同时,软法在金融领域的大量存在,也体现了这种没有严格批准程序、更低成本、更加灵活、更易达成协议的合作方式的独特优势,有学者甚至指出这种以国际金融管理网络为代表的机构间合作方式表征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对于这种合作产生的软法获得遵守的动因的分析能够推动这种新的合作方式取得更好的效果。本文详细阐述了两种经典的动因理论以及随着“全球治理”、“合法性危机”等引起的动因理论的新发展,评述了各种理论的不同及利弊。
一、国际金融“软法”的界定及特征
Ulrika Morth在其主编的专门探讨软法的一本书中谈到,“几十年以来,软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用来形容和描述全球政治中一种显著现象——没有政府的治理”。“软法”一词如今虽然在法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梁剑兵副教授曾综合国内外学者的各种观点,概括为12类,其中甚至包括了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梁剑兵.软法律论纲——对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一种界分[A].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在国际法领域,有的学者认为“软法”是义务内容不明确的协定,有的认为是对国家有较少约束力的协定,有的学者认为“软法”是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制定时是期望可以通过国内法或者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获得法律效力的协定。法国学者Francis Snyder在其1994年的文章中提出了目前最为大家广为接受的定义——“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
从“软法”一词的构成便能看出其两个主要的构成要素。首先,它是一种“法”,区别于一般的完全没有约束力的规则、观念、信条等。同时它又具有软性,即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又有不同之处。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同,使它一直以来受到法学家的忽视。如一位学者所言,迄今为止,对软法关注最多最早的还是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而法学的关注则晚得多,这与法治领域中严格的程序主义有一定的关联,这种严格的程序主义影响了法学对现实的敏感性*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受分析实证主义的影响,传统法学一直认为法律应该是由权力机关依据相关程序制定的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而目前被称为“软法”的这些文件并不具有实证主义上所说的法律效力,这一特点过去常常受到法律学者的诟病,被称为是一种“言论商店”(“talking shop”)*Florian Hoffmann, International Actors, 102 Am. Soc’y Int’l L. Proc. 450, 451 (2008) (describing “the classical model of essentially horizontal forms of rule-guided interstate exchange, a form that could be called the ‘talking shop’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而“软法”渐渐进入法学视野则是由于它具有的一种事实上的约束力,规范着相关主体的行为。
在国际金融领域相比于其他国际经济法领域,存在着更大量的软法。这不仅是因为在涉及经济命脉、高度敏感的金融领域各国难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也因为金融软法存在的诸多优点决定它是一种更加适合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方式。例如,金融软法的制定更加“廉价”,正是由于其非正式性带来更小的谈判成本,也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谈判、生效程序,金融软法的制定和修改更加灵活,不会给国家带来过多的“主权成本”(sovereignty cost),这对于需要采取迅捷措施以应对全球性金融风险来说非常重要*见Chris Brummer, Why Soft Law Dominates International Finance—And Not Trade, 13 J. INT’LECON. L. 623 (2010), which states“Soft law... provides a decisively cheaper means of agreement-making. It carries what can be thought of as low bargaining costs due to its informal status. Perhaps most importan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quir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by heads of state or lengthy ratification procedures. ”。概括起来,这些软法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制定主体看,国际金融软法是由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的国际金融组织与国家、非国家实体之间互动磋商而形成的。它的制定主体远远超出了国际金融条约的主体范围。除了主权国家以及具有特定金融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欧盟、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以外,主要包括活跃在国际金融各领域的专业性标准制定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督者协会、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结算支付体系委员会等。一些非政府组织、国家行业协会、跨国公司、国际银行等非国家实体也可以参与国际金融软法规范的创制过程,并可以成为软法规范的实施及其监督的权利义务主体,例如国际融资贷款的《赤道原则》。
第二,从表现形式看,国际金融软法多由一般原则和“最佳实践”构成。实践中,国际金融软法的形式渊源多种多样,其中既有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制定的内部政策指南和操作规程,又有国际性金融标准制定组织发布的指导性文件,还有国际金融业界的自愿性承诺和最佳实践做法,其规范文本大多以宣言、原则、标准、指南、建议、准则等形式出现。
第三,从制定过程来看,国际金融软法具有明显的非正式性。Joost Pauwelyn教授曾称,新型的非正式的国际法有三个特征:非正式的程序、丰富多样的参与者、非正式的结果*Joost Pauwelyn, Informal International Law-Making: Mapping the Action and Testing Concepts of Accoun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金融软法的制定并不需要像条约那样的谈判磋商程序及民主程序,常常是国家监管人员或相关专业人士通过一些国际性商讨会议协商一致制定的,没有固定的程序范式。
第四,从调整范围上看,国际金融软法调整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主要是相对于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等具有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的文件而言。目前,涉及国际金融的多边条约仅在GATS中的金融服务开放部门有所体现,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成立文件,但软法却广泛存在于银行监管、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结算支付、金融犯罪等领域。
第四,从效力上看,国际金融软法虽无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效力但却可能产生实际法律效果。这些金融软法没有特定的生效范围,也没有强制执行机关,从实证主义角度,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从社会法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的认识角度,由于金融软法在实践中的实际约束力,可以认为它具有类似于法律的效力*关于不同学派对法律效力的认识,参见张根大.法律效力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4-48.。以巴塞尔文件为代表的国际金融软法规范为例,通常在其文本的前言或篇首直接载明“不具有或不打算具有”任何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但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却逐渐得到金融业界、国际组织乃至许多国家的接受和采行,最终成为普遍公认的、统一的国际标准。德克萨斯大学的弗拉西诺教授在考察国际法院50年司法实践之后也认为,软法规范虽没有法律强制性,而仅具有建议性,但它能从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甚至形成类似于或强于国际法的效果*转引自涂亦楠.论国际金融软法及其硬化——以国际信贷法为例[J].湖北大学学报,2012,(5).。
二、国家对金融“软法”遵守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理性主义产生于启蒙运动。从认识论的角度,理性主义是指相信“理性”是一切知识的主要来源。从政治角度,理性主义指一种“政治理性”,以“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世俗主义(secularism)”等为中心要点。而将这一思想引入国际法遵守动因分析则相对更晚。John K. Setear曾在一篇文章中从理性主义角度分析对国际法的遵守和违反,Benedict Kingsbury在一篇文章中对理性主义作出了系统阐释*John K. Setear, Responses to Breach of a Treaty and Ration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Rules of Release and Remediation in the Law of Treaties and the Law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83 Va. L. Rev. 1 (1997) (examining breach and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from a rationalist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nedict Kingsbury, The Concept of Compliance as a Function of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19 Mich. J. Int’l L. 345 (1998) at 350-56 (describing rationalis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mpliance).。这一理论认为,国家在国际社会是一个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主体,国家是否遵守国际法或国际上的标准习惯都是在衡量它可能对本国带来的物质利益或其他损失基础上的理性决策,国家总是通过成本——利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来对待国际法和与他国的关系。国际法并不能对国家带来压力,只不过是国家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造成国家遵守某项国际上的协定(无论是软法还是硬法)只能是两个动因:希望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此处强调是从一国自身出发可得的物质利益,若是因国家名誉带来的无形利益不应归于此处,否则,这种“利益”会无所不包,各种学说都会变成一种“利益说”,没有区分的意义。;对可能带来的国际抵制的顾虑。
由于国际上的文件只有很弱或者有限的执行方式,也很少会有带来抵制的风险,这决定国际上的合作在深度上是有限的。有学者论说道:在不带来任何损失时,国家会言不由衷地表达它们对某些盛行观点的同意,而一旦开始存在一些军事、经济或其他国内压力时,就会放弃作出任何承诺*Jack Goldsmith and Eric Posner,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200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ich argues“nations mouth their agreement to popular ideals as long as there is no cost in doing so, but abandon their commitments as soon as there is a pressing military or economic or domestic reason to do so.”。
这种理性主义学说在学者解释国际金融软法获得遵守的原因时得到了广泛体现。以巴塞尔协议为例,外交关系委员会1999年的一份工作组报告认为,对于新兴市场而言,促使其遵守巴塞尔协议的动因主要有三个:可能的市场回报;IMF与世界银行的资金支持;巴塞尔协议下更低的风险评估*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Safeguarding Prosperity in a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17, 1999.。概括起来,学者认为国家执行巴塞尔协定通常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认为这种监管规则可以帮助规避系统性风险,二是认为这样一致的资本要求有助于创造公平一致的竞争环境,避免恶性竞争。三是遵守这种国际性标准能够增强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对本国金融领域的信任,打开国际市场。
另如,国家违反反洗钱规则可能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反制措施。FATF在世界范围内公布“不合作国家和地区名单”(List of Non Cooperative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以及有政策缺陷(Strategic Deficiencies)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不合作国家和地区,FATF呼吁其他所有成员国和非成员国采取反制措施,被形象的称为“黑名单”(blacklist);对于第二种名单,FATF则仅呼吁其成员国考虑该国家制度缺陷造成的风险*截至2012年6月,FATF公布的第一类名单国家包括了伊朗、朝鲜,第二类名单包括了玻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印尼、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圣多美与普林西比、斯里兰卡、叙利亚、坦桑尼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见以上引用21。。这两种名单都是开放性的,因此只要名单上国家采取符合反洗钱最低标准的措施,就将被剔除。这些名单特别是黑名单往往会遭到其他国家的金融部门和企业的集体抵制、封锁,会给本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虽然理性主义从这些角度能够一定程度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遵守没有效力的软法,但在很多问题上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相反,这些金融软法反而成为学者批判理性主义的论据。
首先,这种学说并不足以解释国家遵守动因的全貌,对于某些国际协定(例如人权公约),国家不能通过加入获得任何物质利益,仍然有大量成员国。在金融软法中也是一样,以日本为例,其在经济困境时仍坚持8%的资本充足率,即使是耗费很大的成本,仍然不惜这种物质利益损失进行执行*Charles K. Whitehead, What’s Your Sign?—International Norms, Signals, and Compliance, 27 Mich. J. Int’l L. 695.。
其次,虽然存在FATF建议这样可能给不遵守的国家有效实施反制措施的金融软法,但这种情况在国际金融软法中十分少见。大量的国际标准、规则根本没有对不执行国家的抵制措施,并不能对国家的经济利益带来有形损害,却仍然被各国广泛遵守。
在理性主义这种遵守动因分析的基础上,国际社会似乎很难通过对一个国家施加影响来构建国际制度和秩序,对如何增进国家遵守金融软法也基本没有有效对策。对于如何促进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存在一种“执行学说”(Enforcement school),这种学说认为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深度有限,国家加入一个协定是希望得到加入协定的每一个成员国的遵照执行,因此,要使一个协定获得最广泛遵守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强其执行力*See Gorge W. Downs, Is the Good News about Compliance Good News about Corporation? 50 Int’l Org 379 (1996).。然而,这种增进遵守的学说在软法领域似乎难以适用。在松散的国际社会,增强执行力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法中尚且困难重重,何况是在软法领域。
三、国家对金融“软法”遵守的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m)
与理性主义不同,构建主义学说并不认为国家在国际社会完全以自身经济利益权衡来进行决策,而是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国际社会习惯的影响。构建主义的学说代表Alexander Wendt认为,国家间的体系并不是物质化(material)而是交互影响(intersubjective)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某种程度上是在这种交互结构中构建起来的,他强调国家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国家会从其他人的角度定位自身的意义*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88 AM. POL. Sci. REV. 384, 384-85 (1994).。 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国际社会中,各国经济联系错综交织,在国际社会发生作用的是习惯(norms)和交际网(network)。国家不可能只是做一个仅关注本身利益、追求本国目标的自私自利者,而是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隐形压力*这里可以借鉴组织社会学上经典的霍桑实验。在其中一个实验里,公司政策规定,单位时间做的工作量越多所得收入越多,但工人宁愿牺牲自己挣得的更高的工资,也会遵从集体设定的日工作量、限制产量的群体规范,以免被公司职工孤立和疏离。这个实验揭示了在社会心理层面,工人并非是简单的经济人概念。人是具有多重目标和价值观的复杂人。笔者认为这种社会学上对人的分析能够很恰当地类比到构建主义中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有学者说到:这是一种道德力量,成员国家遵守规则的动机来自同伴的压力*Cheltenham, Edward Elgar: Soft law in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2004), p.169.。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会影响国家对利益的判断。国际社会的合作程度和合作领域都在不断扩展,在交往中会有各种习惯产生,在这个越来越重要的舞台上,国家会更加重视自己的形象、信誉,积极去遵守国际习惯,否则便会在国际合作中举步维艰*See Chris Brummer, Why Soft Law Dominates International Finance—And Not Trade, 13 J. INT’LECON. L. 623 (2010).(“agreements frequently memorialize consensus on issues with important domestic import for parties. As a result, defection from even informal agreements can have reputational costs that hamper a regulator’s ability to promote its policies abroad.”)。
FATF建议执行中的互评机制(peer view)便是利用国家间的同行压力对国家的执行情况进行追踪。互评的目的是确保各成员国内反洗钱措施跟进修正后的“40+9”建议,有效预防不断发展中的洗钱活动。从2005年1月起到2010年止,FATF 对FATF成员进行第三轮互评。与前两次的互评相比较,第三轮互评是根据修正后的“40+9”建议而制定评估的方案和程序,要求更为严格。按照考核标准的要求,对成员国执行建议的实际情况划分为四个级别:合规(C,与建议有关的所有强制性标准得以完全遵守)、基本合规(LC,绝大部分强制性标准被遵守,只存在少量的缺陷),部分合规(PC,大部分的强制性标准未被遵守,存在严重缺陷),不合规(NC,由于一国结构、体制或法律制度的原因,某个建议在该国全部不适用)。
与此相类似,2011年,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规则相符性评估项目”(Regulatory Consistency Assessment Programme ,RCAP),以监督和评测各成员国政策与Basel Ш的相符情况。它定期对各国执行巴塞尔协议的情况(分阶段按采纳、执行、实际效果来推进)进行分析。在其发布的文件上会明确列出各国目前的执行情况,而未执行或未完全执行会显著标记*见以上引用13,从不执行到完全执行分别标记为红色、黄色、绿色。。巴塞尔委员会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敦促其成员遵守其协定。2013年9月27日,巴塞尔委员会的Committee’s Regulatory Consistency Assessment Programme (RCAP)发布了关于中国执行Basel Ш的评估报告*Assessment of Basel III regulations-China, released by Regulatory Consistency Assessment Programme. Available at http://www.bis.org/bcbs/implementation/l2_cn.pdf。在此之前,该委员会也陆续发布了对欧盟、日本、新加坡、荷兰、美国执行Basel Ш的报告。这些评估报告虽然没有任何强制效果,但利用国家对自身声誉的顾虑,给其带来隐形压力,敦促成员的遵守。
一种最有名的构建主义学说是Abram和Antonia Chayes提出的“建设模式”(managerial model)学说*Abram Chayes & Antonia Handler Chayes, The New Sovereignty: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1998) (arguing that a“managerial model”of compliance in which nations cooperate in a problem solving approach to problems should replace the coercive theories that say nations comply because of sanctions).,认为国家确定是愿意去遵守国际上的习惯的,正是习惯的作用而非对报复措施的顾虑引发了国家的遵守,一国的不遵守往往是出于本国信息的缺乏和高昂的成本,而并非完全自私自利的决策。因此,他们认为,要增进国家的遵守,劝说和“建设”遵守比强制遵守更为有效。建设遵守包括给国家提供相关国际法信息,说明其在国际习惯中的重要性,为其提供遵守的财力和技术支持,帮助其建立遵守的能力。这一过程并不是因为对抵制或封锁的顾虑而是害怕在国际交际网(international network)中被疏远。
这种构建主义学说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在不存在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去执行一些金融软法,同时也提出了增进遵守的方法,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入,可以预见,这种学说会获得越来越强劲的生命力。
四、国家对金融“软法”遵守的私人主体分析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私人主体分析并非一种自成一统的学说,而是一种新型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同时体现在理性主义和构建主义的发展之中,它们都开始剥去国家的外壳,直接关注到国家内部的私人主体。有些国际标准则直接越过国家,使私人主体成为国际标准的直接遵守主体,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例如有名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它由民间机构制定,目的是确保企业的生产和服务符合社会道德标准。2007年5月1日起,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强制推行SA8000标准认证,将劳工权利与出口订单、普惠制挂钩,要求跨国公司在采购商品和服务时要审查对方企业是否达到这一标准,对不达标者,必须取消订单。这一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敦促我国上万家企业接受并通过SA8000审核。。
不论是上述理性主义还是构建主义,都是从国家整体的角度判断遵守的动因,而国家作为一个十分概括和集合的概念,对其进行动因分析往往只是一种理论推断,难以找到实践中经验的支持。近年来,随着全球治理、世界公民的兴起,私人主体在软法获得遵守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直接寻找私人对金融软法遵守的动因以增进其遵守可能比通过国家遵守再映射到私人更加直接和有效,毕竟这些金融软法的最终目的是影响和规范私人的行为,国家执行金融软法并不代表真正落实到私人主体。
这种以私人为主体的方法可以从一项研究中明显反映出来。在一项对FATF建议的遵守情况及其动因的研究中*Shima Baradaran, Michael Findley, Daniel Nielson, J.C. Sharman, Does International Law Matter? 97 Minn. L. Rev. 743(2013).,向182个国家的1015个公司以咨询者的身份用各种别名发送邮件,邮件内容为想要成立一个保密的、限制其法律和税务责任的公司(邮件接收者并不知晓这是一项调查),虽然邮件主要内容相差无几,但仍然通过一些小变化来调查不同的遵守动因,例如有的告知收件人这种行为被国际文件视为非法的,并可能遭受惩罚。公司如果回复需要发件人经验证的身份文件视为完全遵守,仅需要照片等文件而无需验证的为部分遵守,不需要提供任何文件为不遵守。调查发现,私人对FATF这种信息透明的要求的遵守程度最多只有51%,可见,国家的遵守和私人的遵守仍有很大差距*见以上引用28,由于在作出回复的公司中仅有不到一半遵守了FATF关于信息透明的要求,作者认为FATF在实际效果上的遵守率最多只有51%。(“In examining whether international law matters, our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that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s 51% at best, as fewer than half the contacted firms complied with financial transparency standards.”)。令人吃惊的是,OECD国家的公司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公司体现更高的遵守比率*另外,此份调查还有很多有趣的结果,如公司是否遵守与该国的能力和财力没有关系,在告知有惩罚的情况下反而容易诱发收件人的共谋(conspiracy)心态,较轻的惩罚措施比没有惩罚措施有更低的遵守比率(weak penalty effect)等等。。这种直接以私人为主体研究对金融软法的遵守目前还很少见,但开拓了一种新的思路。
在理性主义分析之中,有学者分析遵守一项国际软法可能对国内的不同主体带来的经济影响,这些主体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决策。以巴塞尔协议为例,执行巴塞尔协定并不是仅仅将其列入监管法条那么简单,而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利益重新分配。8%的资本充足率需要一些资本不能达到要求的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例如增发股票、抛售资产或贷款项目等,而资本充足的银行则可以乘机以优惠价格购买这些资产,这种利益分配不仅发生在不同国家的银行之间,在一国内部也是如此。在发达国家,由于一般小银行的资本相对于受到严格监管的大银行更加充足,巴塞尔协定的执行往往导致小银行股价上升,而大银行股价下降。但是并不代表大银行不会拥护政府遵守巴塞尔协定。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以内部模式评估市场风险,这正是制度、程序更加健全的大银行所擅长的。一国遵守巴塞尔协定可以为国内的银行吸引投资、储蓄等国际业务,国内的大银行基于这种考虑也会积极游说政府决策。当然,这些考量与一国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民主或专制体制、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银行所有制为国有或私有等因素影响有不同结果*国内主体对一国决定是否执行巴塞尔协定的影响可参见Mark A. Chinen, Lana J. Ellis, Matters of Preference: Tracing the Line Between Citizens, Democratic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 Transnat’l L. & Contemp. Probs. 419.。不少学者将国家利益、国家的决策主体再做进一分解剖析,便会看到国家的发展程度、经济规模、民主制度、政党、国内市场主体、国家代表等各种更加具体因素的影响。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立足于国内制度、私人主体来做更加务实的分析*Daniel E.Ho:Compliance and International Soft Law: Why do Coutries Implement the Basel Acc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2,v. 5, 3. Aug. pp.647-688. Mark A. Chinen, Lana J. Ellis, Matters of Preference:Tracing the Line between Citizens, Democratic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19 Transnat’l L. & Contemp. Probs. 419.。
在关注国际习惯的构建主义中,有学者又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交往习惯。各国在IMF的代表为本国一些银行机构监管者,长期共同的交往会形成自己的“圈子”。这些人一般有比较相近的工作领域、知识结构、政策倾向,这些人经常在一起工作讨论对越来越全球化的一些问题的对策。如果积极配合、协作这个圈子内的规则和制定的规则,会在这些同行面前获得很高的地位和声誉,而违反这些其他人共同承认的规则会给人“不合作”的信号,影响他在圈子里的声望。因此,对这些代表人员来说,也常常会有个人名誉和国家利益间的冲突。“合作”是他们交往中的一种习惯*见Charles K. Whitehead, What’s Your Sign?—International Norms, Signals, and Compliance, 27 Mich. J. Int’l L. 695. 文章中以日本对巴塞尔协议的遵守为例,论述了这种观点。。
金融软法长期以国家为对象研究其遵守范围,而在实践中真正产生的影响或许被高估了*前面已述对巴塞尔协议多样化的遵守现状,另外在前述Daniel E.Ho:Compliance and International Soft Law: Why do Coutries Implement the Basel Accord?一文中,通过社会实验(field experiment)数据,作者认为FATF在实际效果上的遵守率最多只有51%。。以上述巴塞尔协议、FATF建议为例,这些金融软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使银行、公司、个人等主体遵守相关规定,维护良好的世界金融秩序。国家的遵守到获得执行到取得现实效果使个体遵守之间还有很大差距,FATF以及巴塞尔委员会在其评估项目中都将国家的遵守分阶段为遵守、执行、效果,体现了对这种差距的务实的认识。
这种在国际层面打开国家的“外壳”直接涉入私人领域,从个体角度分析其对国家决策的影响、遵守国际协定的原因,也正是体现了“全球市民社会”兴起在“金融软法遵守动因”这一微小研究主题中的反应,可以预见随着个体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这种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和说服力会不断增加。
五、国家对金融“软法”遵守的规则正当性
从实体正义角度,个人对国内法的遵守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从规则内容本身出发寻找遵守动因,也即自然法学派。不管在不同阶段将这种内容的正义归为神或上帝的意旨、理性的体现等,都是从规则本身符合人类的某种理念解释人们对其遵守的动因和正当性。然而,在国际社会,却少有将规则本身维护的价值等因素作为国家遵守的动因进行分析,因为传统都认为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在国际交往中不会形成类似个人的道德观念,不进行价值判断,国家作为成员的国际社会,不存在用以判断国际协定内容正当性的“国际道德”,也不会产生一国因为尊崇协定中反应的理念而遵守一个协定的情况。
然而,必定存在一些人类共同认同的“普世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一个政权在国内的重要任务,是一个政府本身正当性的重要反应,虽然个人往往不是国际关系中直接的权利义务承担者,但国际交往中的各种协定最终都会作用于每个个体,因此,国家也会在国际交往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一个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条约、协定往往能得到更多的国家参与和遵守,这也符合国家的目标追求。例如诸多人权公约,反对一些国际罪行的金融软法更容易得到国家的认同。Thomas M. Franck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一国对国际法的遵守由对其合法性的信任来保障。有效的法律需要成员习惯性的、自觉的遵守,而不应该依靠或主要依靠一种政权要求服从的命令*Thomas M. Franck, Legiti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82 Am. J. Int’l L. 705, 706 (1988) (arguing that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s secured by belief in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e, which requires a belief that the rule came into existence through right process). Thomas M. Franck, Fairnes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 86 (1995) (“To be effective... law needs to secure the habitual, voluntary compliance of its subjects; it cannot rely entirely, or even primarily, upon the commanding power of a sovereign to compel obedience.”).。
从程序正义角度,近年来,金融软法制定的“合法性危机”“民主赤字”等问题广受争议。如巴塞尔委员会、FATF等组织最初都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参与,而其标准、建议的制定经常只是这些国家少数管理者、专家共同商讨的结果,巴塞尔协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任何预防效果,这些都引发和加剧了对金融软法正当性的怀疑。在过去,这种程序上的正当性很少被人关注,因为这些规则本身没有强制约束力,由各国自愿遵守,因此并不需要去苛求这些规则制定过程中的民主性。然而,随着这些规则获得越来越大范围的执行,其“法”的特征越来越凸显,这使得各国特别是因为遵守获得消极影响的国家开始怀疑其程序的正当性。而这些金融软法想要在这种已存在的现实影响力下进一步推动其影响范围和深度,其本身制定过程中的民主正当性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
有学者就从FATF规则本身的合理性、明确性出发,分析其获得广泛遵守的原因。与巴塞尔规则的许多原则性规定不同,它有着十分明确具体的内容,对于每一条反洗钱的40条建议和反资助恐怖分子的9条特别建议,都有各自的基本标准(Essential Criteria,E.Cs),还有其他因素(Additional Elements)予以补充,以明确该规则获得完全遵守的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这些建议还会通过Working Group and Plenary类似判决的决议以及解释性说明(interpretative Notes)、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红旗指标(Red Flag Indicators)、指引(Guidance)的发布进一步明确其含义。而且,根据其专家对国际金融犯罪的研究,这些规则会根据现实中的情况不断进行改进,以帮助国家解决不断新出现的犯罪形式。自1990年发布40条反洗钱建议以来,为应对洗钱方法和技术的发展,1996年第一次对其进行了修订,2001年纳入了反资助恐怖分子的8条建议,2004年新增反资助恐怖分子的第9条建议,在即将完成第三轮互评(mutual review)的2009年7月,开始了对其规则的再一次修订,并于2012年2月被采用,经过修改,完全融合了反洗钱与反资助恐怖分子的规则,并首次纳入了反资助核扩散(counter-financing of proliferation)的措施,不断适应国际金融犯罪的演进*Navin Beekarry, The International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mbating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Regulatory Strateg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mpliance Dertermina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31 Nw. J. Int’l L. & Bus. 137.。至今,FATF建议已有1990年、1996年、2003年、2004年、2012年五个版本。另外,这些规则常常是依附一些“硬法”制定的。如FATF建议中关于洗钱的定义便是基于和来源于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1988)(1988 UN Vienna Convention on Drugs)及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 Palermo UN Convention on Organized Crime)。
六、总结
世界范围内国家管理的衰落与公共治理的兴起,全球化以及国际组织的推动都使得软法在更多领域中产生,在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领域,国际上在应对诸如“系统性风险”等全球问题时越来越经常地采用一种“政府机构间”的合作方式(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如在应对危机时发挥了主要作用的G-20峰会。有学者甚至指出这种以国际金融管理网络为代表的机构间合作方式表征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见Anne 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2004) (arguing that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are critical component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he sorts of cross-border agency cooperation represented b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ory networks may mark a “new world order”),再如Kal Raustiala,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43 Va. J. Int’l L. 1, 4 (2002) (“[T]ransgovernmental networks are expanding rapidly, and their growth is especially apparent in regulatory cooperation.”).这种没有严格批准程序、更低成本、更加灵活、更易达成协议的合作展现了国际金融软法的独特优势。然而,金融软法在执行中仍然面对着传统阻碍因素——效力和执行力的缺乏。同时,根据一些学者从私人主体角度的分析,金融软法获得遵守的情况被高估了,实际落实到私人主体的情况仍不容乐观。
动因理论可以促进金融软法在未来获得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遵守和执行。总结上述关于金融软法遵守动因的学说,理性主义仍然会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种动因理论,而全球化的发展正逐渐使各国国家利益存在越来越多的重合,金融风险越来越体现出的传导性、系统性内生地增进了国家对金融软法的遵守。
随着各国的交流和交往不断深入,国际习惯和关系网络不断强化,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社会性”,而非单纯的以本国为中心的个体。金融软法可以继续和加强利用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对声誉的重视和形成的同行压力,增强信息透明、互享、评估、公布,为国家提供遵守的财力和技术支持,扫除非立场方面的障碍。
私人主体分析方法给金融软法遵守促进寻找了新的思路。从理性主义的私人主体分析方法中,可得到的建设性启示是,金融软法在制定、推行过程中不应仅从国家管理角度,而要关注这些规则可能对国内私人主体带来的利益影响,积极利用这些主体的自觉利益选择和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构建主义的私人主体分析,意识到具有社会性的个人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加强各国代表间的互相交流,增强其共同体意识,促进国际社会合作的深入。
另外,虽然软法并非传统意义上需要民主制定程序的法,但规则的合理性和其制定过程中的广泛代表性也是进一步促进国家和个人遵守的必要前提。而这一因素可以为金融软法获得遵守提供最耐久、持续的动力,也是最可靠的遵守动因。
就如同个人遵守国内法、公共道德时不同的遵守动因,国家或个人在选择遵守金融软法中也可能存在着多种动机和意图。而金融软法想要获得更好遵守,应当从上述多个方面和角度作出努力,结合不同国家不同的特点,最大限度增进遵守的广度和深度。
Analysis on Motivation Theory of Observ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oft” Law
ZHANG Qing-lin, WANG Gui-lin
(WuhanUniversityLawSchool,Wuhan,Hubei430072,China)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oft Law has its selves features differ from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law in its legislators, formulation procedure,characteristic, justification range, legal effect,etc. Rationalism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analytical model when we analyzed the motivation theories of observ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oft” Law. But constructivism will give play to more and more greater role along with going deep in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anwhil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ole and motivation of private subjects in observ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oft law is important supplement and development to traditional excessively theorization and abstraction analysis on State subjects observ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oft law. Moreover, comprehensive representative and reasonable rules in the soft making procedure are also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promote States and private persons observing i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oft Law; observed motivation; rationalism; constructivism
2014-05-27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制度改革与中国的法律对策研究”(11JJD820018)的阶段性成果。
张庆麟,男,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学;王桂林,女,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DF962
:A
:1672-769X(2014)04-00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