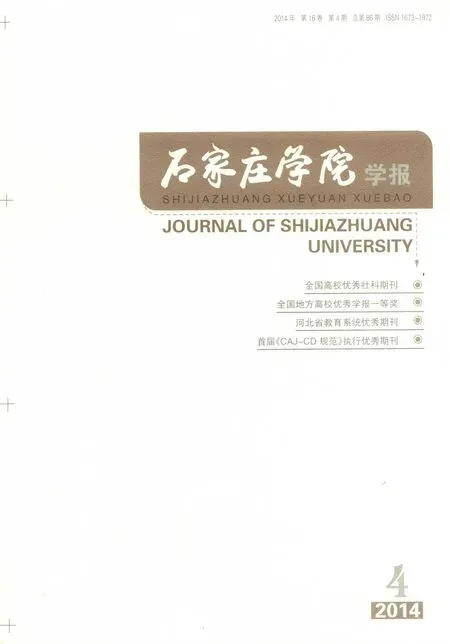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价值观
2014-04-10任晓伟
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价值观
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命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自青年时代起就牢牢确立起了把自身个体生命溶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中的崇高生命价值观。在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受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当他们处在生命价值实现后的人生顶峰,有“名”有“权”时,却又表现出了极度的清醒和冷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理论研究和革命斗争事业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恪守和彰显的生命价值理念,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一个重要支撑。
马克思;恩格斯;生命价值;理论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价值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和推进工人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对自身个体生命价值的全面思考和系统认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不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同时也要不断增强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生史的了解和学习,不断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生命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中去感受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命力量,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命奋斗中去体会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要求 “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作为不断学习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新内容,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命价值观的学习不仅对于进一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有益的,而且对于当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也是重要的。
一、个体小我与人类大我的结合:把个体生命溶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
作为近代以来人类思想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对于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观念形塑作用。一位西方著作家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世界影响时曾说:“对于几代工人来说,马克思是他们获得摆脱贫困和焦虑的具有人性的生活的象征。从《共产党宣言》发出战斗号召开始,工人就追随着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化了工人的阶级意识,鼓舞着他们为政治经济权利而斗争,并指导他们的思想向人性的最高目标发展。对于整个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建立在马克思学说基础上的运动体现出了伟大的文化价值。没有这样一个运动,过去世纪的历史和我们整个的文明都是不可思议的。”[1]157这一评价无疑是客观的,也是深刻的。但是,对于当代的人们来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上的这一地位,在这一问题之下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从个体生命成长的角度去思考,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作出这一伟大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是出身于较富裕的家庭。马克思出身于一个有良好社会地位的家庭,并娶了当时普鲁士贵族大臣之女燕妮为妻。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Heinrich Marx)是当时有名的律师,他曾明确告诉马克思:“我希望你能成为我若是出生在你这么好的条件下可能成为的人。你可能会实现我的最美好的愿望。”[2]128恩格斯出身于一个较富有的商人家庭,但他“在生活道路上完全和家世背道而驰”[3]36。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会选择另外一种充满曲折和跌宕的人生道路?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人类工作,把自己的个体生命溶入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人类历史发展之中,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立下的鸿志和人生担当。在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少数人富有和自由、多数人贫困和不自由的一种社会制度,是不符合人性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应该有一个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被决定的,同时也是被选择的。正是这一人生志愿和生命担当支配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推动着他们为人类的未来而进行艰难的理论研究、政治组织和社会动员工作,由此他们毅然放弃了在旧制度内体面和无忧的生活,把自己的个体生命投入到为改变社会大多数人命运的斗争中。
1835年8月,马克思在即将中学毕业时写的论文中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4]7这里马克思已经表达了支配其一生的献身于人类整体幸福的生命价值观。1837年11月,在大学学习的马克思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围绕着自己的学习情况谈到,“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4]14,15。虽然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尚不明确“新的神”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安置”进去,但是“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表明马克思不满足于既有的知识和教育,试图去对寻求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冲动和朝气。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在青年时代不安于雍容华贵的生活。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讲到自己在曼彻斯特经商的生活时说:“我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最体面的庸人所盼望过上的日子,恬静而舒适、虔诚而正派,成天坐在房间里工作,几乎不出大门一步,就像一个德国人那样规规矩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真担心上帝会无视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5]291845年3月,恩格斯在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则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念:“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6]273这生动地表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不满于现状、献身工人阶级解放和人类进步科学事业的人生取向。
1871年10月21日恩格斯给母亲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对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选择非常重要,也非常典型。恩格斯在信中说:“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30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当事变需要,我就不仅会坚持它,在其他方面也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想必你也没有感到意外。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是我把他引坏了。”[5]366从这封信来看,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人曾互相指责对方把自己的孩子“引坏了”,反映出家人对自己孩子所从事事业的不理解,当然这种不理解其实也是对自己孩子的深刻关爱;第二,面对家人的怀疑,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志向。“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既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眼界和志向已经远远超越了家人,同时也表明了他们一旦选定了自己崇高的人生轨道,把个体小我溶入人类大我,把自身的完美与人类的完美相结合,就始终会坚守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人民群众,但历史的发展在任何时候又深深受到历史伟人成长过程中生命价值追求的影响。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放弃了现实生活的华贵、富足而选择了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进步而工作的生命事业后,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个体生命成长,而是整个占人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命运。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7]89
二、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背后的生命承担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历史伟人,他们的生命都是一个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统一的过程。自然生命是与生俱来的,而价值生命则是社会性的,是在自身自然生命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对整体,即对他人、国家和人类的价值。理论上说,每个人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都以一定的方式完成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统一,但在客观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完成这种统一,因为这个统一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曲折、挫折、痛苦甚至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放弃了对生命价值的追求,选择了回归和安于现状,享受自身的自然生命,有些人则坚持了下来,在经受住种种考验后,用实实在在的成就完成了个体的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统一,完成了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追求,也完成了对人类发展的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生奋斗,无疑是属于后者。他们在完成自己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统一的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困顿和折磨,但也因此表现出来了坚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承担意识。
从马克思个体生命的视角来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背后很大程度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体现出来的高度的生命承担,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有许多材料表明了这一点。比如,1857年12月18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描述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危机问题时的工作状况时说:“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四点钟。”[5]141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不过,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5]143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信中谈到自己决定分册出版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打算时说,这是因为“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仆人。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册出版,那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5]149。1865年5月20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现在像马一样地工作着,因为我必须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时间,痈现在依然存在,尽管它只使我感到局部疼痛,而没有影响脑袋。”[5]228如果这些书信还只是表明了马克思的工作和身体状况,那么在马克思践行自己生命价值的过程中,有远远比工作劳累和健康恶化更折磨、也更使马克思感到挫折的东西,那就是贫困。
19世纪60年代是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发展中最为关键一个时段,但同时也是马克思生活最为顿挫的一个时段。1862年4月28日,马克思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解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迟迟没有出版的原因时说:“至于我的书,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极其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5]180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信中说:“1861年,由于美国内战,我失去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纽约论坛报》。我给这家报纸的撰稿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因此,为了不致使全家真的流落街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从事大量的零星工作。我甚至下决心做一个‘务实的人’,并打算明年年初到一个铁路营业所去做事。但是由于我的字写得不好,没有谋得这个差事,我不知道这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5]196-1971866年2月13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正在完成《资本论》时的心境时说:“昨天我又躺倒了,因为左腰部的毒痈发作了。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厂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5]234上述书信中,马克思所说的“为了不致饿死”“为了不致使全家真的流落街头”“明天被投到剥皮厂上”等等,所反映出来的正是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和实现人类知识革命性变革的过程中生活的困顿和内心深处的艰难。
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自己经济情况时说:“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您知道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 (因为这种事决不能公开)能借给我大约1 000塔勒,利率大约5%或6%,时间至少两年?我现在出20%-50%的利率借小额款项,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无法应对那帮债主,因此我面临着彻底破产的危险。”[5]2451866年时,马克思48岁,时值中年,应正当事业有成、家庭富足之时。但是,马克思却面临着四处举债而不得的生活状态。这是马克思在放弃了旧有的生活并与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为敌后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窘迫,但这也正是马克思生命的崇高之处。此外,这也表明了马克思在实现自己的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的统一中必然要经历的人生发展道路上的挫折、困顿和艰难。1867年4月30日,马克思在写给迈耶尔(Meyer)的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5]253由此来看,一个人,即便是像马克思这样的伟人和巨人,问题的关键也并不在于这些挫折、困顿、艰难本身,而是如何应对它们,是放弃自己的生命价值追求转而寻求一种安逸,还是继续坚韧地推进自己生命价值的实现。“马克思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当代世界以及当代世界思想的许多方面,如果离开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认识,是无法被掌握的。”[8]100而在马克思对于当代世界和人类这一巨大贡献的后面,则是他强有力的生命价值意识和坚强的生命承担。
马克思拥有一切普通人所拥有的一切正常情感,在马克思的“革命执著”的面孔下,人们可以发现很多马克思的“柔情和多愁善感”[9]214。虽然马克思及其家庭备受穷困、疾病的折磨,但正如燕妮所记述的,马克思“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孩子们向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2]174。马克思一生的奋斗史说明,在更大的价值目标前,马克思一次次抑制了普通人正常情感的束缚,以坚强的心性,历经困难和挫折,实现了自身生命的自然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把自己的生命价值献给了更大的整体。马克思对人们生命价值奋斗和追求的启示,也恰恰正是在这里。这一点,在恩格斯的生命史上也表现得非常鲜明。
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一方面表现在恩格斯独立地对许多问题的钻研。比如,在遇到马克思之前,恩格斯就已经完成了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巨著,影响了后来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人生道路的抉择。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领导人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回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自己的影响时说,正是恩格斯这些著作“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本书为我的生活道路奠定了基础”[3]29。在完成这些研究著作的过程中,如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同样经历了许多常人所无法经受的困难。恩格斯的理想是完全献身于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但在1870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他“仿佛过着两重生活。一个星期当中有六天,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他是商人,职务主要是用几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并出入交易所”[3]21。只有到了晚上,“恩格斯摆脱了商业事物的奴役,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这时他就又成为自由人了”[3]22。在这种“双重人”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想像到恩格斯在科学研究中所遇到的和经受的心性上的折磨。如果说,这是一种痛苦的话,那么,另外一种更大的痛苦则是和马克思的关系。德国社会党著名的领导人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在回忆恩格斯时说,恩格斯“同马克思的友谊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同时也是一种秘而不宣的痛苦。他为友谊所做的牺牲真是太多了,甚至最勇敢的人也难以做到这样的牺牲。但是,他自觉自愿、毫不勉强、毫不反悔地服从于更伟大的天才,这比他自己创造最伟大的思想功绩更为光荣。他深知马克思的威力对工人阶级的意义,所以他善于克制自己”[3]216。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恩格斯这一“秘而不宣的痛苦”虽不是由于贫困、疾病导致的,但其实丝毫不亚于因为贫困、疾病所导致的痛苦。在“更大的天才”面前,恩格斯更多地选择了梅林所说的“牺牲”或“克制”,在对马克思的长期帮助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着与马克思不同但却又与马克思密切关联在一起的生命价值。也可以说,马克思是与恩格斯一起以坚强的心性和生命承担意识谱写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生命画卷的底蕴。
三、当马克思恩格斯有“名”有“权”时生命巅峰背后的冷静
人们经常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世界历史的伟大进步,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经受住检验的。但是,这一作用的发挥是逐步被认识到的,逐步被实践所检验的。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10]16。即便是在 《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后,也并没有立即就引起太多的反响,欧洲 “评论界的沉默如尖刀般地刺痛着马克思的心灵”[11]118。但是,真理的光芒是无法被遮蔽住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断深入到工人阶级的同时,其所包含的知识真理也逐渐被当时的知识界所接受和认可,开始不断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仅像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这样在欧洲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对马克思的理论才能和理论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是过去一些马克思理论上的反对者也开始改变了对马克思的态度。比如,俄国19世纪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Aleksandr Herzen),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深刻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重:“要知道,我对马克思党人的种种敌视,都是从巴枯宁那里来的啊。”“这位德国学者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的。”[11]233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断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当时的一些年轻漂亮女孩甚至表达了对马克思的爱意:“要是他仍然年轻,没有那可怕的黑胡子,又不戴着那副难看的眼镜,我会多么地爱他呀!”[11]441
面对学术知名度和社会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生活逐步好转,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保持一种以无产阶级节气为基础的巨大的冷静,虽名而不骄,拒绝歌功颂德,继续坚守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生命价值。1877年11月10日,马克思在给布洛斯(Wilhelm Blos)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恶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5]422-423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在法国,许多年轻的大学生纷纷加入到法国社会党。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针对一些人只会援引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而不作进一步历史研究的情况不止一次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2]691。多年来,人们对于马克思这句名言的含义争论不休,其实,如果深入到马克思的真实内心世界,这句话揭示出来的其实正是马克思不以随者众多而自满、不以名气巨大而自足。对于马克思来说,在扎扎实实的学问中体现出来的科学性是首位的标准,马克思既以此律己,也以此来律人。
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成为了“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7]88。19世纪80年代后,无产阶级运动事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开始普遍建立。在这一基础上,1899年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即 “第二国际”宣告成立,把社会主义事业的运动水平和组织层次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带着遗憾地说:“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13]265在这种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远比马克思更多的直接和普遍的政治影响”[14]4。其实,比起马克思在世时,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的20多年中,不仅更有“名”,而且在具体指导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也更有“权”。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向恩格斯汇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恳求他的建议以及他的权威的认可”[9]219。但是,正是在这一人生的顶峰,恩格斯并没有与马克思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功,相反却多次明确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1884年10月,恩格斯在给贝克尔(Becker)的信中提出了“第二小提琴”的著名论断:“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应该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12]667“第二小提琴”的著名说法,不仅表明了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形成中他和马克思二人之间分工的明确看法,同时也表明了恩格斯内在的谦谦君子品质。
此外,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并没有在理论研究上停顿下来,去享受生活、经营学术和展示成就,而是把内在的谦和转化为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除了不倦地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外,恩格斯还不断地钻研新的问题,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批理论新著,而且还不断根据资本主义和时代发展的新条件反思和修改过去的认识和观点,为自己以及马克思的旧著撰写了10多篇著名的导言,从而使这些著作能够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地时代化。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和政治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新情况的结合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斗争的结合上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与非西方国家历史发展的结合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这些成就,恩格斯却认为不值一提。1893年7月在给梅林的书信中,恩格斯说:“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该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12]725-726在恩格斯这一谦虚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处在人生和事业高峰时对待生命的敬畏和庄重严肃的态度。
1893年2月,施穆伊洛夫(Vladimir Yakovlevich Shmuylov)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祝愿恩格斯能够活到90岁,恩格斯在回信中说:“您友好地祝愿我活90岁,我非常感谢;如果我仍然能够像现在这样,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我的肉体和精神注定要像许多人那样变得呆滞的话,那就敬请原谅,我不能从命了。”[12]720恩格斯在这里鲜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生命以及死亡的科学态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生命价值在于不断思想、不断深入整体价值的实现和不断推进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和历史事业,而不简单地在于延续自然生命。在恩格斯看来,缺失了生命价值的自然生命将是一种无意义的生命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命价值观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个体性历史人物在创建马克思主义和推进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客观上呈现出来的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也是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在献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历史事业的过程中必然恪守的基本人生观念。如同刘少奇所说的,共产党员在马克思主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15]104。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重要支撑,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不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命价值观,把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研究和传播建立在对马克思生命价值观继承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1]Werner Blumenberg.Karl Marx[M].London:Verso,1972.
[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回忆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回忆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Jonathan Wolff.Why Read Marx Toda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9]David Riazanov.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ves and Work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3.
[10]David Mclellan.Introduction[M]//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11][前苏]伽·谢列而里雅柯娃.生命的顶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STEENSON G P.After Marx,Before Lenin[M].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1.
[15]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张 转)
A Study of Marx and Engels’s Views on Life Value
REN Xiao-wei
(School of Politics&Economic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2,China)
Marx and Engels’s views on life valu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arxist theory.Since their youth,Marx and Engels had firmly established the supreme views on life value of integrating their individual life with the liberation cause of proletariat and human kind.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ir life value,they experienced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However,at the pinnacle of their life,becoming famous in academics and politics,Marx and Engels showed great calmness and sobriety.Thei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revolution struggle in their life time fully showed the idea of life value to which Marxists should adhere.This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Marxist truth.
Marx;Engels;life value;theoretical education
A715
A
:1673-1972(2014)04-0033-06
2014-02-15
教育部2012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12JDSZK045)
任晓伟(1974-),男,陕西清涧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和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