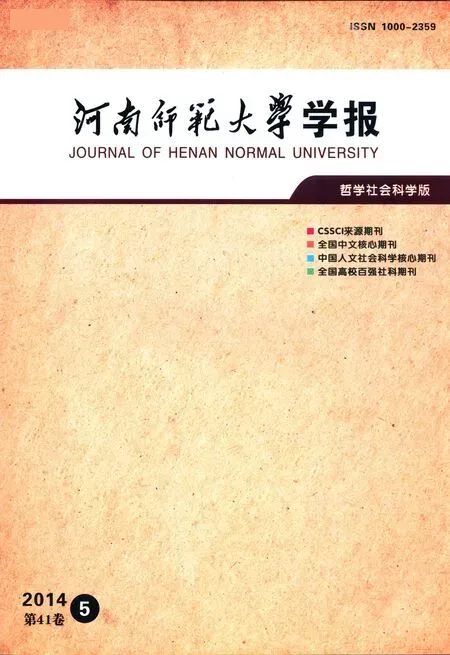宋明理学的五系说——以高攀龙的划分为中心
2014-04-10李卓
李 卓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401120)
宋明理学的分系问题是现代学者讨论的一个焦点。代表性看法有传统的二系说(程朱、陆王)、现代牟宗三的三系说、劳思光的一系说(一系三型说)、四派说(气学、数学、“理学”、心学)、四系说(理、气、心、性)等。明儒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后改字存之,别号景逸)从他对理学史的理解出发,提出了五系的分类,并上溯到孔门弟子和传人,提出了或许是最早的宋明理学分系说。钱士升谓景逸“其论心性理义,如茧丝牛毛,而学脉流派参订最精”[1],即是指此而言。对于景逸(为行文方便,以下均用其别号)的宋明理学分系思想,虽然现代学者已有所讨论,但只是稍带提及,专门的考察尚付阙如。本文以相关论说为考察对象并加以辨析疏释,以期全面呈现他的宋明理学分系思想,为我们理解宋明理学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资源。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学者的主要是从一些基本的哲学观念出发,将宋明理学划分为不同的义理系统。比较而言,景逸的划分在逻辑上就不够严密。景逸关于宋明理学分系的表述集中在他与弟子彦文的一段问答中:
彦文问:“康斋与白沙透悟处孰愈”?
曰:“不如白沙透彻”。
“胡敬斋先生何如”?
曰:“敬斋以敬成性者也”。
“阳明白沙学问何如”?
曰:“不同。阳明与陆子静是孟子一脉。阳明才大于子静,子静心粗于孟子。自古以来,圣贤成就俱有一个脉络:濂溪、明道与颜子一脉;阳明、子静与孟子一脉;横渠、伊川、朱子与曾子一脉;白沙、康节与曾点一脉”。
彦文曰:“敬斋、康斋何如”?
曰:“与尹和靖子夏一脉。”
又问:“子贡何如”?
曰:“阳明亦稍相似”。[2]21
据此,可知景逸于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划分为如下五系:1.周濂溪、程明道,绍承颜子;2.王阳明、陆象山,绍承孟子;3.张横渠、程伊川、朱子,绍承曾子;4.陈白沙、邵康节,绍承曾点;5.胡敬斋、吴康斋、尹和靖,绍承子夏。
景逸这里不同于现代学者的是,他将每一系都上溯至孔门弟子。宋明诸儒于孔门弟子之所推尊,与宋明儒者各自学术有莫大关系,“盖千百世之上下,人心之所契,皆绝无偶然,而若合符节”[3]。尽管这里宋明儒与孔门弟子之间的关联,主要是由景逸所“建构”出来的,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关联。而景逸所论也全非无据,如明道推尊颜子,象山契合孟子等都是明显的事实。
首先,颜子、濂溪、明道一系的特点是高明浑化,“无据而难学”。颜子在圣门最贤,于夫子只差一间未达。不过景逸并不提倡学者学颜子之学。程子云:“孟子才高,学之未可依据,且学颜子。”景逸于此则谓:“颜子才高难学,学者且学曾子有依据。”[2]25“颜子难学”的理由在于颜子个人的气禀清明,根器高而私欲少,一觉即化,直悟本体,学者欲学之而无据。同样,濂溪之学亦无据可依,景逸称赞濂溪说:“先生三代以后之圣人乎!无辙迹可寻,无声臭可即。无极太极,太极无极,是之谓易妙于未画,圣人洗心退藏于密以此。”[4]“无辙迹可寻,无声臭可即”、“未画之易”、“洗心退藏于密”,皆无形象可见,“一点伎俩不形”,都是学之无据之意。这一特点在明道亦然,景逸说:“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5]26明道喜说悟后之语,故其言高明浑化,朱子所谓“明道说话浑沦,煞高,学者难看”[6],便是指此而言。所以颜子一系的特点是“无据而难学”。
此系的另一个特点是直见仁体,见道之全体。景逸称赞颜子说:“箪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约礼是何修持,不迁不贰是何力量,是之谓不违仁。识仁者当识颜子所以为仁。”[4]56认为颜子是学者识仁的典范。对濂溪之学,景逸说:“濂溪主静,主于未发也。”[5]10而在景逸的言说脉络里,未发即是性,是仁体。而明道更是宋明儒中论识仁之大者。景逸说:“泾野先生一生极喜明道,与明道学问极有契合,全是仁体。”[7]又说“彼(吕泾野)教学者,只以安贫改过四字,看来学问除此四字,亦无学问矣”[7]。安贫,即颜子箪食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改过指颜子不贰过。安贫、改过都是颜子直见仁体所至的境界,可见体仁是颜子一系的另一个特征。
其次是孟子、象山阳明一系,景逸划分依据或在这一段文字:
圣学由“知”而入,这“知”字却最关系。学术之大小偏正,都在这里。……所以谓“知”之一字,关系最大,古今学术,于此分岐。何者?除却圣人全知,便分两路去了。一者在人伦庶物、实知实践去;一者在灵明知觉、默识默成去。此两者之分,孟子于夫子微见朕兆,陆子于朱子遂成异同,本朝文清(薛瑄)、文成便是两样。[8]30
景逸以“知”之一字的不同将古今学术划分为虚实两路,虚者致力于灵明知觉、默识默成。“虚学”微肇于孟子,后继以象山、阳明。不过景逸只是说孟子开其端绪,他的批评更多集中在象山和阳明,如说:“一向不知阳明、象山学问来历,前在舟中似窥见其一斑。二先生学问,俱是从致知入,圣学须从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虚灵知觉虽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知岂有二?有不致之知也,毫厘之差在此。”[2]25又说:“陆氏之学,从是非之心透入性地,不可谓不是,然而与佛氏以觉为性者相近,阳明良知之学,亦是如此。一边是仁体,一边是知体,仁统四端,而知不能兼仁,故仁者无不觉,而觉不可以名仁,源头处杪忽差殊耳。”[9]3这都是说孟子一系重知,但致知不由格物,在源头处即有差失。此外,景逸不将子思列入此一系之中,应该不是以子思、孟子为一派而有意略去,更可能是子思并不符合“虚学”的标准。
再次是曾子、横渠、伊川、朱子一系。曾子之学的特点是遵从絜矩之道,下学而上达,悟后便是一贯,便是上达天德。景逸说:“如曾子一生用力忠恕,唯前如此,唯后亦如此。但唯前之忠恕,与唯后之忠恕,天人之隔,霄壤不侔耳。”[8]37又赞曾子说:“一贯者,子之悟道也。大学者,子之传道也。絜矩又何不贯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为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贯之矣。”[4]56曾子戒慎恐惧的道德意识甚强,一生战战兢兢,“临深渊,履薄冰”,“易箦”时仍不肯苟且违礼,所以景逸说:“曾子当启手足时,一个身子完完全全,洁洁净净,如精金百炼,如白璧无瑕。此时方了得修身为本四字。”[5]21这一系的特征是注重下学上达,先有格物致知之功,而后言一贯之道,所表现的道德严肃感最强。横渠主张穷神知化、尽性至命,与之相近,所以也归入这一系。
第四系是曾点、邵康节、陈白沙一脉。景逸罕言曾点,不过“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气象”,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理学话题,可以说代表一种自然和乐的狂者胸次(如阳明诗句“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朱子谓“曾点不可学”,因为“点自是一种天资,不可学也”①“曾参曾点父子两人绝不类。曾子随事上做,细微曲折,做得极烂熟了,才得圣人指拨,一悟即了当。点则不然,合下便见得如此,却不曾从事曲折工夫。所以圣人但说‘吾与点’而已;若传道,则还曾子也。学者须是如曾子做工夫,点自是一种天资,不可学也。伊川说‘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点则行不掩,开见此个大意了,又却要补填满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见之。此与一贯两处是大节目,当时时经心始得”。朱熹:《朱子语类》,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34页。,“今人若要学他,便会狂妄了”②“某尝说,曾皙不可学。他是偶然见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时被他说得恁地也快活人,故与之。今人若要学他,便会狂妄了”。朱熹:《朱子语类》,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32页。,牟宗三也说:“其不可学倒不在那一时的‘风乎舞雩’,根本是在不可把学问(实践的工夫)当做四时景致来玩弄”[10]236。在景逸看来,康节即有曾点的“舞雩之趣”,同样也有玩弄光景之义,“遗书”载:
彦文曰:“明道许康节内圣外王之学,何以后儒论学,只说程朱”?
先生曰:“伊川言之矣。康节如空中楼阁,他天资高,胸中无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2]25
不过景逸对康节本人有“精微”的评价,他说:“二程中正,康节精微,要知康节之学与圣人少差一线,圣人便不如此。康节从图南一脉来,有些仙气。尝观与伊川论雷从何处起,伊川云起处起,康节便要知其起于某方某向,多此一算。故明道云康节欲将传与某,某兄弟那有此闲功夫。然康节之学是洁净精微,又不可以数学拟之……”[7]景逸于白沙所论不多,认为“盖白沙于性地上穷研极究,以臻一旦豁然”[9]47。
后来黄梨洲也有将曾点、康节、白沙引为同调的讲法,如他说白沙之学“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此可无疑者也”[11]80。又说:“盖自夫子川上一叹,已将天理流行之体,一日迸出。曾点见之而为暮春,康节见之而为元会运世。故言学不至於乐,不可谓之乐。至明而为白沙之藤蓑,心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处最难理会,稍差便入狂荡一路。所以朱子言曾点不可学,明道说康节豪傑之士,根本不贴地,白沙亦有说梦之戒。细详先生(王东崖)之学,未免犹在光景作活计也。”[11]719大略不出景逸所论的范围。唐君毅先生认为慈湖、白沙之学相近,指出:“慈湖之学与白沙之学,皆有自得之乐,言不起意,与静中养端倪之工夫,亦有鞭辟近里之义。然皆高明之趣多,而艰难之感少,其言皆不足以励学者之志,而不宜于立教。”[12]可以说这一论断也适用于景逸所言的曾点一系。
最后是子夏、尹和靖、胡敬斋、吴康斋一脉。景逸比较子张和子夏之学说:“子张之学是阔大的,于细密处有不足焉;子夏之学是谨细的,于阔大处有不足焉,二贤正相反。”[8]26他认为子夏一系的特点是谨细,谨细即“敬而无失”之谓。子夏答司马牛有言:“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而尹和靖、胡敬斋、吴康斋三人皆重主敬工夫。尹和靖的主敬之法是“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他说:“敬有甚形影,只收敛身心,便是主一。”[13]胡居仁也谓“端庄整肃、严威俨恪是敬之入头处;提撕唤醒是敬之接续处;主一无适、湛然纯一是敬之无间断处;惺惺不昧、精明不乱是敬之效验处”[14]。不难发现,二人的观点非常相似,而景逸对胡敬斋之学的评价是“敬斋以敬成性者也”[2]21。
有人认为康斋不及白沙透悟,景逸答道:“盖白沙于性地上穷研极究,以臻一旦豁然。康斋只是行谊洁修,心境静药,如享现成家当者,快乐受用而已。然其日渐月磨,私欲净尽,原与豁然者一般。即敬轩先生,亦不见作此样工夫,至其易箦之诗谓‘此心惟觉性天通’,原是此样境界,不可谓其不悟。”[9]47-48这是说康斋以渐修工夫同样至于透悟之境。
总之,颜子一系高明浑化;孟子所开为心学一脉;曾子一系重下学上达而一贯;曾点传统属狂者胸次;子夏一系以敬成性。景逸于五系当中有所轩轾,在他看来,颜子与曾子为儒学正统最主要的两系。如说:“孔子以下曰颜、曾、思、孟,孟子而后曰周、程、张、朱,却象配定一股,非偶然也。”[7]又说:“孔门之学,以求仁为宗,颜、曾、思、孟之后,惟周、程、张、朱之传为的。”[9]3这都是以前面所说的颜子、濂溪、明道一系和曾子、横渠、伊川、朱子一系为孔门正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景逸这里特别提到了孟子,却不言孟子一系的象山、阳明。正是出于前面所说的“致知不在格物”而其学“虚”。在宋明儒中,“周、程、张、朱是为天地干蛊之人,白沙、康节是享现成家当者。若其间最苦心竭力者,又莫过朱夫子,于世上无一事不理会过”[2]24。
象山、阳明一系的流弊自不待言,即以朱、陆二先生为例,景逸便认为象山之学有粗处而逊于朱子。他说:“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即宋之朱、陆两先生这样大儒,也各有不同。陆子之学是直截从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处。朱子却确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为教,使人人以渐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陆子将《太极图》、《通书》及《西铭》俱不信,便是他心粗处。朱子将诸书表章出来,由今观之,真可续六经,这便是陆子不如朱子处。”[2]22
对于正统的两系,从立教的角度而言,应该说景逸更推重曾子一系。其理由便是前面提到的“颜子才高难学,学者且学曾子有依据”。总的来看,颜子一系属于儒学传统中的上根之人。景逸解释“仁者先难而后获”时说:“颜子克己,若红炉点雪,不必言难。‘天下归仁’,反从获上说。樊迟根器大不同,故曰‘先难后获’。”[2]19就是说颜子为上乘根器,气禀清明,合下即化,无须种种对治工夫,故不必言难。阳明年谱记地藏洞异人“惊曰:‘路险何得至此’!因论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15]1225阳明谓“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15]118,同是此义。所以景逸对明道推崇备至,甚至感叹:“明道先生三代后圣人也,诸葛武侯三代后伊吕也。”[16]“明道先生真亚圣也”[7]。颜子一系为学工夫的特点是在心地上用功,高明易简,因此杨慈湖、王龙溪等重视先天正心的学者都特别推尊颜子。而景逸最尊朱子,他自己就是以朱子为宗,所谓“辱教展《朱子节要》,知龙之学以朱子为宗。龙何能宗朱子?殆有志焉”[17]。两系相较,应该说以曾子一系立教,更为稳健而无弊。
景逸判释宋明理学的五系,并不够十分的明晰和严密,他也并未措意于此。这是因为他始终从工夫进路之差异的视角出发,着眼于兴学立教,以期敦风化俗,转移世运。而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现代学者,则主要以理气心性等本体论的范畴来划分。两者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1]钱士升.忠宪高公神道碑铭.高子遗书(附录)[M].明崇祯五年刻本.
[2]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五[M].明崇祯五年刻本.
[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91.
[4]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M].明崇祯五年刻本.
[5]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M].明崇祯五年刻本.
[6]朱熹.朱子语类:卷九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58.
[7]高攀龙.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M].清雍正刻本.
[8]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四[M].明崇祯五年刻本.
[9]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上[M].明崇祯五年刻本.
[10]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牟宗三先生全集:卷29.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2003.
[11]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80.
[13]尹焞.和靖集:卷七《师说下》[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40.
[14]胡居仁.居业录:卷二[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
[15]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6]高攀龙.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M].清雍正刻本.
[17]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下[M].明崇祯五年刻本: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