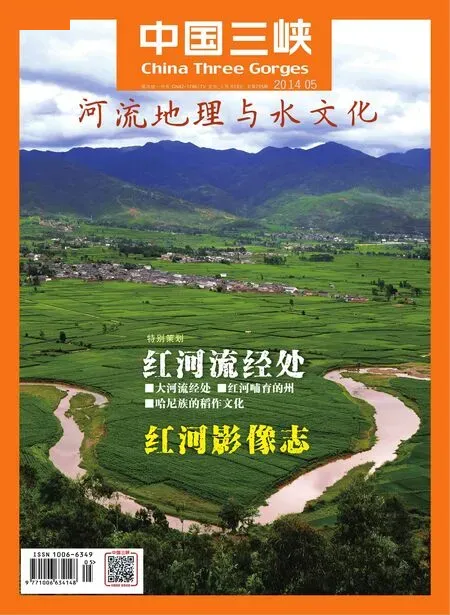柴 房
2014-04-10
柴 房
文/贾生奎 编辑/罗婧奇

多年前,我老家两层野墅后边暗暗猫着间柴房,它在我近二十年的记忆里难以磨灭的印象是古老、温暖、顽强而又孤独。
起初它在我颇记事时就已经是一副破旧的样子。陈旧的砖,陈旧的瓦,黑不溜秋腐朽的房梁总是挂满蛛网,还有两扇不像样的小窗上不完整的玻璃总是模糊灰暗,窗棱隐约看得清斑驳的红漆,窗台上厚厚的灰尘彰显着它久无人打理的惨淡光景。那老式的木门低矮狭窄,却有两块门板,门板转轴已腐朽得岌岌可危,只能像对待老人一样对待它,稍加粗鲁那门板就会掉下来。不过我很早就知道怎样将它取下来、装上去。门底下还有道老式的门槛,对我来说可有好处,矮矮平平的就像小板凳,坐上去正好。
这柴房是有历史的了。据说是我爷爷或更远一辈住房的残留部分,后来父亲盖了新房,它便成了厨房兼柴房。里间放柴,外间有个小灶,小时候我吃的香喷喷的饭菜皆出自那小灶。大概是灶的构造不合理,柴烟老是排不出去,而总是往屋里漫。这可苦了我啊,因为一向我是“火夫”,我的工作就是坐在火膛口,不时往里添柴,保证火不熄。我一直想,这灶太小了,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灶。
现在想来,那灶是令人温暖的。虽然我在它背后吃了不少苦,流过不少泪,但时间总会因人的本能过滤掉不愉的记忆,将那些已逝的幸福收集。小灶煮出的饭和锅巴粥是如今即便是五星大酒店都无处找寻的美味。最开心的期待是每逢过年,母亲用小灶上的这口大锅炸出的藕夹、鱼夹、豆果等各类腊月小吃。不仅小灶,整个柴房都若我的天堂般,总让我倍感温暖,尽管它是那样矮小阴暗。就像它里边唯一的电器——那盏吊在半空中的15瓦的白炽灯一样,虽然落后陈旧,但那橘黄色的暗光自然散发着一种足以渗入心底的暖流。在陈旧的历史背后,我觉得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藏有我期待的事物,有些是我自己藏的,有些不知从何而来。我将心爱的书和玩具放在一个木箱子里藏在角落。门的后面,我把自己做的许多木剑竖在那儿,混杂在锄头、扁担、铁锹等农用工具间,还有我的小钢锯、锤子之类的工具也挤在墙角。另些角落,立着我的鱼竿、鱼叉,还清清楚楚记得渔具放在一个鞋盒子里藏在某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地方。诸如此类的小玩意儿现在也道不清了,当初我常常坐在门口那道槛上摆弄它们。
里间空间基本被柴垛占领,占了大半个屋子的柴垛垒得高高的,里面蕴藏似乎更加丰富。我不会忘记墙边靠着的那辆20寸的小自行车,简单漂亮的样式,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墙上挂着我自制的弓箭,是我引以为傲的作品。我的猫喜欢在柴垛里睡大觉,轻唤一声,它便立即刺溜爬出来,竖起尾巴“喵”的一声凑到我脚边。柴房总是充满善意的,经常也会有别家的猫从窗户溜进来睡觉,它们都跟我挺熟,一点也不惧我。有一回,有只别家的猫在里面下了一窝崽子,柴房温暖融融,我有一阵子不敢进入里间,生怕惊扰了它们母子。还有我家养的鸡经常躲进来下蛋,偶然一次我进去取柴把子时发现了,四五只蛋挤在被老母鸡压得平整的小窝里,让我着实惊喜了一番。至此以后,我会常常去瞧瞧小窝,有蛋的话便悄悄捧回家,老母鸡似乎毫不知晓,一如既往在里边下蛋,还以为骗过了我们。诸如此类的“新大陆”在那样一个幽闭的狭窄空间里,也在一个孩童的幼小心灵里一次又一次地绽放,充实着那个贫乏缓慢的年代。
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独立支配的空间,我有一间柴房,因而我的世界变得宽广。我一个人默默布置着、丰富着自己的世界,默默地与它分享喜悦、忧伤和孤独。那时我经常会自豪地邀许多小伙伴来玩儿,他们自然十分乐意。我们会坐在门槛及周围闲侃、分享故事,会在柴房里外玩捉迷藏,在小灶里烧几个柴把烤红薯……
那时候的我不知道,有一天,这种时光会断然从我生命中消失。我不知道,童年时光在老柴房的屋檐下渐渐流逝,就像落日的余辉缓缓悠悠地将灿烂的阴影投射到房子的古色陈瓦上,带着些许幸福,些许遗憾,沉积下去。年轮无情地在一个成长的生命和古老衰败的摇篮间拉开了越来越宽的鸿沟。
我慢慢长大。陈旧的柴房经过多次狂风暴雨的打击几乎要垮塌,屋角的瓦被掀去一片,秃了顶似的,一条深深的裂缝醒目地从烟囱口弯曲下来……没有人愿意管它,其实除了我,老柴房甚至很少有人光顾,因为后来用上了煤炭炉、煤气灶,柴火灶不用了,柴房基本闲置,成了堆积破烂杂物的地方,里边乱七八糟的物什叫人不愿意踏进半步。
等我离开家去了城里、继而去了外地读书,无人光顾的老柴房便静静沉睡了。门窗更加腐锈,台阶砖缝间爬黏着青苔,残网老灰堆满窗台和灶台,里间的柴垛早已经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潮湿的冷酷的煤球。在聚少离多的偶然探视与回首间,它骤然老矣,一股衰败荒凉的气息,一种让人扶都扶不起的感觉,使我黯然又孤独。尽管如此,在周围的乡村野墅越来越漂亮,在故乡的面貌被推土机拔山平湖,在日新月异的岁月里,它始终在风雨阳光中撑立不倒,静静地沉睡。
虽然基本闲置了,但总不能放任不管,后来有一天,父亲在装修房子的时候,顺便也将老柴房修葺了一番。随着我的童真伴着老柴房在记忆中褪去,柴房已是面目全非。我不再是那个狭窄世界的孩子,进门都要低头跨过门槛,也再找不着自己原先存放的一些小玩意。经修葺后,柴房顶上那些黝黑片瓦全都换成了土黄厚实的瓦,黑不溜秋的腐朽的梁木也换成了粗大全新木,这些改变使柴房看起来崭新稳固得多。但这时,它似乎对任何人都不再有用了。再面对它时,虽没有童话般天真热爱之情,但总有种特殊感觉从心底暖暖升起,并且随着时间的久远,我日渐需要它在我的记忆里跟我讲述那些远去的故事,重温再也体会不到的温暖。有时我会怀疑那些画面存在的真实性,在走过天南地北,无数新陈代谢之后,我遗憾已找不到来时的路。
某天,一条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京曾经的居住房被一夜拆毁的新闻震惊网络,有人痛心,有人谴责,而我的内心没有半点波澜,一如听到老家要拆迁的消息时的平静。毁了就是毁了,愤慨等情绪除了助长我们内心的麻木与无助感,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努力想要铭记的,总有一天终会无可挽回地忘却。现在看来无比重要的事物,很快就连旧闻都不是。能做的,就是心里存着那间孕育过包括我在内无数生灵的柴房,承诺此时此刻埋藏在心,用这样一篇文章诉一诉说一说。
很久都没有回去了。我的世界延伸到了很远之外,一路漂泊,再无需柴房那样固定狭小的空间。直到它被拆毁的那一刻我亦没有亲眼见到。我不知道假若当时我在家,眼睁睁看着它被夷为平地会是怎样的感受。我想,没有看到最好,这样我就会一直觉得,我的柴房,连同我的故乡,土生土长的一切,依然静静地存在,待外面的世界有一天突然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