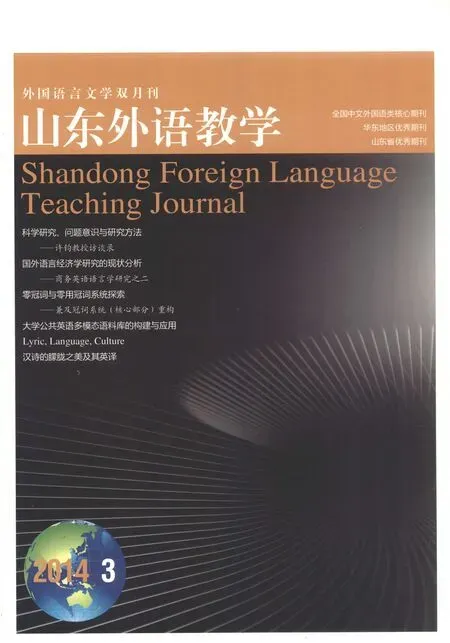族裔性对美国华裔文学接受的影响
2014-04-09刘增美陈华
刘增美,陈华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族裔性对美国华裔文学接受的影响
刘增美,陈华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族裔文学是相对主流文学而言的,族裔性作为族裔文学的根本属性是一种“差异”符号,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具有双重影响,它可以促进族裔文学的接受,也可以导致族裔文学的独白。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的接受是伴随着“族裔性”减弱而进行的,而华裔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却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彰显了华裔文学的族裔性。尽管我国学者的“中国文化情结”深化了华裔文学的研究,但对的族裔性的过分关注却限制了华裔文学接受范围的扩大,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美国华裔文学;族裔性;接受;影响
外国文学的接受研究早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学界更加聚焦的是国外主流文学的接受,而较少探讨非主流文学的接受。在美国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关心福克纳、海明威等美国文学经典作家的创作及其接受研究,而当代美国华裔文学虽已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对其接受研究的研究仍比较缺乏。
美国华裔文学诞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华裔文学不仅得到美国读者和学者的关注,走进了学校课堂和主流文学选集,成为学术研究的内容,在国际上也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在中国更是出现了一个接受高潮,这与华裔文学的独特性——族裔性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族裔性是华裔文学的立命之本,但作为差异符号却具有两面性,它可以促进华裔文学的接受,也会阻隔其与主流文学的对话,影响其更大范围的传播。作为族裔文学,华裔文学在美国的接受是一个族裔性与美国性不断对话的过程,族裔性的减弱不仅有助于华裔文学接受范围的扩大,也能促进华裔文学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然而,华裔文学在我国的接受却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特点,这与中国学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研究理论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确,中国学者的文化视角深化了华裔文学的族裔性研究,但对族裔性的特别关注对接受具有引导作用,族裔性强的作品得到更多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接受内容的相对集中。探讨族裔性对华裔文学接受的影响,比较华裔文学在国内外接受上的不同,有助于我们思考华裔文学在我国接受过程中存在的偏颇,对其他族裔文学在其母国文化语境中的接受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0 族裔性:族裔文学接受的双刃剑
族裔往往与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君主制时代,种族与“血统”相关,“血统”是否纯正是衡量人们出身的重要标准。在19世纪人种被看作是一种生物群体单位,受遗传因素影响,并被划分为优劣等不同级别。进入20世纪这些看似科学的概念开始遭到质疑。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 illiams)明确指出:种族“一直被用来贬抑非我族类的不同群体”,并“产生负面影响”。(威廉斯,2005: 378)亚当·库柏(Adam Kupper)认为“种族”是“‘霸权文化'强加给别人的他的规则,使得别人因为不同而受诬蔑”(Kupper,2004),而霸权文化通常是指欧裔白人的、中产阶级的、男性的和异性恋的,揭示出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种族歧视本质。种族理论也成为帝国主义向外扩张殖民的借口,但在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K.Bhabha)看来,“殖民主义话语”常以“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一话语策略”来虚构和歪曲事实,如“关于亚洲人欺骗成性和非洲人禽兽般的性行为的话语就从来没有被真正地证实过”。(黄怀军,2007:297)显然,“种族”概念是人为建构的结果、是白人霸权文化强加给他人的产物,是对少数族裔群体、特别是有色人种的歧视。为了颠覆霸权文化的种族偏见、解构“刻板印象”,“族裔”一词逐渐用来取代“种族”。
“族裔”最初是一社会学概念,“是与种族与阶级相对的”。(Sander,1998:19)美国社会学家施墨恩指出,族裔是指“一个有着真实或假设的共同祖先,有共同的被分离的和被命名的群体意识;拥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的族群的文化象征物”。(廖炳惠,2003:222)“族裔”突出的是族群的共同点,与族群的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族裔是与WASP,即信奉新教的欧裔白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相对的,是少数族裔群体建构身份自我命名的一种手段。
族裔性作为一个批评术语进入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是与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批判性相关。作为族裔群体的独特品格,族裔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差异”符号,是后现代批判精神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它可以促使研究者对文学文本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差异”进行反思。(王晓路,2002:64)但“差异”作为身份建构的基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忽视“差异”则会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则意味着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如果过分突出“差异”,则与族裔群体建构共同身份的旨趣相违背,建立在“解构”基础上的身份面临被解构的困境。对“差异”认识的不同形成了两种身份研究方式。一种观点着眼于同质,认为文化身份指涉“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能够反映一个种族和民族的“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突出了族群身份的整一性和稳定性。另一种观点则着眼于异质,认为文化身份“不是固定的本质”,而是由一些“深刻的和重要的差异点”构成的“真正的现在的我们”,强调身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黄怀军,2007: 296)前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而后者采用的是解构主义的认识论。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实则反映了少数族裔文学在族裔性建构过程中遭遇的矛盾困境。如果突出族群内部的差异性,则不可能建立起整一的族裔身份;但如果无视族裔群体内部的差异,则意味着失去建立身份赖以存在的方法论基础——差异。可以说,族裔性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差异性。在华裔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在初期,族裔性更多的表现族裔群体的共同性,但随着华裔文学的发展,其族裔性则呈现多样性。
美国华裔文学的接受有其特殊的社会语境。作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之一,华人群体曾为美国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美国历史上,华人却长期处于“无声”状态。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促进了少数族裔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批亚裔知识分子首先带头在文学和政治领域发起抗争,他们通过挖掘、整理亚裔作家的写作,并结集出版,旨在建构亚裔之美国身份、解构“刻板印象”、重塑亚裔历史。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要在美国多元文化中寻得一片立足之地,凸显华裔文学的族裔性无疑是集群体之力、发出最强、最大声音的有效策略。
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主要表现在作家的“华裔感性”(Chinese American Sensibility)和作品描写的“华裔美国经历”,突出了华裔群体“差异”的共同性,并成为界定华裔文学的标准。1976年陈耀光 (Jeffrey)等合编的《啊咦!美国亚裔作家文集》(以下简称《啊咦!》)(1991)被《党派评论》比作“美国华/亚裔文艺复兴的宣言”。该选集的编辑之一、著名的华裔文学作家和评论家赵健秀依据“华裔感性”将华裔作家分为“真伪”两种,认为只有站在华裔群体内部,书写该群体的历史或经历的作家,才是真正的华裔作家;而站立在族裔群体外部,作为外人(outsiders)进行创作的作家是“伪”华裔作家。“内”“外”之分突出了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对立和差异。在内容方面,《啊咦!》选集收录的作品主要以传记和写实小说为主。族裔性的突显也表现在最早的亚裔文学批评著作《美国亚裔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中,该书作者也突出了亚裔群体共同的“美国经历”的重要性。的确,在华裔文学发展初期,亚裔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对族裔性的重视不仅有助于激发华裔群体的身份意识,建构华裔同盟,也有助于引起读者和学界的关注,获得认可。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早期学者为突显华裔文学的独特品格,对“族裔性”做的种种限定反过来对华裔文学的接受具有反作用。建立起身份后的华裔文学在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随着创作的发展,华裔文学内部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族裔身份不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如果过分突出差异性,一部分族裔性较弱的作品则会被排除在华裔文学之外,如《啊咦!》选集曾把黄玉雪、汤亭亭等人的作品排除在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这样做似乎保持了华裔文学的纯洁性,但却不利于华裔文学的多样化发展。长此以往,华裔文学将陷入尴尬的“独白”境地。只有将华裔文学的独特性融入美国文学传统中,华裔文学才能摆脱其边缘地位,走向中心。因此,华裔文学在美国的接受也是一个族裔性建构并不断超越的过程。
2.0 族裔性的超越:华裔文学接受的美国化
作为族裔文学,华裔文学要确立自己的身份,是以凸显其族裔性开始的。但是要获得读者和学界的认可,却首先要经历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人们往往将华裔文学被收录进主流文学选集看作华裔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将此看作华裔文学在接受方面取得的成功,这说明文学性或艺术性并非仅是主流文学的评价标准,也是衡量族裔文学的重要标尺。因此,华裔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作品的族裔性表现为一个由强渐弱的过程,这是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不断互动对话的结果,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必然。
华裔文学族裔性的强弱对接受有很大影响,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受读者期待视野的限制。《女勇士》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被收录进多部主流文学选集,将华裔文学带进千家万户,标志着华裔文学接受的第一高峰,这与当时的接受语境密切相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众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特别是电影对中国武术的演绎引发了美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非常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可谓恰逢其时,当然,女权运动对其接受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汤亭亭打破了早期学者对华裔文学族裔性的界定,对中国文化做了“美国化”的改写,曾遭到赵健秀等学者的强烈批评,但却满足了美国读者的期待视野。试想一下,如果汤亭亭不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故事进行改写,《女勇士》是否还会得到美国普通读者和世界各国读者的认可?其艺术性是否还能达到如此高度?尽管这样的假设似乎并不成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家在作品中描写的花木兰和岳飞等形象并非是为了忠实地传播中国文化,而是为作家的艺术创作服务的,因为一部作品的艺术性越高,越能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抵达更多读者,成为经典。
族裔作家的创作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族裔性表现,并对接受产生很大影响。人们通常认为族裔作家应该担负起一种社会责任,他们被看作是族裔群体的“代言人”。但很多族裔作家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是艺术创造。尽管不同作家对族裔性的解读不同,表现迥异,但无论是赵健秀、汤亭亭、谭恩美还是移民作家哈金,他们都把自己看作是美国作家,他们的目标是要创作出大写的“美国文学”,因此,他们对族裔性的描写不是为了表现华裔群体的差异性,而是借华裔文学的“族裔性”表现出这一文学独特的艺术性。回顾华裔文学的接受历程,不难发现,能够成为华裔文学经典、收录进美国主流文学选集的作品并非单纯描写华裔群体生活的写实性作品,而是族裔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作品。《女勇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论在文类上、还是内容上《女勇士》都超越了早期华裔学者对华裔文学的界定,该作品以传记形式出版,被看作继承的是“西方的传统”,背离了中国文化传统,曾被排斥在美国华裔文学选集之外,并引发了关于族裔性的争论。但作家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故事的有意背离和改写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的美国化”过程,不仅拓宽了华裔文学的生存空间,也创新了华裔文学的艺术形式,促进了华裔文学更快更广的传播。
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的接受是伴随着作品族裔性的减弱而发展的。以汤亭亭的创作为例,《孙行者》是作者继《女勇士》和《中国佬》后的第三部作品,与前两部作品相比族裔性明显减弱。但1998年修订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将《孙行者》收录其中,而不是其他作品。众所周知,《诺顿美国文学选集》致力于表现主流文学思想史,能够反映主流学者的审美旨趣。如编辑所言,此次修订的目是为了“表现50多年来在散文方面的各种变化,重点放在族裔多样性与实验写作方面”。(Baym,1998:xxx)作为一部后现代小说,汤亭亭运用戏仿、拼贴和语言游戏等后现代艺术手法,表现当代美国文化语境中族裔身份建构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该作品不仅满足了主流文学对族裔多样性的要求,而且在艺术创新方面具有引领作用。尽管时代更迭转换,评价标准趋向多元,但艺术性仍是评判作品优劣的最重要的标准,华裔文学要抵达更多读者,不能完全脱离主流文学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族裔性的表现不是目的,而是为文学性诉求服务的。
族裔性的减弱还表现在其他作家的创作中。例如谭恩美的近作《拯救落水之鱼》与其早期作品相比,族裔性已明显减弱。在年轻一代华裔作家的创作中,这一倾向表现更为明显。如任璧莲、雷祖威、黄哲伦等年轻一代代表作家,他们出生、成长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教育,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除了父母的口口相传,更多地来自学校教材和大众传播工具。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形式创新方面,都与早期华裔文学大不相同,他们关注的是年轻华裔群体或者说少数族裔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他们常常有意模糊作品主人公的族裔背景,淡化族裔色彩;在形式上也不再拘泥于写实性作品和传记,小说、戏剧、诗歌等创作形式越来越多。但需说明的是,尽管华裔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族裔性表现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表现方式更加多样。
当然,也有华裔作家并不描写族裔内容。如苔丝·格里森(Tess Gerritsen)创作了近20部小说作品,作品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汉语在国内出版。尽管苔丝·格里森本人及部分主流文学学者将苔丝·格里森看作是一名华裔作家,认为“描写非族裔内容……是一种突破”(Sander,1998:22),但由于其作品没有描写美国经历,也没有表现华裔情感,她的创作不被看作是华裔文学,也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这也说明,族裔性作为华裔文学的独特性,其表现形式可以多样,但不会消失,因为缺乏族裔性的作品不能算作华裔文学,只有族裔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作品才能成为华裔文学的经典,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
3.0 族裔性的突显:华裔文学接受的中国化
华裔文学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激发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华裔文学在我国的接受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外国文学杂志登载的关于华、亚裔文学介绍性文章。自90年代开始,美国华裔文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理论的发展为这一新型的文学形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华裔文学研究渐成风尚,逐渐形成以吴冰、张子清和饶芃子等老一代学者为领军人物的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同时,以华、亚裔文学为题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等研究中心的成立、华裔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版等都进一步促进了华裔文学在我国的接受。华裔文学研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并形成一股研究热潮,涌现出一大批华裔文学学者和爱好者,以华裔文学为题的研究成果也逐年增多,甚至成几何倍数增长。据北外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资料显示,自1999年至2009年间,以美国华裔文学为研究内容的博士论文有30篇,至2012年,国内出版批评华裔文学教材、研究专著、访谈录等多达30余部,发展速度惊人。
与华裔文学在美国接受的“美国化”不同,华裔文学在我国的接受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特点。受西方后现代理论影响,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受到冲击,文化研究则异军突起,华裔文学成为理论实践的试验田。而中国学者独特的文化背景为华裔文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保障,文化身份研究成为热点。研究者不仅从中国文化视角评判华裔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也重视中国文学传统在华裔文学中延伸或变迁。特别突出中国文学与文化对华裔文学的影响。在2007年之前国内出版的12部批评著作中①,有10部作品将其中的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有研究者将美国华裔文学看作“跨文化的中国叙事”(高鸿,2005)或“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卫景宜,2001);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华裔文学与大陆新文学传统具有相同的文学品格和文化特质”。(胡勇,2003)甚至有学者建议将华裔文学与华文文学归并在一起,统称为华文文学。有研究者将水仙花、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等华裔作家与聂华苓、严歌苓等华文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女性作家建立的女性写作传统是“中国文学延伸到异域的一道彩虹”。(肖薇,2005)在这些研究中,中国学者更倾向于探究中国文化或文学对华裔文学的影响,以此建构华裔文学自身的文学传统。可以说,中国学者的这些研究进一步凸显了华裔文学的族裔性,也引导了华裔文学接受的倾向,即族裔性强的作品得到更多关注。的确,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视角丰富和深化了华裔文学的解读,但同时也造成了接受内容的相对集中。
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情结”突出了对华裔文学“族裔性”的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对华裔文学独立身份的重视。在美国,美国华裔文学的接受基本上是在亚裔文学研究的框架内,是与日裔文学、韩裔文学、菲律宾裔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华裔文学往往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进行的。当然这与华裔文学在早期亚裔文学中的地位有一定的关系。在早期,华裔文学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在亚裔文学中都占据很大的优势;在早期研究者中,华裔学者也占了很大比例;在研究方法上,为了突出华、亚裔文学身份的整一性,研究多采取“整体化”(totalizing)策略。因此,早期华裔文学研究与亚裔文学研究基本保持同步。但随着亚裔文学版图的扩大,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亚裔文学的疆界已拓展到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菲律宾裔、越南裔以及印度裔作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华裔文学在亚裔文学中的“中心”地位已被多个“中心”取代,美国华裔文学与亚裔文学研究不再保持同步。但从当前华裔文学在我国的接受看,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情结进一步突出了华裔文学的族裔性特点,但这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华裔文学的文学性诉求,不仅造成了研究内容的相对集中,也造成了研究范式的相对单一。相对忽视了年轻一代华裔作家的创作,而哈金等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的确,近几年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在我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对具体作家的研究更加深入。如方红的《华裔经验与阈界艺术——汤亭亭小说研究》探讨表意手法与阈界艺术在作品中的运用,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2007)。吴冰与王立礼主编的《华裔美国作家研究》是国家社科项目成果,在作家研究方面堪称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华裔文学研究进入一个理论建构和反思阶段,如张琼的《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体反思》将华裔文学置于美国文学背景下讨论其艺术性(2009)。刘葵兰的《变换的边界:亚裔美国作家和批评家访谈录》则通过对作家和批评家的访谈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2012)。此外,以美国华裔文学为题的研究项目也逐渐增多,如蒲若茜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亚裔美国文学批评范式与理论关键词研究”,笔者2011年教育部课题“族裔性与文学性的融合——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等致力于华裔文学理论建构和批评研究。但研究的深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内容相对集中的偏颇,应该引起重视。
4.0 结语
如其它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一样,华裔文学的族裔性是其有别于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其身份符号,但族裔性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促进华裔文学的接受,但过分突显族裔性则会切断与主流文学的对话,影响其更大范围的传播。与美国主流文学在我国的接受不同,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在我国的接受是一个“华裔文学的美国化和华裔文学的中国化”的过程,这里存在着华裔文学与主流文学融合及跨文化接受的问题。作为多元文化的产物,美国华裔文学是在美国文学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族裔性不可能脱离美国文学的普遍性。只有将华裔文学置于美国文学的传统中,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充分认识其特殊性,美国华裔文学在我国的接受才会更加全面和客观。这不仅是美国华裔文学在我国的接受面临的问题,同时其他少数族裔文学在其母国文化语境中的接受也会面临同样的挑战。
注释:
①这12部作品为: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2002)、胡勇:《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2003)、石平萍:《母女关系与性别、种族的政治:美国华裔妇女文学研究》(2004)、赵文书:Position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sted Terrains(2004)、张龙海:《属性和历史:解读美国华裔文学》(2004)、肖薇:《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海外华人女性写作比较研究》(2005)、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2005)、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2006)、张琼:《矛盾情结与艺术模糊性:超越政治和族裔的美国华裔文学》(2006)、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2006)、薛玉凤:《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2007)、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2007)。
[1]Baym,N.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5thed.)[C].New York:Norton,1998,(2):xxix-xxxii.
[2]Jefferry,P.,F.C.Chan et.al.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M].New York:Penguin Books USA Inc,1991.
[3]Kupper,A.Culture,difference,identity[A].王晓路等.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377-389.
[4]Sander,L.G.Introduction:Ethnicity-Ethnicities-Literature-Literatures[J].PMLA,1998,(1):19-22.
[5]方红.华裔经验与阈界艺术——汤亭亭小说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6]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7]胡勇.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8]黄怀军.差异[A].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3-301.
[9]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10]廖炳惠.关键词200:Key Words in Literary and Critical Studies[M].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
[11]刘葵兰.变换的边界:亚裔美国作家和批评家访谈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12]王晓路.种族/族性[J].外国文学,2002,(6):62-66.
[13]卫景宜.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J].华文文学,2001,(4):69-73.
[14]吴冰,王立礼.华裔美国作家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5]肖薇.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
[16]张琼.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体反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Influence of Ethnicity on Recep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LIU Zeng-mei,CHEN Hu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China)
Ethnic literature usually gains its recognition as opposed to themain-stream literature.Ethnicity,a symbol of difference,also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 of ethnic literature,has influence on its distribution and reception,and itmay promote its reception or lead to itsmonologue.Recep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America goeswith theweakening of ethnicity while its reception in China is a process of being localized,which highlights its ethnicity.It's true that Chinese scholars’“Chinese culture complex”has deepene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toomuch attention on ethnicity,however,limits its reception range to a certain extent,which isworthy of not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ethnicity;reception;influence
I106
A
1002-2643(2014)03-0079-05
2013-08-02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族裔性与文学性的融合——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1YJA752012)的部分成果。
刘增美(1966-),女,山东昌乐人,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陈华(1982-),女,山东五莲人,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