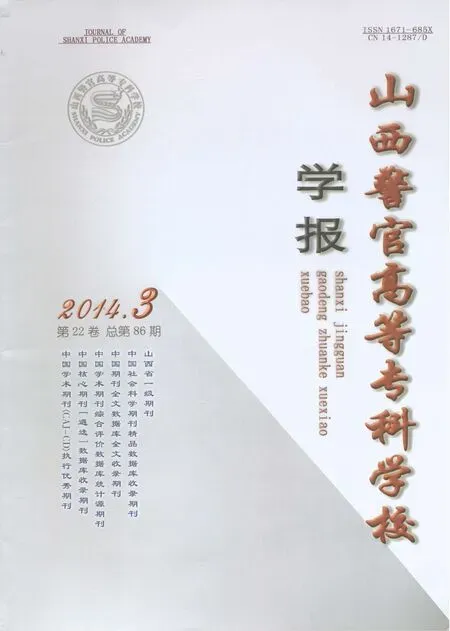农民工组织化犯罪的侦控对策
——以地缘组织“老乡帮”为研究对象
2014-04-09张欣欣
□彭 勃,张欣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犯罪与对策研究】
农民工组织化犯罪的侦控对策
——以地缘组织“老乡帮”为研究对象
□彭 勃1,张欣欣2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以“老乡帮”为主要犯罪形式的农民工组织化犯罪日益成为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一颗毒瘤。而“老乡帮”的存在是社会环境、群体因素、自然因素等多重作用的结果。通过对“老乡帮”制度性根源和侦控漏洞的剖析,提出信息化、协同化、组织化的侦控策略,可以为压缩“老乡帮”的生存空间提供理论支持。
老乡帮;组织化犯罪;侦控对策
当前,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活跃着大量的“老乡帮”。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上海先后发现以抢劫为主的“东北帮”,以扒窃为主的“贵阳帮”,以倒卖车、船票为主的“温州帮”和以盗窃工业原材料为主的“江苏帮”等等 。[1]这些“老乡帮”具有极强的社会危害性,如义乌的“定远帮”、“开化帮”等“老乡帮”,他们私底下收取“保护费”,并打着“为老乡出气”的旗号,威胁企业主,暴力行凶、敲诈勒索,煽动罢工,诱发群体性事件,同时具有明显的组织化分工和严密财务制度,并且等级森严,成为危害一方社会稳定的毒瘤。
“老乡帮”是非出生和成长于本地的外来人口,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占据和控制一定行业或领域,以非法占有财物为主要目的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具有紧密组织形式的犯罪组织。目前,外来人口以农民工为构成主体,而农民工的犯罪多以较为严密组织形式的“老乡帮”出现。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称,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去年已接近2.3亿,在此背景下,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介绍,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2]。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却没有市民的身份认同,饱受歧视;他们从事着繁重的劳动,却收入微薄,居无定所;特殊的生存环境,影响着特殊人群的心理和行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农民工犯罪的社会环境。以北京市丰台区为例,从2001年1月至2005年6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有11741人,其中农民工8183人,占69.3%;被治安拘留的有17562人,其中农民工12727人,占72.5%,如果依据近20年来北京市公安局对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情况的统计,在已抓获的刑事案犯中,进城农民工所占比例分别是:1990年为25.5%,1992年为37.6%,1994年为50%,1996年为56%,2000年为58%,2005年为61%,2007年为64.4%,17年间基本上平均每年增长0.5% 。[3]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农民工犯罪多以团伙形式为主,在犯罪团伙成员关系的构成上居于首位的是同乡关系,其比例高达 71.3%。[4]而团伙形式的犯罪中又多以地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结成各种“老乡帮”。“老乡帮”一般开始是农民工同乡组成的小组织,往往通过介绍工作、娱乐、留宿等形式相互关照,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或感染后,逐步演化成分工严密、等级森严的犯罪组织。由此可见,“老乡帮”主要吸纳成员为农民工,而农民工组织化犯罪则以“老乡帮”为主要形式。
一、“老乡帮”犯罪特点与侦控现状
(一)聚集性明显,分布广泛
目前,我国的地缘犯罪组织“老乡帮”呈现出数目众多、分布广泛、聚集性明显的特点。首先,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狭隘的交际网络,农民工多是从老乡、亲友处获得招工信息,而且大部分又流入同一地区甚至同一企业;其次,在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城市生活中,由于共同的传统、习俗、语言、生活方式更容易凝聚在一起形成“抱团”现象;再次,基于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生活需要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出现了相同流出地民工的流入地聚居现象,这种聚居地多有以诸如“四川村”、“安徽村”“广西村”等地名为开头的民间称呼。不仅聚集、抱团现象明显,“老乡帮”“同乡村”的数量较多,且外来农民工的参与度极高。据深圳警方统计,仅深圳市属于“同乡村”概念的群体就有 643 个,近 200 万人,其中聚居人数在1000 至 3000 人的“同乡村”达 437 个,73 万多人;6000 至 1 万人的 50 个,36万多人;万人以上的同乡村有 15 个,23 万人。[5]上述环境催化了同乡会、同乡联谊会、老乡会等农民工组织形成和发展,而这些集体成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又十分重视老乡成员间的感情,极易被极端分子、前科人员等拉拢利用,形成带黑社会性质的“老乡帮”。上海曾经出现的“苍山帮”、“淮阴帮”、“淮安帮”、“阜阳帮”等犯罪团伙,就曾臭名昭著于沪上,近年来,涉嫌参与毒品及盗窃犯罪的新疆“老乡帮”也让上海警方头痛不已。[6]
(二)组织关系紧密
以地缘联结的农民工“老乡帮”,具有严密的组织形式和明确的分工,尤其是侵财型犯罪组织,这些组织一般都有自己的“老大”、“老板”、“工长”、“出纳”,甚至有的组织还对其成员进行犯罪手法培训。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协作,容易达成共识,组织认同度高,能够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上因素,使得“老乡帮”组织制度严明,成员间关系紧密,组织中的骨干成员较为稳定,帮派与帮派之间的利益边界划分明确,往往不同地缘组织控制着不同的领域。在一项对珠江三角洲某区外来农民黑帮的调查中发现,区域中的三大帮派各自独立,极少发生“黑吃黑”的现象,“湖北帮”专事围标,“湖南帮”专收商贩“保护费”,而“四川帮”则控制大型娱乐场所。[7]这些可看作“老乡帮”组织关系紧密的真实写照。
(三)侦查难度大
“老乡帮”既具有组织化犯罪形式的一般特征,也存在区别于其他组织化犯罪的特性,侦查难度大。一方面,由于农民工本身较强的流动性,导致团伙性质的犯罪具有跨地域性、流窜作案等特点,往往是犯罪事实一旦暴露,犯罪组织就流窜到其他城市以合法的工作为掩护继续作案或者干脆分散回家乡暂避,这给犯罪后的排查和追捕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破案率低,逃脱了法律制裁,又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亲密的地缘性关系往往使成员之间知根知底,并对其家庭成员情况了如指掌,如果某一成员落网,未供认其他组织成员,其家庭成员往往能够得到“老乡帮”的照顾,免除“后顾之忧”。而一旦该成员供出其他成员或者协助公安机关破案,其家族成员往往会受到其他“老乡帮”成员的报复。较强的组织联系,致使公安机关很难从其成员身上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四)防控漏洞多
“老乡帮”的防控漏洞多,可以从流出地和流入地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转型期,对待农民工问题的各项制度还不够成熟,流出地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十分有限,大多既不组织技能培训、法律教育、招工咨询,也不收取其他费用。而流入地,公安机关对农民工的人口信息管理还存在很大漏洞,未登记、少登记、误登记的情况大量存在。天津市1996- 2007 年的问卷普查表明:在犯罪的农民工中,到天津后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分别占79%、69.1%、63.2%、38.8%、93.7%、86.7%和 97.5%;据1999- 2007 年问卷普查,在犯罪农民工中,原户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不知道其在津居住的地方和工作单位的分别占 35.1%、52.4%、 43.2%、 77.2%、 64.6%、79.7%。[8]
另一方面,流入地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由于房租较低、生活成本低、监管松懈等特点,使大量的农民工聚居于此。与此同时,这里的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也使得“匿名性”降低了犯罪成本,减少了暴露风险。而脱离了乡里的维系,又没有社区支持的农民工也极易寻求“同乡会”等处于灰色地带的组织庇护,极易被拉拢、利用,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
二、“老乡帮”的犯罪根源分析
农民工加入“老乡帮”并实施犯罪是一种个人与社会环境冲突后的越轨行为。对其根源的剖析仅仅从单一变量入手必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群体因素多层次、多角度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组织化犯罪。
(一)城乡发展失衡,社会流动受阻
由于制度供给的不足,农村与城市呈现出严重的发展不均衡。在户籍壁垒尚未打破的情况下,农民工从乡村流入城市的社会流动机制受阻,缓慢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农民工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农民工从事着底层繁重的劳动,却不能与市民享受相同的薪酬、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农民工难免产生被剥夺感,心理出现失衡抑或产生对城市的对抗情绪。没有当地的身份认同,加之缺乏来自流入地的社会支持,饱受歧视的农民工只能寻求其他组织提供的情感支持,或者为单纯追求金钱利益而走上歧路。
(二)缺乏社会组织支持,诉求渠道不畅
近年来,一些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案件时有发生,在工伤、克扣工资、强迫劳动等农民工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很难与处于强势地位并拥有当地社会支持的企业主平等对话;农民工在寻求司法渠道解决问题时,又有着诉讼成本高、时效长、取证难等不可逾越的难题;社会组织和社区支持的缺位更使农民工处于丧失话语权、走投无路的境地。不可否认,“同乡会”的非正式组织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工安全及情感的需求,一旦遇到上述情况,农民工可以寻求老乡或者由“同乡会”中的“能人”出面协商解决。“同乡会”这种灰色组织中的成员未必通晓法律,实际的协商中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一些“同乡会”也会从“老乡”薪水中抽取相应的报酬,通常有可能演化成“情大于理”的“老乡帮”采取极端的非法手段解决问题,将问题扩大化,甚至非法组织罢工、静坐、堵塞交通等扰乱社会稳定的活动。
(三)群体亚文化交叉感染
农民工离开农村,却又不能立即融入城市,作为城市“边缘人”的“打工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就业方式既脱离了原有的农民价值体系和文化标准,也不融于城市市民生活,而是形成了以新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代表自身特色的亚文化。[6]在“金钱至上”的城市生活中,道德淡化,脱离家族成员的监管,属于“老乡”群体的亚文化很可能偏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当农民工发觉“先前一同外出打工的老乡突然过上体面的生活”,当“不管来路,有钱就有面子”思想强化,就会产生错误的认知并交叉感染继而在其他同乡的带领下进行诈骗、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而群体成员由于长期受到压抑,心理失衡和“求富”心态交叉传染,以至于相互鼓励,淡化和分散了道德风险,从而使盲目性、冒险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老乡帮”的侦控对策
(一)创新社会管理,整合社会资源
创新社会管理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倡导以人为本的精神,构建以社区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将农民工充分纳入社区的管理服务体系。整合社区内的服务中心、街道办、警务室、司法所、居委会、社区门诊等社会资源,为农民工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配合农民工的亲戚、朋友、邻居、房东、工友等构成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避免农民工被“老乡帮”等带黑组织拉拢、利用。以各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文化交流、教育培训、医疗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社区对农民工的融合功能,倡导社区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助,增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信任与理解,避免农民工受到群体亚文化的熏陶,提高抗拒“老乡帮”等势力拉拢的能力,推动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
(二)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强监测分析
充分运用情报信息技术和其他侦查力量,联合公安、工商、司法、民政、社保等相关部门,构建完善的农民工信息管理系统,构筑流入地和流出地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实现对农民工信息的动态管理。作为农民工犯罪的打击主体,公安机关需要以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的出租房、工棚为重点,同时对地下交易市场、典当铺、旧货市场、珠宝行、修理厂等重点单位进行阵地控制,避免出现信息漏洞。
公安机关作为信息搜集的主体,要转变以往被动破案的思维,主动全面地搜集各种信息,尤其要注意对重点高危人群的日常监测,及时发现可疑的行为轨迹。加强信息的研判与分析,构建专门的农民工组织化犯罪预警系统,整合重点高危人群、重点地点、可疑轨迹等信息,实现人、物、地信息的碰撞对比、关联互访,为决策提供支持。
(三)提升组织化水平,压缩“老乡帮”生存空间
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是政治自由的前提”。[9]自古以来,我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模式造就了极为脆弱的刚性维稳体制。社会组织能够畅通利益诉求渠道,维系组织成员,增加社会弹性,有效地化解和吸纳各种冲突和矛盾。而工会作为全国性维护劳工权益的半官方组织,对农民工的接纳度还不够高,维权效能还比较低。非正式社会组织如“老乡会”“同乡联谊会”“同乡会”没有挂靠部门,也没有注册登记,往往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提高农民工组织化水平,一方面,可以代表农民工的权益,畅通农民工的诉求渠道,提供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减少非理性维权。另一方面,正式的社会组织满足农民工情感和安全需求的同时可以取代“老乡会”“同乡联谊会”“同乡会”的职能,极大地压缩“老乡帮”的生存空间。目前,还未曾出现全国性的农民工组织,但在地方层面,许多社会组织已得到政府的认可,如2009年广西籍农民工全桂荣在苏州市木渎镇这个城乡结合部组建的工友家园,帮助农民工维护权益,普及法律知识,满足交往需求的同时也丰富了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得到苏州市委的认可;江西籍农民工徐文财于 2006 年发起的民工关爱组织———“草根之家”的实践,为农民工社会管理这一难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得到杭州市政府的认可。[10]
(四)健全防控网络,推动社区警务
农民工组织化犯罪具有地域性和流窜性,需要以流入地和流出地为依托,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发挥群防群治的功能,构筑健全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在农民工居住地,要发动社区警务室、居民治保会、保安公司、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动态化的防控网络,并以和谐警民关系为依托,提高社区农民工与居民主人翁意识,强化农民工归属感,倡导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人际互动,提高防范意识,从而实现警民对社区的共建、共管、共防。要保证治安防控体系的社区“全民参与”,防范为主,及时发现,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犯罪的成本,形成对农民工组织化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竭力挤压“老乡帮”的生存空间。
[1]范志权.转型期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行为失范问题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3.
[2]国务院新闻办.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 月均收入2609元[EB/OL ]http://www.agri.gov.cn/V20/SC/jjps/201402/t20140220_3791900.htm.
[3]张勇濂.流动与犯罪:转型期中国农民流动的社会秩序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4]张宝义.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及其分析[J].湘潮,2007(7):5-7.
[5]胡武贤,游艳玲,罗天莹.珠三角农民工同乡聚居及其生成机制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1):10-14.
[6]许祖琪.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问题分析及防治对策[D].上海:复旦大学,2008.
[7]唐晓容.大城市外来农民黑帮化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对珠江三角洲S区中湖北帮的个案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20-27.
[8]王志强.双重转型中的农民工犯罪趋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1(3):26-40.
[9][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0]沈念祖.2012年社会组织十件大事出炉[EB/OL]. http:/ / www. chinanpo. gov. cn / 1940 / 59885 / index.html.
(责任编辑:刘永红)
InvestigationandControlMeasuresontheCrimeofOrganizedMigrantRuralWorkers——In view of geographical “fellow-villager gang”
PENG Bo1,ZHANG Xin-xin2
(ChinesePeople’sPublicSecurityUniversity,Beijing100038,China)
In the background of dualistic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crime of organized migrant rural workers with “fellow-villager gang” as main crime form threatens social order gradually,which resulted from social surrounding,group factor,natural factor and other factors.After analyzing the systematic origin and investigation leaks of “fellow-villager gang”,measures of informationization,collabor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reducing the living space of “fellow-villager gang”.
“fellow-villager gang”;organized crime;investiga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2014-05-23
彭 勃(1990-),男,北京昌平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2级侦查学硕士研究生;张欣欣(1988-),女,山东潍坊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2级侦查学硕士研究生。
D917.6
A
1671-685X(2014)03-005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