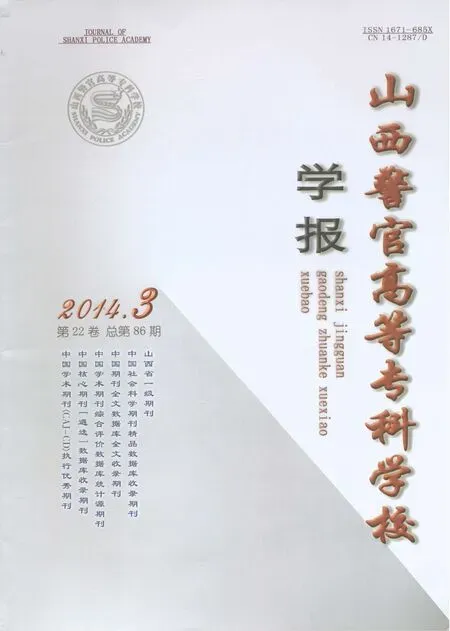论诽谤罪中的“情节严重”
2014-04-09王超凡
□王超凡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法学研究】
论诽谤罪中的“情节严重”
□王超凡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诽谤罪中的“情节严重”就其性质而言,是表明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应该是故意的认识内容。但是诽谤罪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有的突破违法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性质,有的则是准兜底条款。对此,应该用刑事政策来解释司法解释中突破违法的构成要件要素性质的规定,对于准兜底条款当通过把握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和坚持综合标准原则来严格限制。
情节严重;刑事政策;原则;例外
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了诽谤罪,成立该罪要求“情节严重”。“在我国刑法中,以一定的情节作为构成犯罪要件的,称为情节犯。”[1]也就是说,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只有定罪情节才是视为情节犯。而诽谤罪的中的“情节严重”就是成立犯罪的必备条件,即定罪情节,因而是情节犯。但即便将其视为情节犯,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定性,其对于研究诽谤罪的定罪标准的意义极为有限,故有必要探究其本质。
一、诽谤罪中“情节严重”之定性
对于情节犯的“情节严重”的性质,学界大致存在以下几种观点:1.“罪量”说。该说认为,由于犯罪情节中既有客观要素又有主观要素,因而其独立于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只能视为犯罪构成要件中独立于罪体和罪责的罪量要件,其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既然独立于罪体和罪责,就不属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1]2.“整体的评价性要素”说。该说认为,当行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基本要素后,并不意味着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处罚的程度,需要在此基础上对行为进行整体评价,以表明行为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我国刑法分则中诽谤罪的“情节严重”的规定就属于这种整体的评价性要素,而这种整体的评价性要素也是构成要件要素。[2]3.“客观处罚条件”说。该说将我国刑法中情节犯关于情节的要求视为客观处罚条件。[3]4.“整体性规范评价要素”说。该说在承认“整体的评价性要素”说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微调,认为情节是包含主观与客观方面的综合性因素,但是故意的认识内容只可能是客观的情节。
另外,该说认为我国情节犯中的情节,并非是完全紧贴构成要件的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展开的,而存在众多的超出构成要件基本不法量域的情形。属于基本构成要件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的情节,应该在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范围之内,以“整体性规范评价要素”的原则处理,对于超出这个基本不法量域的情节,依具体情形再次进行教义学的定位,即按照结果加重犯,或者按照客观处罚条件,或者按照其他刑事政策方面的因素确定其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关系。[3]
以上四种观点中,“罪量”说存在自相矛盾之嫌。既然认为罪量要件是表明行为对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要件,则罪量要件就是违法要件,其只能包括客观要素而不能包括主观要素,因为主观要素并不对法益侵害产生影响。换言之,就是不承认主观的违法要素。一般来说,只有行为无价值论者才承认主观的违法要素。对此黎宏教授的举例能很好的解
释该问题,例如行为人向牵着狗散步的人的方向射击,子弹从狗和人中间穿过的时候,按照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如果行为人的意图是杀人的话,那么该行为就具有故意杀人的危险,构成杀人罪(未遂);如果行为人的意图是杀狗的话,那么该行为就不具有故意杀人的危险,仅只构成毁坏财物罪(未遂,不罚)。因此,在这一案件的认定中,确定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便成为关键。但是,在上述场合,子弹从人和狗中间穿过的时候,无论行为人的意图何在,子弹对人的生命的威胁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换言之,行为客观对人所具有的危险完全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行为人的意图是杀人还是杀狗而改变。[4]即行为人的主观要素并不会影响法益的侵害程度,其只影响责任。因而罪量要件应该排除主观要素,那么罪量要件也就划入罪体要件,失去存在的必要性,故“罪量”说不可取。
“客观处罚条件”说也存在问题。德日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就某些犯罪而言,除了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之外,只有具备其他事由时才能处罚,这种事由就是客观处罚条件。[5]如果认为此处的“情节严重”是客观处罚条件,那么“情节严重”就不是表明违法性的要素,但是恰恰相反,诽谤罪的中的“情节严重”就是表示违法性的定罪情节。任何行为的违法性只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才有可能认定为犯罪。当刑法分则条文对罪状的一般性描述,不足以使行为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时,就会增加(或者强调)某个要素,从而使客观构成要件所征表的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2]238例如,一般的诽谤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但是还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于是刑法条文规定达到“情节严重”,才以犯罪论处。故诽谤罪中的“情节严重”就是表明违法性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的违法要素,如此才能准确区分民事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以正确定罪量刑。因而“客观处罚条件”说也不可取。
“整体性规范评价要素”说是在承认“整体的评价性要素”说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微调,但从实质而言其与“整体的评价要素”并无二致。“整体性规范评价要素”的微调之处——认为情节是包含主观与客观方面的综合性因素,则存在问题,如上文所述,既然认为情节是违法要素就不应当包含主观的要素。即“情节严重”从应然的角度而言,其性质仍然是“整体的评价要素”,换言之,就是表明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应该是故意的认识内容。但是由于实然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规定可能突破违法性的构成要件的性质,造成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与冲突,所以“整体性规范评价要素”说将超出构成要件基本不法量域的情形定位于结果加重犯、客观处罚条件,或者是刑事政策的因素。但在笔者看来凡是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或者说违法要素的,都可以将其解释为刑事政策。
二、诽谤罪司法解释中的“情节严重”规定之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诽谤解释》)第二条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二)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三)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诽谤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规定,虽然给诽谤罪提供较具体的定罪标准,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经不住仔细推敲。
首先,《诽谤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忽视了不同信息网络工具的功能和影响力的差异,使得该规定难以发挥应有的定罪标准的作用。例如,甲在微博上有数万粉丝,其在微博上故意发布自己捏造的侵害他人名誉的信息(以下简称微博案),由于微博特殊功能,一旦发布或者转发信息,其粉丝皆能看到此信息,如果粉丝并不转发、评论此信息,此微博信息就不能反映点击、浏览、转发的数量,那么就不符合该规定的5000次或500次的规定,但是客观上有数万粉丝可以看到此信息,其法益侵害性早已达到值得科处惩罚的程度,理应构成诽谤罪,故此案例中该规定难以发挥定罪标准的功能。
其次,《诽谤解释》第二条第二项和第三项并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并不是诽谤行为直接造成的结果。因为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诽谤行为通常并不会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因而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也就不能将这些严重后果直接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的诽谤行为,其违法性并不一定能到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并且受过行政处罚的诽谤行为并不会增加再次诽谤他人行为的违法性,使其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前后两个行为应该独立评价。“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只能表明行为人的主观可责难性大,其属于主观要素或者责任要素,但是“如果行为本身的违法性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那么即便其主观上再值得谴责,也不应当认定为犯罪”。[2]242即司法解释将并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的内容强行纳入构成要件来归责于行为人,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甚为明显。
最后,《诽谤解释》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是一种准兜底条款的规定。“兜底条款是指刑法对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列举规定以外,采用‘其他……’这样一种盖然性方式所作的规定,以避免列举不全。”[6]该规定虽然不是直接规定在刑法条文中,但是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有权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其类似于刑法的兜底条款,故暂且称为准兜底条款。刑法条文中的兜底规定因其不具有明确性而有违罪刑法定主义之嫌,从而备受责难。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事立法规定必须明确。在德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甚至直接称之为明确性原则,其要求立法者必须在法条或者解释中明确说明行为违法性的前提,也就是构成要件的应用范围。依据在于,规范遵守者必须能够从法规中预见到,从事何种违法行为会面临刑罚。[7]否则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进而侵犯人权。刑法条文中的兜底规定面临违反明确性原则的责难,司法解释中的准兜底条款同样难逃其责。而且司法解释相比刑法的兜底条款规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通过司法解释对刑法的兜底条款加以明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明确性问题的解决之道”,[6]即如果刑法的兜底条款不够明确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可以补救,但司法解释本身不够明确又该如何补救?难不成对司法解释再进行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法律有时会入睡,但绝不会死亡,即法律必然存在漏洞。对此,“应当从更好的角度解释疑点,对抽象的或有疑问的表述应当做出善意的解释或推定,将‘不理想’的法律条文解释为理想的法律规定”。[8]
三、《诽谤解释》问题之解决
(一)第二项与第三项的困境出路——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影响
《诽谤解释》第二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的实然规定并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应然要求,这种应然与实然的悖论恰恰是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使然。有学者对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的关系进行历史梳理,认为自费尔巴哈提出刑事政策的概念起,刑事领域便正式面临如何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经历费尔巴哈模式、李斯特模式和罗克辛模式三个阶段,其中费尔巴哈模式、李斯特模式皆将刑事政策放在刑法体系之外处理,由此形成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相互割裂的局面,而罗克辛模式则是将刑事政策引入刑法体系中,将其作为刑法体系的一个内在参数。[9]即主张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分离模式是认为刑法体系是一个全面的、封闭的而又无所不包的规范体系,该体系本身构成逻辑自洽的系统,无需引入刑事政策。而我国刑法理论基本上主张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分离,尽管我国学者储槐植早在1993年就提出刑事政策对刑法具有导向与调节两大功能,[10]但此后并未在此基础上作实质性的推进。近年来,开始有学者涉猎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关系的处理,然而对二者关系的定位始终是二元分离的关系。[9]换言之,我国刑法体系从应然的角度而言,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以犯罪论为核心的体系,倘若用德日刑法理论解释我国的犯罪构成,就是以违法和责任为支柱的犯罪论,因为一般认为构成要件是违法类型,构成要件要素也即违法要素。即从应然的角度而言,诽谤罪的“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要素或者说是违法要素,而《诽谤解释》第二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的实然规定却是对应然的违反,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从刑事政策角度加以阐释。
工业革命与现代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秩序与方式,在给人类的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的同时,也衍生了众多的风险,诸如交通事故、电子病毒、核辐射、环境污染等等。“工业社会由其自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11]风险社会引发公众的不安全感,而以保障公众安全为己任的现代国家也必须更多地以管理不安全为目标。如此,公共政策的出台便是国家对政治需要的积极回应。“公共政策旨在支持和加强社会秩序,以增加人们对秩序和安全的预期。公共政策的秩序功能决定了它必然是功利导向的,刑法固有的政治性与工具性恰好与此导向需要相吻合。无论人们对刑法的权利保障功能寄予多大期望,在风险无所不在的社会中,刑法的秩序保护功能注定成为主导。现代国家当然不可能放弃刑法这一秩序利器,它更需要通过有目的地系统使用刑法达到控制风险的政治目标。刑法由此成为国家对付风险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借此大举侵入刑事领域也就成为必然现象。”[12]最好的表现就是刑事政策对精密刑法体系的入侵或者说“破坏”,而此处《诽谤解释》第二条第二项和第三项的实然规定便是实例。
虽然刑事政策会入侵或者破坏精密的刑法体系,甚至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是也要看到这种“破坏”的“必然性”,其合理性不容质疑。因为,其一,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本身的属性决定了“法律随时代更替而变化,因此对刑法应当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同时代的解释,同时代的解释是最好的解释,而且在法律上最有力。”[8]17而刑事政策就是时代需求——控制风险的反应,《诽谤解释》可能考虑到诽谤行为会“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虽然该后果不是诽谤行为直接造成的,但是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是不争的事实,其与诽谤行为脱不了干系,并且近年来网络诽谤行为的风生水起,其对公民的名誉权等造成严重侵害,出于社会安全、社会防卫或者法益保护等刑事政策的考虑有必要严惩诽谤行为。同理,“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也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其二,从哲学上而言,“任何原则都有例外,任何原则都允许例外。”[8]454因而将因刑事政策的考虑的司法解释之规定作为精密刑法体系的例外之规定,也未尝不可。倘若“将刑法视为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或者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无涉的自给自足的规范体系,沉湎于由古典犯罪阶层体系所发展起来的体系性、逻辑性思考,虽然其合体系性与合教义性的逻辑演绎结论可能无懈可击,但这种唯美主义的体系性思考,无视刑法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解决问题的客观需要”,[13]显然会使刑法丧失生命力,捍卫刑法的初衷反而可能导致刑法因缺乏实践解释力而最终难以保护法益、难以控制风险。即例外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动力源泉就是国家治理与风险控制的现实需要。换言之,就是刑事政策的考虑与需要。
(二)第一项和第四项的困境出路——对准兜底条款的限制
尽管《诽谤解释》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忽视不同信息网络工具的功能,无法规制上文所举出的“微博案”,但是可以用《诽谤解释》第二条第四项规定的准兜底条款规制,即“微博案”属于“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诽谤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规制网络诽谤行为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至于该项规定无法规制的行为当考虑是否属于“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因而重点在于如何合理界定或者说限制“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当坚持以下原则来限制“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的适用范围:
第一,严格把握原则与例外的关系。从应然的角度来说,“情节严重”是违法要素,故原则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也只能是违法要素,不包括责任要素。当然凡事皆有例外,“问题是,如何确定该原则的‘例外’范围,如果没有严格的标准,就会导致许多有损法治的结果。由于例外是最严格的解释对象,例外应该放在最后考虑。”[8]454原则可以为例外所突破,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侵犯原则所保障的权利,偏离原则需要具备正当理由。要构建例外,超越刑法基本原则保障的权利,应该具备以下条件:(1)存在压倒性紧迫的公共利益;(2)没有合理的替代手段,且建构例外与惩罚的目的并非不一致;(3)非此不足以保护公共利益,或保护成本太大,刑事司法体系不能承受;(4)建构例外不会压制社会可欲的行为;(5)存在提出积极抗辩的机会,且达到优势证据或引起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即可;(6)有明确的适用范围限制;(7)可以无偏私、非歧视地进行处理,且在操作上可行。[12]即当同时满足以上7种合理根据时,可以考虑在违法要素之外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如此才能既保护法益又不侵犯人权。
第二,坚持综合标准的原则。所谓的综合性标准就是,在诽谤行为并不完全符合《诽谤解释》第二条的前三项规定,但综合考量案件的全部情况,也可认定为本罪的“情节严重”的情形。综合标准主要是为了解决诽谤行为虽不完全符合《诽谤解释》第二条的前三项任何一项规定,但又达到一定临界点的入罪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本罪“情节严重”综合标准的适用必须坚持以下四个原则:(1)补充性原则。综合标准是《诽谤解释》第二条的前三项的重要补充,只有在不符合《诽谤解释》第二条的前三项任何一项的前提下,才能考虑适用综合标准。(2)全面性原则。在考察本罪的“情节严重”时,必须予以全面的分析和判断,不仅要考察案件的客观事实,而且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和倾向;不仅要考察显性的情节,而且要考察隐性的情节;不仅要考察积极的入罪情节,而且要考察消极的出罪情节。(3)综合性原则。综合标准是对全案情况的综合考察,这种综合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综合即意味着必须避免对行为过程中所呈现的诸多情节的简单相加;另一方面,综合即意味着必须对行为过程中的诸多情节进行系统考量,进而加权计算。(4)酌定性原则。综合标准的实质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情节犯实际上是立法者在定罪问题上所作的一种无奈的权力让渡。[14]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必须要遵守刑法的基本原则,综合考量行为的违法性程度。
通过解释与限制方能合理确定诽谤罪的“情节严重”,才能发挥《诽谤解释》应有的定罪标准的功能。
[1]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国刑法的探讨[J].环球法律评论,2003(3).
[2]张明楷.犯罪构成要件与构成要件要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9.
[3]王 莹.情节犯之情节的犯罪论体系性定位[M].法学研究,2012(3).
[4]黎 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3.
[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47.
[6]陈兴良.中国刑法中的明确性问题[A].梁根林,[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0.
[7][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中的法律明确性原则[A].梁根林,[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5-46.
[8]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
[9]劳东燕.形势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考察[J].比较法研究,2012(2).
[10]储槐植.形势政策的概念、结构和功能[J].法学研究,1993(3).
[11][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2.
[12]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3]梁根林.责任主义原则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考察[J].清华法学,2009(2).
[14]利子平,周建达.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初论[J].法学评论,2012(5).
(责任编辑:王战军)
On“SeriousCircumstance”inLibel
WANG Chao-fan
(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0042,China)
“Serious circumstance” in libel is a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crime in nature,so it is the identification content for intent.However,some regulations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n “serious circumstance” in libel are out of the nature of criminal constitutive element,some are quasi-miscellaneous provisions.So provisions out of the nature of criminal constitutive element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interpreted by criminal policy.Quasi-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keeping the balance of principle and exception and holding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standard.
serious circumstance;criminal policy;principle;exception
2014-05-19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资助项目“自媒体言论构成诽谤罪的判断标准研究”(20142228)
王超凡(1991-),男,河南许昌人,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刑法学。
D924.34
A
1671-685X(2014)03-0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