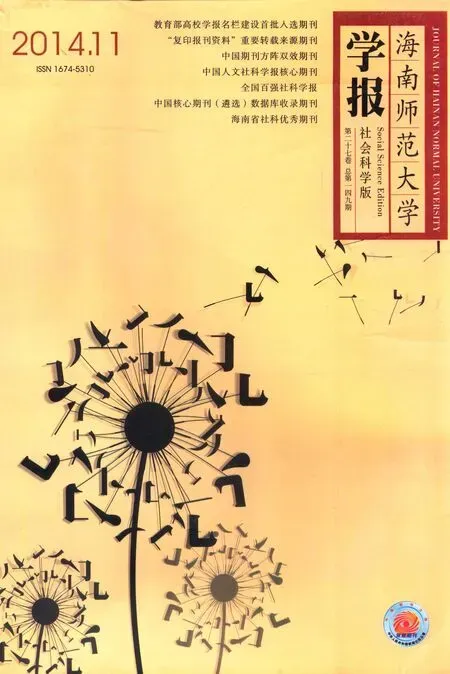论刘再复“ 第二人生”的文艺理论研究
2014-04-09古大勇
古大勇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论刘再复“ 第二人生”的文艺理论研究
古大勇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刘再复“第二人生”的文艺理论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对于“主体间性”理论的构想;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整体评估和学术定位;对文学本质的重新认识和界定;提出 “罪与文学”、“文学的超越视角”、“文学史悖论” 、“告别诸神”等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和主张。
刘再复;文艺理论研究 ;“第二人生”; 研究成就
前 言
刘再复曾经说:“我把48岁之前(1989年之前)的人生,视为第一人生,把这之后到海外的人生视为第二人生。”[1]在刘再复的“第一人生”中,他曾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和《文学评论》主编,这样的位置决定着他要引领文学研究新方向,倡导文学研究新思维,推动文学理论新建设。其“第一人生”的学术成就可以用“鲁迅研究‘三书’”和“刘氏三论”来概括,前者指《鲁迅与自然科学》《鲁迅传》《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后者指“文学主体论、性格组合论和国魂反省论”。[2]“刘氏三论”特别是前“二论”产生了重大的时代影响,是使刘再复“暴得大名”的关键性因素。1989年刘再复离开故土去到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二人生”,他把学术研究中心转向古典文学,但仍然关注文艺理论建设与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
一、对于“主体间性”理论的构想
“主体间性”理论的前理论是“文学主体性”理论,“文学主体性”理论是刘再复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其意义在于它冲破了僵化机械的前苏联反映论文学理论模式长期统治的历史格局,改变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模式,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不可否认。但时过境迁以后,我们也会冷静发现该理论的学术未圆之处:刘再复将“文学主体性”等同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抽去了这个普遍主体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内涵,把受具体历史制约的有限主体,变为摆脱和超越历史限制的绝对能动主体,从而导致这个普遍主体的虚幻性。另外,刘再复对于主体的认识也不太全面,只突出主体性,忽略主体间性,忽略了这个主体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的制约,不能摆脱客体的限制以及其它主体关系的限制。
去国以后,刘再复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缺憾也有所认识,例如他认为,“我们讲主体性是为了张扬个性,但个性不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而是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所谓主体间性就是主体的关系的特性。因此也可译为主体际性。叔本华说:人最大的悲剧是,你诞生了。人一诞生,就被抛入一种关系中,就被关系所制约。这就规定了人的主体性是有限的主体性,而不是无限的主体性;也规定了人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而不是无限的自由。”[3]15“仅仅从主客体对立范畴去探讨‘何为主体’,会产生一种局限,或者说,会给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宇宙间和人间真有一种完整的、统一的、具有纯粹本质的主体。而事实上,处于人类社会中的主体都是不完整的,常常是分裂和破碎的。这是因为,人都生活在各种关系中,被这些关系所割切、所异化”。[3]16因此,在一篇和杨春时的《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的对话》中,刘再复初步提出了自己关于“主体间性”的理论构想。他认为“主体间性可分作外在的主体间性和内在的主体间性”[3]16。外在主体间性已经被西方学者所注意,并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海德格尔、胡塞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都提出过有关外在主体间性的理论。刘再复提出要特别关注内在主体间性,创造出属于中国特色的内在主体间性理论,“内在主体间性,是自我内部多重主体的关系。我曾经称自我是一个内宇宙,是与外宇宙同样广阔无边的世界。在自我世界中有无数的自我,他们也形成关系,这也是一种主体间性”。[3]16他随后举出庄子、禅宗、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等的有关理论来展开论述,认为庄子所谓的“心为形役”就分别展现出一个“形主体”的我和“心主体”的我,前者是外部的社会性主体、社会关系总和的“自我”,和后者形成了一种矛盾性质的“主体间关系”。刘再复认为禅宗的打破“我执”并非否认主体性,而是要打破这个限制扭曲“真我”的“假我”,“真我”指自性真性的“自我”,而“假我”类似于庄子所谓的“形主体”的“形我”,这种“真我”与“假我”之间的关系就是内在主体间性。其它如巴赫金的“灵魂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的论辩”涉及到的也是内在主体间性。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关系,事实上探讨的也是内在主体间性。他还特别提到高行健的小说,高行健的很多小说中都有我、你和他三个人称,但这三个人称不是彼此无关、互相独立的三个人物,而是一个人三个自我的分化,你就是我,你我对话就是我我对话,即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然后又产生另外一个主体——他,他是从自我主体派生出来的,是对自我主体的评论者、关爱者、审视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内在的主体间性。”[3]20
刘再复对“主体间性”理论最集中的思考也就体现在他与杨春时的这篇对话录中,他没有像“第一人生”中那样撰写如《论文学的主体性》之类的具有体系性的宏篇大论,而只是提出了一个大致的理论框架和设想,由于他忙于散文创作并“返回古典”,专注于《红楼梦》等古典文学研究,尚无余裕就此理论深挖下去,建构一个具有体系性和逻辑性的理论主张。倒是他的朋友杨春时在刘再复的期待和启发下,对“主体间性”理论不舍不弃,执着钻研,取得系列研究成果,成为中国“主体间性”理论的代表人物,在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很显然,刘再复作为“主体间性”理论的奠基者、倡导者和推动者,其贡献同样不可忽略。
二、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整体评估和学术定位
刘再复的《李泽厚美学概论》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进行了一次“大检阅”式的系统梳理、宏观把握、整体评价和学术史定位。学术界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研究虽早已展开,但综观这些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针对李泽厚美学“矿藏”中某一个小的地点进行挖掘,就李泽厚美学的某些局部性内容或某个时间段的美学思想进行共时性或历时性的研究,所关注的也就是三两的“树木”,而不见整体的“森林”。也就是说,少有学者从整体宏观的层面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进行全盘检点和整体评价,并从美学史的链条和坐标上对李泽厚的美学成就进行学术定位;或虽有个别学者有此自觉的意识,但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和学术估价也许并不准确到位。
刘再复认为李泽厚的美学是“真正原创性的美学”,[4]4他提供“一个又一个经过论证与提炼的未见于前人笔下的范畴性话语:‘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一个世界文化’、‘西体中用’、‘历史积淀’、‘主体性实践’、‘情本体’、‘新感性’、‘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工艺——社会本体’、‘文化——心理本体’、‘情感信仰’、‘历史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还有谁创造了这样的人文科学的话语系谱。而20世纪西方哲学、美学、人文科学界又有谁的话语谱系如此独特、如此丰富?”[4]9刘再复认为李泽厚美学第二个特点是“体系性”,“李泽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建立美学体系的哲学家。中国古代并没有‘美学’这一概念,更没有美学这一学科。只有‘美’这一概念,当然也有中国自己的审美系统。因此,可以说李泽厚是‘美学’概念传入中国、美学学科在中国确立之后第一个建构体系的人。”[4]13除此之外,刘再复认为李泽厚的美学还有如下特点,即是“拥有哲学、历史学纵深的美学”、“近似曹雪芹的大观美学与通观美学”、“马克思与康德互补的历史本体论”、创造了“由感知、理解、想象、情感四要素变化组合”的“美感心理数学方程式”、“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与‘情感真理’的发现”、“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现代话语谱系”。[4]20~66
刘再复的上述几点评价都是从宏观整体的层面来观照李泽厚美学,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原创性”和“体系性”这两点,这两点也足以确立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足以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4]1。就“原创性”而言,李泽厚美学辞典中这些耳熟能详的美学词汇,如“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情本体”、“历史积淀”、“主体性实践”、“人的自然化”等名词,哪一个不是李泽厚首先创造,经过多年的检验和运用,已经被学术界所认可,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并成为约定俗成的惯用学术名词?而我们在使用这些名词的时候,是否所有人都能想到,它们的首创者就是李泽厚?就李泽厚的美学的“体系性”而言,并非说李泽厚前后的美学家的美学都没有体系性,如朱光潜、蔡仪、宗白华等美学家也有自觉或不自觉的美学体系性追求,但是,就严格的理论体系特征来说,非李泽厚莫属。李泽厚的美学具有独创的范畴系统、美学中轴和体系性特征。按照现代汉语的概念,体系泛指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是不同系统组成的系统。刘再复给李泽厚列出了两张“美学图式”*两张“美学图式”见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2009版,第16-17页。,即“美学概论图式”和“美学史论图式”,前者由“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社会学”三大板块组成,后者由“经”、“史”两大部分构成,其中史分“外篇”、“内篇”和“补篇”,内篇为《华夏美学》,外篇为《美的历程》。看到这两张纲举目张、骨架清晰、脉络分明、布局有序、如人的肌体一样完整和系统的“美学图式”,你一定会恍然折服于李泽厚美学的“体系性”。刘再复从整体上高度评价李泽厚的美学成就,但也有对李泽厚具体美学观点的商榷和批评,如刘再复就不同意李泽厚把庄子的美学思想置入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之中,认为“把庄子思想放入历史系统和放入美学系统很不相同。我只欣赏李泽厚那些放在美学系统的阐释,而推广到现实层面,我则有所质疑,例如‘天人合一’,放在审美层面上,它确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可是,如果放在现实的层面上,却容易导致人对自身有限性的忽视”[4]95。
三、对文学本质的重新认识和界定
什么是文学?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刘再复认为:“文学离不开三项基本要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心灵是第一要素,一切好作品都必须切入心灵,《封神演义》虽有想象力,但未切入心灵,所以不是好文学。文学批评离不开两大标准:精神内涵与审美形式。精神内涵包括思想内容、情感内容、心理内涵、知觉内容、社会历史内涵等等,杰出的作品必定具有精神内涵的深度、广度与高度。……文学事业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功利的事业,但它具有广义的功利内涵。换句话说,文学不追求具体的、短暂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延续、提升的‘功利’,这便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是王国维所说的‘无用之用’。”[5]在此基础上,刘再复又提出了“文学自性”的概念,“‘文学自性’的对立项是文学之外的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新闻性、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市场性、集团性等。‘自性’一词来自大乘佛教及其中国化了的禅宗。禅宗讲的是自性本体论。……强调打破我执,而这种我执,是假我,不是真我。本文所讲的文学自性的回归与再生,从作家主体意义说,是真我的回归,从客体作品说,是文学应当回归文学的初衷,不为他性所掌握,这种回归之路乃是文学的自救之路。文学要确认自身,首先应当确认自身的有限性,它只能为自身开辟道路,不可能为他者开辟道路,特别是不能为任何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开辟道路。”[6]
什么是文学?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答案。在中国,有《尚书》中的“诗言志”,《论语》中的“兴观群怨说”,《文赋》中的“缘情说”,《文心雕龙》中的“感物说”……在西方,早期有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的“摹仿说”和亚里士多德的“虚构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7]强调文学的虚构性本质特征。按时间的发展演进,西方先后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等。其文学观念分别体现为:文学是对个性情感的表现和想象力的再现;文学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美、是一种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文学是直觉、幻觉、梦呓、无意识心理的表现;文学是一种“反文学”的文学。而在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之间,由于受到马列文艺思想、苏联“反映论”文艺模式以及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影响,文学被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及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形成了由“意识形态论”、“反映论”和“工具论”合成的社会主义文学观念体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刘再复提出了“文学主体论”,冲破了“反映论”文学理论体系,之后,“活动论”、“审美论”、“主体间性论”、“人学论”等新的文学观念又陆续产生。[8]
比较以上“文学观”可以发现,首先,刘再复的“文学观”是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反拨,是对20世纪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间广泛存在的“政治化文学观”的一种纠正和颠覆,认为文学不能成为政治、革命、意识形态的工具,在当下市场经济社会下,文学同样不能成为金钱和市场的奴隶。文学要坚守属于自己的独立“自性”,一切外在于文学的“他性”都要被拒绝。当然,文学不是不可以表现政治、革命、意识形态、经济、市场等相关内容,但绝不能为后者所左右、为后者所“摧眉折腰”,而要以一种有距离的、超功利的态度来观照和审视。鲁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容易成为官的“帮忙”与“帮闲”以及“商”的“帮闲”与“帮忙”,而在面对大众文化时,又容易“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9]。 而文学的命运何尝不是如此?在当下大众文化一统天下的背景下,刘再复的文学观无疑有一种特别的警醒意义——文学绝对不能成为大众的“帮闲”与“帮忙”,丧失“自性”。其次,刘再复的文学观力戒以上各家文学观之偏于一端、执于一点的弊端,而有机吸收各家合理因子,然后进行高度提炼概括,形成其既有别于任何一家、但又有机融合多家精华的独特文学观。在刘再复的文学观中,你可以发现到陆机的“缘情说”, 刘勰的“感物说”,亚里士多德的“虚构说”,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想象力,唯美主义的审美形式,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精神内涵等各种文学观的影子。第三,刘再复认为“精神内涵”是文学的本质特征并视之为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认为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不仅要看其审美形式,更要看其精神内涵和灵魂深度,这也是极有见地的主张。正是在这样的标准下,他认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也未必并比得上屠格涅夫,但他们的作品却因为有巨大的精神内涵而超越屠格涅夫并构成的文学巅峰”。[10]78同样在“精神内涵”的标准下,刘再复在回应夏志清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超过鲁迅的观点时,认为鲁迅比张爱玲卓越。[10]56~74
四、提出“罪与文学’、“文学的超越视角”、“文学史悖论”等系列创新观点
在刘再复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导言”部分,作者点明了自己的写作动机:“此书现在取名《罪与文学》,主要概念是文学中的忏悔意识,主题是灵魂维度、人性深度的探索。忏悔实质上就是内心展开灵魂的对话和人性的冲突。……具有深度的罪感文学,不是对法律责任的体认,而是对良知责任的体认,即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体认。忏悔意识也正是对无罪之罪与共同犯罪的意识。但伟大的忏悔文学,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罪不认罪的问题,即不像教堂中向神与神的中介确认自己的过失问题,而是人的隐蔽的心理过程的充分展开与描写。正因为看重揭示心理的过程,读者才会看到实实在在的灵魂的对话和人性世界的双音。”[11]19《罪与文学》的学术价值在于,从文学的忏悔意识和灵魂维度来深入系统地探讨中国文学的根本缺陷,《罪与文学》可以说是第一本集大成式的专门性著作。它在西方文化的坐标上,以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证,犀利地直陈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和灵魂论辩维度的根本性缺陷,无疑具有振耳发聩的警醒意义。虽然在此之前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触及到这个主题,但因为是一个宏观性的中西大文化命题的比较,着眼点在于“文化”,并没有如《罪与文学》那样紧紧结合具体中国文学文本来探讨。至于在《罪与文学》诞生的前后,也出现若干从忏悔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但是由于单篇论文的篇幅限制,无法做到像《罪与文学》那样深入而系统。值得注意的,近年来出现了系列有关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之类的著作,*如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 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 》,学林出版社,1995;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王列耀《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但综观这些著作,都在探讨基督教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及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但事实上,这种影响仍然是局部的、表面的、肤浅的,并不能从整体上推翻刘再复对中国文学根本缺陷的论断。
刘再复提出“文学的超越视角”,认为“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地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11]90“文学的超越视角”就是主张文学要超越世俗的、政治的、集团的、现实的、批判的等功利性视角,表达对人自身的关怀与同情、对人类的爱与悲悯,成为一种听命于良知的个人事业。这也是刘再复的文学观之一,与刘再复的“文学自性论”是一脉相承的。
“告别诸神”也是刘再复提出的一个文艺理论观点,所谓“告别诸神”就是“告别在本世纪中流行过的,并且被自己的心灵接受过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10]127。“告别诸神”的第三点内涵对当下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仍有启发意义,即告别“普罗米修斯”,“告别窃火之神,这是仰仗外国的某种主义过日子的模式,在文学理论上,就是把从外国引入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某些文学理论视为精神救主的模式。”[10]128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五四”时期,西方几百年的文艺思潮,短短数年间就被引入中国,几乎被囫囵吞枣地接受;新中国成立之后,则全盘转向苏俄文艺理论;新时期以后,又重蹈“五四”覆辙,各种“新方法”鱼贯而入中国。中国的文艺理论总是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下,患上“失语症”,缺乏理论原创力,没有属于自己的独创性理论。因此,刘再复提出“告别诸神”,就是期待中国走出“诸神”的阴影,建构属于自身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也是我们当前文艺理论建设面临的急迫任务。国内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忧虑,如曹顺庆就曾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提出医治“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代文论的“话语转换”。
刘再复还提出“文学史悖论”的命题,列出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若干组悖论,即“文学发展,文学无发展”;“文学发展具共时性,文学发展具历时性”;“文学的周期性,文学的非周期性”;“文学时间不可逆,文学时间可逆”;“文学有规律,文学无规律”。[10]92~106“文学史悖论”打破了单一内涵的文学史观,把文学史看成一个多种走向、多种内涵、多种特征和多种话语系统互相交融的过程,承认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利于打开“重写文学史”的思路。
结 语
刘再复“第二人生”由于不在国内,所以他的文学理论主张也就没有产生如“第一人生”那样的时代影响,但毋庸置疑,他“第二人生”的文艺理论研究成就不容忽视。国内“主体间性”美学是建立在刘再复“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刘再复虽没有对“主体间性”理论作系统阐释,但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刘再复作为“主体间性”理论的奠基者、倡导者和推动者,其贡献同样不可忽略。其次,刘再复对李泽厚美学进行了全盘的检点和学术史地位的确认,《李泽厚美学概论》的系统性、整体性、宏观性、科学性和公正性是其它同类著述所不具备的。而《罪与文学》可以说是第一本从忏悔意识和灵魂维度来深入探讨中国文学根本缺陷的专门性著作。至于刘再复提出的“文学的自性”、“告别诸神”、“文学的超越视角”、“文学史悖论”等理论主张都具有创新性特色,对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和研究不无借鉴意义。
[1] 刘再复,吴小攀.走向人生深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3.
[2] 夏中义.新潮学案[M].上海:三联书店,1997:1.
[3] 刘再复,杨春时.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的对话[J].南方文坛,2002(6).
[4] 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9.
[5] 刘再复.文学十八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7.
[6] 刘再复.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M]//刘再复讲演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24~25.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8.
[8] 古风.1949年以来文学观念的演变与文学的发展[J].学术月刊,2010(3).
[9]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社,2005:104.
[10] 刘再复.人文十三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1]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毕光明)
OnLiuFuzi’sStudyoftheLiteraryandArtTheoryon“theSecondLife”
GU Da-yong
(SchoolofLiteratureandCommunication,QuanzhouNormalUniversity,Quanzhou362000,China)
Liu Fuzi’s achievements in his study of the literary and art theory on the “second life” are as follows: the conception of the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the overall evaluation and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Li Zehou’s aesthetic theory; the re-recogni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literary nature;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a series of innovative ideas and proposals like “crime and literature”, “the vision of literary transcendence”, “the paradox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 a farewell to all deities” .
Liu Fuzi; studies on literary and art theories; “the second life”; study achievements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刘再复学术思想整体研究(1976-2013年)”(项目批准号:14YJA751004)
2014-10-20
古大勇(1973-),男,安徽无为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10
A
1674-5310(2014)-11-00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