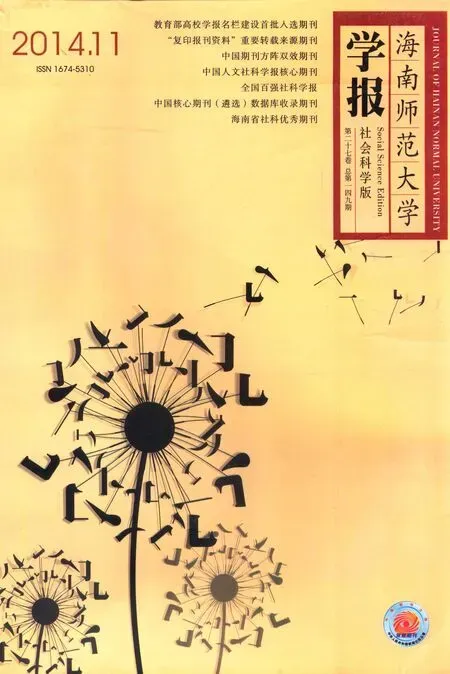新中国外交“ 革命化”趋向的初步显现
——刍议《列宁主义万岁》的写作背景、过程及其影响
2014-04-09汪振友
汪振友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东北农业大学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新中国外交“ 革命化”趋向的初步显现
——刍议《列宁主义万岁》的写作背景、过程及其影响
汪振友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东北农业大学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了争夺当代世界的控制权,竞相高举“和平”之大旗。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由于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封锁和遏制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步疏离的巨大挑战,所以,选择全面“革命化”的外交战略就有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在世界两强竞相施压的大背景下,中共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希望推动苏共重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但是却遭到苏共的反对并反击中共偏离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西方国家通过双方激烈的理论交锋逐步确认中苏之间存在重大分歧,并设法利用之分化社会主义阵营以从中获益。
新中国;中苏关系;《列宁主义万岁》;大论战;外交“革命化”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确定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总路线,而中共认为“和平共处”是延缓世界战争的策略手段,不赞同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总路线。中共主张采取全面“革命化”外交路线,即以保卫中共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同时以革命化战略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团结起来,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对抗美苏两强的霸权主义,推动世界革命发展,以革命斗争争取世界和平、人类解放。1960年4月,中共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为契机,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即《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集结成册冠名为《列宁主义万岁》。全面阐明自己对时代、革命、前途等问题的基本立场。这是中共第一次系统化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提出自己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尽管《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但国内除回忆录性质的书籍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258-266页;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7-79页。个别章节略有涉及外,未见有系统地对其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及专著。为此,本文尝试运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及相关资料,对《列宁主义万岁》的写作背景、过程及其国内国际影响进行一番历史考察。
一、《列宁主义万岁》写作的历史背景
(一)二战以后美苏竞相高举“和平”旗帜
1.苏联提出“和平共处”外交政策
列宁是提出“和平共处”政策的第一人,但主要是当时苏联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策略手段。斯大林基于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强调“和平共处”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更长的发展时间,以达到做好世界大战准备的战略目的。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所处环境近似,因此,对“和平共处”政策的定位和内涵解读更为接近。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根本变化。短暂主政的马林科夫提出,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实现苏联改革的条件之一。他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为此苏联应执行诚实而非虚伪的政策,以赢得政治伙伴乃至对手的信任,从而实现国际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1]1954年3月,赫鲁晓夫的讲话赋予“和平共处”政策新的内涵和地位:“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遵照着伟大的列宁关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指示。苏联政府认为,在目前国际形势中,没有任何争端是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的。”[2]7月,《真理报》发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的文章,反映了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对外政策的思想变化和基本态度。1957年12月14日,在苏联的主导下,第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以77票对零票审查通过了政治委员会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决议案。决议认为,有必要扩大国际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通过和平方法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纠纷。[3]由此可见,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原则基础,比较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且得到联合国大多数国家的认同,迎合了二战后苏联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珍视和平的心理,赢得了舆论上、道义上的支持。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主要针对美国而言,赫鲁晓夫的讲话指出:“如果美国和我国之间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制止它。这将是一场浩劫。因此应尽一切努力,不要用战争来解决现有的争执问题,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证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4]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外交战略,从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也被今日的现实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苏共要求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服从其战略,根本不考虑中国等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斗争一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现实需要,甚至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必然遭到具有独立自主传统的中共的抵制与反击。
2.美国提出“和平战略”外交思想
1953年4月1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针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的柔化政策,发表了题为《和平的机会》的演说,他强调:“如果苏联能够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他们也准备欢迎和平,美国将用裁军省下来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国际援助与重建……帮助各国人民享受生产自由的幸福。这种新‘战争’的标志将是公路与学校、医院与住房、食品与健康。”[5]对于这篇演说,世界各地反应热烈。但是,美国虽然描绘了和平的美好愿景,但其对苏联的和平诚意充满疑虑。为了打消美国的顾虑,苏联采取从奥地利撤军、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等一系列措施,并多次向美国提出恢复中断的两国首脑会议的建议。1955年7月,四国首脑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在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致开幕词说:“美国人民希望同苏联人民成为朋友,我们的人民或国家之间并没有天生的分歧,也没有领土上的冲突或商业上的竞争。从历史上说来,我们两国一直是和平共处的。”[6]此时,“和平共处”不仅是双方争取世界人民的口号、策略手段,更是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现实选择:“不同于其他时代,我们今天追求和平,是因为我们已受到现代武器的威力的警告:和平可能已成为人类生活惟一赖以存续的条件。”[7]日内瓦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意义的成果。但是,美国从双方的接触中感觉到存在运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准备全力以赴推进共产党统治区域的和平变革。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提出了“和平战略”和“灵活反应战略”,其目标不仅是保证国内民主社会的稳定,而且是要帮助推进人类自由和世界秩序的事业——正义和持久和平的全球性事业[8],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为依托,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
由于美苏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国际局势出现缓和的迹象,双方均追求在实力均衡的条件下,追求和平外交的主动性。美苏合作炮制的奥地利国家条约、“日内瓦精神”、“戴维营精神”给冷战中的世界人民带来一丝和平的曙光。但是,美苏关系的缓和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首先,美国并没有改变封锁和遏制中国的既定政策,依然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战争威胁;其次,苏联为维护其自身利益,欲把中国纳入其外交战略框架中,甚至提出让中共放弃武力攻台、在边界问题上向印度让步等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不合理要求,这不能不引发中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和有力回击。
(二)中苏外交战略定位分歧
1.“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赢得稳定的、安全的周边环境,中国与缅甸、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可与认同。但是,中国仅将“和平共处”作为新建政权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策略手段。而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为了贯彻“和平共处”等新的改革措施,采取批判斯大林的极端做法,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混乱,西方国家趁机掀起反苏反共活动。为了“回击西方反苏反共”[9]活动,中共中央分别于4月和1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普遍价值、斯大林的功过评价、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等问题进行深入的阐释,委婉地批评了苏共的一些观点,表达了中共欲帮助其回归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观意图。1958年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马等一系列事件,使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向“修正主义”蜕化的判断不断加深。1959年12月,毛泽东讲话指出“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们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10]。因此,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这样可以帮助苏共、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旗帜,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优势。[11] 242中共采取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希望通过辩论明辨是非,帮助苏共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轨道。而恰恰相似的是,苏共认为自己也掌握列宁主义真理,希望中共的政策与其保持一致,两党均笃信真理“单一化”,理论冲突势成必然。
2.“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只能有一个外交政策”
1958年,中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视之为中国探索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但赫鲁晓夫对此却颇多微词,特别是1959年5月看到了彭德怀准备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备忘录[12] 22-23,更强化了这一认识。而中印边境发生冲突时,中共一再奉劝苏共不要发表“中立”性声明,而苏共仍然自行其是,将中苏分歧公开化。10月,赫鲁晓夫携访美的成果“戴维营精神”访问中国,在会谈中不客气地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12]25,并举远东共和国的例子,暗示中国可以暂时允许台湾独立,当即遭到毛泽东的拒绝。会谈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赫鲁晓夫在回程中发表讲话称中国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11]22712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一是不赞同中国国内“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政策,批评中共领导人头脑发热,有“冒进”思想。二是不赞同中国的外交政策。称1958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相符合,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利益不相符合。批评中国处理台海危机的方式影响了苏美关系,中印冲突使苏联处于尴尬境地。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只能有一个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偏离苏联外交政策轨道,就是偏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13]317-318以上两点充分显示出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情结,尤其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是十分不恰当的,其外交决策始终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不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甚至牺牲中国的利益,必然遭致中国的抵制和回击。
3.“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都不能对中国有约束力”
赫鲁晓夫在核武器威胁人类生存的背景下提出“和平共处”外交路线。常规部队存在价值式微,火箭部队发展备受重视,裁军自然而然成为“和平共处”的衍生策略。1960年1月1日,赫鲁晓夫在谈到苏联在联大提出的裁军计划时说:“如果我们的建议被采纳,我们准备随时解散我们的军队。”[14]如果“冷战”拥护者采取争论拖延的策略,苏联甚至可以考虑单方面裁减武装部队,用火箭保卫边界。8日,他致信毛泽东说: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从苏军人员中裁减120万人。[15]中共不反对苏联采取单方面裁军的措施,但是反对苏联替中国承担义务。2月4日,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康生在会议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声明:“中国一贯主张普遍裁军,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一贯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都不能对中国有约束力。”[16]143理性分析,中共的声明并非是无理的,中国一直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封锁和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战争威胁之下,中印边界又发生冲突,承担裁军义务是不现实的。赫鲁晓夫对此作出的反应有些过激,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他攻击毛泽东是没有用的“老套鞋”,引发中共的强烈不满。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说明他为与西方达成协议,用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16]143。这一分析确有一定道理,苏共与中共的强硬外交路线拉开距离,可以反衬出其“和平共处”外交之诚意。实质上,赫鲁晓夫提出“全面彻底裁军”亦是一种策略,欲争取世界舆论逼迫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裁军,以达成部分裁军的退而求其次的目标,以保障“和平共处”目标之实现。在当时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是不可能的,尽管苏共对美提出“全面彻底裁军”的策略是正确的,但不应该强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承担同等的义务,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实质上,让中国游离于国际组织、国际条约之外,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灵活地应对西方的敌对政策。苏共片面承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裁军义务是错误的,极易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这是美国“和平战略”目的之所在。苏联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已经可以和美国相媲美,其周边安全有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拱卫,赫鲁晓夫提出的裁军问题顺应了世界人民的和平意愿,有利于提升苏联的国际影响力。而中共认为,苏联作为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故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后方,理应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援助中国及其他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是谋求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达成妥协。由此下去,苏共有可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走向“修正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大党的中共自认为有责任有义务阐明革命的立场和观点,帮助苏共认清自己的错误,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从列宁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阐明中共的立场,更容易被苏共理解接受,是帮助苏共的最好形式,因此,1960年4月列宁诞辰90周年的纪念文章正是可资利用的最佳资源,《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由此诞生。
二、《列宁主义万岁》的写作、出版及其影响
(一)“要反映革命”:列宁论著小册子的出版
1960年3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修正主义等问题的文章,并编辑成册,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前夕发表。22日、3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纪念活动和出版《列宁选集》、列宁有关论述集的编辑问题,他指出:“我们和苏联针锋相对的思想就是关于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列宁有关论述的小册子要认真推敲,要反映革命。”[17]4月11日-21日,邓小平多次召集彭真、陆定一、康生、陈伯达、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等开会,讨论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编选列宁有关论述集和撰写纪念文章的问题。这些论文集和文章是: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列宁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论战争与和平》、《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列宁论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陆定一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4月10日,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向对外文委、外文出版社、国际书店等部门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陈列和赠送“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等六本小册子外文版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国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编辑出版的6本小册子,已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出版了俄、英、法、德、日、西班牙文6种文字的版本。这6本小册子的外文版除应在各地外文书店和有外宾来往的机场、车站、旅馆、书亭、阅览室等处广为陈列外,各外宾接待单位可通过接待工作人员,在适当场合以适当方式,把这6本小册子外文版出版的消息告知外宾,并试探外宾是否要看,如外宾索要,可以赠送,如外宾没有主动索要,则不要勉强赠送。6本小册子的各种外文本由对外文委负责供应。[18]由此可见,中共开始主动对其他国家施加意识形态影响,最突出的是向外宾主动宣传、免费赠送,这种做法是很鲜见的。这些小册子也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三篇重磅文章的出台提供了理论准备和材料基础。
(二)“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写作、出版
为了从中共的视角阐释列宁思想,批判“现代修正主义”。4月初,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确定了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三篇文章的分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从时代问题切入,着重从理论上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阐述清楚,说明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着重分析当时形势,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和战争政策,强调只有斗争才能维护和平;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着重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和平过渡的观点,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三篇文章分工明确,各击一隅,彼此互应。毛泽东就写作原则作了指示:“文章要充分说理,对于我们要同他辩论的人们,要区别对待,要留有余地。集中指向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对苏联人的观点我们不要直接引用,特别不要用赫鲁晓夫本人的话。”*参见崔奇《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261页。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引用苏共的话,而是集中批驳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且篇末都强调要加强团结,但是三篇文章的论点却直击苏共中央外交战略的灵魂,即“和平共处”对外政策总路线,这是用团结的口号所无法掩饰的,当然也是中共不想掩饰的。
陈伯达领头的《红旗》杂志编辑部于4月16日第8期发表了社论《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2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牵头、吴冷西协助起草的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22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作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同时转播大会实况。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发表此报告。
4月21日,人民出版社向中央宣传部请示,打算把《列宁主义万岁》印成小册子出版,一来可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理论的需要,二来可以保存发表这篇文章的纪念意义。另外,想把《列宁主义万岁》、于兆力的《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并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以及在纪念大会上陆定一所作报告,编在一起,作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论文集出版。[19]256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包之静向周扬书面汇报:关于出版小册子文章排列的次序和书名问题,胡乔木与康生商量过,文章的次序可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书名为《列宁主义万岁》,[19]257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向邓小平提交了请示报告。后未加入于兆力的文章,由《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合订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出版,并译为英文、俄文、德文、日文、法文,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新华社等驻外机构在苏联、东欧及世界各国散发。[20]人民出版社的《列宁主义万岁》于1960年4月出版,小32开本,99页,62千字,印500,000册,定价0.20元。
(三)《列宁主义万岁》的精神和论点成为中共衡量政治思想是非的重要标准
《列宁主义万岁》的发表对国内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4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三篇文章的通知》指出:《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坚持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要求通过这次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高度发扬列宁的彻底革命精神,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六本列宁言论摘录可作学习的参考资料。学习时间和办法均由各地党委自行规定。[21]《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出版,引发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学习热潮,即使身在国外的留学生也按照中共的指示分批回国参与封闭的政治学习[22],《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精神成为中共衡量政治思想是非的重要标准。5月9日,文化部发出《关于结合学习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进行一次书籍质量检查的通知》,通知要求用三篇文章的精神和论点来衡量理论著作和通俗政治读物、反映现代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内容。科学技术出版物,也可以选择可能涉及这方面问题的书籍进行重点抽查。通知谈到,某些论点同文件精神违背的书籍不是没有。例如,在谈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时,片面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向公社社员宣传社会主义的通俗读物中,强调若干年后帝国主义不可能发动战争了;在翻译的文学作品中,宣传和平主义思想;等等。[19]258中共认为结合学习三篇文章对书籍进行一次质量检查是必要的,有利于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实质是清除苏共观点对中国干部群众的影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明辨是非,使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于中共中央的观点。
三、《列宁主义万岁》的国际影响
(一)针锋相对:苏联对《列宁主义万岁》观点的激烈回应
4月23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举行了万人集会,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列宁的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论点进行批驳。巧合的是5月1日,在美、英、法、苏准备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前夕,却发生美国U-2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此事成为《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观点的有力注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抓住时机转发了苏联政府的抗议,并发表评论支持苏联政府对美国挑衅的谴责。20日,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组织120万人参加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朱德、宋庆龄、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会议。但是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苏联政府深信,即使不是美国本届政府,就是下届政府,不是下届政府,就是再下一届政府总会明白,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以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想歪曲苏联立场的企图,是混淆不了世界舆论的视听的。至于谈到最高级会议,每个人都明白,通向这种会议的道路仍然是敞开着的。这就要看美国政府了,要看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了。美国政府破坏了会议,但是,原来应该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23]契尔沃年科讲话的主旨与大会的主题极为不协调,也昭示着中苏之间的思想分歧并未减少。6月2日,苏共致信中共,建议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机,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4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指出,考虑到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的形势,有必要更广泛地宣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里面所阐述的观点,要正面宣传,不是批判苏共或南共的观点。现在宣传更加有利,时机也很合适。美国蛮横的态度正是给我们一个好时机,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本质没有变,不能对它抱有幻想。[11]275-276按此方针,5日至9日,中国工会代表团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人理事会上阐述《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观点,遭到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退席抵制。16日,彭真率领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翌日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会谈。科兹洛夫指责《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理论是错误的,在北京世界工人理事会上宣传中共观点犯了组织错误。双方争吵8个小时,这让中共代表团有了不好的预感。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代表大会。22日,赫鲁晓夫与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会谈时,对中共通过各种途径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并对中共的“大跃进”、“百花齐放”、“斯大林问题”、“中印冲突”等政策提出了指责。23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信,此信早于21日以《通知书》的形式发给其他参会的党团,信中主要宣传苏共以和平共处为核心的观点,驳斥《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观点。会议后期苏共带头围攻中共代表团,逼迫中共代表团在会议公报上签字。中共代表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意签字,但散发了中方的五点声明,赫鲁晓夫对此十分不满。7月13日,科兹洛夫向苏共中央全会作了关于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若干原则问题上所持错误立场的报告。科兹洛夫对《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大加指责,认为这些文章是把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左倾空谈与片面解释列宁主义原理,说成是正统地捍卫列宁主义。[13]32416日,苏共中央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果的决议》,决定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会后不久,苏联政府即照会中国政府,指责中国向苏联专家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小册子,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苏联专家”,并说中国不尊重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劳动。特别强调:1960年5月19日,广州市的电工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向该所的苏联专家建议,就在专门印成俄文的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里所提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对这本小册子所登载的文章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一系列的苏联专家组里,中国的工作人员硬塞给每一个苏联专家一本这样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里,如所周知,登载着反列宁主义的论点,这些论点是苏联人所不能同意的。[24]以此为借口,苏联单方面决定召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7月25日,苏联政府不等中国政府答复就直接通知中国方面,所有在华苏联专家将在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全部撤回苏联,同时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25]216-217中方在7月31日复照中指出,《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阐述了中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立场。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中方从来没有把这些观点强加于任何人的意图。广州市电器科学研究所的中国同志,顺便问问苏联专家是否有兴趣看看这三篇文章,这表示在政治上对苏联专家的关心,并不能证明来照所说中国同志企图把苏联专家拖入某种他们所不愿意的辩论中去。[26]苏联领导人毫不理会中国政府挽留苏联专家的愿望,依然在一个月时间里,撤走了全部援华苏联专家1,390名,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217这导致中国大批受援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一些重大项目被迫中途夭折,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扩大到国家关系、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标志性事件,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党两国的关系。此后,双方论战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两党关系的中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的分裂。
(二)“渔翁得利”:西方国家捕捉到中苏关系的不和谐之音
美国对于中苏分歧的认识,是一个由发现苗头但不太确信到逐渐确认并制定政策分化利用的过程。从1958年起,美国开始注意到中苏之间出现分歧的迹象,但是没有找到更强有力的证据,并且怀疑苏共与中共制造不和的假象迷惑美国,以使美国作出错误的决策。美国远东事务助理饶伯森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莫斯科和北平已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单以期望和揣测为基础就决定我们的政策和行动,那将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27]1959年9月,美国得到消息称中苏关系极度紧张,但美国怀疑这是苏联有意策划的,以显示苏联与中国强硬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谋求赫鲁晓夫访美期间达成某种协议。同时,也找到可靠证据证实中苏在人民公社、中印冲突等重大问题上观点冲突,但美国依然认为这些矛盾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不会削弱中苏同盟关系的基础。[28]10月1日,赫鲁晓夫到访北京并发表讲话,强调“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紧接着中国国防部长发表了一篇调子完全不同的讲话。但杜勒斯依然认为中苏的冲突是潜在的,中共在公开场合是“赞同美苏联合声明的”。[29]美国认为中苏关系存在坚实的互利互惠基础,虽有矛盾但中共依然认可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1960年4月,《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发表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中苏交锋,使西方国家逐步确认中苏分歧的事实存在。西方媒体捕捉到《列宁主义万岁》与苏联倡导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和谐之处。路透社北京4月19日电指出,中共的“‘美国或其他帝国主义者’如果发动核武器战争,那么它们就要被毁灭,而绝不会是人类的毁灭”观点,与赫鲁晓夫所说的核战争将导致人类毁灭的思想格格不入。路透社香港19日电摘录《列宁主义万岁》中“老的修正主义当时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现代修正主义则企图证明列宁主义已经过时”*参见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第3545期,1960年4月20日(上),第21页。的观点,与赫鲁晓夫所说的“人们不应该闭眼看当时的具体条件,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在重复伟大列宁在十分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说的话’”[30]494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媒体认为,《列宁主义万岁》是中共对赫鲁晓夫同西方首脑可能在巴黎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讨论禁止核武器、和平共处和可能拟订一个左右东西方关系的行动准则[30]489等问题表示不同意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法新社北京19日电直接指向问题的实质:《列宁主义万岁》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全面攻击”,是一个宣传运动的顶点,这一宣传运动除了针对正式所说的敌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以外,看来还是直指国际和解的心脏的。[30]490西方国家已看出中共的长文“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公开倡导一种与苏联完全不同的路线,即23日法新社报道中重点强调的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关于革命的观点:“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30]491中苏布加勒斯特会议发生激烈争论后,西方国家发现赫鲁晓夫已经走向中苏争论的一线,即确认中苏分歧完全公开化。6月23日,英国《卫报》刊载佐尔扎的《赫鲁晓夫认真对待中国:帝国主义本性》一文,该文指出:布加勒斯特演说之所以值得注意,不是因为它回答了中国的论点,而是因为赫鲁晓夫先生现在已感到有必要亲自出马,而原先他是把对付中国挑战的工作交给他的下手做的。这很可能意味着,苏联领袖们认为有必要公开地表示他们不同意中国人的观点,不管这样做会给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造成什么样的风险。[30]49430日的西德《世界报》以《布加勒斯特的胜利》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想让赫鲁晓夫担当一个挥舞马刀的世界革命的先锋的角色。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切关于和平共处的胡说都只能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让卫星国的中央表示态度,让东欧国家领导干部准备着同中国有害的理论进行争论[30]493。苏共利用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必然遭致中共的激烈回应。合众国际社东京23日电指出,陆定一在北京举行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谴责“修正主义者”企图“模糊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间的区别,并在人民中间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利用所谓的积极共处作为一种招牌,企图以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伪善观点迷惑群众”,“妄图使人民放弃反对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对派的斗争,以便取消革命”。[30]4951961年8月8日,通过情报评估,美国认为中共是有意于1960年将中苏分歧公之于众,号召其他共产党反对苏联政策。由此确认中苏分歧“正在扩大”,[31]特别是得到苏联从中国撤离大批专家的有力证明。这种趋势的发展,会极大削弱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效率,这将给“西方提供可资利用和施加影响的机会,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获取重要的利益”。[32]
四、余论
《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体现了中共“革命化”外交思想的雏形,中苏论战的升级使之不断系统化,形成“革命化”外交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其思想成为辨别大是大非的价值标准。从中共“革命化”外交思想形成的过程来看,实质是对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提出新的外交战略的因应思想,并且通过双方的论战不断系统化,上升到意识形态战略的高度,导致中苏均将自己的思想视为本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的体现,不能妥协退让半步。双方都明确团结的重要性,但最终没能找到协调双方矛盾的沟通机制,导致两党断交、阵营分裂甚至兵戎相见。学界对中苏论战的基本评价,是“消极面”大于“积极面”,但是,其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历史经验,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一)最高领导人高度重视并参与意识形态工作
中苏双方的高层领导均亲自参与到意识形态工作一线。《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均经过毛泽东亲自把关,并且形成了中共官方发声的特有形式——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33]赫鲁晓夫更是亲赴前台发声,阐述苏联的新外交战略,从某种程度上引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和平共处”思想的重视,无论主动理解还是被动接受,基本达到统一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的目的,使其紧随苏联对中国进行斗争,同时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受关注度高,使世界各国难以忽视其外交思想的新变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4]充分说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二)制定外交战略要始终抓住“和平”的旗帜
和平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具有很强的人心凝聚力。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说:“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35]虽然有些片面,但世界历史的发展印证了“和平共处”政策的相对合理性和正确性。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已然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但不同制度的国家却可以和平共处,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外交思想虽几经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抓住“和平”的旗帜。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始终贯穿着和平的思想,这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理解、认可和支持,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将来依然是中国高举的旗帜并且是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
(三)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在国际事务中的延伸和体现,它与国家的核心利益紧密相联。邓小平始终强调中国的外交战略应该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基础,服务于国家利益。1989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36]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遍及全球,这增加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与竞争的机会。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时,必须坚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前提。作为现代国家在国际交往中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不能以牺牲他国利益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只能导致矛盾加剧,两败俱伤,甚至发生战争。这也就是2011年9月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所指出的:“中国多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积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只有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让更多人分享发展成果,世界和平稳定才有坚实基础和有效保障,世界各国发展才可以持续。因此,中国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与他国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真诚期待同世界各国并肩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37]
[1] 〔俄〕安德烈·马林科夫.我的父亲马林科夫[M]. 李惠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76.
[2] 〔苏〕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加里宁选区选民大会上的讲话[G]//赫鲁晓夫言论:第3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215.
[3] 萧洪,等.主编.20世纪世界通鉴:下卷[M]. 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2449.
[4] 〔苏〕H.C.赫鲁晓夫.没有武器的世界 没有战争的世界:第2卷[M].陈世民,张志强,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497.
[5] 〔美〕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M]. 董浩云,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184.
[6] 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艾森豪威尔在开幕会议上的发言(摘要)[G]//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16.
[7] 余忆飞,李小峰,罗锦贤.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309.
[8] 〔美〕阿兰·内文斯.和平战略 肯尼迪言论集[G].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19.
[9] 朱德年谱(新编本)(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544.
[10]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01.
[11]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2] 〔英〕彼得·琼斯,西安·凯维尔.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M].郭学德,朱耀先,黄飚,译.太原: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13]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三分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4] 沈志华,于沛,等.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539.
[15] 让伍修权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赫鲁晓夫的一段话[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8.
[16] 刘岩,李岳.中俄关系的大情小事(1949-2009)[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17]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537.
[18] 中国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对驻外使馆指示;苏联驻华大使举行电影酒会[B].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117-00765-08).
[19] 人民出版社关于编辑出版《列宁主义万岁》向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R]//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袁亮,主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20]阎明复.随康生参加华约首脑会议[J].百年潮,2007(4):13.
[21]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三篇文章的通知[M]//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58.
[22] 曹强.中苏大论战前后的留苏学子[J].湘潮,2010(10):38.
[23] 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苏联正义立场、反对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大会材料(中文、俄文)[B].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117-00784-02,1).
[24]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使馆给外交部的照会[B].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109-00924-01).
[25] 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26] 1960年7月31日外交部给苏联的照会[B].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109-00924-02).
[27] 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致代理国务卿赫脱备忘录[G]//陶文钊,牛军.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58-1972):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496.
[28] 情报与研究局局长(卡明)致国务卿赫脱备忘录[G]//陶文钊,牛军.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58-1972):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498-499.
[29]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20次会议备忘录[G]//陶文钊,牛军.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58-1972):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500.
[30] 方华,史册.大参考启示录 国事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1] 情报与研究局备忘录[G]//陶文钊,牛军.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58-1972):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503.
[32] 国家情报评估[G]//陶文钊,牛军.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58-1972):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512.
[33]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N]. 人民日报,1956-04-05.
[34]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35] 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R]//赫鲁晓夫言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38-39.
[36]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0.
[37] 中国的和平发展[N]. 人民日报,2011-09-07.
(责任编辑:袁宇)
ATalkontheWritingBackground,ProcessandtheInfluenceofLongLiveLeninism
WANG Zhen-you
(SchoolofMarxism,Re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OfficeofRecruitmentandEmploymentGuidance,NortheastAgriculturalUniversity,Harbin150030,China)
After World War II, USA and Soviet Union competed to uphold the banner of “peace” in order to contend for the control over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challenged by the total blockage and restraint by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ommunity headed by USA and the gradual estrangement from the socialism camp led by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of some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real rationality for China to adopt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overall “revolutio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uccessive pressure from USA and Soviet Un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ublished three articles entitledLongLiveLeninismin the hope of impell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ack to the track of Marxism-Leninism, which was opposed and retor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that accus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departing from the genuine Marxism-Leninism line. What is more, the Western countries came to be aware of serious divergences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 via their drastic theoretical confrontation and tried to profit from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ist camp.
New Chin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Union;LongLiveLeninism; major debates;diplomatic “revolutionization”
2014-09-01
汪振友(1979-),男,黑龙江双城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2012级博士生,东北农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苏关系史。
D829
A
1674-5310(2014)-11-01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