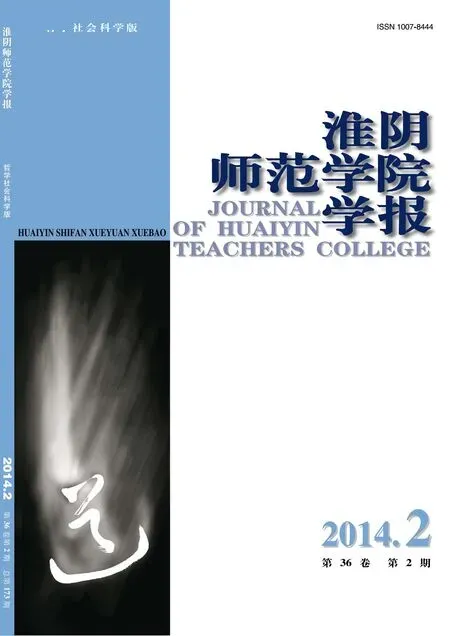成长小说界域辨析
2014-04-09张国龙
张国龙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成长小说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20世纪初引入中国文坛,称作教育小说。成长小说是一种着力表现稚嫩的年轻主人公历经各种挫折、磨难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小说样式。成长主人公或受到导引,得以顿悟,如期长大成人;或若有所悟,有长大成人的可能性;或迷茫依旧,拒绝成长,成长夭折。其美学特征可概略如下:1、成长主人公通常是不成熟的年轻人(主要为13-20岁),个别成长者的成长可能提前或延后;2、叙说的事件大多具有亲历性;3、大致遵循“天真→受挫→迷惘→顿悟→长大成人”的叙述结构;4、成长主人公或拒绝成长,成长夭折;或若有所悟,具有长大成人之质;或顿悟,长大成人,主体生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成长小说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学样式。一方面,它与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和人类社会学等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在文学内部,它既是成人文学中重要的一极,又是儿童文学不可规避的话题。成长小说的多元性生成了其边界的辽阔,同时也造成了作者、读者和一部分研究者对其疆界的庸俗化理解。长期以来,成长小说的疆域存在着过分广袤之瑕疵。本文就这一属于文学范畴论的问题予以厘定,希求为成长小说划分比较合理、明确的疆界,为成长小说的书写、阅读、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为成长小说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契机。
一、成长小说与成长主题小说
“任何关于成长的叙事,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不管是顺利的还是曲折的,也不管是同胞的还是异族的,都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它满足了我们每个人对自主、自强、自由的渴望和冲动。成长,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人类个体生命的重要体验,必然成为文学,尤其是小说,表现和探索的对象。”[1]在文学书写的诸多主题中,“成长”与“爱”、“死亡”、“生命”等一样,不但常写弥新,且具经典性和永恒性。显而易见,成长,成为重要的文学书写资源之一种。文学与成长的亲密接触,是一场场必然发生的心灵之约,是对自我/他者的一次次深度的窥视、体察和观照,更为文学/成长本身赢得了一次次凤凰涅槃式之契机。
根据上文对成长小说的概念界定,显而易见,“但凡涉及成长主题的小说样式就是成长小说”的观念有失公允。也就是说,成长小说是以书写“成长主题”为主旨的一种独特的小说样式,但并非涉及成长主题的小说样式都可划归入成长小说之林。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成长主题小说的性话语》一书中论及,“……相比较而言,‘成长主题小说’更契合中国当代小说书写‘成长’的实况。也就是说,中国当代小说对‘成长’的书写还处于‘成长’之中。许多文本虽落笔于‘成长’,但因缺少了‘成长小说’基本的美学要素,以‘成长小说’命名颇为牵强,而冠以‘成长主题小说’更适宜。‘成长主题小说’可看作是‘成长小说’的一种未完成状态,或者说是‘成长小说’的雏形”[2]。简而言之,但凡涉及“成长”话题的小说样式,可以“成长主题小说”命名;但凡符合“成长小说”基本美学规范的“成长主题小说”,乃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
二、成长小说与儿童文学
作为一种以“成长”为书写重心的小说样式,成长小说注定与儿童文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厘清二者之间的姻亲关系,本文需要阐释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
在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上,颁布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中,《公约》第一条规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低于18岁”。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儿童”即“未成年人”。与“儿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成人”,因此,“儿童”即“未成年人”的总称。其二,“儿童”的分类。很明显,“儿童”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从年龄结构和心理特征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幼年(0—6岁)、童年(7—12岁)和青少年(13—18岁)。由此可见,“儿童文学”是指为0—18岁的所有人服务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根据阅读对象接受心理与领悟能力的差异,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王泉根对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的划分,即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3]12。
所谓“幼年文学”(或称“幼儿文学”),是指为3-6岁的幼儿服务的文学(处于幼儿园阶段)。这一时期,孩子的生活主要是游戏,心智处于启蒙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别注重娱乐和趣味,丰富幼儿的语言知识,强调正面教育。写法简单、纯净、浪漫。主要文体形式有儿歌等。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叶圣陶)、《鹅》(骆宾王)等。主要是在成人的帮助下阅读。
所谓“童年文学”(或称狭义的“儿童文学”),是为7-12岁的儿童(小学阶段)服务的文学。此时期,孩子的生活以学习为主,富于幻想,求知欲旺盛。因此,童年文学注重想象与认识,以正面引导为主。创作方法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互补为特色。既有类型化的人物形象,又有性格丰满的典型。主要文体有童话等。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等。以儿童自主阅读为主,成人引导阅读为辅。
所谓“少年文学”,是为13—18岁(中学阶段)的少年服务的文学。此时期他们迎来了成长的黄金时节,生理/心理成长突飞猛进,如同化蛹为蝶。尤其体现在“性的成长”。他们将面临成长的诸多问题,迷茫、困惑、彷徨……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简单、幼稚日趋复杂、深刻。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皆进入他们的视野。此时期的文学注重全景式的生活描写,主要是讲述有关成长的故事。以少年小说为主体。比如,《草房子》(曹文轩)。
儿童文学中的“小说”,统称为“儿童小说”。它除了具备小说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儿童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按照不同年龄段读者的接受差异,儿童小说可分为“儿童故事”、“童年小说”和“少年小说”。其中,儿童故事属小说的雏形,多用拟人体,描写一人一事,简单、明了,读者对象为学龄前的孩子;童年小说多描写现实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注重故事性,以幽默、风趣见长,读者对象主要是小学生。少年小说多表现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生理/心理的旺盛成长,尤其注重描写他们个性、人格成长的心路历程。少年小说作为书写“成长”主题之一种的小说样式,亦属“成长小说”范畴。
在西方文学中,“少年小说”(Teenage Novels或Young adult fiction)是除“成长小说”外书写“成长”主题的重要文学样式。一般认为,这一文学概念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罗丝·威尔·德雷恩的《让风暴怒吼吧》是标志性作品。在此之前尽管已出现以少年为主人公专为少年人写作的小说文本,却未形成少年小说这一概念。专为少年人创作的小说大量出现在19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斯蒂文森的探险小说《宝岛》、《绑架》和《黑箭》,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历·费恩历险记》,以及托马斯·哈格斯的《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等。总之,少年小说属于少年文学范畴,是一种为13—18岁的孩子服务的小说样式。少年小说中的少年主人公大多进入了生理学意义上的“青春期”(Adolescence),是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被称为人生里程的十字路口。其突出的特点是生理、心理迅猛发展,尤其是“性”发育(包括性生理和性心理)的突飞猛进,又称为“性成熟期”。性意识的萌动、发展是少年人告别童稚岁月,跨入成人门槛的重要表征,亦是童年和少年的本质区别。由于处于青春期的儿童情绪不稳定,亦称为“危险期”。因此,少年小说应“特别重视美育与引导,帮助少男少女健全地走向青年,走向成熟……强调正面教育的同时,应注重全景式的生活描写,引导少年正确把握和评价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3]504-505。由于少年人的感知和认知能力较童年时期有了质的飞跃,阅读能力大大增强,少年小说除主要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外,还应适当尝试运用意识流、象征、哲理化等多种现代派创作技法,以增加作品的深度、厚度,既满足少年人旺盛的求知欲,又能提高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力和感受力。
综上所述,成长小说可归入少年小说范畴。但并非所有少年小说都是成长小说,只有少年小说中的部分作品(符合成长小说审美规范)是成长小说。中国的大多数少年小说只关注“成长”的某个片段,缺乏对成长的完整性描述,许多处于成长之中的主人公并没有长大成人。因此,这样的成长主题书写是不完整和不完美的。从对成长主题书写的深度来看,国内的少年小说文本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其一,描写完整、完美的成长状态。比如,曹文轩的长篇小说《青铜葵花》。小说讲述了一个令人备感温暖的纯美故事:在“文革”非常年月里,与母亲阴阳两隔的城市小女孩葵花,跟随被下放到农村的画家爸爸像浮萍漂流到大麦地村。不久,爸爸溺水而亡,葵花成了孤女。不幸中的万幸,哑巴男孩青铜一家收留了她。他们待葵花如同家人,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爱和呵护,让葵花很快忘记了丧失双亲的伤痛,重新找回了童年的无忧无虑。几年后,城里来人接葵花回城,葵花悲悲戚戚不忍离去。她走后,青铜终日坐在高高的大草垛上盼她归来。日复一日,奇迹终于发生了:青铜似乎看见了葵花归来的身影,极度的兴奋让他奋力大声呼喊她的名字。这个哑巴少年居然又能够开口说话了。小说着力展现了苦难岁月里苦难生存境遇和人生际遇中的“纯美”,包括苦难本身之美,即苦难是必然的、永恒的,面对苦难时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苦难之中漫溢着的善良、正直的人性之美,即平凡、朴实的青铜一家,给予了葵花真切的体恤和爱护。这份爱超越了血缘界线,因为无私、高贵而纯美;苦难之中少年相依相守的纯情之美,哑巴少年给予了伶仃孤女葵花无言的手足之爱,葵花和他心有灵犀,他们一起走过的稚纯岁月里,留下了一串串温暖的脚印。这纯美的真情真爱,驱散了苦难的阴霾,驱散了多舛命运的梦魇,甚至驱散了病魔的阴魂,从而照亮了成长的天空,被命运欺愚的成长得以“完整”、“完美”。
其二,作品描写成长的某一个片段。在文本结束时,成长者的个性、人格仍处于成长之中。比如,秦文君的《花彩少女的事儿》等。林晓梅等尽管逐渐褪去了童年时期的稚嫩,但她们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个性等方面,皆未能完成“化蛹为蝶”的质变。这样的作品可看作成长小说的一种未完成状态,本文将其命名为“成长主题小说”。成长小说是成长主题书写的最高形态,是成长书写最有效的文学样式。考虑到成长书写的复杂性和中国成长小说书写的具体情况,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和纠缠不清,本文把成长小说分成两大部类:其一,未完成的成长——描写成长片段的少年小说,或称成长主题小说;其二,成长完成——成长小说。所谓成长完成,是指展现了成长的完整过程,涉及成长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重点描写了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核心(标志性)事件,诸如受挫、离家、性成长、顿悟……成长主人公在经历了这些事件之后,并非按照经典成长小说模式那样一定会长大成人。但作为成长小说,一定要将成长的过程尽可能纵深地展现出来。
总之,由“成长主题小说”向“成长小说”进化,乃成长文学书写的演进轨迹。由于对成长小说理论认知的苍白,许多论者将“成长小说”和“成长主题”混为一谈。
[1]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
[2] 张国龙.中国当代成长主题小说的性话语[D].北京师范大学,2006.
[3] 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