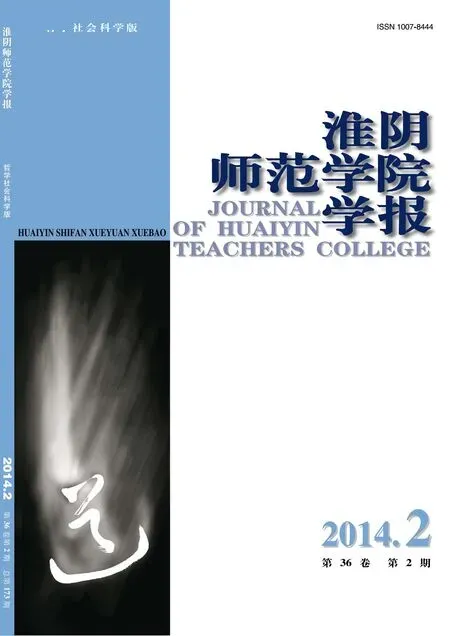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伤痕美术”与“伤痕文学”的对照解读
2014-04-09李徽昭
李 徽 昭
(1.淮阴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处,江苏淮安223001;2.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八十年代文化意识》在2006年分别出版与再版,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返八十年代”相互应和,“八十年代”逐渐成为一个历史化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文化热”、“方法论热”与“伤痕反思小说”、“伤痕美术”、“乡土美术”等系列事件与文化思潮,促进了“八十年代”和五四时期一样,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已初步确立了独立学科体系的美术和文学重新面向西方文化,不断探出渴切的目光,在西方现代思潮中张望、逡巡,也以此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术传统,而现代美术与文学的主题内容、艺术形式、理论演进互动交织,形成了美术与文学共通互融的80年代文化思潮,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
80年代首先由“新时期”开启,“新时期”之所以为“新”,首先应该是“伤痕文学”揭开了“文革”时期所遗留的历史“伤痕”,为新时期的发展演进打开了通道。不单是“伤痕文学”,“伤痕美术”在艺术主题、艺术手法上与“伤痕文学”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了“文革”后最初一段时间社会政治的解冻、思想文化的复苏。从当下来看,“伤痕美术”对于艺术形式的探索要远比“伤痕文学”更为自觉。由于“伤痕美术”主要采用油画的艺术形式,其架上绘画的“物质性存在”的历史意义和其视觉艺术的画面感所营造的历史空间已经远远超越了“伤痕文学”。
“新时期”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可以看作“八十年代”前期以及其中的一段时间,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新时期已经开始”[1]。
但此前美术界和“地下文学”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已经为“新时期”的开启打开了通道。在隐秘的渠道或者个体意义上,早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黄永玉所创作的毛泽东纪念堂坐像后面的全景式中国山水画(后以此制成壁毯)已经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这幅具有“卡通风格的全景式中国山水画”,“作品安详、浩大、宁静,没有宣传性的暗示,也没有对领袖的颂赞”[2]。卡通风格的作品消解了“文革”中惯常使用的写实性传统绘画风格,将中国山水画全景图案作了一定程度的归纳、夸张与变形,不仅与“文革”时期美术“红光亮”拉开了距离,也可以说在图案风格上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意义。黄永玉的这一作品并未公开展出过,黄永玉也“并没有因此项成就而获得荣誉”[2],但这一作品在美术思潮中可以看作超越了“新时期”内涵的现代艺术风格的初步尝试,也可以说,在某种公开的意义上,美术的形式探索已经超越了文学一小步。
新时期以“伤痕文学”打开了思想与文化变革新通道,毛泽东去世一年后,刘心武在1977年1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班主任》,一般将这视为“伤痕文学”的起点,随后1978年8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为“伤痕文学”命名提供了依据。在文学批评界的推动下,“伤痕文学”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潮流。尽管伤痕文学“用了‘文革’的叙事模式讲出了一个反‘文革’的故事”[3],甚至也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如程光炜所说,“‘伤痕文学’的不少作品是为‘落实政策’而写作的”。“‘十七年文学’仍然是它的重要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之一,二者在文学观念、审美选择、主题和题材诉求等问题上,是一种同构的关系。”[4]但“伤痕文学”“有着很多面向,也存在不同层次。就前者而言,其所触及的‘伤痕、’,有政治层面的、心灵层面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的缺失层面的,也有看似正常的社会组织和机体的内在空洞、信仰和观念的缺失、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等等”[5]。所以其影响不仅在文学界,而是打开了面向“文革”思索、反省的情感闸门,进而逐渐传播到社会文化界,对美术、影视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以视觉形式传递情感的现代油画,一些具有知青经历的油画家创作了一系列展现“文革”记忆的成功画作,后来被文化思想界称为“伤痕美术”。在文化意义上,“伤痕美术”并非仅仅是命名与主题上借用了“伤痕”一词,而是有着自己的艺术表现、绘画风格。“伤痕美术”不但在视觉意义上展现了审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文化与心理伤痕的新视角,更在主题表现、艺术手法上领先了文学一步,甚至也可以说,在现代艺术形式上,美术视野中的“伤痕美术”已经作出了视觉艺术形式上的重要探索。
“伤痕美术”多采用善于表现重大题材的西方油画艺术形式,主要“以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揭示它留给一代人的心理创伤”[6]。在创作主体的创作动机、绘画主题等方面可以说是对“伤痕文学”的一种呼应。作为一种艺术思潮,与“伤痕文学”一样,“伤痕美术的创作灵感也同样来自于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体验”,来自于创作者“文革”中痛苦的生活体验、情感与思想经历[7]。正如《农机专家之死》的作者邵增虎所说:
我在强烈的悲愤心情中作完了《农机专家之死》一画,我之所以悲愤,是感慨于像农机专家那样许许多多不该死的人都悲惨地死去了;而一些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人却还健康地活着——人们熬过来十年的苦难生活,文学艺术家们本该在生活中多多播种一些欢乐的情绪,引导人们向前看,可是我却又一次触及人们伤痕的心灵。[8]
这与卢新华创作小说《伤痕》的体会大致相近:
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我们的报纸杂志讲得最多的便是说“四人帮”将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我则忽然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贯穿始终的那条极“左”路线,给我们的社会造成的最深重的破坏,其实主要是给每个人的精神和心灵都留下了难以抚慰的伤痕。由此,下课后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有关《伤痕》的故事和人物便开始躁动于我的腹中。[9]
无论是美术还是文学,“文革”所造成的“伤痕”在文化意义上形成了“伤痕文学”作家与“伤痕美术”画家巨大的情感创伤与思想痛楚。面对社会、政治异动中的“文革”文化痛苦,创作者的思考主要来自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直观体悟与深切感受,也与当时社会政治层面对“文革”进行清算与政策落实互相呼应。总体而言,对“文革”时期个人经历和感受的深情表达是“伤痕文学”与“伤痕美术”创作者艺术表达的情感需要,也与当时社会政治主流思想贴近,这是“伤痕美术”与“伤痕文学”共同的创作动机。
除创作动机相似,二者艺术主题也极为相近。“对‘文革’事件和知青生活的批判与反思是早期伤痕美术中两个鲜明的主题”[7],高小华的《为什么》以“文革”中的四个人物为主体,一个受伤躺在地上,一个扶腮沉思,一个埋头似在疲惫地休息,画面中心人物的头上缠着绷带怀中抱着枪支,眼神面对着油画的观众,透射出由“文革”创伤而来的深切疑问: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样的民族悲剧?何多苓1978年创作的《春风已经苏醒》,标题即是主题,“春风”寓意着“文革”后的社会政治日益清明,已经取代了“文革”中非常政治的苦难悲伤。画面中,一个衣着破旧的小女孩在河滩上面向远方眺望,黑发在春风中浮动,寓意着希望的萌发,河滩草地虽黄,但已透出绿意。陈丛林1979年创作的《1968年×月×日》则直接呈现了“文革”时期两派之间武斗后的场面,负伤者被搀扶着处于画面中心,周围场景一片狼藉。这三幅画作对环境与氛围渲染比较多,人物表情也具有较为明显的情感色彩,有着文学性的情节冲突,与“文革”时期多数绘画的叙事性特点甚为相像,正如伤痕文学一样,也可以说是以“文革”美术中的某些惯性沿袭而来的审美意识在批判“文革”。
“伤痕美术”中还有罗中立的《父亲》、王川的《再见吧!小路》等其他作品,这些作品展现出与“文革”迥然不同的底层人物肖像,从另外一个角度贯穿着对“文革”与知青生活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主题与“伤痕文学”中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韩少功的《月兰》、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相一致。如卢新华的《伤痕》叙述了“文革”小将王晓华与“叛徒”母亲之间因“文革”而阴阳两隔的伦理情感,对“文革”有着深切的控诉,揭露了“文革”对普通中国人情感与生活造成的巨大心灵创伤。其他伤痕小说与油画作品也多直接或间接地对“文革”进行了控诉,在控诉中透射出在个人生活命运与体验基础上的对历史的深度思考,也间接地实现了文学与美术对现实的历史批判作用。在历史批判与思考中,伤痕小说中的文字情绪多弥漫着忧伤的氛围,伤痕油画的画面更为直观,人物情绪多显得忧伤与沉痛,因此“伤痕美术”与“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多数暗含着对“文革”状况与历史命运的一种感伤情绪。
在艺术形式上,“伤痕文学”与“伤痕美术”均有“文革”时期流行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处理方式。伤痕小说的叙事模式与“文革”近似,例如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从结构上看,“仍是一篇‘文革’模式的小说”。“《班主任》是张老师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作品中的主体,他领导好学生石红,团结以五学生为代表的广大同学,同受反动路线和错误思想毒害了的学生谢慧敏和宋宝琦进行斗争,最后以张老师充满胜利信心结束。”[3]这正贴合着“文革”文学的叙事手法,以英雄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唤起群众对反动路线、势力进行斗争,最终英雄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取得了胜利。到了小说《伤痕》中,尽管“‘文革’模式的几大基点全都被虚化了”,显现出小说艺术手法上的新进步,弱化了小说的政治性,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突出出来,但小说叙事总的基调依然是前后比较、忏悔的革命现实主义模式。与之相似,其后大量涌现出来的“伤痕小说”,如郑义的《枫》、金河的《重逢》、茹志鹃的《家务事》、肖平的《墓地与鲜花》、莫应丰的《将军吟》、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体上具有类似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安排的故事情节也多是前后对比突出路线正确的套路。
“伤痕美术”中的画面感突破了“文革”的“红光亮”,但就构图而言,罗中立的《父亲》、王川的《再见吧!小路》,与“文革”时期的主流绘画也未有多大变化。如果说有不同,那么主要是画面人物的主角由革命英雄人物换成了农民、知识分子、青年一代。值得审视的是,由于部分美术家的艺术自觉,对油画艺术语言作了较为大胆的尝试,也涌现出艺术手法与“文革”模式不同的美术家。例如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不再重视具有戏剧化的艺术冲突的环境,画家只是把视觉所察看到的人物直接列入画布中,在构图上,将“文革”时期重视场面与情节冲突的艺术形式作了改变,强化了画面的视觉效果,也走出了流行多年的美术写实套路,展现了另外一种真实。高小华的《为什么》尽管仍有情节性的画面形式,但在色调选择上,选用了铅灰色的调子,笔触也显得厚重,人物情绪显得低暗,而且采用了俯视构图,完全走出了“文革”时期“红光亮”的油画艺术形式的束缚。
在艺术手法探索上,美术是走在文学前面的。尽管油画的主题与“伤痕文学”相仿,但“伤痕美术”通过艺术手法的新颖处理所体现出来的情感更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画面中的人物气质、场面氛围带有一种浓厚的与政治拉开了距离的忧伤感觉,观众通过画面可以更为深切地感知时代的创伤,在面对画面时受到独特的艺术震撼,更为深切地思考人类的历史命运。这充分显示出“伤痕美术”所体现出的架上绘画历史性、丰富性的重要一面,也是美术发挥视觉艺术独特的社会功能的重要一面,因其如此,美术的社会功能影响一直延展到当下社会。21世纪的今天,当伤痕文学和伤痕作家们大多退出历史舞台,伤痕美术与伤痕美术家却日益受到中外艺术市场的共同青睐,而且陈丹青、罗中立、高小华等美术家持续爆发创造力,其影响也由美术界扩展到文学文化界,显示出强化了艺术性的美术独特的历史价值,而过于重视主题、忽视艺术性的伤痕文学则沦为社会变迁历史资料的悲剧处境。可以说,“伤痕美术”保留的历史画面更具有历史意义,其物质性存在也凸显出“伤痕美术”更多的文化反思价值。
这也不难理解,当20世纪90年代艺术市场启动时,陈丹青、高小华等重要画家的“伤痕美术”作品及手稿受到了收藏家的更多青睐,也拍出了极高的市场价格。而卢新华、刘心武等人的“伤痕文学”作品因为艺术手法的陈旧,已经令人不忍卒读,不再具有多少艺术价值,只能沦为文学史、社会史研究资料。这也深刻地体现出文学与美术在文化演进中承担角色的不同。或者说,伤痕文学一些“想象图景所赖以生成的美学资源,与‘文革’时期主流文学的资源其实并无根本的不同,这是由那时的相近的文化语境决定的”[10]。因此,文学敏感的思想神经触动了社会文化的新思潮,引领了美术主题与内容的探索,而美术在艺术形式上,由于独特的视觉艺术形式特点,受当时政治领域的制约相对较小,与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拉开了距离,有了更为良好的发展。
此外,由于文学与美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文化上的共通性,视觉艺术可以补充语言文字抽象思维的不足,加上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连环画具有大众性,在普及意义上可以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在“伤痕文学”兴起的时期,连环画艺术也开始介入到文学中,出现了一些以伤痕文学作品为题材创作的连环画,“如尤劲东的《人到中年》(1981),与陈宜明等的《枫》(1979)等,使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传播到社会基层”[11]。这也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文学与美术共同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艺术互补性。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伤痕美术”与“伤痕文学”,尽管它们都是“‘文革’后新现代性意识形态总体战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3],它们都共同地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当时政治的支持,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共同地以艺术的方式对社会履行着批判的功能,体现出与政治相互配合的辉煌篇章。但在细微的差别上,由于油画架上绘画的物质性存在方式,“伤痕美术”的历史记忆、文化社会影响要更为久远,美术的形式探索也更有艺术自觉的意义。在80年代话题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上,这一点应该凸显出来,这是美术意义上的另一个“80年代”,这个80年代中,文学与美术齐头并进,美术以形式上的探索显示出视觉艺术的独特价值,文学则在历史的检验中不得不沦为思想史、文学史的资料,这也昭示我们,在文学研究中,美术视角的关注与学科意识应该具有独特的价值。
[1]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N].人民日报,1979-11-20.
[2] [英]迈克尔·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M].陈卫和,钱岗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 张法.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J].江汉论坛,1998(9).
[4] 程光炜.“伤痕文学”的历史局限性[J].文艺研究,2005(1).
[5] 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J].当代作家评论,2008(3).
[6] 高名潞.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5.
[7] 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 邵增虎.历史的责任[J].美术,1980(6).
[9] 卢新华,汪建强.卢新华:直面“伤痕”的心灵直白[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8(3).
[10] 王一川.“伤痕文学”的三种体验类型[J].文艺研究,2005(1).
[11] 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