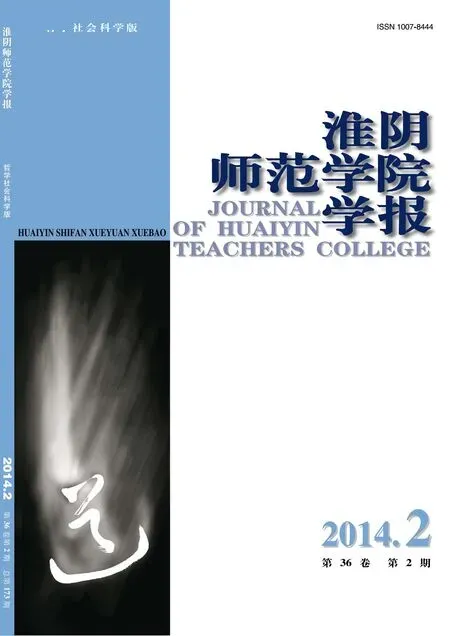阴阳五行与中国艺术
2014-04-09胡健
胡 健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223001)
中国古代的艺术有着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艺术的鲜明的审美特征,这个鲜明的审美特征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影响很大,它昭示给中国艺术以一种“仁的境界”;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也很大,它赋予了中国艺术以一种“游的精神”;而阴阳五行的学说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同样不能轻视,从一定程度上讲,阴阳五行学说由于是一种世界观,因而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艺术形象构成的基本审美特征方面,在这方面,它的影响甚至要比儒家、道家的学说来得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这不仅在于儒家与道家都是不排斥阴阳(五行)的,而且阴阳五行作为一套把天地人都包括在其中的系统的世界观与宇宙观,可以说渗透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政治、医学、建筑、军事、艺术,等等,甚至对我们的民族性都有很大的影响,而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艺术与审美的影响,正是本论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作为一种世界观或宇宙观,阴阳五行学说基本完成于汉代。从中国宇宙观发展的历史情况看,它有一个从最初如神话中反映的神性的宇宙观,到其后如老庄哲学中所反映的理性的宇宙观,再到其后阴阳五行的宇宙观的演变过程。阴阳五行的宇宙观虽然基本完成于汉代,但无论阴阳还是五行,其思想的起源都是很早的。殷商西周之际就出现了用阴阳或五行来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情况,其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即从《吕氏春秋》、《淮南子》到《黄帝内经》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阴阳或五行可以说才得以真正融合起来,而这种融合的基础则是“万物皆气”的理论。阴阳五行说把天、地、人都包括在其理论解说之中,而作为“五行之秀气”“天地之心”的人则是其中心。阴阳五行宇宙学说,后来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宇宙学说,而且也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基本的信仰,因而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广的影响。阴阳五行说对中国古代艺术与审美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综合考察。
首先是阴阳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阴阳二气是由原始意义的朝阳(阳光照耀)和背阳(阳光遮蔽)发展而来的,朝阳有利于作物的生长,背阳有利于作物的收藏,因此,阴阳的区分最初是与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与万物的生生化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到了《易经》阴阳有了哲学意味,《易经》中虽然没有出现“阴阳”的字样,但它却用“ ”“ ”来代表宇宙间两种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属性,这显然与阴阳的观念是一致的,所以《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阴阳学说用阴阳来表示宇宙天地间两种最基本的矛盾势力,进而又发展为表示事物矛盾对立的两种功能属性。阴阳伏根于气。“太极生两仪”,“太极”就是元气,“两仪”就是阴阳二气,这也就是说阴阳二气也是由元气生出的,而且,太极就是阴阳,宋代周濂溪对此有很好的解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这也就是说,事物呈现于当前,便是正面或阳面,它必然有与之相联系、相作用、相影响的背面或阴面,正反阴阳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就构成了全部的世界。“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学说认为,宇宙间万物的发展变化的原因,就在于事物内部有阴阳两种对立因素在相互起着作用。而要体道与悟道,就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或阳面,还要体察到事物的背面或阴面,这就不能仅运用感知,而且还要运用想象,才能由正面或阳面而进入背面或阴面,才能真正全面地体道与悟道,而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玄览”。
阴阳学说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影响是非常深广的。在著名的太极图中,阴为虚为白,阳为实为黑,而在中国古代艺术中阴阳的对立互用主要体现为艺术形象的虚实与显隐的对立互用。“虚实相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创造方法与美学原则。先看绘画。如果把中国古代的绘画与西方古典绘画相比较,就可以发现,西方古典绘画常呈现为一种感觉上的逼真性,即实体上的假中似真,而中国古代的绘画形象的特点则在于,它呈现为要靠人们的想象才能生活起来的虚实相生性。中国古代绘画“以山水画为上”。清人蒋和在《学画杂论》中说:“山水篇幅以山为主,山是实,水是虚。”中国的山水画画幅上往往并不画满,它讲究有实有虚,所谓实画山而虚画水,画上一些,空着一些,而这些空却不是“非画”,相反,它就如清人张式所说:“烟云渲染为画中流行之气,故曰空白,非空纸。空即画也。”(《画谭》)“空即画也”,这可以说是中国绘画的重要特点。清人笪重光对这一特点也有很好的解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观。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论画》)在阴阳观念影响下的“虚实相生”可以说就是中国绘画创造艺术形象的基本法则,宗白华先生对此曾有深刻的分析:“中国人的根本的宇宙观是《易经》上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画面的空间感也凭借一虚一实、一明一暗的流动节奏表达出来。虚(空间)同实(实物)联成一片波流,如决流之推波。明同暗也联成一片波动,如行云之推月。这确是中国山水画上空间境界的表现法。”[1]72再看诗歌。伏根于阳阴对立互用关系上的“隐显互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形象创造的基本方法与美学原则。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艺术形象的隐显关系作过深入的探讨,南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中曾引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的二句佚文:“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秀”就是“显”,它是就艺术形象具体的显露的部分而言的,刘勰认为:“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秀以卓绝为巧”,而“隐”则是就艺术形象中寄寓着的言外之意而言的,正如刘勰所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故“隐以复意为工”。在刘勰看来,真正好的诗文必须是有秀(显)有隐的,隐秀(显)互伏才是诗歌艺术形象基本的特征,只有“隐显(秀)互伏”的艺术形象,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且以唐人元稹的《行宫》为例:“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首诗以寥落的古行宫、寂寞的宫花与白头的宫女为艺术形象的显的层面,但这个显的层面却了无痕迹地暗含与潜伏着一个重大历史与人生流变的隐的层次,正因为显(秀)隐的互伏,这首诗才真正达到“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境界,就如清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所说:“只四语,已抵一篇《长恨歌》矣。”可见诗歌的艺术形象只有显(秀)隐互伏,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审美价值,只有显(秀),或只有隐,那是无法形成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的。其实,何止是中国画与中国诗呢?虚实相生、隐显(秀)互伏的创造方法或美学原则可以说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各种门类的艺术的形象创造中的,讲究“计白当黑”“书天地之阴阳”的中国书法艺术是如此,把“虚(水)实(山)相济当作造园艺术的一项基本原则”的中国园林艺术是如此,强调“以鞭(实与显)代马(虚与隐),以桨(实与显)代船(虚与隐)”“一个圆场(实与显)数十里(虚与隐),八个龙套(实与显)十万兵(虚与隐)”的中国戏曲表演艺术是如此,就连微小的印章艺术也莫不如此……可以说,受中国古代阴阳学说的影响,中国古代艺术是把虚实相生、显隐互伏当作艺术形象创造的基本方法与美学原则的,所以,中国古代成功的艺术形象总是具有实里含虚,虚实相生,显中带隐,显隐互伏,从而虽虚亦实,虽实亦虚,似隐还显,似显还隐的美学特征。这种虚实相生、显隐互伏的创造手法与美学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中阴阳对立互用原理在中国艺术创造方面的具体体现与运用。因而欣赏中国古代艺术,不仅要重感知,更要重妙悟(想象与思想),其道理就在这里。这也是中国古代艺术与讲究审美幻觉上的实体性与逼真性的西方古代艺术不尽相同的地方。
其次,五行与阴阳五行学说。“五行”说的起源也很早,一般认为,“五行”源出于殷人对“五”的数字崇拜。最早明确提出“五行”的是《尚书·洪范》篇。西周末年,史伯始创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又以“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为说。它在先秦的发展依次经历了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并列、相杂、相克、相生等阶段。春秋末年,五行相克(相胜)的观念开始出现。五行与阴阳结合起于《管子》与《礼记》。《礼记·月令》不仅把阴阳与五行联结起来,而且还把四时(春、夏、秋、冬,或表述为春、夏、季夏或长夏、秋、冬)、(地上)五方(东、西、南、北、中)、(天上)五官(东、西、南、北、中)与五行配搭起来,而且把种种自然事物以“五”归类,分别纳入“五色”、“五音”、“五虫”、“五脏”之属,然后也与五行、四时等相匹配,从而构建起一个关于宇宙世界相互联结、互相推荡的完整自然哲学体系。而人则禀阴阳而体五行,所以,《礼记·礼运》称:“人者,天地之心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中说:“天地阴阳金木水火土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并依阴阳五说的说法,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阴阳、四时、五行在相互联结中给出的规则为依据。阴阳五行家不仅以“阴阳”的观念说明了自然世界的复杂关系,而且还借着阴阳五行编织出了一个贯穿自然与社会的宏大宇宙图式。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中,宇宙包括人事,按阴阳五行的法则组织成一个大系统,万事万物依一定的格式发生普遍的联系,它们同受四时与五方的影响,具有相同的阴阳五行结构,又各自形成一个小系统,依照一定的节律运行、变化。因此宇宙中存在着普遍的相似性,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都具有与宇宙相似的全部特征。这就如《吕氏春秋·情欲》所说:“人与天地也同,万物其情虽异,其情一体也。”(在阴阳五行宇宙一体化的基础上,自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说,在这种宇宙图式中,“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时间给空间化了,空间给时间化了,不仅如此,这里的宇宙还具有“盘桓往返”“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合一的特点。因此,阴阳五行宇宙观可以说是一种生命化与音乐化的宇宙观。
阴阳五行这种重整体关系重整体功能的生命化与音乐化的宇宙图式,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时空意识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与巨大的。中国艺术中的时间不是直线的,而是往复的;空间不是无际的,同样也是往复的。“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杜甫的诗句很好地表现出了作为“天地之心”的人——中国古代艺术家们在体察宇宙万物时,所采取的“随心”与“游目”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艺术家要用心灵的俯仰的眼睛来观看时空中的万象,因而他们的眼睛从不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从而去把握全境的阴阳开阔、高下起伏的节奏,来组织自己的艺术境界。因而,中国古代艺术家所把握的时空意识与西方艺术表现出的那种心往不返而目极无穷式的不同,它是“无往不复”,“返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式的。宗白华先生对此曾有很精彩的分析:“我们的诗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像那代表希腊空间感觉的有轮廓的立体雕像,不是像那表现埃及空间感的墓中的直线甬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1]83以中国画为例,它的时间与空间从不是无始无终的直线延伸,而总是表现为一来一往、一盛一衰的曲线回环。历代的画家对此都有很好的论述。如南朝的宗炳就曾主张:“竖划三寸,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画山水序》)宋人张怀邦也曾强调:“蕴古今之妙而宇宙在乎胸,穷造化之源而万物生于心。”(《山水纯全集·后序》)明人董其昌则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画禅室随笔》)中国古代画家作画时总爱“仰观俯察,远近游目”,而画幅则追求着一种“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音乐般的境界。再以中国诗为例。不妨看一下杜甫的《秋兴八首》的第一首:“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连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在这首诗中,有近景也有远景,有仰观也有俯察,同样给人展示了一种“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音乐般的时空境界。诸如“海上升残月,江春入旧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些诗句也都莫不具有“仰观俯察”“循环往复”“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审美时空方面的特点与意趣。由上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古代艺术总是从有限中来显出无限的,而又是于无限中来回归有限的,它的意趣不在于一往而不返,而在于回旋而往复,《易传·卷二·泰第十二》中所说:“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因而中国古代艺术中表现出时空意识便如宗白华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不复是几何学的科学性的透视空间,而是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趋向于音乐境界,渗透了时间节奏。它的构成不依据算学,而依据动力学。”[1]210中国古代艺术时空方面的这一重要审美特征,或者说中国古代艺术的独特的审美时空意识,显然是与不重实体而重功能与关系的阴阳五行宇宙图式的影响密不可分的,而且可以说是以此为形而上的基础的。
还有气的学说。如前所说,阴阳与五行的思想之所以能融合在一起,关键在于气的学说,可以说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都是建筑在气的学说的基础上的,或者说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都是以气的学说为其基础的,这就是它们能够融合到一起的原因。“万物皆气”,“天地一气”。气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根本,因为气既是宇宙的根本,也是宇宙的运动。“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公羊传·隐元年解诂》)“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张载《正蒙·乾称》)在中国哲学家看来,是气生出了宇宙,气化流行,形成万物,而天地万物,气聚而成物,气散而形亡,从而又复归于宇宙流行之气,生生不息。“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礼记·礼运》)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人在宇宙中有着崇高的地位,是“天地之心”。因而,气不仅体现为宇宙的特点,而且也影响着中国思维的特点。正像张岱年先生指出的:“气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气非无,乃是有;气又非形,乃是无形之有而能变成形的。”[2]这也就是说气是可感而不可见的,是一种灵动的虚体,它很有些像老子所说的不可言说的道。气的哲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在于,使中国美学在形状之外,而更重视情、神、韵、态这样一些灵动的虚体的东西,并把这种“灵动的虚体的东西”视作比表面可见的形体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宗白华先生在分析中国画时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画的光是动荡着全幅画面的一种形而上的、非写实的宇宙灵气的流行,贯彻中边,往复上下。”[1]71“这说明中国人的宇宙观……是虚灵的,是出没太虚自成文理的节奏与和谐。画家依据这意识构造它的空间境界,所以和西洋传统的依据科学精神的空间表现自然不同了。”[1]93
受中国哲学中气的学说的影响,中国古人把“气韵生动”视作中国美学的崇高境界。“气韵生动”就是强调艺术在表现对象时,要突破人为的束缚,表现出事物的本真,表现出事物的自由自在与多姿多彩。“气韵生动”最先是由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物画一旦超出“空陈形似”的水准,而表现出了所画人物内在的“风神”“韵度”“神态”,就达到了空灵的“气韵生动”的崇高境界。随着后来山水画的兴起,在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山水居要”的情况。“气韵生动”也随之由对人物画提出的美学要求,转变为对山水画提出的要求。如前所说,气既是宇宙中的一切生命的根本,也是宇宙中的一切生命的运动,所以气是中国宇宙观的根本。“山水以形媚道”,“以一管似太虚之体”。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家莫不视这虚体的空灵的气韵为山水内在的生命。清代唐岱说:“自天地一阖一辟,而万物之成形成象,无不由气之摩荡自然而生。画之作也亦然。”(《绘事微言》)清人石涛说:“天地浑熔一气。”(《题画》)黄钺说:“栩栩欲动,落落不群,空兮灵兮,元气氤氲。”(《二十四画品》)……所以,随着“山水居要”的绘画风气的兴起,作为品评人物画的美学范畴的“气韵生动”便被挪移到了山水画上了。元人汤垕说:“山水看气韵”,(《画鉴》)明人王世桢说:“山水以气韵为先”(《艺苑卮言》),唐岱说:“画山水贵乎气韵。气韵……是天地间真气……有气则有韵,无气则板矣。”(《绘事微言》)汪柯玉说:“所谓气韵,乃天地之英华。”(《跋六法英华册》)清人王昱也说:“元气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画外者为上称。”(《东庄论画》)宋荦说“蟹爪树枝鬼面石,河阳大幅太行图,挂起淋漓元气在湿,真成惊倒倩人扶。”(《论画绝句》)方薰说:“气韵生动为第一义,然必以气为主,气盛则纵横挥洒,机无滞碍,其间韵自生动。老杜云:‘元气淋漓幛铸湿’,即气韵生动。”(《山静居画论》)由上可见,从人物画到山水画,中国绘画所追求都不是西方古典绘画所追求的那种模仿与感觉意义上的逼真,元气淋漓而生动远出的空灵境界才是它真正的审美追求与崇尚。这就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庄子:天,积气也)。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中国画的主题‘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1]110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绘画在中国古代气的学说的影响下,自然地把“气韵生动”当作了自己的最高的美学原则,它表现出了中国古代绘画并不太重视形似却更重视情、神、韵、态这些虚体的灵动的东西的美学特征。
阴阳讲和,五行也讲和,阴阳五行对和的重视对中国艺术也产生了深广的影响。阴阳学说认为,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阴阳学说也讲阴阳之间的“搏”、“争”,但其基本的关系却是互根与互助的,阴阳学说认为,阴阳的调和才是变化成物的依据,而且,阴阳学说还把阴阳的协调发展理解为阴阳之间的反馈与调节,认为阴阳之间能够通过相互约制和补充使阴阳保持动态平衡,而这种平和的状态正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理想条件,也是万事通用的处世原则。五行的结构在形式上与阴阳不同,但是在指导思想上二者却是相通的。五行理论认为事物的五行结构之间,在一般情况下,有生有制,相胜相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这也是一种理想的平和状态。但由于外力的干扰,可能使五行出现太过或不及,使其间的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因而造成灾难。这种超出正常的灾害作用被称为“胜气”,在这种情况下,五行结构内必定会产生出一个与之方向相反能量相等的反作用,使五行的结构再归于平和,这种反作用力被称为“复气”。五行理论把这称为“子复母仇”。西方哲学家也讲和谐。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才能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3]显然,西方的和谐观与中国阴阳五行的和谐是明显不同的。西方的和谐观是以矛盾双方相互斗争为基础的,它的和谐是斗争带来的新的和谐。阴阳五行的和谐观强调的却不是矛盾双方的斗争,而更多的是强调矛盾双方的互补与相济,这是一种由中和带来的和谐。阴阳五行的和谐观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影响是很大的,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同样是很大的。
中国古代与西方古代不同,它讲究以理节情,不追求过于强烈的对比,而更讲究适度的平和或中和之美,这显然是与阴阳五行理论的影响分不开的。中国传统音乐很少像西方交响曲那样冲突狂放,中国古代音乐总是在强调“音亦有适”,强调“中声”,强调“凡乐,天地之和,阳阳之调也”(《吕氏春秋·大乐》),而反对所谓的“隆音”、“侈乐”、“糜音”。中国古代音乐对平和或中和之美的追求显然是与阴阳五行的和谐观分不开的。阴阳五行的和谐观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也很大。这里以紫禁城(故宫)为例。紫禁城的建筑布局完全是按照阴阳五行说来安排的。世界上的一切皆分为阴阳,紫禁城“前朝后市”的整体布局就是依“一阴一阳以为和”来安排的,“前朝”是阳,“后市”为阴,一阴一阳以为和。世界上一切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因素构成,地上的方位也分作东、西、南、北、中五方,天上的星座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宫,颜色分为青、黄、赤、白、黑五色……五行说把五种因素与五方、五宫、五色等联系起来组织成有规律的关系。例如天上五宫中中宫居于中间,紫微星又处中宫之中,是天帝所居,地上的帝王既然自称天子,其居住的宫殿则被称为紫禁城,与天上紫微星相对。还有,紫禁城原处北京故城的中心,故又有“东、西、南、北、中”的居“国之中”的寓意;紫禁城中的用色,除依东青、西白、南朱、北黑的说法外,更以黄为主,因为黄色是中央之色,是土地之色,在古代社会土地是具有特殊地位的,所以黄色成了五色的中心,紫禁城所有的宫殿屋顶都用黄色琉璃瓦这就不奇怪了。紫禁城所体现的艺术境界正是一种“天、地、人”太和的境界,这种境界与阴阳五行的和谐观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与西方体现的人神相分而相和的充满斗争与象征的基督教教堂的和谐是完全异趣的。这正像楼庆西先生指出的:“如果说西方古代建筑艺术主要表现在个体建筑所表现的宏伟与壮观上,那么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主要表现在建筑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博大与壮观上。”[4]还有戏曲。西方的戏剧以强调斗争与灾难的悲剧为主,而中国的戏曲却喜欢大团圆的结局,这显然也与中国人的和谐观有关。中国人在五行相生相克思想的影响下,具有一种“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时间一到,一切全报”的信念,这就使得中国的戏曲中大团圆的喜剧多于悲剧,因为喜剧更为平和,也更能满足与安慰人心。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说儒家思想昭示给中国古代艺术以“仁的境界”,道家思想赋予中国艺术以“游的精神”,那么,阴阳五行学说则催生了中国古代艺术形象虚实显隐互伏互用的创造方法,启迪了中国古代艺术“宇中有宙,宙中有宇”的生命化与音乐化了的审美时空意识,孕育出了中国古代艺术重视虚体的灵动的“气韵生动”的审美崇尚,催生了中国古代艺术以平和为美的审美理想……而这些也对应地要求人们在欣赏中国艺术时心须具有一种重想象与领悟的“玄览”的审美心态。可以说,中国古代艺术中的许多重要的基本的审美特征的形成与特点,都可以从阴阳五行的学说中找到很好的理论阐释与把握。
[1]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0.
[3]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19.
[4] 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M].北京:三联书店,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