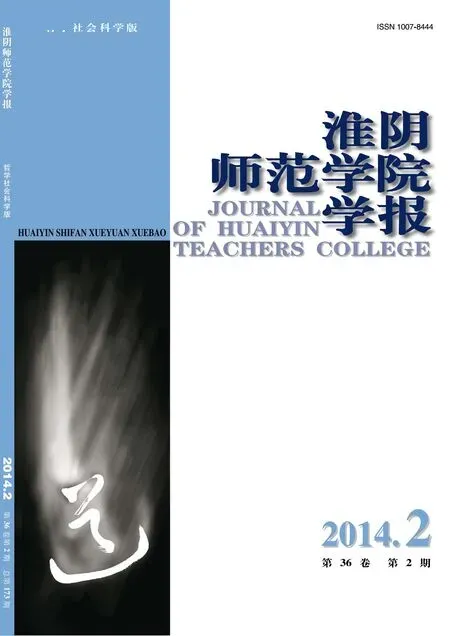汉画中祈禳巫术考释
2014-04-09朱宏亮刘振永
朱宏亮, 刘振永
(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江苏淮安223001)
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把行使神仙方术的人称为“巫觋”“方士”,这些人声称自己能通神飞升成仙,采用的许多手段均与巫术有关。两汉间对“方士”的称呼逐渐改为“道士”。虽然自战国起巫觋的地位在官方开始跌落,但在民间仍有极大的影响力。秦汉时,不论是宫廷还是民间的婚丧嫁娶及其他各种重大活动都活跃着方士、道士的身影。在丧葬中更是离不开方士、道士的主持,在汉画像中出现的道士形象,其主旨便是帮助升仙、解除等活动。在四川南溪县长顺坡砖室墓3号石棺右侧画像中,仙人半开门图的,门口有一着宽衣长袍、手持节杖的人。节在汉代是使者执行朝廷任务的凭信,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道士身份就像使者,可以往来于人、神、仙之间,此图中道士驾着神鹿来到西王母跟前,帮助墓主求赐仙药,很显然这种往来神人间的神通便是一种巫术。大通县董场乡建木羽人画像砖,画面中间有一穿交领衫者,头戴树枝,身插羽毛,极似一位正在降妖作法的方士或道士。葛洪在《神仙集》中说:“有召神劾鬼之法,又使人见鬼之术。”[1]由古代文献和汉画可知,汉代道士在丧葬环境中已相当活跃。[2]在梁代刘勰的道家三品中,下品称为下袭张陵,即指活跃于民间的做法道士。道安《二教论》亦云:“……三者符箓禁厌。”在道教中第三品便是祈禳方术。张陵曾客居蜀地,学道于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符水疗病,传行气、导引、房中等术。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令病人叩首思过,以符水给病人喝,病好了就是信道,不好,便是不信的验证。由此可以看出汉代道教主要流行于下层民众中,已具有严密完整的宗教组织系统,在修持方术上,仍保留大量驱鬼祈祷的巫术性质。
一、汉画像的巫术性质
为丧葬制度服务的汉画像艺术,主要任务是为墓主升仙长生禳除不祥而制,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早期道教的精神、思想和手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在众多画面中,则体现了道教的修持方术和巫术。
在以往汉画图像意义界定中常出现很多歧义。对于最常见的几大母题如中央拜谒图、车马出行图、桥上战斗图、泗水捞鼎图、庖厨图等,均有不同的见解[3]。近些年有专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①如巫鸿提出汉画的研究应注重在仪式中揭示意义;朱青生提出应关注各种器具和装置在特定环境中所体现的意义。,希望能有所突破。由于汉画像依附于墓葬建筑,是汉代丧葬制度的产物,汉画像艺术的民间性和早期道教的民间性相融合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运用巫术原理解读分类汉画像内容,可以使许多问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巫术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巫术凭借浓厚的民间信仰参与了传统中国文化品格的塑造。在中国文化底层一直涌动着巨大的巫术暗流,这股暗流平时潜伏着,遇到合适的时机,它便泛至文化之河的表面。道教是由阴阳五行学说、黄老学说、民间鬼神信仰等构建起来的非常驳杂的宗教体系,其创建主要是由巫师完成的,因此道教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大量的巫术因素[4]。最早的道教组织天师道、太平道、五斗米道皆以“鬼道教民”,以“符水咒说”为人治病,或以“造作符书”等巫术手段,把驱鬼降妖、祈福禳灾视为自己的使命。巫术虽然不能等同于道教法术,但却是道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的最终目标是成仙,是使个人肉体和生命永恒不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研究祈福禳灾、祛病延年、长生不死的各种法术。长生成仙的目标促进了道教中包括巫术在内的各种技艺的发展,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对成仙不老的技术热情或者说是巫术热情。
中国古代巫术依据的原理主要有两种:一是关于操纵控制超自然的观念,二是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观念。英国著名民族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对此类巫术作了细致的分析。他将超时间和距离的相互感应的巫术统称为“交感巫术”。“交感巫术”形成有两大原理:“相似律”原理(由此产生的巫术叫“模拟巫术”)和“接触律”原理(由此产生的巫术叫“接触巫术”)。依据以上巫术原理,从广义上则可以认定,整体汉墓建筑包括附属的汉画像及陪葬物品均是一种巫术行为,如坟丘和所谓宇宙结构式的墓室,属于形体的模拟;汉画中的升仙、现实生活是对人间的慕仙和理想现实场景的模拟,这应属于顺势巫术。祥瑞和辟邪则运用了超自然神力和交感巫术相结合的原理来施展威力。限于篇幅,本文将狭义的巫术限定在祥瑞和避邪及现实生活、升仙中的部分图像上。
二、汉画像中祈祥的巫术表现
在汉代祥瑞表达有多种含义。一种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祥瑞:凤凰来仪、黄龙出水、宝鼎再现、醴泉突涌等现象是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象征[5],此类祥瑞是“受命之符是也”,被视为上天继续庇佑汉代统治者的证据。在汉武帝时只见过10种祥瑞,到了章帝时则出现了29种祥瑞,其中包括麒麟、凤凰、青龙、白虎、大尾狐、三足鸟、连理树、神鼎等①董仲舒:《春秋繁露·符瑞》(卷6)。。祥瑞被方士赋予巫术性,反映在墓葬环境中,同样表达了墓主人对死后世界的道德理想、政治观念。公元前110年,武帝在封禅泰山时,让人将远方进贡的珍禽异兽放满漫山遍野,营造了一个仙界的景象,希望以此来感召神灵显现。祥瑞观念并不仅是汉代统治阶级玩弄的政治权谋,而是汉代社会一种既强烈又普遍的现象。墓葬环境主要是表达个人升仙长生愿望的地方,用祥瑞来营造仙境,在当时应是最重要的一种道具。
汉画像中的祥瑞主要有动物、植物、云气纹等,这些祥瑞图形多是参差并置在汉画像中。《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125、126、127是邹城市高庄乡金斗山出土的一批画像石,刻绘了西王母、东王公、九尾狐、龙、熊、独角虎身怪兽、双人头怪兽及周围的云气缭绕,构筑了一片仙境、人境不分彼此的永生之境。江苏睢宁县旧朱集九女墩墓门楣上刻羽人、祥禽瑞兽和双龙缠绕;西门扉上刻凤鸟,下刻铺首;东门扉上有仙人戏凤,下刻人、铺首衔环;中室壁和前门正中刻祥禽瑞兽、龙、鱼、鸟等,其他部位均有祥禽瑞兽图像[6]。另外表现祥瑞图像比较密集的还有苍山城前村元嘉元年墓、沂南汉墓等。还有很多墓、祠、阙、棺等汉墓构成物件,均在不同部位装饰了大量祥瑞类图像,它们所表达的巫术意义历三百多年的发展,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异性。生命永生是一大主题。为了达到永生的目的,汉墓中设置了祥瑞之物,以期得其护佑而得到心灵的安宁。
在汉画中除了常见的祥禽瑞兽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图形符号作为灵异之物,如:宝鼎、胜、摇钱树、灶、井等频繁出现,兼具有其他巫术功能。汉画中表现升鼎的有西王母前置鼎、升鼎或衔鼎,鼎旁立人。《史记·封禅书第六》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盘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7]由此可知汉代人认为鼎可助人升天。另外在道教中鼎是重要的炼丹工具,在画像中刻画鼎的形象应是表达墓主升仙的巫术祈求。“戴胜”是西王母的象征,胜一般戴在西王母头上,有时则刻于墓中门柱、门楣上。胜纹代表仙界,作为一种神异图像,表达了汉代人死而复生、生命永恒的愿望。在山东安丘董家庄墓中壁龛上、四川中江白果乡神仙洞崖墓壁龛上、四川宜宾、泸州的石棺上等都能看到这一神秘符号。胜纹作为仙界的象征,其具体来源和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中国古代有一种古老的游戏叫“六博”,盛行于先秦两汉,现已失传。汉画中博弈的棋盘即“式盘”或“式图”。先秦两汉流行的宇宙模式是天圆地方“盖天说”。大地是向四面八方的延伸平面,天穹下掩而与地平面相切,其俯视平面图可以看作方圆叠合的平面,式即是这种理解的模拟[8]。式是宇宙的抽象二维模拟,汉墓结构则是宇宙三维立体模拟。古人发明这个模型,主要是借它作神秘推算,以便沟通天人、人神。六博在汉画中也是常见的主题。六博是人间的游戏,但古籍和汉画中常见仙人之间的博弈。《风俗通义·正央》:“武帝与仙人对博,棋没石中。”式图代表着模拟宇宙的同时,还具有祈祥的神秘含义。
摇钱树形象常和西王母、佛的形象相混,何志国认为其体现了汉代人对财富的赤裸索求[9]。四川茂汶出土一摇钱树,枝上部是西王母和其两侧的阙形天门,天门外有一人正担着方孔圆钱离去,表明此人之钱是从天门之树上所得[10]。摇钱树除了代表求财心理外,钱的外圆内方的宇宙模拟和西王母、佛等大神的存在,更多表达的应是天人、人神相通相感,求吉纳福的巫术观念。
仓、灶、井、厕作为明器模型,是汉墓中非常普遍的陪葬器物。这几种和汉代人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东西,除了表示阴间实用功能外,还与灶、井、厕等的神异功能有关。自原始灶具出现后,便产生了灶神崇拜。至汉代祭祀灶神风气更盛,少君曾言于武帝,“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黄金”,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祠灶。灶可养生、长寿、通神、荫子孙,灶在汉墓中以明器和画像大量出现也就是正常现象了。井在墓葬中出现也具有特殊的巫术意义。《淮南子·地形训》云:“井者,黄泉之象,天地之中介。神龙潜入浮上的地方。”“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之埃上为黄云。”泉、云相接,汉代人认为是跨龙升天[11]。从《庄子·秋水》“彼方跐黄泉而登大皇”来看,黄泉是一个登天的阶梯。黄水又名丹水,后来道士所造“不死药”即名为“丹”,此二者必然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古传黄帝之胄来自昆仑,人死归到祖先处,所以鬼(归也)归于黄泉。后来神仙思想发展,九泉变为仙乡,泉的具体形象则以井体现,在汉代人看来,井便因与昆仑仙乡“不死水”相关联而具有神奇的功能了。
汉画像中的祥瑞动物、植物和其他物品,有些比较明显,如龙、凤、麒麟、鹿、羊等,有些则比较隐晦,如摇钱树、灶、井等,有些则是抽象图,如式图、胜等,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从巫术角度来看,凡是能给人世带来吉祥美好如升仙和不死的,都应是具有祥瑞性质的。
三、汉画像中的辟邪巫术
中国古人认为,不仅阳宅会遭到冥冥中的凶魅邪祟干扰,阴宅同样有游魂野鬼的侵袭,为了保卫死者的地下安全,要借助巫术手段,在墓室内布置镇墓御凶厌胜之物以辟除不祥[12]。中国古代对付鬼魅邪祟基本上借用超自然神力。因为鬼魅无形,无法接触实物,因此古代人主要借助神灵、巫师和各种灵异之物的神奇力量来驱鬼除邪。古代解禳活动常用祓、禳、解除、厌劾、厌胜、辟、镇、禁等术语表示。如汉代传说喜欢吃死者肝脑的恶鬼“罔象”最怕虎和柏树,因此当时人有“墓上树柏,路头(立)石虎”的风俗,就体现了镇压邪魅的一种巫术方法。
镇墓祛魅的神灵之物担当护卫的重任,一般安置在墓中要冲部位。如门扉、门楣、门柱、墓室后室后壁以及其他重要部位。门扉上最常见的是铺首衔环、白虎、熊、力士,其上常置凤鸟、龙等;门柱上多置门吏、神荼、郁垒、方相氏等;门楣多配置祥禽瑞兽等。汉代四神多被刻在墓顶、墓门、墓柱上。四神纹在汉代十分流行,其和方向有关,用于瓦当上镇四方,在墓中起到辟邪求福的作用。石棺画像上的御凶辟邪图像如铺首,有的在棺盖后端如郫县新胜2、3号砖室墓1号石棺,有的在棺盖前端如石羊上村王晖砖室墓石棺。驱鬼图分布在石棺一侧,如新津县宝子山崖墓5号、6号崖棺等。庙阙和墓阙都是为祭祀鬼神所设的“神道阙”,墓阙与地下墓室以及地上祠堂是一组互为表里的丧葬性建筑[13]。画像表现的重点是人与神祇间的关系,因此铺首作为护卫墓主安全的重要神物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东汉时期墓葬中解除瓶上的文字和道符来看,在当时人的心目中,阴间世界是充满恶鬼的可怕世界,为了克服对死亡和死后世界的恐惧,辟除、镇压墓室外的恶鬼,避免阴间恶鬼骚扰死者魂魄,汉墓中刻绘了众多铺首、方相,或放置了实物镇墓兽、解除瓶、刚卯、印章、灵符等各种辟邪之物[14]。
汉画中最常见辟除邪恶的有铺首衔环、神荼、郁垒、蚩尤、蹶张、龙虎等。铺首一般被刻画成虎或熊的样子,秦汉时人们认为最凶猛的动物莫过于这两种,依据鬼怕恶人或凶猛动物的原理,将这种兼具熊、虎特性的图像放置墓室门户或室内易被鬼魅侵扰的地方,则鬼怪不敢入侵。铺首图像一般是将虎或熊最凶恶的部分如眼睛、牙齿和牛角以及山形冠中间的桃形符进行异物同构。铺首嘴咬或鼻挂的圆环应是玉璧,璧在古人心目中是通天神物。环下系一丝带。在这类图像组合中体现了巫术的基本原理:眼睛、牙齿、牛角是动物最厉害的部分组合,属于交感巫术中的模拟巫术[15],桃形符则和汉代人身上佩桃印,门户上插桃枝、挂桃板驱鬼辟邪有关。玉璧下边系的丝带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也应是辟邪的一种灵物,虽然暂无法确定其颜色,但从其辟邪的功能,可以推断可能是古代流行久远的朱丝驱邪术的延续。春秋时晋国大臣荀偃曾“以朱丝系玉二珏”向河神祝祷。受朱丝辟邪说的影响,后来的巫师、道士常用红布作为辟邪灵物,至今民间术士仍习用它做辟邪灵物。桃形符、玉璧、朱丝、山形冠历经发展,最终演变成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圣灵物。在当时人看来,这些灵物和凶猛铺首组合在一起被放置在门户、楣、墓室后壁等重要部位,会对鬼魅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威力。
关于汉画中方相氏、蹶张、蚩尤、力士、兵器等辟邪图像,目前论述较多[16]。方相氏本属于保卫国家和平安全的周礼夏官,其起源据《云笈七笺》云:“帝周游行时,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以为祖神。令次妃嫫母监护于道,因以嫫母为方相氏。”“嫫母,黄帝时极丑女也……今之魌头是其遗像。”[17]西汉王朝曾专设这一官职,其职责一是在国家遭遇灾难时,领相关人员举行傩礼,每年定期三次,另一职责是入墓驱邪。后来方相氏退出官职,但其驱邪功能不变。《周礼·夏官》提到,方相氏由“狂夫”四人组成,“狂夫”指疯狂、凶猛的男子。从驱邪功能上看,方相氏就是巫师。巫的地位由极崇高逐渐跌落至民间,成为为人禳灾辟邪、预测吉凶、修炼丹药的术士。表现驱傩逐疫画像较典型的有沂南北寨画像石和武氏祠后室石刻等[18]。
临沂汉墓后室北壁承过梁隔墙东西两翼对称刻方相氏,东面呈蹲立状,左手握桃杖,右手挥舞作驱妖状;西面双手操长钺作挥击状。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和和林格尔壁画墓中画面门上刻绘了手操桃茢的神荼郁垒像。武氏祠后室中有一方相氏,蒙熊皮戴假面,头上弓弩,手足操执剑、戟、刀、勾等兵器。其他人则拿着刀、符瓶、铲、桃符枝、剑、杖、桃梗等器物作扑打状。这几幅方相氏辟邪图中使用的辟邪物有狰狞的头、剑、刀、桃符、桃板、桃梗等。桃木辟邪说是中国古代巫术体系中普遍流行的说法,因为木料不易保存,在汉墓中难以见到辟邪的桃木。沂南汉墓中室门柱方相氏画像和另一幅墓门中立柱蹶张拉的如同玩具似的弓弩、刀、剑,我们推断其可能是桃木作的桃弧棘矢。汉代方士说,用七支桃枝当箭,用桃弓依次射出后重新捡回,与四块青石埋于院四角,家中不会遭殃[19]。在东汉大傩仪式上,方相氏带领一群童子边击鼓边放箭,他们的弓箭也是桃弧棘矢[20]礼仪志中:刘昭注引汉旧仪。用弓箭射击鬼怪是古代巫术中的重要法术,一般不用实物弓箭而是用桃木制弓,用酸枣枝制箭,称为“桃弧棘矢”。据说楚国先王熊绎曾把桃弧棘矢作为贡品送给周天子[21],可见此种辟邪灵物在古代人心目中的分量。邳州燕子埠元嘉元年缪宇墓前室南横额图像下层右边有一人,引弓仰射,弦中无弓。在巫术中,有时做一下模拟动作也同样起到巫术效果。汉画中还有较多描绘武库的画面,如沂南汉墓前室南壁中段武库、徐州白集墓中西壁北图像下层武库等,画面兵器架上陈列了刀、枪、剑、戟、叉等古代常见兵器。兵器是杀戮利器,将其和战神蚩尤、蹶张、力士、执棨戟门吏、神荼、郁垒等威猛雄壮之士一同放置在墓中重要部位,可以起到辟邪、威吓、禳除阴间鬼魅的作用。
有一些图像如孔子见老子、胡汉战争、水陆攻战、二桃杀三士、纺织图、拥彗持便面等,研究者常将其置于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中,对其意义作表面化的解释,歧义也较多。近年来有研究者从为墓主服务的功能角度来研究,提出新的阐释,即所有墓葬都不是以表现为目的,而是围绕着墓主人冥界享用或死后升仙的功利性旨趣。张文靖从辟邪镇墓功能角度对“荆轲刺秦王”、“二桃杀三士、”“完璧归赵”、“周公辅成王”和“孔子见老子”进行论证,提出了全新的解释[22]。下文将从辟邪巫术角度对其他相关图像进行分析。
汉画的内容可划分为升仙、理想家园和为安全而进行的各种辟邪。刻画圣人和孝子,可以理解为是理想世界的行为楷模,但汉画中圣人、孝子题材却极为少见。在私人性空间中,永享生命的快乐远比伦理束缚重要得多。在汉代人眼里,周公、老子、孔子等圣人已进入超凡入圣的境地,已离神仙界很近,把他们置于画像中当具有震慑作用。汉代人认为孝可以通神明,《后汉书·列女传》记载:“赤眉散贼经诗里,驰兵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时岁荒,贼乃遗诗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20]2783东汉时,人们认为儒家经典如《孝经》具有驱鬼除魅的神力。在汉墓中出土的《周易》《孝经》,马王堆出土的其他帛书和圣人孝子图等,在汉代人看来具有巫术性质,因凝聚着超常的法力而具有辟邪功能。
在山东临沂、枣庄等汉墓门楣或其他部位常见战斗场面。如苍山前姚汉画像描绘了车马过桥发生激烈战斗的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桥两端分别立有两杆,上端饰有如铺首头上的桃形符。兵在古代和“凶”是同义,将凶杀画面置于墓中,依据以凶制凶的巫术法,可以起到辟邪作用。在一般汉人墓中描绘这一图像,我们有理由怀疑它和墓主人的人生经历有任何关系,它的功能可能就是儆示一切敢于侵犯墓主的邪恶鬼怪。
纺织图、持便面、拥彗持茅图,在汉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纺织画像一般分布在山东、徐州、皖北一带,比较有名的如铜山洪楼祠堂后壁左下石图像、宿县胡元壬祠堂后壁图像等。单独看是汉代纺织场景的现实反映,但若从整石画面看,其周围场景安排有祥禽瑞兽、击鼓通神、星相图等,那么它的意义就可能不仅是表面所呈现的这些。古代祭礼中人们常在放置祭品的几案上搭一块三尺新布当“道布”。新布作为巫术灵物源于周人祭祖时须找一位同姓族人装成祖先直接享用祭品,扮演先人的人用手抓食,需一块手巾随时擦拭油污,“道布”即是为这位“先人”准备的,用干净的新布无非是为了讨好神灵,布的巫术功用在丧礼中表现最明显。在四川中江民主乡八村七社塔梁子3号崖墓一图中前绘两个跽坐似在做功的人,后绘一人左手持便面,右手持一匹布朝二人走来。新织的麻布比较洁净,常用于祭祀丧葬活动,因此人们便认为它沾染了神性而具有了辟邪除凶功能,演变到后来新布便被当成了辟邪灵物。两汉时在民间普遍流行用新织布辟除邪祟,汉代人常把新布条缝于衣襟或挂在门上,认为以此可以避瘟疫和兵器伤害。应劭在《风俗通义》中云:“今家人织缣新,皆取着后嫌(缣)绢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新布演化成辟邪灵物的过程与白茅相似。茅即茅草,南北朝以前,茅草一直被术士当作驱鬼除邪的工具。《周易·大过》有“藉用白茅,无咎的爻辞”之语。古人常用白茅制品向神灵祭献美酒佳肴,久之,便认为白茅和神灵间有某种联系,沾染了神的灵性和威力。白茅便被当成通神之物和辟除邪恶的武器。春秋时人们用白茅制作旗帜,称“茅旌”,茅旌除具有旗帜的功能,还具有辟邪开道的意义。离石马茂庄和平元年左表墓室门侧图像中导骑和车骑手中均持茅旌,胡元壬墓中画像两持白茅者导从,铜山茅村墓后室北壁上层图中左边两导从肩扛茅旌等,都是以茅旌为先导,辟邪开路。秦简《日书·诘篇》说,人无故受到伤害,用白茅加黄土遍洒四周,鬼即逃去。汉武帝相信方士栾大的异术,授予他“天道将军”玉印,仪式在夜间举行,武帝的使者身穿羽衣,站在白茅之上,栾大也穿羽衣,站在白茅上面接受玉印。汉代是各种巫术交流荟萃的时代,包括白茅等各种辟邪法术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便面是汉代人使用的扇子,彗即扫帚。便面和彗在汉画中常见,或是仆从、侍者等持便面为主人服务,或主人自持,如宿县胡元壬墓前室西壁墓门南侧图像一层、三层和四层大部分持便面,一层右两人持似毛刷物(可能为白茅制),四层左边一人持彗。南阳市七孔桥汉墓有一小吏双手拥彗,侧身而立。南阳市另一汉墓有一图为女侍者拥彗,回首侧身欲行。此类图像在汉画中也很多,依巫术观念,这也同样表达了辟邪目的。扇子主要功能是扇凉,挥扇既带来凉风又可扇去不洁之物。将其置入墓室内,以之比附扇除阴间邪气。拥彗是汉代迎宾时的一种礼仪。《汉书·高帝纪》:“太公拥彗,迎门却行。”颜师古曰:“彗者,所以埽地也。却,退而行也。”表达了洒扫清洁恭请光临的意思。先秦时巫师常用工具有两种:一是桃棒,另一则是萑苇扎成的笤帚。两物配合用则称为“桃茢”。西周春秋时君王去大臣家吊唁,由巫师持茢引导开路,进入死者家后,巫师先用桃棒和笤帚在尸体周围挥拂,以扫除死者的凶邪之气,保证君主的安全①详见《仪礼·士丧礼》《周礼·丧祝》《礼记·檀弓下》《礼记·丧大记》。。汉画中为我们保留了众多拥彗图像,彗和便面具有同样的功能。宋人黄休复讲过道士雍法志用棕帚为人扫病的故事,清人袁枚在《朝野佥载》中记载用笤帚扫除走尸的传说[23],这些均反映了古代人对笤帚扫除邪魅的巫术迷信。
在汉画图像中,还有很多图像及其组合按常理解释不通,仍困扰着研究者,如:屋上放置鲤鱼、野外交合一般于桑树下、牛耕图、连理枝树、凤鸟衔三星珠等。如将这些图像重置于当时的民间观念、丧葬习俗、生死观之下,便会发现,其内容设置无论是升仙祈祥还是辟邪禳灾,一般受巫术影响都较大。秦汉时期巫风大盛,而巫术又和道教关系最密切,早期道教正是在巫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研究汉画之宗教因素,另一不容忽略的是汉墓大量出土的镇墓文、镇墓瓶、符箓咒语、刚卯、道士常用印、铜镜、厌胜钱、宝剑等器物文字。将这些早期方相氏、方士、道士在墓中进行巫术做法的灵物与汉画中的辟邪灵物相参照,可以看出早期道教对巫术的吸收和利用。在汉代方士、道士和众多民众的共同作用下,很自然地汉画中呈现了大量的巫术因素。
[1] 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卷二[M]//诸子集成: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
[2]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M].成都:巴蜀书社,2002:199-200.
[3] 陈亮.武氏祠研究综述[M]//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239-240.
[4] 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78-80.
[5] 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M].济南:齐鲁书社,2004:415.
[6] 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83.
[7] 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9:1394.
[8]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1.
[9] 何志国.论汉魏摇钱树的格套化与商品化[M]//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237.
[10] 张善熙,等.“天门”图像钱树初探[J].中华文化论坛,1999(3):72-74.
[11] 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98-99.
[12] 李锦山.汉画像石反映的巫术习俗[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10):120.
[13]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94.
[14] 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J].考古学报,1991(1):45-56.
[15] 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9-21.
[16] 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 雕玉集:卷十四·丑人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8]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
[1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一·引淮南万毕术[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0] [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1] 左传·昭公十二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2] 张文靖.论汉代墓室画像石中三个历史题材的辟邪镇墓功用[M]//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284.
[23] 袁枚.子不语:卷五、卷一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