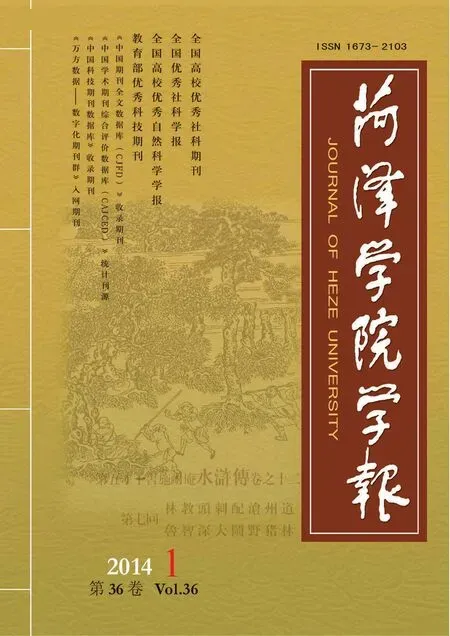德国电影《死亡实验》的角色分析——以埃里希·弗洛姆的“逃避机制”为理论依托*
2014-04-08王林
王 林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4)
《死亡实验》是德国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在200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本片以1971年美国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为原型,旨在探讨极端的人为情境对人格产生的影响。在处理选材上,《死亡实验》和德国导演丹尼斯·甘塞尔在2008年拍摄的《浪潮》一样,基于真实事件改编,并试图挖掘出意识形态层面的“弦外之音”。二者都有着浓厚的纳粹反思意识,但都不约而同地避开了直面地表现历史中的法西斯,而是选择从当代生活入手,设定一个假定性的情境,前者是监狱实验,后者是课程作业实践。事实上,通过提供假定情境或极端情境,来承载某种所指的电影叙事手法,在好莱坞早已作为商业元素渗透到类型片的创作。从恐怖惊悚片《电锯惊魂》系列到动作片《饥饿游戏》,其实都是在假定性的故事框架内发展真实的人物关系。美国独立电影或欧洲电影倾向于从更严肃的意识形态领域为假定性题材寻找灵感。2012年圣丹斯电影节的参赛影片《服从》便是如此。影片表面上讲述了一起变态电话恶作剧,但不难看出其背后对权威主题的影射意图。由此可见,极端情境的给予无疑为电影思想主题的代入提供了某种便利,极端情境中的人物关系也更加简单直接。《死亡实验》本身就是一项极富戏剧性元素的现实实验,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在对该素材的电影化处理上,亦是尽量遵循了实验原型中的基本情节,除了用电影手段进行了具象化的视觉还原,为更好地服务于电影叙事层面的矛盾冲突,影片又赋予了角色更鲜明的意指性,如代表权威人格一方的看守头目博鲁斯、代表着规则挑战者的77 号犯人塔瑞克、代表着规则牺牲品的舒克等等。甚至为强化戏剧冲突,有意将实验结局改编为二死三伤的悲剧后果,包括处于实验情境外的项目主管克劳斯·杜恩博士,也被卷入这场悲剧式的屠杀。
电影《死亡实验》里的监狱模拟实验所提供的极端人为情境,使每一个角色在行为的背后又有着不可名状的动机所在。这些动机涉及到特殊情境对人格的强烈影响,相比弗洛伊德贯穿着生物学观点的传统精神分析法,人性的历史性以及社会、文化等其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则更符合本片的考察角度。而这一点也正是以埃里希·弗洛姆为代表的于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重要观点。该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蓬勃发展,战争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是其发展的内在原因。弗洛姆的代表作《逃避自由》集中探讨的权威人格理论、逃避机制等,不失为影片角色分析的绝佳理论参考。下面,笔者将以弗洛姆的精神分析观点对《死亡实验》中不同角色和行为进行分析。
一、权威主义性格:受虐狂和施虐狂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把常人而非精神病患者身上的施虐—受虐性格称为权威主义性格。施虐与受虐的特征总是指对权威的态度,所以用这个术语是正确的。一言以蔽之,权威主义性格“羡慕权威,并欲臣服于它,但同时又想自己成为一个权威,要别人臣服于他”[1](P112)。《死亡实验》里的看守博鲁斯正具有最典型的权威主义性格。
1.受虐冲动
按照弗洛姆的说法,受虐狂和施虐狂表面上看处于对立面,但实质却是相互依存、一致和共生的。二者都是内在孤独感和恐慌感的表现,且都倾向于某种外在的权威或力量的认同。尽管作为看守的博鲁斯在表面上更像是施虐的角色,但事实上他的性格中隐藏着强烈的受虐冲动。弗洛姆认为,受虐冲动最常见的方式有无能为力、深度自卑、个人的微不足道。这些人往往有一种倾向,自甘懦弱,自我贬低,不去做想做的事,而是臣服于事实上或假想的外在力量的命令。影片在多处细节处展现了博鲁斯性格中敏感自卑的一面,并暗示了他失败的家庭生活。实验刚开始时博鲁斯因身上的臭味而遭到其他几个看守的嘲笑,在后来矛盾激化阶段犯人也曾以此来激怒博鲁斯,致使博鲁斯暴怒失控。还有一处是看守们在聊天时,其中一位看守开玩笑说博鲁斯不是一个好父亲因为他没有将女儿的照片带在身上,博鲁斯对此的易怒反应显然过于敏感。这或许暗示着他的家庭遭遇变故或处于不幸福的状态之中。
“受虐冲动的一个重要行动便是企图成为自己之外的一个更大更强的整体的一部分,融入它并分享它。这个权力可以是人、机构组织、上帝、国家、良心或心理机制。”[1](P106)在《死亡实验》里,这个所谓的“更大更强的整体”便是以实验主管杜恩博士为代表的实验操纵者。它实质就是以博鲁斯为首的看守们所依附的权威力量。博鲁斯全身心地依赖、依仗这个权威,实是逃避内心的无力感、不安全感。就像弗洛姆所说:“渴求权力并不根植于力量而是软弱。它是个人自我无法独自一人生活下去的体现,是缺乏真正的力量时欲得到额外力量的垂死挣扎。”[1](P110)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实验有一项至关重要的规定,就是不得发生过激的暴力冲突,如果发生就停止实验。这个规定看似具有保护意义,但实际上正是权威树立威信、实行统治的伪装。因为对于暴力强度的界定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就为“看守”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可供缓冲的庇护所。以致当实验操纵者中有人对实验中已经出现的暴力提出异议并要求停止时,杜恩博士的反应竟是继续观察,其直接后果便是对暴力行径的姑息纵容。事实上,在《死亡实验》2010年的美国翻拍版中,实验有一条明确规定便是:“一旦发生暴力冲突警报就会响起,实验就会结束。”某种意义上说,警报的象征意义就是弗洛姆所说的“匿名权威”。“它不言自明,根本用不着发号施令……根本不用施加任何压力……在匿名权威中,命令和命令者全都踪影全无,就像受到了看不见的敌人的攻击,任何人都无还手之力。”[1](P114)在美版《死亡实验》里,在最后一次越狱暴力之前,警报始终保持沉默。
2.施虐冲动
相对于受虐冲动,博鲁斯的施虐倾向更容易解释。弗洛姆认为施虐冲动的本质,是完全主宰另一个人,使之成为其意志的无助玩偶,可任意玩弄他。羞辱与奴役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最激进的目的是让他受苦并强迫他忍受苦难。在《死亡实验》中,以博鲁斯为首的看守,将犯人裸体铐在铁栏上、往犯人嘴上贴胶带、往77 号犯人身上撒尿并命令其用自己的囚服擦马桶、用警棍实施暴力,并以此得到满足,表现出了越来越疯狂的施虐倾向。就像博鲁斯在影片中说的那样:“我曾读到过,想要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住局面,就得让他们丢脸。”片中交待了一个细节:博鲁斯在第一次施暴后,被幕后的女研究员捕捉到了一个他因兴奋而手抖的镜头。
如果说弗洛伊德将人的施虐—受虐欲归结为死亡本能的结果,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把它当作“自卑感”和“权力欲”来看待的话,那么弗洛姆仍坚持认为这种冲动来自于人内心无法摆脱的无能为力感。人人身上都可能有施虐与受虐特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必然是精神病患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特定情境。那么表现在《死亡实验》中,施虐—受虐人格的激发显然是以监狱实验营造的人为情境为前提。博鲁斯的施虐行为显然并非单纯始于破坏欲本能的驱使,他首先有个被刺激的诱因,那就是来自以77 号犯人为首的挑衅。实验起初,犯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将被置于被动的处境,在早上集合、喝牛奶、叠被子等例行规定中他们尚有嬉闹挑衅的余地。直至这种挑衅让整个局面陷入失控边缘,看守们很快意识到树立权威的必要性时,实验才开始真正的转折,并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失控局面。应该说在模拟监狱的极端环境下,77 号犯人不断施加刺激,从而使以博鲁斯为代表的看守的权威主义人格被激发了出来。他们开始一步步树立权威,并变本加厉。事实上,博鲁斯完全可以被看做希特勒的化身。弗洛姆认为大部分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下层中产阶级的典型性格就是施虐—受虐性格,而希特勒正是这一阶层的典型代表。希特勒本人在自传《我的奋斗》中便称自己是“无名小卒”。这个阶层的人一方面渴望臣服于那些掌权者,另一方面又渴望亲身统治无权者从而建立自己的小权威。博鲁斯在监狱实验中的表现与此如出一辙。
二、机械趋同:逃避自由的另一种形式
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中的核心词汇是“逃避机制”。弗洛姆认为,人生而为自然的一部分,但人又不得不超越自然,这就是人的“个体化”进程,在这个个体化进程中,人一方面摆脱自然的束缚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自然创设的原始关系带给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如果我们把这种失去归属感所产生的不安全感理解为一种荣格式的“集体无意识”,那么,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心理的“逃避机制”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即放弃个性的冲动,把自己隐没在外界中,以此来克服孤独无力及无权利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逃避自由”。前面权威主义性格(施虐—受虐冲动)就是逃避自由的逃避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就像德国反思电影《浪潮》中的一段,当文格尔先生要求学生们为他们的“集权主义”组织确定一个制服时,一个女生高兴地说:“太好了,以后就不用为每天早晨决定穿什么衣服犯愁了。”看似抱怨的几句台词,却深刻反映出现代人具有的一种孤独彷徨的精神状态。他们宁愿放弃个体的自由,放弃自身的完整,迫切地投身于权威,以此赢得安全感。
依据弗洛姆的归纳,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机械趋同。即自我的丧失,按照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失去自我和主题性的模式,为了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而被迫与他人趋同,通过某种“皈依”来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伴随于此的便是意识里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感一起消失。在《死亡实验》里,被博鲁斯所带动起来的看守以及被看守所驯服的没有反抗意愿的囚犯都是机械趋同的一类人群。
1.被煽动起来的看守
在影片中,实验角色的分配在一开始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群体。一边是行动相对自由的看守,一边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人,并且犯人没有姓名,只有编号,这是典型的淡化人的个体性。在实验的最初,作为较有主动权的看守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角色认同感,他们对犯人的小打小闹感到无措。直到77号数次挑衅后,看守开始越来越重视手中的权力并逐渐沉迷于其中。而幕后监督的研究员尽管给出一次警告,但杜恩博士本人实际上是对暴力有种出于私心的纵容,至少没有给予果断的制止,这对于看守来说相当于行为被权威的默认。这不难让人联想到1961年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进行的一次“权力服从实验”。该实验的参与者为不同年龄、阶层的普通市民,实验考查的是被试是否愿意服从科学家的指令,操作电击控制器对隔壁的人进行电击,以及将会进行多大强度的电击。实验结果是,参与者即使听到了隔壁痛苦的尖叫声,并感觉到强烈的道德不安,但他们仍旧继续服从科学家的指令。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威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超出自身日常尺度的行为。再回到《死亡实验》,杜恩博士代表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而日渐疯狂的博鲁斯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看守团体中的小权威。他的暴力行为具有极强的煽动性,一方面使得其他看守性格中的施虐倾向被激发出来,另一方面机械趋同的心理不允许他们脱离组织从而造成孤立感。影片适时地给出这样一个细节:其中一位较为善良的看守因暗自帮助囚犯而被博鲁斯发现,并以背叛组织的名义贬为囚犯。这是极为讽刺的一笔。联想到法西斯主义,如果说被煽动的看守正是意味着纳粹意识形态所吸引的一类人群的话,那么,在这种极端情境下,不被煽动甚至与之对立的人的确处于一种危险的、被孤立的境地。
2.失去反抗意愿的囚犯
在模拟监狱中,失去反抗意愿的囚犯同样是典型的机械趋同人群。即便这些囚犯在影片中更多是以群像形式处理,但这恰恰代表了一种极端环境下最普遍、最具必然性的群体行为基数。他们是逃避自由的,面对看守越来越入戏的暴行,他们选择失去自我、埋没于集体中以消除内心的恐惧。弗洛姆形容这种机械趋同类似于动物的保护色,它与周围的环境极其相像,以至于很难辨认出来。于是与77 号飞扬跋扈的性格不同,绝大多数囚犯在初尝到违抗作乱的后患后,都开始有意抹煞自我存在感,避免成为“与众不同”的那一个。但事实却是它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的生活常常只是些机械的强迫活动。机械趋同地臣服权威之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依然活在被迫的、痛苦的境地中。这也是为什么影片表现了数名囚犯出现了不能自制的恐慌发作症状,包括一直活跃反抗的77 号本人。
三、结语
综上所述,《死亡实验》所提供的模拟监狱,是法西斯主义的缩影。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政治创伤,法西斯极权所引发的反思视角不仅仅在于战场上的残杀和战后的哀鸿,还有对人性的历史性的思考。弗洛姆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逃避机制”理论,对法西斯主义产生和流传的心理根源进行文化层面的解读,是对集体意识的一次精湛心理学分析,也是那个时代深刻的哲学反思。以弗洛姆的“逃避机制”为理论依托,对电影《死亡实验》里的角色进行深层次分析,既为电影文本找到了精神分析领域的文化阐释,也更益于观众理解影片所传递的批判意识。
附录一:剧情简介
《死亡实验》是德国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在2001年拍摄的一部电影。本片以1971年美国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为原型,讲述了出租司机塔瑞克·法德被报纸上一个模拟监狱实验所吸引前去应聘,在实验中他与其他19 名应聘者被分为两组,其中“囚犯”12 名,“看守”8 名,“看守”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定来管理“囚犯”,在不发生暴力冲突的前提下,顺利完成为时两周的实验,每人便各可获得4000 德国马克的报酬。实验前夕,塔瑞克暗自与自己两年前曾供职的报社做了笔交易,决计实验完成后他将把整个实验过程报道出售。故作为77 号“囚犯”的塔瑞克,在实验过程中为制造新闻噱头而故意挑起事端。与此同时,在实验中作为“看守”角色的博鲁斯正一步步走向暴力极端。“囚犯”与“看守”的针锋相对使得实验结果越来越难以预料……
附录二:斯坦福实验原型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监狱暴乱频发,并酿成了一系列悲惨事件,从而引起公众对于美国监狱内部管理制度的批评和怀疑,也引来社会科学家、心理学家对监狱管理者与犯人相处的真实情境进行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Haney、Banks和Zimbardo 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开始操作实验,其目的便是研究监狱环境对人格心理的影响。
经过筛选共有24 人通过测试参与实验中,他们遂被随机分成两组角色,即囚犯与看守,而Zimbardo 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实验不仅力求在监狱环境以及角色的穿着上保持与实际监狱一致,在囚犯进牢时,同样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进行裸体搜身。看守的角色在实验中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研究者用录音装置和闭路电视监视犯人和看守的反应,并定时与他们进行私人谈话。被试们被允许随时退出实验。
然而,原计划两周的实验在六天后不得不终止。原因是随着实验的进行被试的行为和人格开始出现异常。同实际中的监狱情形相似,“尽管看守和犯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任何形式的相互作用,……他们的接触倾向于是负面的、敌意的、侮辱性的、不人道的”[2]。看守们被随意安排的角色内化,越来越具有施虐倾向,甚至一些在实验开始前的人格测试中表现为和平主义的人也很快开始对犯人产生攻击性的行为。犯人的情绪遭受了剧烈的冲击而变得焦躁、易怒、抑郁。一些犯人开始祈求退出实验,也有些人盲目屈尊于看守们的威慑下。眼看犯人与看守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逆转,实验被迫停止。
[1]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2]朱新秤,舒莹.监狱环境的心理负效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启示[J].政法学刊,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