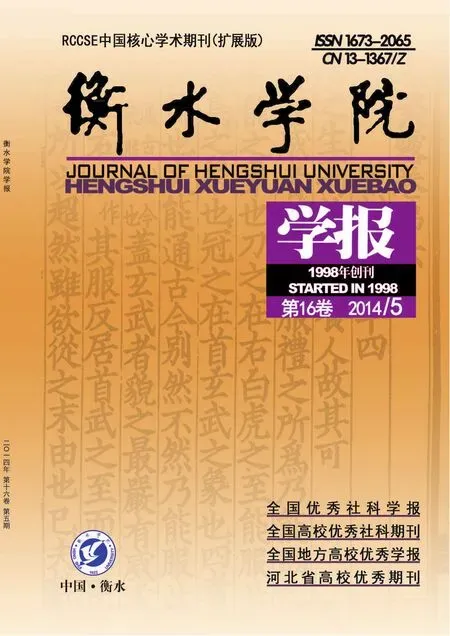中西对话:直面中国道德传统
2014-04-08李存山
李 存 山
(2014年5月10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和中国哲学研究室举办室际研讨会,主题为“直面中国道德传统”。以下内容节选自这次会议的录音整理,甘绍平研究员的发言可能尚未修改而已文从字顺,我的那部分发言略有文字上的修改和补充,发表在这里供批评、讨论。我的观点还可参见拙文《反思儒家道德的情感与理性》,发表在国际儒联编的文集《儒学的当代使命》卷一,九州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甘绍平研究员针对所谓“道德观念从直接性和差异性到抽象性和平等性的变化”这一现象,做了主题发言。他首先介绍了汉斯·约纳斯的远距离的伦理学:从时间上看,不仅目前活着的人是道德的对象,而且那还没有出生的人也是道德的对象。从空间上看,人不再仅仅是对人才有义务,而且对人类以外的大自然、作为整体的生物圈也有保护的义务。受这个所谓远距离伦理学观点的启发,甘绍平研究员提出了人类的道德观念呈现出一种从直接性和差异性到抽象性和平等性的变化过程的观点。而中国儒家伦理可以说是直接性、差异性道德的代表。不可否认,中国儒家学说中不乏闪烁现代文明价值的思想火花,如体现对人的尊严之重视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展示对人的生命之尊重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但从儒家伦理的整个伦理体系而言,直接性和差异性却是儒家伦理的最主要特征。儒家虽视仁爱为道德的核心,但这种仁爱首先是局限于近亲的。这样的道德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这种仁爱是奠立在血缘亲族关系基础之上的,仁爱来自于一种血亲关系决定的天然的道德情感,这种情感虽然强烈与稳定,但属于人人生而皆(应)有之的自然之物,是原始的、质朴的和直接性的。二是这种仁爱具有差等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自然决定了爱的强度的重轻差异:先是爱父母,“亲亲为大”;次是爱兄弟,“友于兄弟”;再次是爱朋友,最后才是“泛爱众”。尽管儒家也不否认应广施爱心,但由于其仁爱的基础是血亲之情、亲族联系,故从近亲之爱如何外扩为对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的普遍之爱,便成为儒家伦理根本就无法逾越的一道逻辑鸿沟。由于无法将遥远的陌生人与自己的血缘亲族等量齐观,则“泛爱众”便很容易蜕变成为一个虽响亮振奋但空乏无力的口号。总之,儒家伦理是直接性、差异性的道德。儒家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自然道德,呈现出重情感、轻理性,重熟人、轻陌生者的不足,表明这种道德思维还仅仅停留在直接性的阶段,缺乏抽象性与超越性,而且这种血亲道德还直接导致了道德顾及的差异性,使平等的意识很难拥有生存的空间。当然,儒家的这种直接性的道德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调节近亲关系永远是适用的。现代性伦理之所以不同于这种源于自然关系的直接性和差异性道德,主要在于现代性道德对象不只是身边的人,而是范围更广的陌生人,因此,现代性的道德对象是抽象的、远距离的人,它的建构是完全不依赖血亲自然关系的重新建构,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这一点最早发生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探索中。苏格拉底在人拥有的所有善品之外,如健康、美丽、快乐、友谊、生命本身,还看到了一种高于所有其他善品的善品。他从诸多善品中,抽象出一种超越所有其他者的最高的价值。这种最高的善品,被柏拉图概括为善的理念,它是一切善行的目的和唯一真实永恒的价值基础,是道德的唯一根源。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思想极致化,认定道德与人的感性思维没有本质的联系,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达到至善的理念。这样,他们就超越了思维的直接性而达致了思想的抽象性,他们通过对一种最高的价值理念——至善的建构,为一种可以向所有的人通达的,并为每个人所平等分享的普遍道德和普世伦理的提出奠立了基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这种有关至善的抽象性的理念,后来被导入进基督教上帝的形象之中。上帝的出现,使人际关系极大地简化为上帝与每个人之间的单纯的关系。由于同属于上帝之子女,人与人之间便享有平等与博爱,这里没有差等之爱,而只有平等的尊重与顾及,只要同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就都应受到同等的善待。可见,抽象的上帝理念,造就了一种平等的观念和对所有的人都同等顾及、同等适用的平等道德,即普世伦理。这不仅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成就,而且也是伦理思想、道德意识的重大突破。近代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思想家们剥除了神秘的上帝外衣,用人性及人的形象来取代上帝的概念,而抽象性、普遍性的,平等待人的道德理念却保留了下来。总之,人类的道德呈现出一种从直接性、差异性到抽象性和平等性的变化过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种变化意味着两种道德的高下,而只是说明两种道德适用范围的不同。直接性、差异性的道德在近亲和熟人社会仍然起着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而抽象性、平等性的道德则成为在广阔的国家性、乃至全球性的社会里发挥普遍效力的行为规范。从直接性、差异性道德向抽象性和平等性道德的变化,反映了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从这个意义上看,道德构成了其所处时代的一面镜子。
李存山研究员首先指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现代转型中遇到的困境,并以儒家伦理的道德起源和道德评价为核心作主题发言。他指出,中国哲学是以伦理道德为主旨的,在现当代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西方伦理学视角作为参照,确实面临着难以定位和评价的难题。因此,开展中、西伦理学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儒家传统的道德体系简单地概括就是“伦常名教”。1840年以后,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的许多思潮相竞汇聚到中国,使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洋务运动思想家冯桂芬曾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而甲午战败证明了中国对于西方文化“遗其体而求其用”是不能达到“富强”效果的,于是有从戊戌变法开始的从器物层面的变革走向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变革。中国传统的“伦常名教”不能为制度层面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撑,相反,如张之洞所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变革,但是以后有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主张复辟的人把“帝制”与“孔教”绑在一起,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若要巩固共和政体就必须有“伦理的觉悟”,此“伦理的觉悟”就是要抛弃儒家的“纲常名教”,因此有“打倒孔家店”之说,儒家伦理的价值和合法性被全盘否定了。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传统文化受到批判,特别在文革时期所有旧文化、旧道德都被全盘否定了。建国以后在道德问题上还有一大失误,就是把道德与政治直接等同起来,在政治的统帅下否定了道德的相对独立性。由于政治的风向是不断变化的,当把道德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就造成了人们只会随政治的风向而摇摆,见风使舵,丧失了道德的操守。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相当一部分人“一切向钱看”,贪欲无止境,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伤风败俗,这也给中国的伦理道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虽然我们也曾提出了“五讲四美”“八荣八耻”等等,但是还没有深入人心,社会效果并不显著。
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依法治国”之外,还需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而“德”要有根,即有民族文化传统的根,这就要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崇尚道德的传统,还要有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张岱年先生在20 世纪30年代作有《道德之“变”与“常”》一文,他认为道德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变化的,但是“变中有常”,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道德有“变”,但是新道德并不完全否定旧道德,新旧道德之间是有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在旧道德中含有一些恒常的、普遍的因素,新道德对这些恒常的、普遍的因素是要继承和发展的。依此,我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要进行分析。事实上,“三纲”并非儒家文化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而作出的一种“变”。在新的时代,我们的道德也要有所“变”,如弃除反映落后时代内容的“三纲”等等,但是我们也要有“常”,即把儒家文化中恒常的、普遍的因素继承下来,如仁爱精神、忠恕之道、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等等。
近年一些学者提出“亲亲相隐”问题,引发了不同的商榷观点。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个问题主要涉及道德起源和道德评价问题。首先,从道德起源的角度看,西方道德的发展脉络如刚才甘绍平所说,先由苏格拉底从诸种善品或德目中抽象出一种超越的最高价值,柏拉图将此概括为善的理念,它是一切善行的目的、道德的唯一根源,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达到至善的理念。古希腊哲学的这种至善的抽象性的理念,后来被导入基督教上帝的形象之中,于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达到了对所有的人都博爱的平等道德,即普世伦理。这样一种道德起源说,在文化上需要有古希腊哲学的“理念”论和西方的基督教信仰,这与中国传统的道德学说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蒙培元先生在《情感与理性》一书中对中西道德哲学的差别作过对比研究。西方文化在道德起源问题上,理性与情感是分开的,至善的理念必须通过理性才能达到。而中国传统在道德起源问题上,情感与理性是统一的。孝悌为仁之本,道德就是从家庭成员的亲亲之情扩展出“泛爱众”“仁者爱人”。孟子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实际上,这句话应理解为“亲亲,仁之端也;敬长,义之端也;无他,达之天下”。到了“达之天下”,也就是“仁”的普遍“爱人”,也就是“博爱之谓仁”。这种普遍的“爱人”是以亲亲之情为开端,经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扩充,进而达到普遍的“爱人”,还可再进至“爱物”,也就是孟子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还提出“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这其中也强调了理性的作用,但情与理是统一的。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思想中,他们提出了“天理”作为道德的本源。这样,“孝悌”就不是“仁之本”,而是“行仁之本”。朱熹有“性即理也”和“心统性情”的思想,“性即理”是讲理性,而“心统性情”则是把理性与情感统之于心。陆王心学将“心、性、情”合一,在“心”之外没有一个更超越的“天理”。儒家道德学说的总的倾向是“情理合一”,而不像西方那样“情理二分”。
反观墨家,组成墨家的主体是一批在外面打工的工匠,他们之间的血缘亲情意识就比较淡薄了,所以墨家不怎么讲亲亲之情,而是强调“爱无差等”。墨家是以“天志”为本,能够兼爱的人受到天的奖赏,否则就会受到天的惩罚。他们是以“天志”“明鬼”的赏罚来保障社会道德的兴利除害,这有点儿类似于基督教,只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罚是在彼岸世界,而墨家的“天志”赏罚就在现世。儒、墨之间的差别,说明不同的道德学说根源于社会生活不同的共同体。而道德最终要达到普遍“爱人”,这在儒、墨两家是相同的,所以后来理学家张载也讲“爱必兼爱,成不独成”。
从社会发展形态看,西方进入“文明”社会斩断了与氏族社会的联系,而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国家”形态是采取了连续性的“改良”方式。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没有了上帝的纽带,人就成了孤零零的个体,西方以上帝为中心的道德观就被瓦解了,而以公民为单位的社会道德必须寻找新的基础。契约论者霍布斯以“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像狼与狼之间的争斗关系为理论假设,提出社会契约论以建构新的伦理和制度学说。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历史发展一直是连续性的,从春秋时期儒家建立起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社会道德学说,中国的以农业村社为主的社会结构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应是儒家道德传统在社会历史上的合理性。再者,从人的生存和社会生活的普适性上说,中国传统伦理从来都不是把“人”看作孤零零的个体,“仁者,人也”,人总是要生活在“二人”以上的社会关系中。事实上,人一出生就不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孤独个体。在出生之前,他(她)孕育在母亲温暖的子宫中;在出生之后,他(她)养育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中。正是在家庭成员的亲情中,人最初体验到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最自然、最真诚的相爱,由此才能扩展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以孝悌为仁之本的道德学说是兼具道德发生论和普遍道德实践之合理性的。正如德国著名的神学家孔汉斯等人在《全球伦理宣言》中所说:“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
人为什么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孟子的性善论中就是因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孝悌是仁之本,而“恻隐之心”也是“仁之端也”。“恻隐之心”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把“同情心”作为道德的根源,这在西方道德学说中也有休谟、亚当·斯密和叔本华等人持此说。无论“同情心”是天赋的良知良能,还是由社会积淀或生物遗传而形成的,人类普遍具有“同情心”应是不可否定的事实。虽然“同情心”可能会有休谟所说的“同情的偏颇性”,即带有“远近厚薄”的局限,但是所谓“至善的理念”可能正是从“同情心”抽象和升华出来的。如果失去了对“同情心”的具体抽象,则所谓“至善的理念”可能成为“纯形式”的东西。
其次,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看,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要达到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平等的道德关系,这与康德并无二致。孔子讲“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体现了道德的自由意志或自觉自律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亲亲之情的扩充。而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已把一切人际关系都抽象成“己”与“人”(他人)的互为主体或相互平等的关系。因此,它是一以贯之、普遍适用的道德“金律”。孔汉思等人在《全球伦理宣言》中也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
孟子讲的“亲亲,仁之端也;敬长,义之端也;无他,达之天下”,就是以孝悌为起点而达到泛爱天下所有之人。仁的本义就是“爱人”,而“爱人”也就是“爱类”,即爱人类所有的人。儒家的道德学说是从差等的孝悌之爱达到普遍的人类之爱,如果放弃了孝悌为仁之本始,也就放弃了道德的起源,普遍的人类之爱也就不可能了。宋代的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此即儒家的仁爱“达之天下”的一种表述。程门弟子杨时认为,《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墨氏之)兼爱”。而程颐指出:“《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蔽,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所谓“理一”就是指抽象的、平等的、远距离的道德,而“分殊”就是指直接的、有差等的、有血缘亲情关系的道德。理一和分殊都要重视:如果只讲分殊,就是“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也就是说,如果把爱仅局限在家庭关系中,那还是“私”,还不是“仁”;如果只讲“理一”,就是“无分之蔽,兼爱而无义”,因此,儒家的普遍“爱人”还不能丢弃以孝悌为仁之本。实行仁的方法是“分立而推理一”,“分立”即孝悌之爱是仁之本,此中也会有“私胜之流”,而能够“推理一”就能够克服“私胜之流”。在这里,所谓“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也看到了休谟所谓“同情的偏颇性”,因此,只有“推理一”才能“止私胜之流”。但是,如何从“分殊”推衍出“理一”,其中的具体“推理”过程是什么,从古至今的儒家一直没有讲清楚;在达到了“理一”,也就是在普遍的或远距离的“爱必兼爱”中,是否还要有“强弱厚薄”的差异,儒家对此也没有明确。在这里,情感与理性可能还要有相对的区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情感与理性可能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比如儒家既有“父子相隐”的思想,但在《左传》中孔子也肯定了“不隐于亲”的司法正义,这里的“隐”与“不隐”就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的君主制社会,虽然是“资于事父以事君”,但也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的划分。在现代的民主制社会,如何从亲亲之情而“推理一”,使之既没有“无分之蔽”,又可以“止私胜之流”,使情感与理性、道德与法治既有相对的区分,又有一定张力下的统一,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反思,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在这种转化与发展中,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价值观,汲取西方伦理学中的至善理念、契约精神、公民权利观念等等,使中国传统道德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常”也有“变”,有相“因”继承也有“损益”变化,我们对传统道德的转化与发展也应处理好常与变、相因与损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