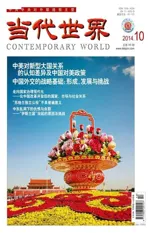中国的大国关系与大国战略
2014-04-08陈玉刚
□ 陈玉刚/文
大国是国际关系的关键,大国影响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如何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大国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革,世界的和平与战争以及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主要看大国。大国的体量占世界经济大部分的比重,大国的经济表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好与坏。大国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产品在世界各地被消费,大国文化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同的时代烙印。对于中国来说,无论从自己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还是发展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出发,都需要有明确的大国战略,都需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
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中国就已是世界大国,这一点毫无疑问。近代百年中国积弱积贫,文明古国沦为“东亚病夫”。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加入国际社会反法西斯战争阵营,成为东亚战区的主力,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一点在牛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拉纳·米特最近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也再次得到了认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来讲,大国问题因此也就有了一层特别的政治含义,即二战后被普遍认可的大国,都是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国家,因而也是对维护战后秩序负有特别责任的国家。大国地位的直接标志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国家的政权在二战结束后发生了变化,而作为大国象征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因此一道转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诞生就面临着大国关系问题。和谁建立外交关系,站在东西方哪一个阵营,这对于任何一个新生政权来说都是极其重大的决定。而中国无论加入哪一方,其结果必然是对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重大修改。“一边倒”的战略抉择,是新中国做出的第一个大国关系的重大决定。中国与苏联结盟,加入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致使美国许多战略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反思,是谁失去了中国。
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确立的。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威望和声势,是在“抗美援朝”中打出来的。作为刚刚诞生、还处于百废待兴的国家,居然打败了二战中实力迅速积聚,战后变得不可一世的美国及其凑合的“联合国军”,这是全世界都难以想象的。朝鲜战争的胜利,确认了二战后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而这个“确认”,不是超级大国谈判出来的,是新诞生的中国打出来的。从此,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了“不信邪”的国格,这种国格赋予了一个大国以铮铮骨骼。
大国还得具有独立的品格。当苏联把一切服务于与美国争霸、暴露出大国沙文主义后,中国对苏联提出了批评,中苏从结盟走向了敌对。当世界各族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形成浩荡之势,中国不但声援支持,而且和印度、缅甸共同倡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形态。当欧洲国家不满美国控制谋求联合自强时,中国明确要把欧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看待。经过这些大国关系的重新定位,中国逐步确立了从国家自身出发的大国关系观,并因此而带动世界其他政治力量在这一问题上看法的变化。
当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后,中国的大国身份回归一体,传统上五大力量的提法也在之后得以确立。但对中国当时大国关系考虑影响最大的,还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五大力量的概念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三个世界理论则是政治和战略的世界把握。无论是五大力量,还是三个世界,中国都在其中占有无可撼动的地位。

中俄高水平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一般结盟意义上的安全关系。形象地说,中俄关系是一种“背靠背”的关系。图为2014年5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和安全竞争让位于经济竞争,一些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主要是德国和日本)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是世界大国,其直接努力就是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使自己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大国概念中多了一个新的成员,即新兴国家。新世纪所讲的新兴国家,一般是指具备大国的底子,而在新世纪的前十年都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赶上甚至超过了一些传统的大国。因此,大国家族里就有了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两类,后者主要以金砖国家为代表。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既是已有大国,又被列为新兴国家,实现了从大国关系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跨越。
在一个新的大国世界胚胎萌生后,中国在大国群体中被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贴上挑战者标签,被推向“修昔底德陷阱”,被断定无法避开大国政治的悲剧。但实际上,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的进程中已明确要致力于历史而不只是逻辑的延伸。历史可以创造,大国可以构建新型关系。
大国关系新常态
大国关系的历史画卷,很容易被历史学家简化为霸权国与挑战国的关系,或者是“均势—失衡—再平衡”的关系。这种逻辑因其简洁而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一旦它转化为实际的国家战略和国际行动,这个过程往往会带来大国战争,甚至是世界性的大战。远的例子不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应对东亚近三四年所产生的问题负直接责任。但是,这种简化版图要被重新描绘也并非不可能,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正在被探索性地构建。这一努力要取得进展,首先必须破除至今影响甚深的大国关系旧思维。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一战给大国关系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结盟。安全困境理论已经揭示,结盟并不能带来百分之百的安全,结盟很容易导致反结盟,而结盟和反结盟的对峙又很容易使得一个小的危机酿成大的冲突。因此,如果大国关系不是以追求世界性霸权为目标,那么结盟战略就应该放弃,单方面的安全应该被普遍安全取代。不过,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现实中,结盟思维还非常顽固。但是,在反结盟不存在的情况下,单方面的结盟动力也会逐步衰减,新型大国安全关系的机会之窗仍然存在。

中国大国战略的主体构想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界定中得到了比较明确的体现,即“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图为2014年3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举行会谈。
一战之前的一百年被历史学家描绘成“百年和平”,其实这个说法只能成立一半。因为从维也纳和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百年中,战争并非绝对没有,而只能说多国性的席卷欧洲大片地区的战争没有爆发。缔造“百年和平”的力量之一是大国协调加势力均衡。但是,通过大国协调与势力均衡维系体系的许多条件在当今世界已难以复制。譬如19世纪欧洲国家的力量均衡可以通过划拨殖民地的办法来实现,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被所谓的正统原则所认可,欧洲大陆的均势和“日不落大英帝国”可以并行不悖。即使如此,19世纪的思想遗产仍被不少大国关系战略家所推崇。
帝国体系是对大国关系的超越。如基辛格所说,帝国所考虑的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大国关系,它自成体系。传统的帝国以领土扩张和殖民为路径,当这一通道被二战后形成的非殖民化运动切断后,新帝国的光环在一些人眼里就越来越炫目,金融、科技、创新体系、网络、军工复合体、跨国精英等成了新帝国的大厦梁柱。这个体系具有平等的表面,等级分化的内在机理。融入这个体系并接受其权力统治的国家被“社会化”,而不愿接受其不平等性的国家则被挞伐为异类,这就是新帝国范式的阳谋。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使命是要破解上述旧思维,而其条件在不少方面已开始具备。旧思维只见国家不见体系,当前的国际体系尽管有诸多不足,但已获得一定的独立力量。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已从最多时的超过一半下降到如今的四分之一略多,说明任何一种力量单独支配国际体系的时代已成过去。无论是对体系本身的渐进改革,还是在传统体系外做增量建设,体系对大国关系的缓冲性和约束性影响已成为大国关系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的国际体系变革战略和目标也正体现在这一点上。
即使国际关系中仍然有“老大”和“老二”之说,但今天的“老大”和“老二”已很难清楚分家,对立关系中已生长出共生关系,共同利益逐步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黏合剂。“老大”和“老二”的关系还不只是双边关系,它也处在一个更大的网络结构中,这个网络结构不是简单的结盟所能代替或覆盖。中国动用其中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影响到网络结构中的“老大”和“老二”关系,使其不再只是遏制与挑战那么简单。
中俄高水平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一般结盟意义上的安全关系。形象地说,中俄关系是一种“背靠背”的关系。中俄两国都可以把背不加防护地露给对方,使正面面向的注意力变得更集中,更有能力应对来自正面的问题。之所以不是传统的结盟关系,是因为中俄战略合作并不以特定的第三方为共同目标。如果设想所有的国家在安全上都可以把自己的背露给其他国家,那么普遍的安全也就建立了。
回到增量体系建设问题。新兴国家的集合体——金砖国家体系构建的影响和能力正在不断提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专注于“授人以渔”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既是对传统体系没能或不愿覆盖到的领域的补充,也在传统体系外发挥了对其改造的影响。从辩证历史的视角来看,当新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包容旧的因素后,新型关系就变得全覆盖了。
经过冷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这种新型关系已成为大国关系的新常态。对于旧思维来讲,接受这种新常态的过程是痛苦的,但这已是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对于中国来说,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以推动这种新常态的发展为运筹大国关系的核心课题。
大国战略
大国战略是大国历史的轨迹理路,也是大国关系的运筹推手。以往的大国战略,一般只讲对其他大国的战略,如美国的对冲战略或离岸平衡战略。但全面地讲,大国战略应该包括两部分:一是通常所讲的怎么对待其他大国的战略;二是一个国家怎么做一个大国的战略。
在如何对待其他大国的战略上,中国已发展出了一个丰富的大国战略思想宝库,构建了全方位的大国战略体系。在对美国这个“老大”的战略上,中国提出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指出太平洋完全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不能让零和思维把中美关系引向冲突对抗的老路。在中俄两个重要邻邦上,要把战略合作不断引向更高水平,用大项目、战略性合作来做实这种高水平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不是让其在高处无基础地空转;中俄要互相借力给力,让高水平的战略合作产生更大的对外影响。在对欧洲国家战略上,要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大国关系,中欧要做“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四大伙伴,共同担负起这四个领域的国际责任,发展高依存度的复合型中欧关系。在新兴大国战略上,中国要推动其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创新实践,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丰富的大国战略内容,体现了中国大国战略设计的针对性和目的性。针对不同大国的特性,中国提出了各有侧重的战略要求。
大国战略更重要的内容还在于如何做一个大国的战略。大国做好了,国际关系自然就会公平公正,国际社会就会风清气正;反之,大国如果乖张暴戾,国际关系的原则就会被恣意践踏,国际社会就处处阻梗赘痈。
作为大国,首要在于坚持一套正确的、经得起检验的义利观,不为利忘义,也不借义逐利。大国在国际关系上不能只讲国家利益,而要举正义,持道义。在国际体系进入转型期的今天,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其重要的道义责任就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法西斯翻案、军国主义回魂。
中国大国战略的第二层要义在于发展自己,惠及国际。大国贫穷落后,只会引起野心者的觊觎;大国发达了,不应天天担心他国搭便车,这有失大国风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蒙古国明确宣布,欢迎搭中国便车,搭中国发展快车。中国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给予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零关税待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战略,以及中国对非洲的“真、实、亲、诚”的理念,都是在诚心地构建共同发展和共享繁荣的伙伴关系。
中国大国战略的主体构想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界定中得到了比较明确的体现。“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既是中欧互相的期许,也指出了中国作为大国的国力所用方向。大国应该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责任,大国应该协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大国应该合作改革国际体系中不够平等、不够包容、不够具有代表性的体制机制,大国应该互相尊重、包容互鉴,共同推动多元文明的沟通对话。
中国大国战略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构建众多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中国不坚持这五项基本原则,也就很难构建起几乎覆盖全部五大洲的伙伴关系网。用伙伴关系替代结盟关系体现了国际关系的进化,因为伙伴关系不制造敌人,而结盟关系无论它怎么声明不针对第三方,仍然要以潜在敌或假想敌为其存在的理由。从双边的伙伴关系到整体的伙伴网络,中国的大国战略面临着从对大国的战略向大国网络战略的升级任务,也面临着新型大国关系战略与大国网络战略的接轨任务。
概括起来,中国的大国战略是以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推动国际体系和平变革为己任,区别实施基于各自目标的不同大国战略,以伙伴关系和伙伴网络推动大国关系的转型升级,担当国际道义,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共同发展,构建并发展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