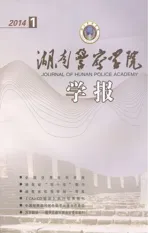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救济制度的法律思考
2014-04-07刘旸
刘旸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81)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救济制度的法律思考
刘旸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 410081)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我国现有政府采购立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现行政府采购法中关于救济制度的规定存在救济主体范围狭窄、救济程序繁冗、质疑投诉处理机构独立性不强、采购暂停规定不健全等问题。在借鉴国际政府采购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应从扩大救济主体的范围、理顺救济程序、确立独立的质疑投诉机构、健全采购暂停规定四个方面着手完善。
政府采购法;救济制度;供应商;采购人;GPA协定
引言
政府采购在国外实施多年,取得了很好的效应且有完善的制度保障。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颁布以来,我国政府采购行为的法制化已走过十年历程。十年间,政府采购规模增长了10倍,由2002年的1009.6亿增加到2011年的逾万亿元,年增长30%左右,《政府采购法》的“保驾护航”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转型,现行政府采购法缺陷——尤其是救济制度操作性不强,存在诸多瑕疵与漏洞;较之国际社会政府采购的参照范本(如GPA协定),我国《政府采购法》中救济制度的相关规定已不能满足政府采购国际化的现实需要,这不能不引起学界和实践部门深思。
一方面,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法的效力冲突、权利义务不对等、程序设计的理想化、现实操作性不强等方面。针对《政府采购法》中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2004年我国财政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行政规章,2010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然而,这些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囿于法律位阶所限不可能违背上位法的规定,这就决定了其不能解决上位法的漏洞,并且在实践中产生了法律适用上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现有问题的妥善解决并不是通过完善实施条例就能够解决,还需要政府采购法本身有关救济制度的有关规定的完善。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背景下,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如何实现在立足国情自成体系之余实现政府采购当事人权利救济的国际化,如何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如何在理论研究层面与现实操作层面寻求黄金切点,是我们优化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政府采购制度的价值基础
政府采购救济制度是指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因政府采购一方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或权利遭到损害时,另一方所采取的补救措施的一系列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是供应商在和政府采购部门发生争议时,当事人能够寻求的对其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或补偿的行政或民事救济方法的总和。总的来说,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价值基础体现在三个方面:公平正义、秩序与调控。
公平正义理论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念,近现代西方思想家将正义用于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甚至被看做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就是基于公平正义观而设计的制度,它通过制定一套公正解决冲突与纠纷的救济程序,即以平等为基础,通过分配正义公平赋予各方权利义务,通过矫正正义来恢复、匡正公平,从而使权利受损者得到应有的救济。为此,从政府采购活动主体方面来说,其救济制度的价值基础源于公平正义的理念。
从社会层面来说,秩序是救济制度的价值基础。秩序作为法的最基本的价值之一,“总是意味着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1]法律制度本身追求的是自由与秩序的兼顾,对政府采购进行立法是为了通过规范政府采购活动来形成公平、自由、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救济制度就是政府采购当事人追求平衡秩序的结果。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如何建立自由安全与公平竞争的社会秩序,确保市场公平运作,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救济制度来维护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正当权益受损的一方。正是秩序的价值追求使得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应运而生。
从国家层面来说,救济权赋予公权机关后,调控则成为救济制度的价值基础。调控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适度规模的政府采购可以从宏观上调节国民经济。完善的救济制度避免了采购人的“寻租行为”,不仅确保了政府采购的目标实现,而且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促进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社会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政府采购的公益性。
二、我国现行政府采购法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救济主体范围过于狭窄
《政府采购法》设“质疑与投诉”专章,规定了供应商权利救济制度。从该法第二十一条、第五十二条来看,实际上主要是从保护供应商权益的角度来规定。由此,我国政府采购的救济制度主要是从保护供应商的权益方面来作规定的,同时,对供应商的范围也作出了界定——“因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的不公遭受损害的供应商;而对于诸如因不公尚未取得投标供应商资格的第三人等潜在的利益受害者,依据条文将不能享有任何救济权利。换句话说,因政府采购活动可能受到潜在利益损害的当事人(如潜在的供应商)就非救济主体[2]。其规定的救济主体范围之狭窄由此可见一斑,这有违于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确保受损害的权益得到及时、合理、有效救济的目的。事实上,不仅投标供应商、潜在供应商权益会受到损害,甚至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采购人的权利也会受到供应商违法手段的侵害。
(二)救济程序设计不尽合理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至五十八条的规定,我国政府采购救济的程序包括询问、质疑、投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从形式上看,救济程序各环节齐全,但仔细推敲相关条文的规定存在救济程序冗余、程序环节衔接不当的问题。
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供应商享有“询问权”,即就政府采购活动中有疑问的事项,“可以向采购人提出“询问”。从“可以”一词的运用可见,该条实际上并没有法律约束力;而且法条即使不作规定当事人也有询问的权利,由此,该条与当事人的实际权益无关联;同时,联系其后法律条文,第五十一条仅与第五十四条有关联,但关键的是,不管是五十一条还是五十四条的规定均没有把询问与质疑形成程序链条,即询问与质疑之间无程序性的先后之分。因此,询问程序环节的设计存在问题。
《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规定了权利受到损害的供应商可以进行依次进行质疑、投诉的权利,如对投诉处理决定不服(或逾期未作处理),可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GPA协定通过法院或者其他实体的审查来保障质疑程序顺利实现。但根据GPA协定,提出质疑并不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也就是说,供应商可以任意选择是提出质疑还是向法院起诉。而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供应商必须经过质疑程序才能进行投诉,必须经过投诉程序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在形式上吸纳了GPA协定等政府采购国际规范的质疑制度,但二者之间却有本质差别。
更为重要的是,因投诉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对“政府采购监督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提出的诉讼,而非对政府采购人的不作为提起诉讼,这意味着采购人的不作为并不能作为供应商提出行政诉讼的正当事由。事实上,在整个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起着主导作用,其一旦出现行政不作为给供应商权益带来的损害更直接。就此而论,我国《政府采购法》只将投诉列为行政诉讼范围,而将政府采购人的不作为行为仅纳入政府采购监督部门监督范畴,实在难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质疑投诉处理机构独立性不强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质疑投诉对象一般是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而《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质疑处理机构是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因此质疑处理机构和质疑投诉对象重合,变成同一主体。在采购活动中,如果供应商对采购过程和结果提出异议,基于其中的利益关系,采购人和采购代理人很难从公平的角度保持其中立性,做到客观的自我评价。
在我国,财政部门作为我国的行政机关,与GPA协定规定的“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的的审议机构”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如美国是由议会审计署和公用事业局的合同申诉委员会专门受理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质疑[3]。财政部门作为投诉受理机构独立性不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财政部门和采购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投诉的处理可能存在隐性或显性的“护短”或“偏袒”;其次,诸如采购方式、文件的确认以及现场监标这些活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早已介入其中,很难在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再次作出客观判断,其中立公正一旦难以确保又何谈作为供应商合法权益的保障[4]。
(四)投诉处理期间暂停规定不健全
《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投诉进行处理期间,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暂停采购活动。也就是说,将提出和采取暂停措施的主动权均赋予了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该条文的立法本意是为了确保政府采购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但事实上,即使在不采取暂停措施将面临不可恢复损失的情况下,供应商与第三人也无法主动提请暂停采购来维护自身权益,而只能被动等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监管职责而作出暂停决定。由此可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暂停采购中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作出暂停决定是为了在投诉程序完成之前避免采购合同生效,以确保提出投诉的供应商的权益。赋予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暂停措施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实现有效的暂停,但是其在监督与纠正采购人的违法行为方面不可能像供应商与第三人那样对权力行使尽最大限度的注意。
并且我国虽然对暂停程序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没有明确暂停救济的适用条件。现有法条仅规定了投诉处理期间的暂停救济,而质疑阶段的暂停救济规定亦是空白。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建议
(一)扩大政府采购救济主体的范围
在政府采购救济制度中,救济的范围一般包括采购人与供应商。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来看,狭义上的供应商仅包括成交的供应商,而不包括潜在的供应商与投标供应商,后两者合称为第三人。
在政府采购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中,政府采购人与供应商(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在政府采购合同授予阶段,由于以采购人的单方行动为主导,容易导致对第三人利益的损害,第三人往往会对供应商资格的认定、采购合同的订立程序、采购合同的授予以及采购合同的条件等提出异议,未中标的第三人理应成为救济的主体;如果中标的供应商为了确保中标成功,采取了欺诈、隐瞒事实等违法手段,侵害了采购人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采购人也完全应该成为救济的主体。在政府采购合同履行阶段,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当事人就采购合同的履行方式、地点、期限等问题产生的矛盾与纠纷,此时无论是采购人还是供应商,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都当然可以获得权利救济。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将进一步放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将参与其中,救济资格的获得是得到权利救济的前提条件,因此,为了保障政府采购各方当事人的权益进而实现采购目的,我国政府采购救济的范围应当包括第三人、供应商和采购人。
需要注意的是,成交供应商易于认定,而对第三人的认定则有一定的难度。为此在确定政府采购救济主体时要综合平衡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要考虑确保受到采购行为不利影响的第三人都能得到应有的权利救济,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滥诉以确保公共利益在政府采购运作中得到顺利实现[5]。
(二)完善政府采购救济程序的设计
救济必须及时、有效。从我国《政府采购法》救济制度的有关法律条文可以看出,现行法律赋予供应商较多的选择权利——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质疑,“可以”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而对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以及有关争议处理机关作出较多的强制性规定——采购人“应当”及时作出答复,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作出处理决定等。显而易见,法律条文对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权益的保护远不及对供应商权利的保护。然而,在有关救济程序的规定中,却将质疑程序作为投诉的前置程序来规定,这又限制了供应商一定的救济选择权。立法本意与法律条文的规定相悖。以供应商为主的政府采购当事人在“受到不公平或不当的待遇时,若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方式,将使整个采购制度的目的,沦为空谈。”[6]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实体权益需要通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来确保,体现在具体的程序中,就使要求简化和缩短询问、质疑、投诉的处理流程。从英国的经验来看,质疑和投诉两个环节是一体的,若供应商有异议,可口头或书面向采购方提出异议,若不能获得满意答复,即可直接提起诉讼[7]。这种简洁的程序设计,加速了救济实现的过程,也极大提高了采购的效率。
而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救济程序如下:
(1)供应商存在异议,须先提出质疑;
(2)如对质疑处理结果(答复)不满,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管机构进行投诉;
(3)如对政府采购监管机构的答复也不满,则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由此可见,供应商不得不在质疑与投诉两个环节上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显然不利于他们尽快地获得救济,甚至可以说,这种“迟到的救济”对注重经济与效率的供应商来说往往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建议,将询问、质疑、投诉的环节进行合并,作为一个整体的质疑救济程序,并取消质疑前置的规定。这样不仅加快了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救济途径,也可以避免将采购人与供应商的矛盾上升为采购监管部门与供应商的矛盾再予以诉讼的情况。
(三)确保质疑投诉处理机构的独立
《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我国采购质疑投诉处理机构是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他们既是质疑的处理机构,同时也是政府采购的当事人。在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的身份决定了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处理过程中和处理结果上很难保持中立和公正。GPA协定对质疑程序的规定要求缔约国应提供一套不歧视、及时、透明而有效的程序,供应商有权对与其权益相关之采购实体违反该协定之行为提出质疑,该套程序必须遵循不歧视、及时和有效的原则。对质疑的处理,应当由法院或者真正具有独立性的审查机构来进行;法院以外的机构在对质疑进行处理时,应当规定特定的程序,这些特定的程序规定类似于诉讼程序[8]。GPA协定中特别规定如果受理或处理质疑的机构不是法院则应当规定特定的程序,其目的也类似于诉讼程序目的是为了保障供应商的合法权益,这无疑体现了要求受理或处理质疑的机构必须具备尽可能像法院一样作出公正的裁定,通过对程序的严格规定来确保在受理及时、受理过程透明有效且不歧视任何当事人方。供应商与采购人发生纠纷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求助于第三方带有诉讼性质、具有独立性的机构,如司法机构或者独立的审查机构。
综合上述考虑,可以在优化质疑与投诉程序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设立一个权威、独立的部门来处理政府采购争议。同时,为了防止因新设行政管理机关而增加行政成本,出于可行性和现实性的考虑,可以将审计机关作为政府采购争议处理机构来考虑。一方面,审计机关在宪法上具备较强的独立性,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受到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扰,独立性是监督权;其次,审计机关具备法律赋予的相应权力,也具备一系列较成熟的处理程序,在程序上也更加独立。
(四)建立必要的政府采购暂停制度
从各国的立法经验来看,主要的暂停制度模式有两种:其一为自动暂停模式,即一旦供应商提出申请,要求采取暂停措施,则采购程序自动停止(法律规定不予暂停的情形除外)。其二为非自动暂停模式,即由审查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暂停采购程序。美国政府采购中,采用的是自动暂停模式,同时规定了不适用暂停的条件(即采购人有正当理由认为政府采购合同符合公共利益需要,或有其他紧急和迫切的理由)。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七条采用的是非自动暂停模式,这保证了政府采购活动的进度,使采购活动部被肆意干扰,但也会导致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救济。在存在损害政府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定情形或者有危害合法权益之虞时,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不能根据相关法条,主动暂停采购程序。在我国政府采购的实践中,当供应商通过相关程序获得救济时,政府采购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权益受损的政府采购当事人职能获得相当于实际损失的赔偿,其数额相对于获得合同机会的收益而言差异明显,其公平地获得商业机会的群益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济。一旦供应商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确在,不仅投诉阶段可以启动暂停,在投诉之前的程序环节也可以启动暂停。此外,在质疑阶段,法定的质疑处理机关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可以作出暂停采购的决定。这些都需要通过建立必要的政府采购暂停制度来明确。可以借鉴美国以自动暂停为原则,不适用暂停为例外的暂停模式,同时可以增加质疑阶段暂停救济规定,赋予质疑处理机关有别于监督管理部门的暂停权力。
政府采购暂停制度也会引起对效率的考量。从表面上看,暂停采购使得采购进程因质疑投诉中止从而增加其成本。但没有暂停制度的保障,如果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出现损害当事人权益的行为,即使违法行为最终得到纠正,对当事人来说都是迟来的正义,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同时也损害供应商公平参与政府采购的机会。建立必要地暂停制度,一方面保障了供应商参与采购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政府采购各方的违法成本,从而从源头上减少了违法行为的产生。
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采购的规模已逾万亿,对象范围逐年扩张,越来越多的供应商参与其中,而对其合法权益给予保障的救济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我国的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应进行适当的变通和创新。具体来说,要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应当从完善《政府采购法》救济制度的有关规定出发来解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问题。救济模式应当是偏重赋予第三人、供应商的权利救济,同时不忽视对采购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采取分阶段救济的基础上,适用于公法救济为主、兼采司法救济的模式。同时,逐步理顺政府采购救济程序之间的衔接,特别是解决相关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问题。
[1]肖北庚.政府采购之国际规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70.
[2]叶姗.政府促进公平分配权力的体系性思考[J].时代法学,2012,(2).
[3]John Cibinc,Jr&Ralph C.Jr.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Contracts,Washington.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3rd Edition,1995,1311-1312.
[4]焦富民.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65.
[5]刘晓宁.我国政府采购中供应商权利救济机制的法律分析[D].兰州:兰州大学,2012.
[6]罗昌发.政府采购法与政府采购协定论析[M].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0:325
[7]刘军民.英国政府采购对中国的启示(4)[EB/OL].http://www. xj71.com/2012/1102/692281_4.shtml.2013-12-10.
[8]张海洋.我国政府采购救济制度体系的缺陷和重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64.
Improvement of theRelief Systemin the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LIU Ya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
With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curren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egislation can not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reality.There are many problems of the relief system in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Firstly,the range of participants is narrow;Secondly,the relief procedures are inappropriate; Moreover,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and the procurement moratorium are insufficient.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nd combined with 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China'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ystem should extend relief scope of the subject,streamline relief procedures,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complaint mechanism and improve procurement moratorium.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relief system;suppliers;procurer;GPA agreement
D922.112
A
2095-1140(2014)01-0061-06
(责任编辑:天下溪)
2013-10-23
刘旸(1987-),女,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2011级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