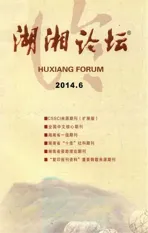法治思维论析
2014-04-07杨叶红
杨叶红
(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0)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不仅仅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建设法治政府和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还应当是个体思维模式转变的问题。如果没有养成法治思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政府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都将不过是美妙的海市蜃楼。执政党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从十八大报告以来党中央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屡屡提及“法治思维”,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法治思维”也引起了全社会特别是法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先后有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法治思维的内涵,本文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法治思维与其它思维之间容易引起误解和误判的地方进行深入辨析,对法治思维内涵进行细致分析,使这一概念呈现出更加清晰的面貌,更好地指导具体实践活动。
一、法治思维内涵分析
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是将法律规定、法律原则、法治精神付诸实施的认识过程。[1]法治思维是在坚持法治理念的前提下,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治精神对有关事项、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过程。法治思维的具体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法治思维以合法与否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法治思维的重心在于“合法性的分析”,即围绕着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益和关系。[2]运用法治思维就要求排除其他非法治思维的干扰,实现法律的优先地位。“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法治思维方式应当具有优先的位次,意味着包括治国者在内的一切人都应首先按照法律的指引来行动和思考。可以说,法治思维优先和合法性优先,是依法治国和法治原则所必然要求的一种思维方式。”[3]
但是,尽管现在很多人在高喊法治,却没有多少人发自内心地信仰法治。循规蹈矩的思想被认为是迂腐呆板,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超越规则被认为是开拓创新。以改革和法律的关系为例,改革总的说来是在前进,而法律相对滞后。如何处理不断变动的改革和相对稳定的法律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早期,主宰两者关系的主导性思维是 “改革先行,待条件成熟,成果显现后,以法律形式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法制建设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有人甚至提出“改革从违法开始”,“不违法就不能改革”,“良性违宪”、“良性违法”的观点一度流行。先行思维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因为过去的改革任务重在“破”,要打破计划经济束缚、要破除陈规,要消除阻力,而且很多方面没有法律,无法可依,需要先破后立,边改边立。而今的改革任务重在“立”,要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是当前的重要任务。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和“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的要求,充分体现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治理理念,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反映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进步与完善。在重大的改革方面,不能够随便突破,也就是说在重大的改革问题上,必须先改法律,然后再来实践;而不能倒过来,先改革,然后再改法律,这是对法律权威性的尊重。改革中的任何创新都必须以“合法”作为底线。
(二)法治思维以权利义务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
围绕权利义务分析问题是法治思维的重点所在。权利义务是法律的基本范畴,法律的目的在于促进个体权利的实现,推动个体适时而合理地承担和履行义务。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对立统一衍生出法律的所有现象。国家治理、社会管理、行政执法、化解纠纷等都需要尊重保护权利、履行义务、承担法定职责。随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理念的宣传,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公民的政治、经济、人身、社会权利多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公众依据法律维护权利的意识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却习于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而非权利义务思维,两者之间的冲突往往导致诸多社会矛盾。
(三)法治思维以平等作为处理问题的价值导向
法律的核心是“平等”,法治思维必然包含平等性思维。平等是一种人与人相互同等对待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4]公民在法律意义上具有平等的地位或权利是现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最基本的法律价值之一。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现代法律中平等价值贯穿法治的各个环节,它是立法的指南,是执法、司法的准则,也是守法的心理基础和精神力量。法律平等性要求行使公共权力时要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政府与民众之间多一些平等协商,少一些颐指气使。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平等的精神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应当指挥或不受指挥;而是我们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不是打算不要主人,而是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人去当主人。”[5]
(四)法治思维以程序正义作为化解纠纷的理性考量
法律非常重视并强调程序的运用,由此派生出作为法治思维组成部分的程序理性思维。程序理性思维要求化解矛盾处理纠纷时以法律的概念、原则、规范、程序作为思维的根据,以法律作为说服的主要工具,抑制非理性的冲动,注重程序的公正性、程序的优先性和程序的终局性。
程序理性强调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强调正当程序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犯。政府滥用权力和司法腐败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了普通违法犯罪分子。如果仅仅为了抓住一个违法者。一个罪犯实现实体正义而违反程序正义,这必然导致政府权力或司法权力侵犯公民权利。通过程序公正来追求实体公正,虽然有时会导致一个不公正的实体结论,但它换来了普遍性的实体公正。上个世纪美国辛普森杀妻案中美国人对程序正义的支持正是法治思维的具体体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指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任意或反复无常的人治之间的大部分差异。坚定地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是我们赖以实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享有正义的主要保证。”[6]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过渡期,政府和民众大多强调实体公正优先而非程序公正优先,重结果而不重程序,认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或认为强调法律程序,严格按程序办事,就是自找麻烦,自缚手脚。国家治理中特事特办、钓鱼执法、刑讯逼供、非法拘禁、从重从快打击等现象层出不穷。公共事件讨论中多的是政治、道德的激烈评判,少的是法律的理性分析。面对公众非理性的情绪,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应当坚持程序的公正性、优先性、终局性,通过以案说法,运用法律的概念、原则和规范来说理,抑制公众的非理性冲动,维护程序的公正与法律的权威。
(五)法治思维以规则底线作为制约权力的基本要求
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是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进步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7]在英国法学家戴雪的概念中,法治是指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民可以依据法律对抗专断的权力。[8]当前在理念上虽已形成法治共识,但在实践的关键环节权力的拥有者却仍然以权力思维代替法治思维,强调法律的管控功能,而非法治的限权功能。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在社会较为普遍存在对权力不信任的当下,领导干部需要抑制权力的过度张扬,树立对法律的敬畏,自觉主动地接受法律对权力的制约,领导干部要坚守权力的法律底线。
二、法治思维与其它思维的比较
法治思维是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等其他思维不同的一种思维模式。
(一)人治思维与法治思维
从治国方略的角度来看,人治是指以领导权威、中央集权和等级秩序等为主的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则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国家治理模式。与之相应,人治思维要求国家治理以统治者或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法律仅是管理工具和手段;法治思维则要求国家治理以法律为依据,代表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最高权威。人治思维强调人格化权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法治思维恪守非人格化权威,法律制度不因人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文化崇尚人格化权威,法律规则作为非人格化权威也要尽量转化为人格化权威,才能被接受、遵从。比如,“红灯停、绿灯行”这一法律规定作为非人格化的权威需要“电子眼”监控或执法人员在场才能生效,如果一个路段没有“电子眼”监控,也没有执法人员在场,这一规则往往就形同虚设,出现“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闯红灯”现象。这种无视法律,不接受法律约束的思维惯性给国家和社会治理带来很高成本和不确定性。
(二)权力思维与法治思维
权力思维的重点在于命令与服从,权力者意志得到执行、社会的表面稳定、公民的沉默服从义务远远大于公民的正当权利。法治思维强调制约公共权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国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对官员而言,他们往往认为法律是自己的工具,拒绝接受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对普通公众而言,国人头脑中始终存在着对强权的崇拜,对贤明领导人的渴望,总是过于相信权力依赖权力,法律则没有权威。权力思维定势对“法律至上”理念构成了强大的排拒力,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法律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发挥作用,甚至演变成了权力者滥用权力的工具,权力者以法律的名义实现了权力效益的最大化。童之伟认为:“许许多多的公权力组织处理事务的原则基本上是这样:法律的规定于己有利,能够约束普通公民,就说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的规定有利于公民,自己的行为受到了相关法律条款的限制,他们就把法律丢在一边。公权力组织最为恶劣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不走任何法律程序,任意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有的地方如此行事居然不给予任何解释,连搪塞百姓之口的借口都不愿找一个。”[9]
(三)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
政治思维的突出特征是一切问题的分析和处理都必须服从于政治需要,服务于政治形势,与政治立场、政治利益不一致的事实就会过滤掉,法律同样如此。法治思维则坚持法律的权威地位,政治权力与利益的博弈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当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普通民众都习惯于政治思维。领导干部推动发展、维护稳定、化解矛盾强调的是政治思维。普通民众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是通过法律而是通过媒体炒作来吸引舆论关注扩大社会影响,将一个维权行动转变为维权斗争,通过制造公共事件以求得问题的解决。信访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思维引导下的制度安排,明明是法律上的争议不走法律途径,却去寻找政治解决。[10]我国的法律救济一直面临着受案数量不足、立案难、审理难、败诉高、执行难等困境,而信访总量始终居高不下。地方政府投入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化解上级政府和上访者施加的巨大维稳压力。而大多数上访者信奉的是,地方政府越是害怕他们上访,他们就越是要不断上访,相信只有不断上访才能最终解决问题。在政治思维影响下的社会维稳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四)经济思维与法治思维
经济思维的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法治思维的重心在于强调法律规则的治理,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当前各级政府和官员考虑经济增长优于法治建设,在比较守法成本与经济收益后将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认为法治思维保守僵化,不利于开拓创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出台了很多违反法律规定推动经济发展的招商引资政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招商企业,对引进企业或一些重点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规定行政执法部门不准检查。在经济思维的主导下地方政府领导视法律为空文对重点企业实行特殊执法保护,而这些企业则借 “保护牌”从事违法活动赚取非法利润。“福建紫晶”矿业污染造成当地渔业损失惨重和“哈药总厂”超标排污事件,就是其中典型案例。
(五)道德思维与法治思维
道德思维的重心在于善与恶的评价,法治思维的重心则在于依据法律来进行合法与非法的预判。道德思维强调实体正义,法治思维强调程序正义。古代中国将“德治”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政治社会生活泛道德化,人们的惯性思维是道德思维。对此,黄仁宇曾指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11]当前人们受惯性思维影响仍习于从道德角度评价问题、推理问题,把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以个案的道德实体正义来取代普遍的法律程序正义。近年来热点案件的舆论反应,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药家鑫案、唐慧案、李某某轮奸案、夏俊峰案中,舆论反应激烈、以道德的名义一边倒地声援“弱势者”、声讨“强势者”,罔顾法律规定毫无原则地为弱者代言。
[1]董节英.法治思维从哪里来[N].学习时报,2012-12-11(3).
[2]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4).
[3]董节英.法治思维从哪里来[N].学习时报,2012.1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7][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8][英]戴雪.英宪精义[M].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9]童之伟.就管理体制向十八大进一言[EB/O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fzyj/article_2012111270860_2.html,2012/12/02.27.
[10]张卫平.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J].浙江社会科学,2013,(12).
[1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