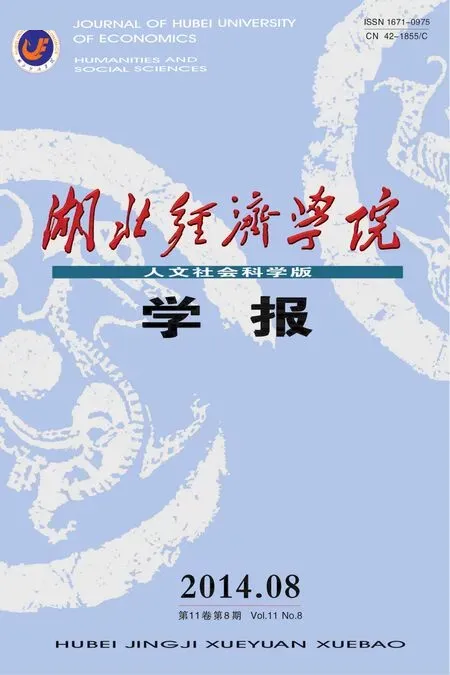中庸的自我性情修养实践
2014-04-06杜小兰
杜小兰
(延边大学 人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中庸》作为儒家传统文化体系的理论基石,是一部具有哲学思辨色彩的著作。中庸之道曾经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几千年后的今天,当西方的“丛林法则”大肆进入中国,我们不仅不能摒弃这一传统理念,反而更应该发掘其中的伦理意义,并利用其修养自我性情,从而实现由“内圣”到“外王”的转变。
一、如何修养自我性情
中庸常因为古人迂腐含糊和模棱两可的作风被误认为是骑墙主义和折中主义,而《中庸》实则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先王的治国之道告诉我们要从正反两反面认识事物,坚持无过无不及的原则。那么如何在处世、治国中修养中庸这一自我性情呢?
(一)坚持“君子慎独”的行为方式
《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便把性、道、教单列出来,并指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自我教育,而教育的目的是修道,是按照道原则复归人类本性。这一章紧接着又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之中,片刻不可离开,君子在人所不知而己独处之境仍然以一种强有力的道义约束着自己,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
“慎独”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缺少监管下的行为方式,联系前句看来,它也是人类修道的自觉体现,是对人性、天理的能动求索。基于对天理的探索和人类自然本性的发掘,社会的伦常秩序便会得到匡正。然而即便是人们认识到了“慎独”的重要性,却依然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不能时刻坚持。“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恐惧自己单独的时刻不能做坏事,能严于律己,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庸》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心灵之诚。”①
(二)秉承“以诚为本”的根本理念
“完全实现天人合一理想的可能性是每个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②这里的天人合一指的便是修行中庸之道的至善境界,前文说过,践行中庸之道需要时刻以“慎独”观念警醒自己,但是人们长期恪守这一准则却并非易事。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他扮演的角色都非常复杂,自身所受的各种诱惑和压力都使他无法坚持 “慎独”,这时,由内而外的“诚”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庸》二十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从之也。这里“诚者”之诚和“诚之者”之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天道,一个是人道;一种是圣人,一种是君子。如果用体和用的关系来表示的话,作为天道的诚是真实无妄的本体,作为人道的诚便是真实无妄之意。《大代礼记·哀公问五仪》记载孔子把人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五仪,我们学习儒学得目的就是不断开启我们的智商,修养我们的性情,不断的由混沌的民之状态向君子乃至更高的境界发展。这时“诚”是我们行为的出发点,也是我们修养的目标。
《大学》八目也强调修养人格境界,并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分为内圣和外王两个阶段。这里言明“意诚”而后“心正”,而后“身修”,也说“诚”是修生途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庸》中,“诚”作为一种本体,它已经超越了一种简单的精神状态,更是一种能动的力量,使人能够天地中并立起来。
二、修道以仁——自我性情修养的目标
《中庸》第二十章提出:“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为人的本性就是“仁”,而亲爱自己的亲人就是最大的仁。“为政”在于人,在于“修身”,文章的第一部分就阐述过自我教育的修身便是修道,而“道”的根本就在于“仁”。结合前文,我们可以理解为“诚”是天道和人道的核心,诚是天命的本质,当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仁”,所以我们在践行中庸之道是应修道以仁,由此实现通过“践人”以“尽性”。
“诚”是天道和人道的统一体,“天命谓之性”,但这个天命也就是人之性是隐而不显的,孔子思想的核心体系之一是“仁”,这也是对君子的一个最好诠释,所以个人应当修养中庸之道来实现“仁”,也就是“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同时“仁”也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在《论语》中,曾有一百多处提到仁。由于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规范,而且它又是自我性情修养的目标,所以它集中了许多道德的、感情的、心里的范畴,我们不能简单的给它下一个抽象的概念和明确的概念。《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里也说虔诚是“仁”的起点,和《中庸》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仁”以诚为出发点,主要包含爱与敬两个方面,细数仁的条目,包括恭、宽、信、敏、惠、孝、悌、爱人、立人、刚、毅、木、讷、勇等,是包罗众德的大端,也是我们在修养君子之道应该着重培养的性情。
结合前两章可以看出,“慎独”、“诚”和“仁”三者之间有着互相作用和转化的内在关联,我们在修养自我性情时,应该长期坚持中庸之道,始终“以诚为本”,做到“慎独”,并修成“仁”这一包罗众德的人格境界。
三、中庸的自我性情修养的当代意义
当代人的生活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厚的表象下,却隐藏着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是来自人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多重矛盾。而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了解中庸的中和观念,对我们今天的行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自我性情修养的伦理价值
“对一个特定民族来说,对一个特定文化生态来说,可以没有伦理,也可以没有宗教,但决不可能同时既没有伦理,也没有宗教,否则便会造成行为的失范、价值的失衡、情感的失调,因为它意味着社会失去规范性和引导性的文化力量。”③中国治国讲求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但却是一个缺乏信仰,孔方兄大行其道的国家。每天媒体上各种骇人听闻的惨痛消息无不使我们震惊:“夺命快递”,“摔童惨案”,“伯母杀亲”等等,让我们开始思考人性善与恶的转变。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看作是伦理性的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中的人神直接对话不同,我们的伦理文化在人与天的对话中有一种伦理的媒介,而这种媒介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误读,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直接的威慑性,在只注重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正逐渐隐退。
我们从《中庸》可以知道,生态伦理的精神危机指向了人的心灵世界,我们的内心由于缺乏“诚”,便身不“仁”,这也是社会上各种惨案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对此《中庸》在解读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中提出了“三达德”、“五达道”的主张。
《中庸》第二十章: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指出,五达道和三达德的内在关系,认为:五达道是古今天下所遵循的共同法则,要靠三达德来贯彻实行;而三达德是使五达道付诸实践的三个有机联系的步骤。上文讲“修身以仁“,天道之诚贯彻到人性之诚上往往转化成“仁”,“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这一切都最终都落脚在仁的上面,因为仁不仅把知和勇包含在内,不仅是一种趋于至善的性,而且还会把这种内驱力外化,转化为情,表现为:夫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此可见,“仁”是一切全体,因为我们在处理自己与内心、与他人的关系时,应践行仁道,践行中庸之道,如此便可天下通行,天下归善了。
(二)构建天人合一的生态社会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则应该使“征服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决策都必须符合系统论和社会生态学的基本思想和原则。④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有两种主流思想:一种是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高于人类,人类必须顺应和服从大自然;另一种则是技术中心主义,认为人居于高于自然的地位,人类可以征服自然。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不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需要。
《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归根于至诚、至善,最终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使人与自然、与环境和谐发展。
《中庸》第二十四章: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也就是说,秉承天命之诚的人,不仅是要爱人,而且还应该“知“,也就是对事物的探究和认知。
和《中庸》所倡导的天人观一致,马克思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反对纯粹的生态主义中心,也要反对自私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古代讲究天、地、人三才,人和自然本就是一种相互交往着的社会存在,双方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如此循环往复并最终走向统一。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深受环境污染的危害,最直观的感受是各大城市的雾霾,不仅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也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而这些不便的根源却是我们自己对环境的征服和破坏。中国古代从来都是敬畏自然、敬畏天的,因而儒家的传统观念也是基于此的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倘若我们今天能合理的利用儒家之道,中庸之道,并将之应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更加友好地对待自然,以及大自然的所有生物,对于解决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以及构建和谐自然无疑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中庸之道的主体思想就是自我修养、自我教育,它通过一系列具有哲理色彩的践行方法,逐渐培养我们的性情,并逐渐完成向至善、至德境界的转化,而且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积极学习内化中庸之道,不仅可以较好的处理人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也能行之有效地解决人与自然、与社会的种种危机与矛盾。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BWW020)
注 释:
① 王岳川:《大学中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② 杜维明:《中庸洞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③ 樊浩:《伦理的文化本性与文化定位》,中州学刊,1997年版,第4期,第77-78页。
④ 肖显静:《生态政治》,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王岳川.大学中庸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张思敏.中庸:儒家君子人格的最高境界[MA].兰州大学,2008.
[5]刘光育.中庸思想研究[D].河北大学,2001.
[6]徐启彬.生命伦理学与《中庸》的生命伦理精神[J].东南大学学报,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