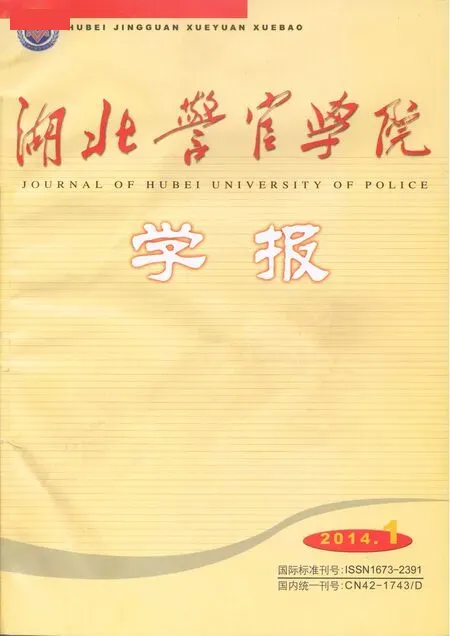晚清的治安体制及其弊端
——以张之洞建警之前的湖北为例
2014-04-06邹俊杰
邹俊杰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武汉430034)
晚清的治安体制及其弊端
——以张之洞建警之前的湖北为例
邹俊杰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武汉430034)
“警察者,警其未然,察其已然。”1902年,在张之洞创设湖北警察制度于武昌之前,湖北社会依然处于传统的治安体系控制之下,其特点是军警不分,政警不分、政刑不分,其百弊丛生、病入膏肓之态在清末社会内外交困的时局下表现得尤为明显。
警察史;晚清治安管理;治安体制;治安机构
警察之制,发端于西欧,为清末之“舶来品”。①这警学界公认近代警察制度的创立者是英国政治家罗伯特·比尔,其于1829年创立了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并提出组建警察的十二条原则,此举被誉为世界警察史上的第一次警务革命。清代在建立近代警察制度之前,政府尚未设立专业的治安管理机构、未颁布专门的治安法律,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持和法条律令的执行一般是由绿营、各级地方政府衙役、捕快和保甲、团练等共同承担。清末近代警察制度尚未引入中国之前,各大都市和各府厅州县城镇,设有保甲局的地方,则有几个局丁跑跑差事,夜里则有几名更夫轮班敲梆打更,多住在城楼上。官府衙门,除规定有差役、民壮听用外,则有“绿营兵勇”穿着号褂子、排成小队,间或在街上查查街。至于绿营的节制,则有参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官弁,随县府辖境之大小,分别驻扎以资弹压而维治安。前清绿营的腐败无用,几乎中外皆知。[1]
下面就1902年张之洞创设武昌警察总局之前的清末湖北社会的治安体制及其弊端加以论述。
一、绿营
绿营兵制实行操差合一的模式,其职责包括操练以备战时军事征调之用及平日承应各种差役。其各种杂役包括解送钱粮、银饷、人犯、守卫仓库监狱城门、缉捕盗贼乱党、侦察邪教会盟秘密会社、查禁聚赌娼妓、巡稽私盐、清道捕蝗等。[2]其中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占有相当的比重。“国家设官定制各有职司,文以抚民,武以除暴。”[3]“州县额设捕役,多者不过十名,少者数名,侦缉势难周到。是以责令营兵协缉。”②辅德:《请定将弁协缉事宜疏》,《清朝经世文编续编》,卷80。时人评价:“从来除盗贼之法,有治之于其源者,有治之于其流者,衣食之,教诲之,使民化而不为盗,此治之于其源也;防闲之,缉捕之,使民欲为盗而不敢,此治之于其流也,二者不可偏废。然治之于其源者,弭盗贼于未形之先,其效深而迟,大而难,当委之于文官,而宽之以岁月;治之于其流者,弭盗贼于既起之后,其效浅而速,小而易,当责之于武官,而课之以功罪。”③王銮:《拟除盗贼策》,《清朝经世文编续编》,卷80。在清廷的制度设计层面,绿营“原为稽查奸匪,缉拿盗贼,护送差使。”④昆冈等撰:《大清会典事例》,卷626、卷634。如绿营兵弁对于盗贼疏于防范、缉捕不力、隐匿不报者严加处分。绿营赏罚条例规定:各地营汛地方,每年需统计盗贼等案件,根据拿获盗贼之数目和破获盗窃案件之多寡分别加以赏罚。绿营各官查盗不严、缉盗不力、讳盗不报者革职。若地方被盗失事,则专汛官停俸,兼辖官罚俸半年,限一年之内缉拿,否则革职。⑤昆冈等撰:《大清会典事例》,卷626、卷634。由此可知,绿营实则承担着社会治安治理的重任。湖北之绿营据苏云峰先生估算在1841年之前约为14,000人,其主要功能为社会治安的维持。⑥苏云峰:《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第17页。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运动,湖北绿营一度增加至20,000余人,后在胡林翼的整顿下大力裁汰,仅留10,000余人。
绿营是湖北军队和治安力量的主力。清廷为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防止将领专权,将绿营兵设为固定职业,一般世代为业,但承平日久,长期以来其缺乏训练,导致军纪废弛,几无战力,太平军所向即一触即溃,这便是有力之佐证。胡林翼认为绿营怯懦,浮报正额,无营制,无纪律,往往“闻警先惊,接仗即溃”,是一支抗敌不足,扰民有余的军队。①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14,第3-4页。“(绿营)饷项虽加,习气未改,亲族相承,视同世业。每营人数较多,更易挟制滋事。……至于调派出征,则闻风推诿。其不能当大敌御外辱,固不待言,即土匪盐枭,亦且不能剿捕。”[4]绿营在承担维护社会治安之差时,轻则敷衍塞责,重则以身试法而为非作歹、扰害一方,屡为舆论所垢弊。
鄂省防营甚多,其中勇丁强悍性成,往往聚众滋事。营务处司道闻之,特于日前会卫出示,严行查禁。略谓:兵勇之设,本以卫民。近闻各营勇丁每三五成群,游行街市,动辄打架斗殴,实属不成事体。②《申报》,1902年3月8日。
鄂省营勇众多,动辄逞强滋事,前经营务处司道会街出示,严切告诫,意细柳中人当无不闻风警惕矣,乃若辈性成强悍,依然怙恶不悛。本月某日,有武防营勇多名在汉口某妓院争闹,突出利刃斫伤五人。夏口同知冯少竹司马以情节重大,立即禀明督宪张香涛宫保,请饬彻底根究,而统领某君意存袒护,辩称勇丁亦受重伤,不肯交出。③《申报》,1902年3月9日。
有鉴于此,张之洞认为:“绿营制兵积习积弊,已入膏肓,无论原营未练之兵穷苦羸弱,无可整顿,即挑练之兵亦狃于积习,非但战守断不足恃,即巡警亦万不可用,只有分年尽数裁撤之一法。”④《申报》,1902年5月3日。张督鄂后,逐年将绿营加以裁汰,用结余之饷而创办警察,后湖北编练之警察和新军逐渐取代了绿营。
二、衙役
湖北各级政府自督抚司道至府厅州县各级官吏,都有维持所辖地方治安之责,并设有佐职官协助督捕盗匪、审理案件和维持秩序⑤关于清代治安问题,可参见朱绍侯《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陈鸿彝《中国古代治安简史》、万川《中国警政史》等著作。。督抚处理全省政事,布政使督促各属编练保甲事宜,按察使督理各属捕务,皆有监管治安之责。道府各官皆有“决讼检奸”⑥赵尔巽:《清史稿》,卷116,志91。之任,各府设有同知、通判等附属佐贰官,协助知府处理所辖各属捕务。州县是帝国政府官僚系统中的最下层,是地方治安的最直接负责组织,州有州同、州判,具体负责“分掌粮马巡捕之事”[5],有专吏“司奸盗、察狱囚、典簿录。”⑦赵尔巽:《清史稿》,卷116,志91。县有县丞、主簿等附属佐贰辅助官,“分掌钱马、征税、户籍、缉捕诸务。”⑧赵尔巽:《清史稿》,卷116,志91。其中具体案件的侦查、缉捕事宜则由主管官吏交由游离于正式行政系统编制之外的差役负责执行,捕快、马快、民壮等差役都具有侦缉捕盗之责。有些地方将马快与民壮合为一役,“名曰壮快,一体操练,分班巡缉。”⑨《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考三。另外,在基层的一些要津和繁华之市镇设巡检司,“掌捕盗贼”⑩嵇璜等,《清朝通志》,卷69,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3页。,就近负责当地的社会治安。清代的巡检司巡检为从九品,各地所设多寡不一,湖北为74人。巡检在治所之地兴建有衙署,内驻扎差役几人至几十人不等,差役一般为弓兵,设有定额,由招募承充,在巡检督率下,巡逻盘查行人、巡缉关道、缉拿盗贼。
在州县治辖之下的广大乡村,由于地域广袤,绝大多数乡民分散居住在农村,且交通不便,政令传达不仅耗时日久,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这极大地限制和削弱了州县政府对于基层的控制。因此,州县政府对基层的治理和控制仅仅依赖职官、佐贰附属辅助官员和差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在究缉奸宄、打击犯罪、维持当地秩序和社会治安领域,保甲、团练等乡里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层面的力之不逮。⑪关于清代保甲、地保、里甲、团练等乡里制度之研究,可参考瞿同祖《清朝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先明《晚晴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刘道胜《清代基层社会的地保》,《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赵丽娜《民国时期湖北保甲制度研究(1927—1937)》(硕士论文)等专著和论文。
基层系统里负责缉捕事宜的差役不仅身份低微,因没有正式编制而游离于国家的官僚体系之外,甚至社会地位低于普通百姓。当时规定捕役及其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和入仕为官。“在所有的衙役中,捕役的地位最低”[6],捕役不仅薪资微薄,官府甚至连工食亦不提供,他们只能通过陋规、赏金等收入为生。为提高办案效率和防止捕役勒索扰民,雍正年间,政府曾下令州县衙门为捕役提供工食,“每捕役一名,将他役工食量为供给,使其养赡充裕。”⑫《清朝文献通考》,卷24,职役考四。但这仍不能满足养家糊口维持生计之资,故收效甚微。捕役虽人微言轻、地位卑微,但其人数不仅很少而且职责颇为繁重。州县捕盗缉贼不得不主要依赖捕役,为提高捕役的积极性,官府亦只能通过严定赏罚以约束和激励其勇,“其捕盗有限,轻则加以扑责,重则质其妻子,能获要盗,赏亦随之。”⑬《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考三。然充当捕衙之人多为市井无赖之徒,或为土棍游民之类,甚至狡盗黠贼亦混身其间,官府平日依靠此辈办案,虽时常催促、重其赏罚,亦颇难对其约束。此类捕役因积习难改,故平日欺压良善、仗势欺人、横行霸道,遇有案件或敲诈勒索,或逼良为盗,或敷衍塞责,“除暴则不足,扰民则有余,索贿则争先,逐贼则居后。”[7]罪大恶极者,甚至与盗贼狼狈为奸,内外勾结。“故每一案出,往往获真盗难伤其类,诬良民亦不患无辞”,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职役考一。“各属州县无不知差役害民,而不能去之者,马快则缉捕倚之,各役则奔走传呼倚之。公费无多,不能养其所欲,于是有票规赌规等名目,与家丁书吏分肥。”②《直督札饬推广巡警裁革差役》,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申报》。另一方面,“差役之为民害,各省皆同。必乡里无赖,始充此业,传案之株连,过堂之勒索,看管之凌虐,相验之科派,缉捕之淫掳。白役之助虐,其害不可殚述,民见差役无不疾首蹙额,视如虎狼蛇蝎者。”[8]差役逼良为贼、勾盗分赃、假公济私、贪得无厌,以此为业,乐此不疲。时人认为:“(差役)盘踞最久,爪牙最多,能施其伎俩无所不为”③《四川官报》,1905年第29册。,“差役不去,则官民隔膜,上下之气永不能通”④陈炽:《仿设巡捕说》,《清朝经世文新编》,卷3。。更有甚者将差役誉为积弱积贫而亡国之首:“古今可以亡国者,曰女宠、曰宦寺、曰外戚、曰强诸侯、曰权大臣、曰匹夫横行,而不曰胥吏。实则胥吏之祸烈于女宠、宦寺、外戚、强诸侯、权大臣、匹夫横行。”⑤尹耕云:《胥吏论一》,《清朝经世文编续编》,卷28。“差役之为民害,各省皆同。必乡里无赖,始充此业。传案之株连,过堂之勒索,看管之凌虐,其害不可殚述。”[9]甚至清廷官方亦不得不承认,“今天下之害民者,州县差役其最著者也。”由于捕役腐败,故其所破获之案件甚少,社会治安难以安宁,其他各类差役莫不如此,差役之弊积习甚深,已积重难返。
三、保甲
清代自入关以来便沿用了明代的保甲制度。保甲的主要功能原在维护社会治安和控制人口流动,里甲则为田赋与劳役之征召。“保甲之设,所以使天下之州县复分其治也。州县之地广,广则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众,众则行之善恶有未详。保长甲长之所统,地近而人寡,其耳目无不照,善恶无所匿,从而闻于州县,平其是非,则里党得其治,而州县亦无不得其治。”⑥沈彤:《保甲论》,《清朝经世文编》,卷74。保甲制度的产生可以一直上朔至周代,但清政府所采取之保甲制度主要是参仿王安石于1070年变法时期所设之制。其实王安石采取保甲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保甲侦查信息和控制犯罪,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之效。清代采取保甲之制的目的亦在于此,其方法是强化乡村人口流动的登记与控制,以防范犯罪事件之发生。入关以后,清政府视保甲制为弭盗安民之良规,因袭明制大力推行保甲制,编练保甲以利控制。政府规定:十户为一牌,设牌长;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各有长。凡造册入户,各登其丁口之数而授之坊厢里各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州县合而上之府,府别造一总册上之布政司。民年六十以上开除,六十以上增注。凡籍有四:曰军曰民曰匠曰口。……督抚据布政司所上各属之册达之户部,受直省之册汇疏以闻以周知天下生民之数。”⑦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9。汉人、旗人甚至无业游民、僧侣、船户等都被编列造册,无论城乡都需办理保甲之制。胡林翼任职湖北巡抚时规定“应有门牌,有册籍。分乡、分团、分里,首列地名即四至八到;继列户口、田亩、漕粮、户柱、邻右、行业、丁口、男女老幼。择一人长十户,择一人长百户,以一人副之;择一人长千户,以二人副之。以平日保正甲长为之役,能进退赏罚之。所择必正直严明之人,官隆礼貌以待之,仿古三老、啬夫、游檄之义。钱粮、刑名、词讼案件皆以此为根,不下堂而一县治”⑧郑敦谨、曾国荃:《胡文忠公遗集》,第85卷,“抚鄂批札”2,第19页。牌长、甲长、保长由辖区民众推举稍有学识、品行端正及有一定身家者,报与官府,由官府任命。凡发觉甲内有偷盗、聚赌、谋逆、邪教、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会党等事及形迹可疑之徒,牌甲保各长及邻里,皆有向有司报告之责,倘有袒护奸宄、隐匿不报,一经核实,必严加惩处。此外,倘若户数增减和户口迁移变动,均需向牌甲保长随时报明并将门牌填明换给。保甲之制的主要功能在于究诘奸宄、弭盗惩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清中叶摊丁入亩之后,里甲的主要功能已不复存在,故逐渐为保甲制所取代。保甲制的职能亦因此扩张,由弭盗安民渐渐充各种差役。另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家庭与宗族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之地位。“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查举”,族长、族正亦具治安之责。⑨昆冈等撰:《大清会典事例》,卷158。家庭与宗族的社会控制职能寓于传统的纲常伦理之中,同时亦为政府所支持,以达到将政府的社会控制职能延伸之目的。
保甲的主要职能为“清内奸”,但保甲之制发挥效用的前提是掌握和编练人口信息,只有对人口施以及时、准确的编查才能确保其健康正常的运行,以便发挥其最大的效应。地方官吏如能实力奉行保甲之制,则“人类良莠,平时举可周知,惰游匪类,自无所容,外来奸宄更无从托迹,于治理最为切要。”⑩昆冈等撰:《大清会典事例》,卷158。将所编练之民置于邻佑彼此监督,施以连坐之法震慑,迫使普通百姓不敢犯事妄为。相比较于周代时期突出“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君子也……”的比闾之法,保甲之制则强调“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职役考一。二者形虽相似,然意却迥然不同。保甲的执行方面,自清代中叶以后,吏治渐坏,地方官长往往玩忽职守,将保甲视为具文,习惯于敷衍了事,甚至置之不理,即便上司下札申斥,不过虚编故事,而在具体编练保甲时则“造册有费,立牌有费,择派甲长保正,亦莫不有费。”[10]在一些地方州县甚至出现“一县之大,每岁仅报滋生口数,……岁岁数目一律雷同”①《清朝文献通考》,卷19,职役考一。之事。“地方有司,向来视为具文,而历任督抚亦任其随意填造,不复加查。”②《清朝文献通考》,卷19,职役考一。时人对此亦深有体会,认为保甲之制办理成效鲜有者,是因为“地方官疲于案牍,不能不假手书差,而一切工料、饭食、夫马之资不无费用,大约书役取给于约保,约保集之甲长,甲长索之牌头,牌头则敛之花户,层层索费,在在需钱,而清册门牌任意填写,以至村多漏户,户有漏丁,徒费民财,竟成废纸。”③方宗诚:《鄂吏约》,《清朝经世文编续编》,卷25。此外,由于保甲一般都掌握在士绅之手,故使得“保甲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控制基层社会的制度,在本质上与乡村社会业已存在的民间权威——绅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清王朝将士绅阶层置于保甲控制之下的企图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切实执行”[11]。
“我之保甲法有不同而除暴安良,初意何尝不美,乃奉行日久,已成具文,夫役日疲,已成积习,吸食洋烟者十之八九,认真办事者,百无几人。于是,人人要钱,事事有弊,敛百姓之财不能理百姓之事,治盗不足,扰民则有余矣,索贿争先捕贼则落后矣,尔百姓试思远而上海租界,近而汉口洋街,果如此乎?”④《鄂垣创行警察示》,《申报》,1902年6月9日。
保甲之制原为惠民之举,已然成为病民之害,“事实上,保甲制度总的来讲是没有效率的。”[12]
四、团练
团练主要是在动乱加剧时期产生的一种地方自卫组织,平时为民,战则为兵,但与保甲等乡里制度密切相关。史载湖北地区最早兴办团练可追溯到唐代,“湖北之有乡团,盖始于唐乾符末,黄巢乱江南永兴(今兴国州),民皆亡为盗,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犯,于是人人知兵,即今日团练也”。⑤民国《湖北通志》,卷74,《武备志十二.兵事八.乡团》。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起义席卷之际,湖北地区为主战场之一。当时清政府为镇压起义,鼓励民间自办团练协助绿营作战以卫桑梓,湖北西北部地区即有兴办团练之举。迨至太平军起,局势糜烂之际,清廷多次谕令各直省大吏督饬地方官会同绅士,“仿照嘉庆年间坚壁清野之法,办理团练,以资保卫。”⑥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5,兵考14。咸丰帝“叠降谕旨,令各省督抚晓谕绅民,实行团练,自卫乡闾,……绥靖地方”⑦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5,兵考14。。朝廷鼓励士绅举办团练,以团勇守望相助,同力抵团贼,以卫乡里。咸丰二年。湖广总督张亮基檄文下令各府州县举办团练,于是湖北各地团练大兴。
应山县:(咸丰二年)应邑正当冲要,知县聂光銮督办团练,编查保甲,严惩土匪,地方赖以清。⑧同治《应山县志》,卷21,《兵荒》。
黄冈县:(咸丰年间)钱家堡以从九邱振声、庠生喻九芝等为团长,李集区以举人张百揆、廪生游鸿远为团长,张集区以卫千总张改清、监生胡廷根为团长……余氏族团则武生余献芳领之……严守待敌。⑨光绪《黄冈县志》,卷24,《杂志.兵志.团练附》。
咸宁县:(咸丰年间)三六都之众推邑绅章蔺室为团长,立保康局……章复篡团练条约二十款,刊布乡阅……其分局之制,自一都至十三都各有局……三局有事则首尾相应,又联武昌、马乡八里局为东南屏障,江夏三二局为东北唇齿,辅车相依,彼此相恃以无恐。⑩民国《湖北通志》,卷74,《武备志十二.兵事八.乡团》。
团练再度兴起,并与保甲互为表里,是士绅阶层借以保存生命财产的地方自卫组织。胡林翼任湖北巡抚其间,为镇压太平军起义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巩固后方,严格厉行保甲团练,借以控制地方基层。胡林翼认为:“不先办团练则匪类之根不除”⑪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第65页、第146页、第148页。但若“办团练必先清保甲”⑫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第65页、第146页、第148页。,“团练所以御外辱,保甲所以除内患”⑬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第65页、第146页、第148页。。曾国藩也认为“弟意办团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体”⑭《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81。需要说明的是此种特殊时期的保甲与团练之关系。台湾的王尔敏先生认为团练是在保甲制度的基础上繁衍而来的地方性质的防卫武力。这可以从保甲制度的社会功能上找到根源。正如王先生所言“团练与保甲不但并非两歧两物,而实是一体之两种转化,可谓平时之保甲,即为战时之团练”[13]。杨国安先生认为“两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或在保甲组织中纳入团练的内容,这种保甲往往是对原有保甲做了变革,其范围和职权均已扩大;或以保甲为基础组建团练,同样这种团练并不是简单地在保甲制度基础上组成的……从保甲到团练的变化实际上表现为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控制体系中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团练的兴起即意味着绅权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对基层社会直接控制力的削弱以及基层乡村权利结构的改变”[14]。胡林翼在组织和编练团练时规定:需“于州(县)治五乡遴选正士为正副团总,由团总结保团佐,由团佐结保什长,由什长结保团勇,其从前从贼之人概不准充”⑮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第138页、第149页。。其再三强调“团练全在访举人才,……必择正直严廉之人为之长。……否则流弊最多,而御辱打仗又不可恃。……平时团首借事敛钱,恃众逞凶,散遣尤多需索。且已养其骄倨安佚之有素,不能别操勤苦,后亦聚而生事”。⑯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第138页、第149页。据罗福惠研究,湖北团练在太平天国初步兴起的1852年到1853年间新增47个,在胡林翼抚鄂的初年(即1854年)便新增10个,1855年新增6个,1856年新增7个,至1866年共编练团练60余个。其中计黄州府12个,武昌府11个,襄阳府9个,郧阳府7个,荆州府7个,德安府6个,汉阳府5个,安陆府4个,荆门府和宜昌府各1个。[15]咸丰年间,湖北地区的团练为了保卫地方,与太平军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伤亡者已超过数万。①苏云峰:《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第86页。团练中有驻守地方者,有随营征剿者,后者中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由于八旗腐败、绿营废弛,战后不少由团练转化而来的军队成为清廷的经制之军。发捻平息之后,清廷为免大权旁落,军队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下令裁撤团练。然晚清之时,社会不宁,治安已然混乱,驻地各团练虽屡经裁撤,但几经变更,不少团练仍得以保存,清廷为治安计,亦不得不妥协。晚清时期,在不少治安形势严峻之地,团练实际上起到了重要的保境安民的效用。
“御外盗”②民国《巴县志》,《卷十七·保甲团练》。是团练的主要职责。然编练团练,需要定期操练才能具备一定的战斗力,亦如此才能担负起保卫闾阎的重任。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清末湖北地区许多地方团练战斗力着实很差。有的团练“一闻贼至,即溃散奔遁,间有一二率众守隘者,辄为贼所败;不安分者,则大肆淫抢,比贼尤甚。”③《重庆府札发整顿团练指陈厉害以励民团告示》,同治朝,微缩号5,卷601。一些团练“未能专打一股或专守一城者,不过随官兵之后,胜则贪财,败则先奔。”④《皇朝政典类篡》,卷338。由于团练主要是士绅领导的在特殊战乱时期为奉行保卫地方的军事力量,湖北地区的团练在清政府平定发捻之乱后已几乎被裁撤尽净,再加上团练的种种弊端,故已不能担负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重任。
清代继续延续传统中国社会实行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军队、民间势力代表的地方士绅都参与其中。在具体参与管理地方社会治安的过程中,三者是一种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三者作用各不相同但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全权负责地方社会治安事务,扮演最为关键的角色;军队一般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协助地方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在地方治安管理中往往能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三者之中士绅因与百姓关系最为亲近,故地方士绅一般参与地方社会治安的治理效果更为适宜。士绅居于官府和百姓中间,时常担任调解人的角色,加之士绅与官府和百姓都有天然的联系,这使得他们更易于获得两方的信赖,因此很多时候通过地方士绅向百姓传达朝廷的旨令往往比通过官方的政府渠道容易,且效果好得多。[16]对此,时人亦多有评论:“巨室者,众民所取信也。州县虽曰亲民,而仁信未孚,愚众岂能尽晓,官之贤否取于绅士之论”⑤《清朝经世文编》,卷23。。政府竭尽全力将控制力向社会基层延伸,士绅为自身利益计亦不可避免地会与官府争权。当清末民变迭起,特别是发捻事起,局势恶化之际,清政府亦只能以牺牲权力为代价换取士绅的支持。因此,官府与士绅对地方的控制力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地方士绅为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势必亦会注重对地方社会治安的治理。关于士绅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胡林翼曾言:“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为”。⑥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68。实际上,清政府一直对士绅抱着猜忌的态度,湘军和淮军在平乱之后即被大量裁撤即为例证。作为朝廷经制之军尚且如此,地方士绅所编练的团练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在近代意义上的警察机构尚未出现之前,清代尚无专门的治安管理机构。其治安之责分散在各级政府、绿营、保甲,团练等机构之中,而职责不分、权责不明,且各机构所辖职责颇为宽泛且各有偏重,维护社会治安实则是他们差使中之一部分,故很容易出现人浮于事、隐匿不报、相互推诿、粉饰太平的局面。这种管理制度的制度性缺陷不可避免地抑制了其效能的发挥。其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人为因素和制度与实际运作不符,甚至相悖的现象,导致其治安效能逐步递减。再次,清代中叶以降,社会矛盾丛生,统治者一直致力于政权的稳固,故将目光多停留在上层,而对于下层的安民之举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往推行的各种保境安民的治安措施多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条文,缺少变通,加之奉行日久,早已成为具文,其种种弊病已是司空见惯,故实际效用已是大打折扣,社会治安状况实已混乱不堪。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创剧痛深,社会呈现急剧变化之势,面临着“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⑦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此时清政府上层仍因循守旧而不敢大步向前,外敌入侵、政治腐败、吏治庸贪导致民变四起,社会治安日趋恶化,原有的社会治安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发展而面临崩溃。时人哀叹:“二十行省之中,乱机遍伏……土崩之势,今已见端”⑧《国风报》,第18期,1910年8月5日。。清末十年,湖北有记录可查的民变据不完全统计就有88起⑨参见郭坤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湖北民变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咸道以降,以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席卷大半个中国,各地不堪其苦的底层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战乱波及所致,一片百业萧条之景,流离失所的百姓因生计所迫而铤而走险者多如牛毛,战后因裁撤军队继而导致各种散兵游勇充斥民间,如此种种使社会不安定因素急剧膨胀。在此等危局之下,民变蜂起,其数量与规模渐成增加之势。在此情况下,晚清的社会治安状况出现了种种新的问题,诸如民教冲突等。而政府的治安体制和力量仍旧墨守成规、毫无作为,社会治安愈来愈恶化。
湖北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亦出现了剧烈的变化。1861年汉口开埠,通商口岸的开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湖北提供了前沿阵地,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武汉、沙市等地投资办厂。湖北最早的一批买办就出现于这些外资企业之中。自开埠以后,汉口作为传统的码头城市,伴随着贸易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剧增,城市面积的扩大,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第三极。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描述:“与武昌、汉阳鼎力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①[日]水野幸吉:《汉口》,1908年版,第1页。清末的武汉是典型的商业城市,眼见有利可图,不少官僚和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他们便是湖北最早的一批资本家。商品经济和市场贸易的发展使得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广大农民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之中。许多因天灾人祸贫穷破产的农民为谋求生计进入工厂谋食。由此湖北城乡社会的演变缓慢发生。
武汉开埠后,伴随着其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导致人口迅猛增长。光绪十四年(1888年)汉口居民有26685户,人口180980人,比1861年开埠之前增加了近一倍②侯祖畬修、吕寅东篡:《夏口县志》,卷三,《丁赋志》,第一页,民国九年刊本。。而据1908年的统计,夏口厅共有47941户,人口244892人,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千米703.7人,远远高于同期的武昌每平方千米168人和汉阳的每平方千米210.1人,而此时湖北省的平均人口密度为124.2人每平方千米。[17]到宣统三年(1911年),汉口人口数量则又增长至59万人之多。③以上数据来自《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夏口县志·丁赋志》,1920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页及李权、皮名庥主编:《武汉通览》,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新增人口中外来务工的体力劳动者和四方汇聚而来的商贾占相当大的比重。根据大致统计,这一时期汉口近代企业所雇佣的工人,达三、四万人之多,在码头、车站、工地、仓库等处从事搬运的工人,总数不少于十万人④[日]水野幸吉:《汉口》,1908年版,第12页。,这些工人中的大部分是外来流入汉口的临近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来商贾亦是新增人口的重要因素,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记载:“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区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⑤[清]叶调元注,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武汉发展成为都市的迅速崛起给城市的环境、治安、卫生、交通、公共安全、社会救济、市场管理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写道:“街路颇为狭窄,无论马车之通行,往来为难。即人力车,亦只得以二辆并列。……特两侧商店之招牌、于道路之上,有为渡桥之奇观”⑥[日]水野幸吉:《汉口》,1908年版,第75页。。城市化带来的诸多弊端亟待解决。
清代原有的治安体制,在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承平日久,这些体制早已百弊丛生,伴随着欧风美雨侵蚀和内外忧患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冲击,其固有的治安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晚清时期社会剧变下的治安急剧恶化,新生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的局面。因此,为有效地加强对社会治安秩序的控制,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新要求,就必须要突破原有体制的藩篱,破旧立新。在此种背景下近代警察制度就应运而生了。
[1]陈师.旧时警政与我的经历[J].武汉文史资料,1993(2).
[2]罗尔纲.绿营兵制[M].北京:中华书局,1984:252.
[3]瞿同祖.清朝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13.
[4]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3632-3 633.
[5]嵇璜等.清朝通志(卷69)[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163.
[6]瞿同祖.清朝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4.
[7]赵树贵,曾利雅.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247.
[8][9]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4742.
[10]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九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223.
[11]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20.
[12]瞿同祖.清朝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53-254.
[13]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D].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4-5.
[14]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37.
[15]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95.
[16]瞿同祖.清朝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6-307.
[17]谭崇台.中国人口.湖北分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 88:55.
D909.9
A
1673―2391(2014)01―0139―06
2013-09-28责任编校:谭明华
湖北省教育厅省级科研课题《清末民初武汉警政问题研究(1902—1928)》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2G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