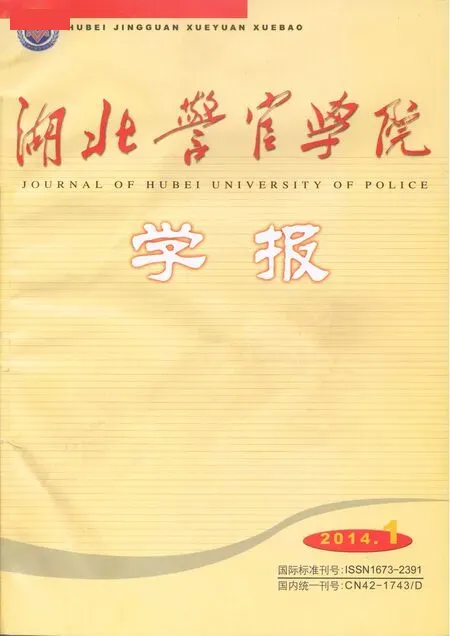犯罪中互动行为的侦查分析价值
2014-04-06蒋俊平徐国春
蒋俊平,徐国春
(1.江苏警官学院,江苏 南京210031;2.江苏省泰兴市公安局,江苏 泰兴225400)
人的行为都有作用的对象或客体,以互动为基础,没有行为的互动就构不成一系列事件和刑事案件。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中都存在着加害与被害的互动问题。互动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行为。就互动的对象而言,有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物的互动和人与环境的互动。
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有三种犯罪的社会互动模式:第一种是传统的“被害人推动”模式,第二种是犯罪原因的“冲突模式”,第三种是“可利用的被害人”模式。[1]传统观点一般将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关系看成是静态的,犯罪由犯罪人引起并促进,犯罪人积极主动,被害人消极被动。这种僵硬地看待加害与被害的观点已被大多数专家学者抛弃。刺激——反应模式认为,被害人的行为(刺激)引起了犯罪人的相应行为(反应),原本处于消极状态的犯罪人由于受到被害人行为诱发而变得积极主动。这种模式虽承认被害人行为对犯罪人所发生的作用,但却简单地将犯罪行为的发生归结为该模式的结果,实际上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动选择。犯罪行为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刺激——反应一种模式,它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2]
互动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客观科学地描述了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将犯罪人与被害人置于社会互动过程中加以考察,被害人是犯罪发生以及控制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犯罪人与被害人都作为主体而活动着。[3]在一般场合下,加害人与被害人表现为一种相互作用的互动行为。随着汉斯·亨蒂格(Hans von Hentig)题为《论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1941)这一富有创见的论文发表,在20世纪40年代,犯罪学发生了研究重点的大转移。接着,本杰明·门德尔松(Benjamin Mendelsohn)发表了题为《生理—心理—社会的新领域:被害人学》(1947),亨蒂格在其《罪犯与被害人》一文(1948)中首次系统地研究了犯罪被害人。从此,被害人在犯罪情景中的作用问题得到了越来越详细的探讨。[4]国内专家、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赵可研究员在“对犯罪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关系的认识论评价”(2001)和“试论被害人和加害人的相互作用及其角色转换”(2002)中讨论了犯罪中的互动行为,为互动行为导入侦查分析领域提供了重要启示。他认为:事物都处于运动、发展和变化中,犯罪作为人的有意识活动当然也不例外。人—人、人—境互动既可能促成犯罪发生,也可能制约犯罪行为。只有当具有犯意的人与客观时空条件和其他相关因素相适应或耦合时犯罪才能发生,否则行为人不会着手。这个过程是主客观因素不断运动和不断相互作用的统一过程。[5]这一论述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是互动行为中的一种特殊情形,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加害与被害体系中,从人数结构上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四种模式:
一是多人对多人的互动,常见于群体性事件、寻衅滋事案件。二是多人对一人的互动,常见于轮奸案件、结伙抢劫犯罪、绑架犯罪和非法拘禁等共同犯罪。三是一人对多人的互动,多见于爆炸犯罪、疯狂枪杀等犯罪,此类犯罪往往借助工具威力。此外,犯罪暴露后被多人围捕也属此类。四是一人对一人的互动,这是互动行为中最基本的模式,也是相对较为典型的模式。为便于理论描述,本文将重点讨论这一模式的互动行为。
一个加害人对一个被害人的情形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绝大多数的杀人案件、伤害致死是在一对一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不考虑轮奸等共同犯罪,那么剩下的所有强奸案件也都是在一对一情况下发生的。这就引导我们要着重研究这类犯罪的行为规律,达到识别行为性质、明确行为人特征、划定侦查范围的目的。
一、被害人调查
对被害人进行全方位调查是分析研判“加害—被害”互动行为的重要途径。需要侦查的强奸或杀人案件发生后,加害行为人是谁是未知的,绝大多数被害人是谁是不证自明的(当然碎尸、抛尸与白骨案件死者身份是需要证明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被害人入手,调查被害人背景、工作情况、生活规律、交往和经济状况,以揭示近期感情纠葛、经济纠纷等信息,解读他(她)与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是地理位置上的,也许是工作关系,也许是按时间先后进行的,也许是同学关系,也许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许还有其他关系;[6]发现致害因素,是性、仇、财、权还是其他因素导致被害;目标是针对他(她)的生命还是他(她)的性、财物;他(她)的存在妨碍了加害人实施其他的犯罪行为亦或加害人为了逃避抓捕或怕被辨认识别而决意杀害被害人……对被害人的研究往往是侦破命案的钥匙。
特维(Brent Turvey)认为:首先要全面了解被害人情况。其次是调查其被害前后发生的相关事件,包括按时间顺序绘制一份“事件、人物与地点的关系图”、建立一份“被害人生前最后24小时活动时间表”,并依照犯罪行为人的视角走一遍被害人走过的路,以便确定谁能接近他们,他们又能接近谁,他们是什么时间、地点以什么方式接近的。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互动行为不局限于现场。个案研究表明,有的在实施加害行为前两者就有趋近、接触行为。我们知道,死者生前接触的最后一个人就是犯罪行为人,那么被害人与行为人最初接近、接触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人际关系就是侦查的重点和突破口。案发前接触的人员要逐一按时间顺序排队,直到找出那“最后一个”。最后是对被害人进行风险评估。[6]
碎尸、抛尸案件中被害人是谁是需要证明的。这类案件的大量工作就在于查明死者是谁,当这一问题解决了,多数情况下,犯罪行为人是谁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人与人之间都存在关系——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犯罪行为出现时这种关系立即演变为犯罪关系——犯罪关系的社会历史性),都存在互动(除非不在同一时空,即使如此,还可借助现代通讯工具发生作用)。行为人不管受什么动机驱使,剥夺了被害人生命就已足够,为什么还要过度加害?是出于逃避侦查还是出于变态目的?这类附加行为本身是否显示了行为的含意?行为人与被害人是否有一种特殊关系?运用关系侦查法能否揭露犯罪行为人?如果不是反侦查行为,该行为是否是反映犯罪目的的恶意标记行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为描述犯罪人特征与确定侦查范围提供帮助。
白骨案件往往存在于一个特殊现场。首要工作是甄别是否移尸现场。如果是原始现场,那么被害人是如何到达这个位置的?不是被绑架劫持与诱惑欺骗而来,是被害人自己走来,那么他(她)怎么会主动到这个地方来?其中必然有一种特殊关系。我们考察所有的情杀案件,甚至能在现场发现同吃、同坐的痕迹物品,都有特殊关系的反映。即使是移尸现场,我们也要问:在众多可供选择的环境中,行为人为什么选择这个地点?道路、运输工具与环境有什么促成或制约行为人选择的条件?这些信息一旦被解读,侦查方向和范围就相应被判定。
被害人调查,实际上就是查清被害人是被犯罪人必然选择的结果,还是被偶然、随机选择的结果。
当下已进入了电子信息时代,这为被害人调查提供了许多技术手段。如手机调阅、视频监控、信用卡使用信息和网络侦查等,给被害人调查具体操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二、现场痕迹物品勘验
在进行被害人调查的同时,对犯罪行为结果发生地进行痕迹物品实地勘验是分析研判“加害—被害”互动行为的又一条重要途径。因为,行为人的各种行为结果必然会在行为实施地呈现,不可避免地会使周围环境中的一些对象发生各种各样变化或使被害人受到伤害,即行为实施地必然会遗留与行为有关的各种痕迹物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场环境中受行为侵害的人或物以及其他互动对象,都是分析研判行为人各种行为的信息载体。由于这些行为的发生大都是在相对隐蔽或只有行为人参与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们一般不能耳闻目睹有关行为人或其行为的发生。所以,现场实地勘验是获取行为及与行为有关的痕迹物品的重要手段。
现场环境中信息的存在方式通常包括两种:一种是实物为信息载体,即储存在现场痕迹、物品及其整个现场现象中的犯罪信息。这种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信息,用肉眼或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就能观察到。常见的有手印、足迹、血迹、毛发、呕吐物、作案工具以及被害人身上的伤痕等。在现场勘验过程中,只要认真、细致、全面地寻找就能发现和提取到。另一种是储存在人脑、计算机或电子监控等储存设备中的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现场勘验人员或其他与案件有关人员的感官,对现场上的痕迹物品的增减、变化等反映或根据印象感知形成的,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储存在人脑中。主要包括由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等所形成的各种反映印象。这种信息主要通过现场访问和检验相关的计算机或电子监控储存设备等收集和挖掘。这种信息容易遭到破坏,它的客观真实性必须经过查证核实。
“加害—被害”互动行为形成的各种痕迹物品在现场这一特定环境中是共存的,它们往往相互交错、相互覆盖和相互依存。哪些痕迹物品是犯罪人所留,哪些是被害人所留,痕迹物品与案件相关与否,与案件有关的痕迹物品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痕迹物品有何特点,能否反映行为人特征?“加害—被害”互动行为进程以及强弱等,都必须通过对现场互动对象的勘验并深入研究和全面分析,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加害—被害”互动行为特点。此外,现场痕迹物品勘验和分析研究现场痕迹物品特点,也是案情分析、确认被害人调查信息的可靠性、寻找犯罪行为人以及印证其言词真伪的重要依据。
三、犯罪实施中的互动模式及研判
在“加害—被害”互动体系中,存在着多种模式。如果从加害与被害间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以及相互作用力量的强弱维度排列组合,可存在以下四种基本模式:加害行为强被害行为弱(强—弱互动)、加害行为强被害行为强(强—强互动)、加害行为弱被害行为强(弱—强互动)与加害行为弱被害行为弱(弱—弱互动)。
(一)强—弱互动及研判
犯罪行为人在随机或随意选择的情形中,被害人在不知、不及、不敢、不能反抗的情况下成为被害人;被害人是被时间和地点选择的结果,是行为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被害人往往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下,甚至被害人没有一点反抗。那么行为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点加害于被害人?被害人是被定点预伏加害、尾随跟踪加害还是被巧遇加害?这类被害人在犯罪开始阶段是不明知的、懵懂的,造成了被害人无任何反抗。例如诱门入室加害的情形:被害人在毫无防备、来不及抵抗、无力反抗和被威逼要挟不敢反抗的情况下成为被害人,反映出在互动行为中被害人无明显反抗。在这些案件中法医尸检只能发现少量抵抗伤或看不到任何抵抗伤。
由于加害人的行为是故意和有备而来的,所以一般居于主动地位,而被害人一般处于被动地位。强—弱互动是较为多见的情形,否则加害行为不会得逞。无反抗行为的被害是特例。一般情况下被害人遇有加害行为时都会出于本能、应激反应或条件反射而反抗加害人,仅仅是这种反抗不足以保全自己而已。性命攸关时“抓也要抓一把”、“咬也要咬一口”,哪怕是微弱的反抗也能留下对侦查有价值的痕迹物品。
行为短促高效、一下致命或使被害人失去反抗,反映加害行为剧烈程度。那么是什么犯意促使其这么做?如果没有后续(性、财)行为,那么本行为是什么性质?有了后续行为是否意味着案件性质变化?后续行为是目的行为还是出于掩盖、掩饰犯罪目的的反侦查行为,如何识别?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侦查员尤其是侦查指挥员结合个案逐一搞清。如果搞不清后续行为类型、性质,那么就应按两个方向组织侦查。
在加害不特定对象的前提下,应考虑是否属于报复社会的情形,是否是精神病人所为。如果看不到行为人自我保护或防范意识,那么就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所为,否则就可能是反社会人格或犯罪人格者所为。加害人的强烈行为反映其主观恶性、前科劣迹、人身风险和继续作案可能性等方面的信息。
(二)强—强互动及研判
这种情形表明被害人与加害人处于对抗地位,最后以被害人对抗失利而被害。
对抗是双方力量和智慧的较量,是双方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表现形式。加害人要尽其所能使用残忍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而被害人却想通过对抗行为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或少受侵害。加害行为发生时被害人必然对加害行为作出反应,可能与加害人直接对抗,虽然被害人明显处于劣势,但这种对抗也不是徒劳和毫无用途的。对抗表现为对打、责骂、拖延时间、设法逃离现场、呼救等形式。
在强—强互动中,并不必然表现为以暴制暴一种形式,而是表明互动双方力量大致相当,应该包括一个范围:前者稍强后者稍弱或者相反都包含在这种模式中。这种情形在强奸案件中最为常见。强奸案中加害—被害作用与反作用的强弱、关系亲疏也能反映其他暴力犯罪中的情况。有性侵行为没有反抗行为,强奸就不能成立(当然要排除被言语行为控制和偷奸的情形);准备实施性侵行为遇有强烈抗暴行为,强奸就不能得逞而成为未遂。互动行为分析对甄别和认定强奸案件很有帮助。
杀人案件中的互动行为更多也更复杂,在趋近、接触、控制、攻击等一系列行为中被害人对抗是有意义的。被害人的对抗行为给侦查提供了条件:被害人击伤行为人,那么现场会留下血迹等生物检材,留下的血迹形态又可以反映攻击行为起、落点以及攻击行为形成,反映犯罪进程;行为人身上的伤痕既可以作为侦查线索,也可以作为认定犯罪的证据;行为人被撕坏的衣物及散落现场的遗留物同样有线索和证据价值;被害人的“抓”“咬”动作会在被害人指甲或口中留下据以DNA同一认定的生物证据。此外,行为人与被害人的言语互动也会造成行为差异。被害人斥责、怒骂或屈从会影响犯罪人的情绪,造成行为人恐慌或愤怒,对犯罪行为有抑制或促进作用。
现场较为惨烈与血腥的暴力犯罪,多为强—强互动形成或多人共同作用形成,较少情形下是标记行为造成。只要是此类互动,犯罪现场往往会遗留大量痕迹物品,经过查证和法庭科学检验即可演变为诉讼证据。
(三)弱—强互动及研判
就犯罪阶段而言,存在弱—强互动的情形;就犯罪进程而言,既存在真性的弱—强互动,也存在假性的弱—强互动。
互动是一个动态过程,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造成了被害人也有可能由消极被动转化为积极主动,并将加害人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将其致伤(致死)、制服。实践中有太多类似的案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弱—强互动。不过有一种情况必须加以注意: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被人发现后想逃,但逃不了,为了不被抓获而反戈一击,迫不得已出手伤及被害人。在犯罪进程的开始阶段被害人处于强势地位,发现人试图抓获行为人时成为被害人。就是说,一开始行为人是为着其他目的实施的是其他犯罪行为,如盗窃,行为人被发现后试图逃逸,被害人自认为能制服行为人,行为人为了自身安全而逃避抓捕,掏出凶器还手,一击(戳)就跑,置被害人死活于不顾,被害人因发现、抢救不及时而身亡。这就是假性的弱—强互动。案发后侦查机关接报的是命案,对这类案件要加以辨别,往往被害人尸体所在位置、倒地状态、衣着状态与财物短缺等现场特征有别于典型命案中的情形。由现场可见盗窃等其他犯罪行为在前,伤(杀)人行为在后。发现了“贼”的线索,那么侦破这类命案就与破盗窃案差别不大了,增加了杀人行为仅仅是增加了认定证据而已。
先盗后杀与先杀后盗虽然都定性为凶杀,但互动行为在犯罪进程中的位置是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过程当然不同,在主观恶性、预谋计划、认知程度、前科劣迹等方面都有区别。先杀后盗是找“强盗”,先盗后杀是找“贼”,现场行为顺序有不同反映,侦查方向和范围也不同。
(四)弱—弱互动及研判
在这一模式中,加害行为弱是相对的,是表现形式上的,犯罪主观恶性并不弱,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巧妙和行为手段的欺骗性。这更加揭示了行为人的智能水平和与被害人的特殊关系。比如毒杀案件,合法的身份掩护、隐蔽的投毒条件是毒杀得以成功的要件或要素。[7]这就圈定了一个范围:这类犯罪必定是发生于至亲、近邻等熟悉、亲密的关系人中的行为;因恋爱纠葛而引发的共同赴死案件,恋爱双方相约同死,或投水、或服毒、或跳楼,被害人死了,加害人却不以相同方式赴死,被害人死亡是加害人诱骗的结果,这就反映了一种恋爱关系;还有偷奸案件,此类案件往往是性行为模式与夫妻性行为模式不同而发案。行为人偷偷摸摸、轻手轻脚居然能把案件做成,反映了行为人的狡猾程度、智力水平和认知状况……
四、结语
以上四种互动行为模式仅仅是为了描述方便从相互作用的若干模式中抽象出来的典型模式,其实在“加害—被害”互动体系中,行为模式多种多样,可以根据各自行为深度、剧烈程度衍生出无数种行为模式,将加害行为从弱到强、被害行为从弱到强依次排列组合,可以发现许多对侦查有用的行为模式,以对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互动的形形色色刑事案件。分析这些行为模式,可以解读犯罪行为,发现“加害—被害”关系,推断案件性质,指明侦查方向,划定侦查范围。
上述讨论以一个假设为前提:不论被害人在互动过程中强势还是弱势,最后都以抵抗失败而告终。如果不以这一假设为前提,被害人阻止了犯罪,当然属于正当防卫;被害人最后战胜了加害人而致伤或致死,超过了正当防卫限度,那就进入了加害—被害角色转换的讨论范围,就演变为另一意义上的加害—被害互动关系。
如果将互动行为加以扩展,延伸到人—物、人—境互动的领域,是否能给侦查带来更多的启迪?本文主要是从加害与被害两者间积极主动、消极被动与相互作用力量强弱维度进行的分析研判。如果将视野加以扩展,转换到交往关系、两者交汇先后时序、罪过或刑责大小等维度思考,能否得到对侦查更有价值的分析见解?答案是肯定的。望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能引起足够关注。
[1][3][4][德]汉斯·约阿希姆·施耐德.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M].许章润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99,4,65.
[2]赵可.对犯罪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关系的认识论评价[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5):26-31.
[5]赵可.试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相互作用及其角色转换[J].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10-14.
[6][美]布伦特·E·特维.犯罪心理画像[M].李玫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136-138.
[7]武汉.刑事侦察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