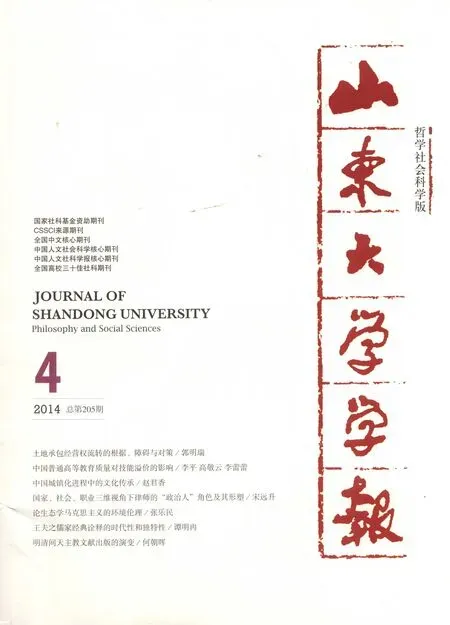“文学生活”概念的提出、内涵及意义
2014-04-05刘方政
刘方政
“文学生活”既是文学的阅读、接受和消费问题,又是美学、文学理论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文化生活、精神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等诸多层面,既是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理论研究长期忽视了的领域,又是当下社会生活要求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并亟待解决的课题。这一论题在相当程度上关联到当下社会的文化生态、精神现状、审美取向和文学创作之间错综复杂而又互动互助的关系。换言之,“文学生活”是一个既具有文学史意义和文学理论意义又具有文学实践意义的命题。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温儒敏先生立足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和文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这一命题,值得我们深入而系统地进行研究。
一
自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代初的3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照搬前苏联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尺度界定作家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探寻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方法,以无产阶级标准衡量作品内容有益还是有害。1980年代中期,欧美文学研究的各种新主义、新理论纷至沓来,结构主义、文本主义、语言分析、心理分析、新批评……打破了社会学研究的一统天下,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研究局面。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年,植根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风靡学界。上述方法都从不同层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它们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局限于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评说,只是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的相对封闭的圈子里进行“内循环”,基本不关注社会大众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譬如普通读者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如何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作家作品如何渗透到当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及怎样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等等。即使是关于现当代文学的“接受”研究,也无非是对作家作品引起的评论或争论进行线索梳理与逻辑整合,只关注文学从业者的“接受”而很少甚至没有照顾到普通读者的“接受”。其二,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所采用的材料一般是批评家与评论者的言论,很少关注并采用普通读者的反应。其实,社会大众的阅读感受最能反映作品的实际效应,理应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虽然他们的阅读感受是零散的而非理论形态的,但却最真实,是研究者进行逻辑归纳和理论提升最充分最能说明问题的原始材料。这两个方面的缺失便是“文学生活”概念提出的学术前提。
其次,从学风上说,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学科建设缺乏活力,存在着脱离实际、硬套理论、陈陈相因等弊病,尤其是在量化要求管理的限制下,忽视了对活生生的文学现实的关注,没有形成与文学生活实际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三,在文化产业化的大环境中,文学刊物的发行、文学书籍的出版和文学网站的建设势必追求利益、利润的最大化,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较大的挑战,现实急切需要将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纳入研究视野。因而,文学研究拓展到作家作品之外,更广泛地认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消费状况,便显得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有意义。
“文学生活”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全新概念,是由温儒敏2009年在华中师大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他“建议学者们像‘田野调查’那样深入读者群的‘田间地头’,了解读者如何看待作家、作品。”①范宁:《温儒敏:文学研究也要走进“田间地头”》,《楚天都市报》2009年9月27日。他在《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一书中认为,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新的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审美方式,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必须重视研究这个“小传统”,并探讨了鲁迅、张爱玲等经典作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影响。2012年1月10日,温儒敏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专论《关注我们的“文学生活”——寻找阅读与研究的源泉》,更加鲜明地提出并阐述了 “文学生活”这一概念,提出文学阅读与研究应当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
“文学生活”概念提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经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一概念做点阐释。
二
笔者认为,“文学生活”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理论的前瞻性;既基于当前社会生活对文学的需求和消费,又基于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只局限于书斋和文本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文学对生活的作用与影响;同时,对于文学史的写作也具有理论上的挑战意义和操作上的启示作用。
“文学生活”概念涉及互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三个层面:什么是文学(本体论)、文学是如何存在的(生存论)和文学是如何发挥它的功能和意义的(价值论)。如果说前两者属于文艺学、文艺美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后者则主要是文学史研究者的职责:文学如何增进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文学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具有怎样的意义和怎样的价值,文学如何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文学应该怎样关注与展示现实人生,文学如何眺望和描绘未来;文学如何增进对人的理解——在文学世界中,人得到了怎样的表现和人到底应该如何,它与现实世界中的人与人生有什么关系。要落实文学对文化的关怀和对人的理解,除了研究文学自身的基本问题(写什么、怎样写以及为什么写)以外,还必须关注文学阅读、文学接受与文学消费等活动,而这,便是“文学生活”这一概念最为重要的方面,它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这又牵扯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是强调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②温儒敏:《“文学生活”概念与文学史写作》,《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文学生活”概念大致包括这三个层面,下面略作分析。
其一,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消费。这是文学对社会生活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作用,研究的对象是普通读者选择什么样的文学读物,阅读文学作品的目的何在,什么时间在阅读,甚至还包括阅读时间多少等;就各社会群体来说,也存在着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读什么、为什么读和何时读。譬如,城市白领、大学生、打工一族等日常的文学阅读状况,便能够反映出当下社会文学消费的走向和层次;又如,社会各阶层对于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的认可程度、认知差异,也能反映出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社会成员的素质水准。对这些问题进行实地的调查、访谈及分析研究,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学的社会作用具有切实的帮助。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社会整体的文学阅读而言,人们似乎有这样一个大致相同的认识:进入新时期,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在商品大潮和趋利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文学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光环(与“十七年”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①这两个时期文学的一枝独秀及在社会生活中的轰动效应,有着深刻的文化与政治原因:文化娱乐手段的单一、官方对文学社会政治功能的极端强调(“十七年”)和文学对现实政治直接而有力的冲击力度(对“文革”的反思与对改革的呼唤)。),她不再是神圣的精神食粮,人们已经远离了文学。但现实生活中文学阅读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据“关于‘文学阅读与当代生活’的调查问卷”显示,有43%的人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阅读,14%的人业余时间都用于阅读文学作品,近三分之一的人偶尔阅读文学作品,只有不到1%的人几乎完全没有文学阅读时间(不是不想阅读)。作品阅读量最大的作家首推鲁迅,最熟悉的人物形象是阿Q,另像“四大名著”、《骆驼祥子》、《雷雨》、《平凡的世界》等都拥有大量的读者,也就是说,经典依然具有较大的阅读群②这次调查的地域涉及山东、湖南、江苏、广东、安徽、黑龙江、四川、河南、福建和江西等10个省份,各年龄层次、各种职业、不同的文化程度都有所覆盖。详见郑春、叶诚生:《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以下除注明外,均出自这次调查得来的数据。。在“阅读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什么”的选项中,“可以提高人的品位、层次”占了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即使有三成的被调查者选择以文学阅读“娱乐消费”,但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并不否定文学阅读能够“提高修养、陶冶情操”、“了解文化、增长知识”。其实,即使某些读者文学阅读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娱乐”也无可厚非,因为娱乐本来就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功能之一;另外,文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部分普通读者的文学阅读虽然是为了打发时日、消闲取乐,但久而久之,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关于文学的消费支出,受访者中的大部分人每月都能购买一定数量的文学书籍(三百元以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基本不买”文学方面的书籍。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虽然文学风光不再,但也绝非昨日黄花。
其二,文学的策划、生产和传播。从实际的操作流程来说,文学的生产在前消费在后,但是,后者既是前者正常进行的必要前提,又是最终目的。在一切以利益利润为第一选择的当下,文学生产同其他物质生产一样,也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而,围绕文学阅读消费的策划就极其重要,策划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对文学阅读消费市场的准确把握和产品上市后有针对性的宣传、推销,也就是说,生产必须紧紧依靠策划和传播来进行。就生产来说,主流的出版社、文学期刊的生产销售过程,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是如何得到出版的,文学期刊的现状如何,非主流(民间)的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生存状况,作品印行情况,如大型企业和大学校园的文学创作和话剧演出等,都值得研究和关注。就策划和传播来说,文学生产的策划和传播是怎样进行的,为什么有的作品面世之后很轰动,有的比较成功,有的则是失败的,其中除了作品本身的因素外,策划与传播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具体来说,有的期刊如《读者》、《知音》和《故事会》等发行量巨大与策划传播的关系怎样,金庸的武侠小说、路遥《平凡的世界》等何以一版再版,等等。
文学阅读决定着文学的策划、生产和传播,某种体裁的作品和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数量取决于阅读人群的大小。如农民工最喜欢阅读的是武侠、传奇、侦探和爱情等题材的通俗小说,即使像《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由于前者更通俗,也占据阅读优势;在期刊杂志中,登载通俗文学作品的《故事会》、《读者》(比例分别达到了68.8%和53.2%)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而较为严肃的文学刊物受欢迎的程度则要差一些。再如,由于戏剧演出的极不景气和诗歌创作陷入困境,文学剧本和诗歌的阅读也受到了空前的冷落,不要说普通读者,就是和所学专业具有密切关系的大学中文系学生,文学剧本和诗歌的阅读比例也只有1.4%和10.1%,远远低于小说的77%③贺仲明、王世诚:《大学中文系学生文学阅读调查》,《“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会议论文集》。,文科研究生的戏剧阅读,更是“完全成为冷门”,诗歌阅读也只有7%的比例①刘东方、杨甜:《文科研究生文学阅读生态状况调查》,《“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会议论文集》。。弄清楚读者的阅读需求,对于文学的生产、策划和传播就显得尤为关键,既可以避免没有消费对象的自娱自乐,又能够反思自我,使文学生产活动主动适应读者的需求。
其三,“文学接受”现象也应当受到重视,因为这也是“文学生活”的一部分。如1978年曾轰动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当年曾“有2700个剧团同时上演这个戏”②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编:《〈于无声处〉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高层将其视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民意依据③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编:《〈于无声处〉三十年》,第2223页。。当时的观众都是“含着眼泪看完”的,纷纷表示“很受教育”、“热烈欢呼这个戏的诞生,热烈欢迎来自上海的演出队!一出好戏力量无穷。这个话剧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人民的爱和恨。”④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编:《〈于无声处〉三十年》,第7576页。文学史如果写这一段,就不能停留于对剧本内容形式本身的评论,最好能把当时热烈的社会反响也加以呈现和评析,以展现“文学生活”的真实状况,其实也是社会精神状况。如果把普通的“文学生活”适当纳入研究视野,文学史的画面就开阔得多,也更真实。
从“文学生活”角度切入研究,会格外关注到文学接受的共时性,会在研究中照顾到同一时期社会各阶层对同一接收对象的共同感受,以及不同阅读群体各自的阅读取向和对同一接受对象认识与理解的差异。文学作品都有自身的生命与灵魂,读者的阅读体验与感受就是重新发掘、唤醒其生命与灵魂的过程,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甚至不同性别的读者对与同一作家作品的感受必然会有一定的差别。譬如,在回答“阅读鲁迅的最大困难”时,18至25岁大专或本科学历的被调查者大多选择“时代差异造成的精神隔膜”,而46岁以上相近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阅读困惑⑤郑春、叶诚生:《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状况调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在金庸武侠小说阅读调查问卷中,请被访者在张无忌、令狐冲、杨过、韦小宝和郭靖五人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物,虽然总的来说比较平均,但18至25岁的人更喜欢杨过,而65岁以上的人则更喜欢令狐冲;文化程度较高的首选郭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则首选张无忌;男受访者最喜欢郭靖,女受访者则最喜欢杨过⑥刘方政:《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三
提倡“文学生活”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丰富文学史写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拓展新生面,使文学研究更完整、更全面、也更具活力。正像温儒敏所说,现有的文学研究大都是在“兜圈子”,只是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的圈子里打转,很少甚至根本不去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和反应。所以,他提出文学研究必须要接“地气”。这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能够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出作家作品实际效果的,首推普通读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参与”文学活动。所以普通读者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不仅理所当然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同样,作为文学研究的“大头”,文学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而应当把注意力放到大量普通读者身上,看他们所传递出的普遍的趣味、审美与判断。因为普通读者才是更准确、更真实、更富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不但要重视专业评论家研究者撰写的文学史,还要关注并写出大众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⑦参见温儒敏:《文学研究也要接“地气”》,《求是》2013年第23期。。“文学活动史”写作将打破传统文学史仅仅以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框框,也即在作家生平叙述、作品的审美分析和文学史地位界定之外,增加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和理解。事实上,从文学的真正“实现”来说,它是由一度创作(作家的文本)、二度创作(读者的阅读)共同完成的,后者是前者得以成为“文学作品”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仅仅由作者意图或作品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系统是一个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模式”①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页。。文学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作品思想上的深刻性或艺术上的感染力有的是最原始的创作构思具有的,有的则是后来的研究者和读者根据时代的需求通过自己独创性的感受与深思另外赋予作品的。因而,“文学生活”理应作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一环,这样,我们的“文学史”才会更立体、更丰满,也更真实。作家作品固然是文学史研究的第一对象,但如果弃置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而只是评论家研究者从知识谱系出发的逻辑整合、概念演绎和范畴认定,这只能是专家的“文学史”,而不是“社会的”(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学史。同样,如果文学活动史的研究做得扎实而全面,也会敦促作家在创作时首先考虑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和欣赏趣味,创作他们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不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
“文学生活”研究的出发点是文学,但落脚点却是对普通百姓的精神需求和文化生活的关注,也即关注民生。诚然,文学研究是科学性的知识话语系统,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全面性、客观性、规范性和准确性。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科学性”上: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阅读并通过阅读增加人文修养,如诗意、哲思和史识,而只是用文学概念代替文学事实、为了创新而推进新知。文学创作是关于人、属于人、为了人的精神活动,就20世纪文学来说,无论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革命文学,还是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主旋律文学,意识形态用语修饰、规定的文学式样,必须经过人文性的调适之后才称得上真正的“文学”,否则,只能是政治口号的叫喊宣泄与狂轰滥炸。同样,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应该始终以人为中心,也就是必须具有人文关怀,这里的“人”不应该仅仅囿于评论家和研究者的圈子,而要以开放的心态,站在惠及大众的立场,审视、考察、衡量文学究竟对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的阶层群体喜欢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包括形式、内容、品味)?不同的文学类型在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情况是怎样的?等等。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固然是生存第一、文学其次,但是,文学阅读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活的些许遗憾:平静浮躁的心灵,创造和谐舒适的生存环境;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家庭观,建设良性的人际关系、清晰的社会底线、人群的集体教养。20世纪后半叶,前期的中国被极端地“政治化”,后期则被极端地“物质化”,政治专制主义的强权意识、物欲主义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波又一波地淹没了“人”的社会,普遍地把理性当作实现物质欲望最大满足的工具而丢弃感性,追求瞬间的快乐、幸福和意义而罔顾未来。21世纪初年,“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的倡导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进步意义,只可惜在金钱主义巨轮的碾压下始终处于萎缩枯黄状态。上述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极其错综复杂,即使人人读书也未必能够从根本上得到匡正,但是,如果社会大众多读书、读好书,用自己的心去领受、感悟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心灵颤动,在心的相遇中获得一种真正的感动,获得自我人格力量的提升,便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和质疑能力,多一些心平气和、温文尔雅,少一些政治喧嚣、金钱痴迷。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灵魂(高尔泰语)、是一个民族的梦想(张炜语),“文学生活”研究必须通过实际而广泛的野外调查、问卷发放、跟踪访谈等形式,探究“灵魂”的精神内核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考察“梦想”的内容生成及其对民众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影响程度。
“文学生活”研究是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它可以为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靠的参照。“弘扬传统文化”是最近几年叫得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弘扬”的目的既是为了传承其中的精华部分,更是以她为资源进行符合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新创造。换言之,传统文化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宝贵资源,只有很好地传承,才能成功地创造。文化传承固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但最重要的首推文学经典:“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因此,当下社会的文学生活成为决定传统文化当代传承的重要因素,而社会转型时期文学阅读的转型更关系到文化建设的走向。”①黄万华:《文学生活: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文学生活的研究便不能够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只是超然地对文学阅读、文学消费,以及出版、传播等依据调查访谈得来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社会学的描述与分析,而应该通过研究发现问题,引导文学消费者积极参与到健康向上的文化建设。目前的新文化建设有两个最基本的倾向需要引起注意——专制文化与商业文化。前者在文学上表现最突出的是喧嚣近十年的铁血英雄主义:表面上歌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骨子里却是挥之不去的专制阴影,英雄人物为了国家的独立、阶级的解放驰骋疆场挥洒热血,尽情地演绎硬汉子的形象,读者(观众)在敬佩他们英雄行为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他们专制的一面:独断专行、“不喜欢军事民主”、将下属和妻儿作为自己的附属品任意打骂等等。尤其是戏剧舞台和影视屏幕上,更是出现了赤裸裸粉饰封建帝王而评论界却一味叫好的现象。后者则对物质主义、欲望主义导致的浮躁的社会心理不但不尽抚慰之力,反而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对金钱的津津乐道和永不满足的攫取,对权势的俯首帖耳与不择手段的争夺,一切底线都史无前例地被颠覆、被解构。“文学生活”研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矫正这两种创作倾向的能力,但却有提醒文学消费者警惕上当、免被误导的责任,进而为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实际的参考。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作为文化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府相关部门,也有责任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为普通民众的阅读提供便利条件。社会阅读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设施是否健全、图书阅读是否方便,因而要创造条件让普通读者有书读、有地方读书——现在的纸质书籍动辄几十、上百元,文集、全集更要四位数以上;打工一族和蜗居阶层吃住的空间都极为拥挤,遑论安静的读书场所,因而,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便显得极为迫切。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为了炎黄之孙素质的提高,政府有义务加大社会阅读的财政投入,将图书馆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