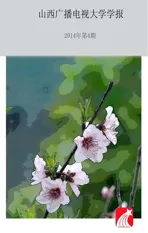《白鹿原》性别政治背后的民族命运——以田小娥形象为中心
2014-04-03翟杨莉胡嫣然
□翟杨莉,胡嫣然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白鹿原》的思想意蕴要用最简括的话来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著名评论家雷达在小说问世不久,就如是精准评说了它的基本意蕴,作家本人也说自己的写作是出于“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我们发现“作品中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形象的光彩之处恰在于她的矛盾性,或曰不彻底性,她不仅是小说中段重要的关联性人物,不仅是具有反抗传统的新人,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精神的产儿,考察这一“新”人形象身上的守旧性因素,辨析其中凸显的性别政治关系与文化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深入理解,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进一步深入由作者提出的对“民族文化命运”的再思考。
一、被物化和打入另册的“妖女”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开始关注“新人”形象,其“新”主要在于对旧世界、旧制度的反抗,就这点而言,田小娥不乏新人性,有论者就认为“她完全是一个蔑视封建旧道德的新的形象”,但这个人物形象复杂矛盾的一面更突出,她并非彻底的时代新人,而是新旧交替时期携带大量传统文化“旧”原型基因的不彻底的“新人”,辨析其背后的文化原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外来妖女”、“依附男性的女人”、“妇人之仁”以及“复仇女鬼”等几种,这些文化原型是这个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所在,原型之间错综复杂的对话关系也暗示着主人公所身处的社会文化走向的复杂性。
雷达先生认为贯穿全书的大动脉是由文化冲突所激起的人性冲突,具体表现为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就田小娥而言,她身上突出的是自然人性、人欲、肉欲色彩,她的悲剧性命运从她作为女子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时就已开始。
无论是小娥的父亲——屡试不第的田秀才,还是她的丈夫——年过七旬的郭举人在对待她的态度上,和后来小娥命运的决定者白嘉轩、鹿三一样,都是封建礼教文化坚定的守护者。他们信奉婚姻的存在就是为了生殖繁衍,为了传宗接代,同时为了生育后代,借种也是这种文化默许的,只要面子上不难看就行。不独如此,婚姻的存在还受传统“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制约,而这二者又是基于门当户对、条件相当的前提的,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中,女性就是“物”的存在,她的价值衡量标准就是婚嫁时换取她们的粮食棉花的多少。
小娥不能见容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是她追求自然欲望满足的私通行为伤风败俗,挑战了上述儒家文化伦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罕见的漂亮”这一原罪,这就是“‘美女祸水’的传统性别歧视观念在作祟了。田小娥仅因其外表就会被白嘉轩视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她的外形对男性形成了致命的诱惑,这种诱惑难免会引向人的自然本能的激情与放纵,这些对于信奉儒家节制为上的道德原则的白嘉轩之流来说是一种威胁,对付这种威胁的最好手段就是将之打入另册,眼不见为净。
我们这里不妨引入“性别政治”这个伴随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思想诞生的概念,一般认为,性别政治是“广义层面上对两性关系作正式阐述的名词”,可认为是“两大性别集团之间的权利关系和结构”,在中国传统男权制的背景下,性别政治特指“将女性排斥于公共政治生活之外,并逐步形成的一系列使女性与政治隔离的礼法、规则与政令等正式制度”,具体表现在“男主外女主内”、“男公女私”以及“男尊女卑”等习惯性观念。这种剥夺女性公众政治生活权利的常用手段就是动用意识形态工具将之打入另册,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小娥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可怕的是,这种观念会潜移默化在受害者身上,后者即便有机会进入公共政治领域,仍然摆脱不了这种传统影响。
二、对男性世界的依附
田小娥就是摆脱不了这种传统影响的女性之一,这不仅表现在她传统家庭生活的向往,她对男性世界的依附是这种传统守旧性更突出的表现,她反抗这个世界的不彻底性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对性别的依赖。
换句话说,田小娥是不彻底的新人,“新”的一面是她身上源于天性以及自然本性的对个人不公命运的非理性反抗,这一反抗由将郭举人的养生妙药扔进尿壶开始,到魂魄借鹿三之嘴的控诉达到高潮。我们不妨考察被迫逃亡后小娥在原上的生存经历,不难发现这时主导她命运的还是她身上根深蒂固的“旧人”性,作为女性她以为男人天然是自己的依靠:不论是与黑娃吃糠咽菜、闹农运,还是对黑娃和白孝文那句动情的“你走了我咋办”,抑或是黑娃逃亡后委身鹿子霖,都体现出这种依附性。依附男性世界的资本就是她作为女性的身体和美貌:黑娃农运失败,被迫逃亡,她想用自己的美貌贿赂鹿子霖换取黑娃的安全,被鹿子霖一步步引入圈套后,又试图用性来拴住鹿子霖,把他作为自己的靠山,保障自己的安全。在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时,她自觉把自己摆在了“破罐子破摔”的位置上,这何尝不是对传统文化秩序的认可呢?成功勾引白孝文之后,二人同病相怜,在饥馑中的世外破窑狂欢,充其量是对将二人排除在外的文化制度的消极抵抗。小娥这些依附男人的行为充分体现出“社会性别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借助道德信仰、风俗习惯、主流意识形态等传承和延续的载体,使男尊女卑、男公女私、男外女内的性别价值观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心目中定型化的性别观念,也使女性更加默认自身的卑贱地位与身份”。归根结底“田小娥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女人,她渴望守妇道,但社会、时代、家族、命运都不给她机会。她只能用极端的方式反抗:用自己的肉体去诱惑、破坏那貌似神圣的礼教。但在破坏的过程中她时时又回到传统女性的状态,只是这状态维持不久,又被外在的压力击碎。”
三、善与“恶”的交织
田小娥不乏传统女性的善良,更不乏天真。善良之处在郭举人家对待众长工的举止就可见出一斑,作为工具被鹿子霖利用并成功地抹下了族长继承人白孝文的裤子之后的举动更能见出她的善良:她同情对方什么也没做却丧失了包括名誉在内的一切,白孝文之后的堕落,小娥最初受人蛊惑的诱惑和二人之后同病相怜在堕落之路上的共同下滑,对白孝文的终极命运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推手罢了。田小娥是传统性别政治的产儿,她身上不乏传统女性因为大门不迈二门不出而导致的善良天真无知的一面,她对白孝文的启蒙(沉迷大烟,不要脸就行)更多是出于天真的无知,男性如白孝文之流,却由于自己对政治事务的天生敏感与参与,自会从这种启蒙中举一反三。
田小娥身上还有天真的“恶”的一面,小说第25章,她借鹿三的身体声言席卷原上的瘟疫是她的复仇之举,这一轰轰烈烈的反抗行动显然携带着大量传统“女鬼复仇”原型基因,但不同与传统的女鬼报复对象主要指向迫害自己的具体人物,田小娥的打击面要广得多,就算白鹿原上的男女老少都不拿正眼看她,是迫害她的愚昧“大众”,用瘟疫夺去他们的性命也着实残忍;尤其当我们思及文中详细叙述的鹿惠氏、仙草之死时,是不是有“相煎何太急”之感呢?
再者,如果说白嘉轩用“一座六棱砖塔”把小娥的尸骨“烧成灰压在塔底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是“男权至上的思想对女性生命力、女性自主精神的压抑与摧残”的话,我们不应忘记小娥借鹿三的口提出的要求,尤其其中“修庙塑身”的要求,更是体现出复杂的文化心理。这个要求激怒了白嘉轩和朱先生,因为这动摇了他们敬神敬祖的传统和他们秩序井然的价值体系,也难怪二人会想出“镇妖塔”这个主意。在我们文化传统中,最有名的镇妖塔是法海加在白娘子身上的雷峰塔,但环顾整个白娘子的传说,白娘子只不过是以妖的身份渴慕人间的生活,从来不曾想过要修庙塑身,将自己神化。所以我们不妨说,田小娥命运悲剧中确实不少令人唏嘘之处,但她也是浸淫了封建社会的恶的,生前的自轻自贱与死后借助超自然力量欲求“修庙塑身”是一对矛盾,也是她身上恶的体现之一。
无可否认,小娥的打击报复浸润着她对自己屈辱一生的愤怒,看似邪恶,却体现出她孩子般的天真。我们不妨说,这种天真的报复恰恰反映出她反抗的不自觉,正如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中的精辟论述:“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很慰安。”活着饱受封建礼教摧残,变成鬼便想尝尝那种被尊敬甚至被崇拜的快感。
我们不否认田小娥这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身上具有反抗性的“新人”的一面,但当我们无条件地肯定她的抗争行为的合理性的时候,甚至认为她是一个“一定要活成一个心理、人格独立而完整的女人”,并因此指责作者基于男性立场的偏颇和虐待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折射出的带有浓厚传统和时代特色的性别政治色彩,这也是陈涌先生概括白鹿原“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意义所在,与其说《白鹿原》是文化保守主义,为儒家传统文化招魂,不如说它表现出了作者对儒家文化颇为复杂的态度:既有对传统文化的赞赏和惋悼,也不乏对传统劣根性的批判。而田小娥以及小说中众多女性人物最终的悲剧结局,以及象征着白鹿原上封建礼教旗帜的白嘉轩的存活,是作者在昭告我们,民族命运的改变需要外来的力量,传统内部的反叛携带着过多旧世界似是而非的因素,注定是无效的。
[1]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1993,(6):108.
[2]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J].当代作家评论,1993,(4):20.
[3]朱寨.评《白鹿原》[J].文艺争鸣,1994,(7).
[4][11]杨一铎.“女性”的在场“女人”的缺席——《白鹿原》女性形象解读[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4,(1):62.
[5]王国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思想——基于“性别政治”视角的解读[J].福建论坛,2011,(12):21.
[6]李晓广.论传统中国性别政治关系的制度演进——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3,(1):92-98.
[7]李晓广论传统中国性别政治关系的制度演进——一项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3,(1):92-98.
[8]杨光祖.田小娥论[J].小说评论,2008,(4):95.
[9]田炜,孟庆千.男权意识下女性的悲剧——浅析《白鹿原》中田小娥人物形象[J].菏泽学院学报,2008,(4):24.
[10]鲁迅.热风[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