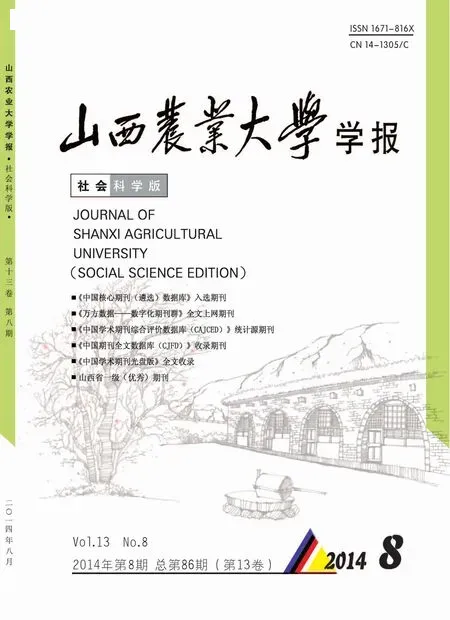论《最后旅程》对《简·爱》男权秩序和殖民话语的消解
2014-04-03张素娣张强宏
张素娣,张强宏
(1.南京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2.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4)
论《最后旅程》对《简·爱》男权秩序和殖民话语的消解
张素娣1,张强宏2
(1.南京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2.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4)
《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模拟女性视角和女性话语,以实验式创作笔法表现女性主义反叛意识和价值观,同时消解了《简·爱》内化了的男权秩序权威(神权、父权和父权)和殖民意识,以戏谑的口吻揭示女性主义视阈可能带来的女性强权,以及女性主义话语强权造成的男性心理生存平衡危机。
女性主义视阈;殖民话语;心理生存平衡
《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以下称《最后旅程》)(D.M.托马斯,2000)以续书的形式对母本《简·爱》(夏洛特·勃朗特,1847)的结局进行了改写,也认同和沿袭了《藻海无边》(简·里斯,1966)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叙事,从女性主义角度,将以伯莎为代表的“疯女人”遭受的多重“他者”化的枷锁一一粉碎,使女性享受充分的精神自由和物质自由,但其戏谑的口吻和对女性自我实现路径的规定,彰显出男性文本的话语霸权和认知暴力。D.M.托马斯将饱受男权中心主义文化压制的所有女性当作一个“共生体”,认为她们是跨越时空的“疯女人”,都在等待着控诉和复仇的机会。
目前涉及《最后旅程》的评论很少,其与母本的对比研究包括该书的书评(杨靖,2006),关于其元小说特点研究和主体行为的精神分析研究(袁洪庚,范跃芬,2005),该文本的非诗性唯丑化叙事(邹颉,2008),与其母本的写作风格比较(周晓红,2009),其戏仿手法的运用和消解功能(刁曼云,2012)。本文将首次从“经典版简·爱”和“现代版简·爱”反抗男权秩序的角度出发,揭示《最后旅程》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女性强权意识,女性主义话语强权如何彻底颠覆《简·爱》内化了的男权秩序中的神权、父权、夫权以及殖民霸权意识,以及女性话语权威可能带来的男性心理生存平衡的危机。
一、颠覆神权和性别政治
《最后旅程》“利用时空转换、身份倒置、互文性和戏仿等手法,使简·爱与米兰达这两位主人公渐渐融为一体,并兼具夏洛特的影子,同时他还赋予这三个身处不同时代的女主人公以相同的精神实质”。[1]作者认为,男权中心文化中的所有女性,无论阶级、地位、种族、肤色、年龄、时代、地理位置,实际上是一个“共生体”,都同样遭受菲勒斯——逻各斯男权秩序的压榨,都有愤怒焦虑的情绪,等待着控诉和复仇的机会。所以,托马斯试图将作品中众多女性合为一体,成为跨越时空的“疯女人”。这是《最后旅程》对女性主义文学的一大突破,也是这部现代实验性小说最大的亮点。这些“疯女人”们随时等待时机要反抗的是“男性对女性不同形式的压迫”,[2]即男权文化中同时将女性“他者”化的父权、夫权、神权和殖民者强权。
宗教信仰不仅可以起到心理引领的作用,而且反过来也影响和控制其信徒们的精神和行为。夏洛特的简·爱是虔诚的教徒,神权在简·爱年幼时严苛地规范了她的思想与行为。在她成年后每每遇到精神的困境,都会求助这位“天国的父亲”并且如愿得到了指引,而神权也成为圣约翰对她进行精神压制的工具。当然,夏洛特·勃朗特在男权社会中心文化的浸染中,内化了性别政治的规范,按照当时的社会道德与伦理体系建构了自我行为意识,完成了主流社会限定的女性角色心理的构建,所以她并不能真正认识到神权、父权和夫权的压迫。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迫切地需要克服将性别政治内化的自我压抑,要克服社会语境造就的“历史惰性”和“心理惰性”,努力激发出自身的独立意识和自救能力。
《最后旅程》对简·爱的婚后生活进行实验式续写,将夏洛特的浪漫主义文本所忽视的生活现实一一呈现,通过“经典版简·爱”和“现代版简·爱”的多重声音叙事模式来颠覆宗教和上帝。“经典版简·爱”质疑牧师在罗切斯特葬礼上的颂词,“我相信这些颂词的公正性,却发现很难相信它们的真实性。我第一次觉得那掷地有声的‘我是复活的耶稣和生命’仅仅是不切实际的希望。”[3]她甚至都在为自己的宗教背叛而震惊,当然这背叛源自对《简·爱》所憧憬的幸福生活的怀疑。继而她在悲痛中失去了信仰,“我天国的父亲死了,就像我尘世的父亲在我出生几个月后就离我而去一样”。[3]而“现代版简·爱”在现代社会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者米兰达,——托马斯借此在精神上解放了“简·爱们”。正是由于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简·爱们”才会如此的胆大妄为,才会有后来的性解放和性放纵行为,而她们的这种疯狂行为也证明了她们对宗教禁欲戒律的无视和唾弃,是对宗教信仰的彻底反叛。
二、颠覆父权和夫权
父权和夫权压制下的大多数女性,努力按照男权社会的标准完成自我的塑造,她们的顺从“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4]《最后旅程》对父权、夫权的颠覆是由“简·爱们”对其父亲、丈夫和其他男性的反抗表现出来的。托马斯的“经典版简·爱”认识到了罗切斯特的生理缺陷和性无能,试图找到治疗的方法以求得生活的完美。但是,当她突破传统与他开诚布公时,罗切斯特觉得自己的男性尊严和权威受到质疑和威胁,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阴郁、绝望的表情……像梦游一般经过我(简·爱)身边走出屋子……最可怕的是这两种表情交替间他看我时所流露出的充满恶意的憎恨。”[3]终于,视力尚未恢复的罗切斯特心理崩溃,疯狂地骑马奔出家门,最后摔死在离家十英里远的沟壑里。“经典版简·爱”的女性意识复苏后,男性的憎恨是不言而喻的。作者不仅对罗切斯特的疯狂行为表达了讽刺,而且通过男性性无能摔死来帮助女性进行鞭挞和复仇。
“现代版简·爱”米兰达在成长过程中饱受父亲的精神支配,她借梦游大骂父亲:“你是个该死的强奸犯,一个精神的强奸犯”,[3]试图用剪刀杀死他。于是米兰达的父亲逐渐萎靡消沉,打算在8月11日发生日环食时到海岬边自杀,去追随米兰达早已去世的母亲。米兰达代表了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简·爱”们,她一方面扮演杰出的社会角色,经济独立又有事业追求(妇女研究专家),另一方面又扮演妻子、母亲、女儿的家庭角色。米兰达婚后没有改成夫姓叫“米兰达·福克斯”,而是沿用父姓叫“米兰达·史蒂文森”,为努力保持和争取女性独立的自我身份,她甚至在自己续写的《简·爱》中用了母亲婚前的姓“特里弗西斯”。 米兰达把自己在马提尼克岛上与当地黑人淫乱的事告诉丈夫令其精神崩溃,还要给他安排疯女人伯莎的下场“把他关在楼上的屋子里,……给他找一个格蕾丝·普尔”[3]——被关在屋里由格蕾丝·普尔看着,分明是男权秩序中“疯女人”伯莎的生存状态。通过“现代版简·爱”米兰达,托马斯将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两性身份与地位颠倒,赋予女性主导两性关系的特权,将被虐待被迫害的“他者”位置反转给男性。在女性主义复苏后的话语强权下,以米兰达为代表的女性们觉得解恨了,但是米兰达的丈夫无法想象离婚后一个人过日子的情形,“整整哭了一个周末,而且行为举止失常”。[3]
福柯认为,“疯癫是一种建构的结果”。[5]男权文化权威憎恶并惩罚妄想僭越社会秩序的女性,把她们规定为“疯女人”,女性是男权社会主流话语机制中“被疯癫”的“他者”。托马斯在文本中隐含的意义是,社会秩序中疯癫的建构不仅适用于女性而且也适用于男性,一旦女性主义意识具备了原有社会秩序中压倒性的优势,男性成为被压迫、被消解的“他者”,男性也同样会因失去心理优势变疯狂,而男性随之而来的言语和行为同样会被女性话语权威定性为疯狂和不理性。很显然,托马斯通过文本传达了他对社会秩序的美好憧憬,即建立一种非男权主义中心、亦非女权主义中心的,两性平等和谐的社会文明和文化秩序。
三、颠覆殖民话语权威
根据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历史上和文学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已经打上了父权化、殖民化过程的标记,变成为经西方女权主义者重组以后的自恋型、虚构型的‘他者’”,主张“为第三世界妇女的‘无言’状态‘发言’,为其‘无名’状态而重新‘命名’”。[6]《简·爱》的“疯女人”伯莎反映出西方中心文化对东方的话语强制和作者夏洛特·勃朗特的殖民话语,以及“(西方中心文化的)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权力话语形成的一种共谋关系”,[7]是西方女性主义文本建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认知暴力的依据。
《最后旅程》关于“疯女人”伯莎的叙述建立在《藻海无边》文本的基础上,通过伯莎和罗切斯特的儿子罗伯特·罗切斯特写给谭波尔小姐的信件,回溯了伯莎的祖母、伯莎的母亲和伯莎在马提尼克岛的生存状态和罗切斯特的变态人格。罗切斯特带着殖民者的优越姿态、对殖民地的天然敌意和对女性的主宰意识,来马提尼克接受伯莎和她的财富。虽然儿子罗伯特的黑人肤色源于黑色基因隔代的出现,但是多疑残忍的罗切斯特以丈夫和主人的特权折磨和殴打伯莎,而伯莎用疯狂放荡的行为来报复男权和殖民意识的迫害。于是罗切斯特失去了理智,一面声称最爱伯莎,另一面却做出将伯莎带离故土囚禁起来的的疯狂举动。在对“经典版简·爱”故事的续写中,托马斯有意地描摹了简·爱和夏洛特·勃朗特作为殖民者的优势心理:“在奴隶交易港戴蒙特,看到来自刚果的奴隶,富有人情味的简为英国已取消了奴隶制而骄傲,她还指给我(罗伯特)看钻石岩,说战争期间它曾被英国占领。她显得非常自豪”。[3]而殖民地人民的自我认识消解了她们的自豪,——罗伯特觉得“我的感受更马提尼克化,对我来说谁占领这个岛并不重要,管他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3]
“现代版简·爱”米兰达已然抛弃了殖民意识,她对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态的了解更多也更深刻。米兰达在岛上游历,恍惚中就能听到维多利亚时代殖民者鞭打奴隶的声音,看到奴隶们身上的血痕。她还发现,现实生活中的马提尼克已经失去了岛国的原始风貌,变成欧洲的缩影,殖民者同化了岛民,使他们失去了野性和自己的文化。更可悲的是,以前的奴隶可以反抗和逃跑,而现在的岛民们被殖民者提供的优越生活条件禁锢起来,并被“要求放弃惟一可以自豪的自尊而成为奴隶”,[3]——托马斯认为这种充满惰性的现代奴隶角色是殖民地人民无法逃脱的宿命。《最后旅程》还描述了男同性恋者胡安,他冒名“夏洛特”男扮女装参加晚会,并且很得意米兰达送给他的《简·爱》,他仰慕并且想成为女性殖民者夏洛特或米兰达。这个细节揭示了殖民地人民的一种疯狂的生存状态:殖民地女性安心接受政府照顾不想嫁人,不需要殖民地男性(除非他们很有钱),甚至一心要找白人殖民者,这种状态严重威胁到殖民地男性的心理生存平衡,他们成为了种族和性别双重“他者化”的对象。
现代女性视阈的文化特征是要重新审视社会文化语境,反抗和挑战将性别二元对立的男权文化传统,以求得两性平等的社会文化目标。事实上,女性的地位越高,心理和生存状态越好,就越能达成两性平等与和谐的社会文化目标。但是,如果殖民主义和女权或女性主义过度发展,形成狭隘的女性自我中心,也是对性别二元对立的反方向推崇,也会反过来对男性社会带来严重威胁。因此,被誉为“美国女权主义的阿凡达”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指出,从长远看女性的解放也是男性的解放,两性的对立无益于和谐共处。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推崇两性平等和谐,非男性主义中心亦非女性主义中心,推翻夏洛特在文本中彰显的殖民话语权威,依此来达成一种任何种族、肤色的男性和女性,都不用呼告各自的独立意识的社会文化和文明秩序。
[1]刁曼云.《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中的戏仿[J].译林,2012,2(4):50-56.
[2]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7(5):22-27.
[3]D.M.托马斯著.吴洪译.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45,48,40,145,148,157,71.
[4]西蒙·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32.
[5]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樱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3:97.
[6]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28.
[7]王勇.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简·爱形象[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21(4):100-102.
OntheSubversionofJaneEyre'sPatriarchalAuthorityandColonialDiscourseinTheFinalJourneyofJaneEyre
ZHANG Su-di1,ZHANG Qiang-hong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Nan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NanjingJiangsu211167,China; 2.ShanxiConservancyTechnicalCollege,YunchengShanxi044004,China)
From the post-modern feminist perspective,TheFinalJourneyof Jane Eyre subverts the hidden patriarchal authority and colonial discourse inJaneEyre, and also reveals the truth that the overwhelming feminist authority might as well trigger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of male's survival, which does the same harm to the social harmony as that of patriarchal authority.
Feminist perspective;Colonial discourse;Psychological balance of survival
2014-04-12
张素娣(1970-),女(汉),江苏金坛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化方面的研究。
I106.4
A
1671-816X(2014)08-0809-04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