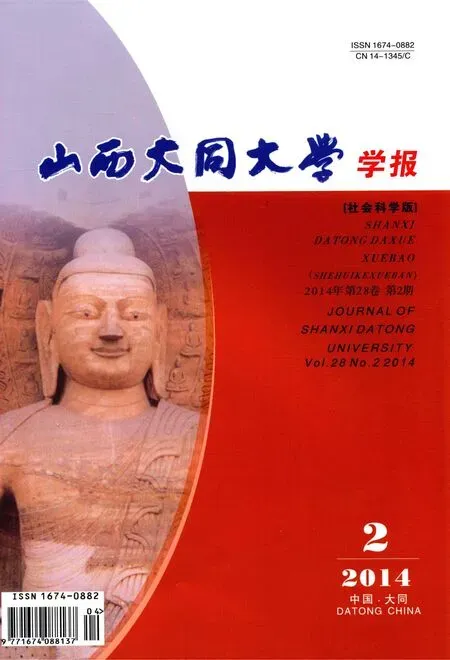唯美主义文学对滕固创作的影响研究
2014-04-03陈利娟
陈利娟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作家中,滕固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的小说创作主要是在1921年到1930年,涵盖了整个20年代。1930年以后,他致力于美术、艺术理论的研究,不再从事小说创作。滕固的创作深受唯美主义文学影响。1925年9月17日,他的小说《一条狗》在《晨报副刊》刊出,当时的编者曾留下一段非常中肯的按语:“滕君自来的作品,常带着一种decadent modernism(颓废的现代主义),他居尝最喜欢读的是Arthur Symons(西蒙士)及Gautier(戈提)等人的作品,……却没有Wilde(王尔德)的那样的装疯,戈提那样的立异,实不过是想借decadent(颓废),来表达他的反抗时代的精神。”[1](P156)滕固非常欣赏注重抒写心灵,以及将艺术的生活和生活的艺术等同起来的倾向,而现实的平庸、粗俗、僵化更激起了他对唯美境界的追求,甚至倾心仿效唯美主义的风格和情调。
一、滕固创作中的唯美主义因素
(一)“莎乐美”式的怪诞的残酷“莎乐美”是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王尔德的诗剧《莎乐美》中的主人公,她的母亲嫁给了希律王,她就成了公主。一天她在王宫的水牢边听到士兵们在谈论水牢中关着的先知,先知不断地说着一些预言。她仅仅听到先知说话的声音就爱上了他,她让士兵放出先知并向他表白,先知拒绝了。随后莎乐美倚仗希律王对她的宠爱,让希律王把先知的头砍下,放在银盘里给她端来,莎乐美一边说着“我爱你”,一边热烈地吻先知带血的头颅,带血的嘴唇。莎乐美通常被人们看作是妖艳、恶毒、残酷的化身。
滕固的作品中也经常描绘这种“莎乐美”式的残酷,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通常对艺术极为敏感,然而在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想、愿望被打击得支离破碎,爱情变得非常渺茫,让他们神魂颠倒的心仪女子们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于是内心异常苦闷乃至变态,最终的结局不是发着热病便是死亡、疯癫,充满了“莎乐美”式的残酷。
滕固的《壁画》主要写了一个名叫崔太始的美术青年单恋破灭的凄惨经历。崔太始在制作毕业作品时,喜欢上了为他作模特的女子,后来又爱上了老师的女儿,但是这些女子无一例外给他带来无尽的失望。这让崔太始感到非常苦恼,整日郁郁寡欢,忍受单相思的折磨。最后他在亲戚的宴会上放浪形骸,豪饮至于吐血,他蘸着自己的血在墙上画了一幅画,“靠沙发的壁上画了些粗乱的画,约略可以认出一个人,僵卧在地上,一个女子站在他的腹上跳舞,上面有几个字:崔太始卒业制作”,[2](P55)以此来发泄自己单恋之苦和内心的悲哀。作者的这种“想象”和“追求完美”,让我们自然地想起《莎乐美》,特别是想到《莎乐美》中由唯美主义画家比亚慈莱画的插图。《石像的复活》中的宗老是一个基督教徒,在大学专攻神学,他到日本求学,励行禁欲主义,撇开一切功名、富贵、妇人,只管研究道学。后来他无意中买了一张裸体雕刻的影片,朋友都笑他是“和尚开戒了”,不但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放在枕边欣赏,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幻觉和变态心理,以致精神错乱,某天宗老在玻璃壁橱里看到一个蜡人,他敲碎了玻璃嘴里说着:“他们把我的爱人藏在这里,他们是强盗,夺去我的爱人!”[2](P76)不久,宗老便被锁在了疯人院。《百足虫》中主人公纪凯得不到迈贞的爱,一天天憔悴下去,最后一病不起,临死前他希望他爱的人能给他一个“莎乐美”式的吻。
滕固小说中的主人公对“爱”的追求达到极致,几乎所有主人公都是因为得不到自己心爱的人,得不到“美神”的眷顾,最后变得疯狂、精神失常或者死亡,对于“爱”的追求和自己心中“美神”的毁灭形成鲜明的对比,呈现出浓郁的病态美和抑郁色彩,有着“莎乐美”式的残酷。
(二)推崇享乐主义,特别是感官享乐 20世纪初,西方的唯美主义开始流入日本,1916-1917年,日本的唯美主义文学发展到巅峰,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潮,它与理想主义的白桦派和新现实主义的新思潮派,一起占据了日本文坛。日本唯美主义者认为,文学应以享乐为目的,生命如此短暂,“人生的态度就是要尝尽世上的一切花朵”,人的一切行为动机都是为了逃避痛苦,追求快乐,就是“尽情享受大千世界的快乐,而艺术就是寻求这种快乐的天地”。[3]实际上是将人生的本质意义,只归结为爱欲和欢乐。他们进而指出,文学应该排斥思想和精神,“所谓思想,无论多么高尚也是看不见的,感受不到的,思想中理应不存在美的东西,所以其中最美的就是人的肉体。”[4]留学日本多年的滕固无疑受到了这些理论的影响,他的作品也不乏对感官享乐的描写。
滕固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处于青年时代的男女,他们对肉体有着强烈的渴望,但是在现实中又往往得不到,所以心中压抑而苦闷。“灵”与“肉”始终不能和谐,结果常常是肉欲得不到满足,心灵上承受痛苦。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以看到男主人公对于女性的渴望。“黄金”、“名誉”和“妇人”是所有主人公的共同目标。《水汪汪的眼》中,何本很喜欢小时候的玩伴阿毛大,后来他外出读书,但心里念念不忘阿毛大,特别是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甚至买了一本《秘书一百种》,照着书中的方法,在梦中与毛大相见。一次假期回家,母亲说起家乡时疫流行,死了很多人。他误以为毛大也死了,非常悲痛,去坟地寻找她的坟墓,沉痛悼念。回来的路上,正好遇到了朝思暮想的毛大。但是毛大很羞涩地绕道走开,回到家里,母亲告诉他,病死的是毛大的妹妹,毛大已经嫁人了。听了这些话,何本“神经麻木……全身的血液,都聚在他的脑髓里,一步紧一步地震荡着,他的眼前暗了”,[2](P97)当夜就发了热病,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只见无数大大小小的水汪汪的眼飞来飞去……《鹅蛋脸》中的法桢,一次吃饭时,见到了店里的一个长着鹅蛋脸的女侍,从此对她念念不忘,想着她的蓬松的头发,娇媚的笑容。随后又去那家店吃饭,但是女侍跟其他客人谈笑,没有理他,法桢很失落。后来“他似乎得了一种离奇的病症,似乎是头晕病,但他不觉得身体上有怎么痛苦。”[2](P302)整天恍恍惚惚,精神颓丧。暑假回到家里,家里的女仆也有一张鹅蛋脸,她是他的乳母的女儿,透着一股乡土美。望着她那丰润的鹅蛋脸,法桢头晕脑胀,发着热病。《迷宫》中的“我”禁不住诱惑,闯进了女性王国,两年半的时间里,倾其所有取悦女王们。结果荒废了学业,耗尽了资财,在他穷困潦倒、举目无亲之时,女王们都离他而去。他流浪在异乡,失恋、穷困、孤寂……“像从兽窟里归来的负伤之兽,往昔的勇气,全归乌有”。[2](P145)《摩托车的鬼》中的子英整日想着初恋女友章女士,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后来又打算践踏一个中年妇女的肉体,追求感官上的享乐。但滕固的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彻底的颓废放荡,随波逐流,所以在享乐之后内心总是后悔悲伤,内疚忏悔,陷入更深的痛苦当中。
(三)疯狂、病态的主人公形象 滕固特别钟情于描写单恋、单相思,他笔下的男主人公是他熟悉的留学生,他们纤细孱弱、神经敏感,似乎一片秋叶落下,也足以让他们全身颤动。而这些敏感的青年又常常受到丘比特的捉弄,他们深情地爱上了某一女神,为了女神倾其所有,但女神不是另有所爱,就是移情别恋,留下男主人公陷在情网中苦苦挣扎,催生出无限的悲哀、痛苦,于是失意颓废,自暴自弃,失魂落魄,最后心理失常、走向变态,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毫不顾惜。《迷宫》中的“我”,“将力所能及的一切,轮流贡献给几位女王”,但最后,“失恋、贫困、孤寂,萃于一身,前途黑暗,可想而知。那个黝黑而庞大之死的问题,突然显到我眼前”。[2](P147)面对苦难,“我”只想到,索性死了,就爽快了。《葬礼》中的式君,曾经为了几个女子,挥金如土,但是也因此在家庭、亲戚朋友面前失去了信用。后来,在大学里当教授,本来就微薄的薪水,也因为战争的影响迟迟拿不到手。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廉价当了几件衣服,才住进了一个小旅店,两天后去取放在原房东家的书籍,书已经被雨水淋坏了。他把这些书包裹在被子里,用情人写给他的信折成二百多个纸锭,烧化了祭奠他的书,火烧着了被子、蚊帐,他在这烟雾中涕泣呻吟。《银杏之果》中的秦舟,《壁画》中的崔太始,《百足虫》中的纪凯,《鹅蛋脸》中的法桢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敏感、脆弱、神经质的青年。
二、滕固接受唯美主义的原因
在众多文学思潮和流派中,滕固为什么对唯美主义情有独钟?这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滕固对唯美主义的选择和接受不是偶然的。“艺术,是艺术家从自己的审美主体出发通过审美感知、审美理想,对审美对象进行重新铸造的结晶,因此艺术创造的过程是主客体相融的过程,其中审美主体居于主动地位。”[5](P274)作家不是像镜子、照相机一样被动地再现审美客体,也不可能在借鉴外来文艺思潮时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作家对外来艺术思潮的选择、接受都和自身的审美需求相密切相关,接受者总是选择和接受那些与他们精神上的近亲者。”[6]
(一)客观环境的原因 滕固的创作与唯美主义结下不解之缘,这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异常开放和活跃,西方各种文艺思潮都在中国文坛上搬演一番。20年代前期中国出现了“王尔德热”,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对王尔德作品的译介和评论性文章非常流行,而西方文艺思潮大都是通过日本这个跳板传播到中国来,当时众多的留日作家就成了非常有力的传播媒介。滕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日本熟悉了英国唯美主义运动,接触了王尔德、佩特、罗塞蒂、戈提等唯美主义作家,尤其是佩特和王尔德对他的影响较大。而当时的日本文坛,也在积极地广征博采,以宽容的态度接纳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西方的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等思潮相继传入日本,并逐渐占据文坛,1916-1917年,日本的唯美主义文学发展到巅峰,成为日本文学的主潮。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如郭沫若、郁达夫、滕固、章克标等都不同程度地热衷于唯美主义,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滕固与创造社的成员联系紧密,小说往往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和唯美倾向。滕固的短篇小说《古董的自杀》、《石像的复活》、《百足虫》和他的中篇小说《银杏之果》尽管都是以两性关系为题材,但是这些作品中没有两情相悦、情深意切,温暖缠绵的浪漫爱情,而多是主人公单恋导致变态疯狂乃至自杀的结局,充满了阴郁、感伤、压抑,伤感情调贯穿全篇,笔触低调而抑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也为唯美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和土壤。国家内忧外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有志青年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地救亡图存。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呐喊几声,就被残酷的现实扼杀了,因而苦闷、抑郁、彷徨也就成为了当时普遍的一种“流行病”。唯美主义文学有着反传统和崇尚自由享乐的特点,很适合这些忧郁、苦闷的时代青年的胃口,因而也很快被中国文坛所接受,正如解志熙所言:“他们最欣赏的其实是唯美——颓废主义者那种冲决一切传统道德网罗的反叛精神以及无条件地献身于美和艺术的漂亮姿态,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唯美的深层基础——一种绝非美妙的人生观。”[7](P66)
(二)滕固自身的原因 第一,孤独的内心世界。滕固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学习古文、古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古典文学修养颇深。同时滕固是一位庶出之子,童年生活单调而孤独,父亲对他十分严厉,导致了滕固性格上的孤傲。《银杏之果》中的秦舟的经历大体上和滕固差不多,从小母亲去世,之后姑姑、父亲都离他而去,少年时期去上海求学,长期缺少关爱,远离亲人,使他内心倍感孤独、悲伤。1918年,滕固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东洋大学哲学系,在日本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弱国子民的境遇,心中苦闷而压抑。这种苦闷、压抑越聚越多,非常需要一个合适的宣泄口,唯美主义的反叛精神和“无条件到献身于美和艺术的漂亮姿态”无疑会深深地吸引他。
第二,婚姻的波折。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滕固很想成家,但是父母已经去世,没有人替他操心这个问题。他的朋友黄中告诉他,有个新寡的文君,容貌美丽,而且是个女医生,自己开诊所,是个不错的伴侣。滕固去诊所看过后,对文君动了心,很快就害上了相思病,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意。黄中又提议,让他先讨好文君身边的小女仆——红娘,几经周折,加上红娘真心实意帮忙,眼看就要成功了。可惜好景不长,文君的婆家和娘家都来阻挠,文君只好知难而退,发出“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悲叹。功败垂成,这对滕固打击很大,失望到企图自杀,原来的相思病成了大病,一个人困顿在旅店中,孤苦伶仃,悲观失望,万念俱灰。这时,善良的红娘来安慰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他,滕固的病慢慢好起来。他发现红娘虽然容貌不美,但内心纯洁善良,随后娶了红娘,相濡以沫的婚姻也算美满。
虽然善良的红娘抚慰了滕固那颗受伤的心,但是跟文君那段夭折的感情已深深烙印在滕固的内心,成了滕固创作的源泉。滕固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敏感、脆弱,而且都陷入了单相思的痛苦中,这些都映上了滕固自己的影子。滕固借笔下主人公之口,尽情抒写自己内心的伤痛,借唯美主义这一艺术形式淋漓尽致地宣泄自己的苦闷、压抑,表达对环境、对黑暗社会的反抗。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时代、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的经历,滕固的创作受到了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不过滕固毕竟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在接受外来文学思潮的时候,不自觉地进行了文化过滤。因此,滕固的唯美主义既不同于西方的唯美主义,也不同于日本的唯美主义,而是呈现出独特的色彩。正如评论家所言,滕固不像“王尔德的那样的装疯,戈提那样的立异”,[1](P156)同样他也没有谷琦润一郎那样的颓废和永井和风那样的放荡。他只是借鉴了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和创作技巧,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对社会的反抗,而且滕固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唯美主义的局限,带上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并以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丰富了二、三年代的中国文坛。
[1]许道明.海派文学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瑞 峰编.滕固作品选[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3]叶渭渠,唐月梅.日本现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
[4](日)谷琦润一郎著,于 雷,林青华,林少华译.谷琦润一郎作品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5]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陈利娟,黎跃进.日本“私小说”对章克标创作的影响[J].长城,2012(06):28-29.
[7]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8]陈树萍.滕固小说论[J].淮阴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6):91-94.
[9]陈利娟.希斯克厉夫的性格及其成因分析[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4):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