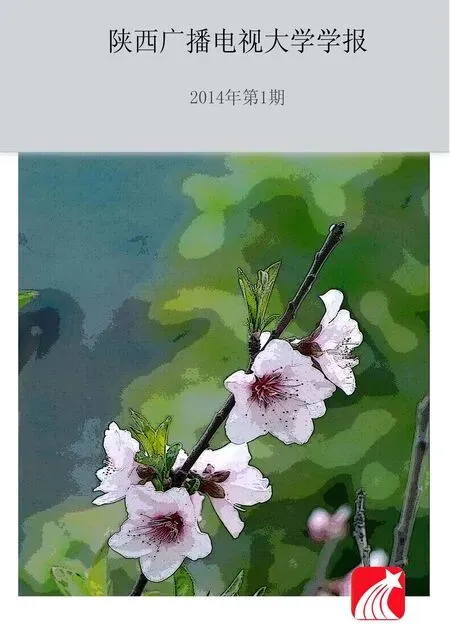试论宋代关中文学家李廌的尊师之情*
2014-04-03李雪丽
李雪丽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李廌(1059-1109),北宋文学家,字方叔,号德隅斋,又号济南先生,华州(今陕西省华县)人。少时发奋自学,以才学文章为苏轼所知,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并与苏轼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苏轼对李廌关爱有加,其中既有老师对学生的赏识与教导,又有父亲般的关怀与帮助,更有朋友间的相惜与勉励。而李廌对苏轼也无限景仰、尊敬与感激,事师如事父,从而成就了一段师生间颇具典型意义的交谊佳话。本文试对李廌的尊师之情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苏轼对李廌的关爱
在苏门弟子中,苏轼与李廌相交最晚,但与李廌的感情最为密切,既有慈父之情,更有严师之恩,还有朋友之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爱惜人才,赏识勉励李廌。
苏门创作群体是北宋重要的文学团体,元祐年间盛况空前。李廌作为一介布衣,能赢得苏轼及其他成员的肯定与赞赏,可见他非凡的文学才华。《宋史·李廌传》载:李廌“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轼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拊其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廌再拜受教”。[1]13117可见苏轼初次见到李廌,就对其文章才学给予很高的评价。李廌的古文成就最为突出,《全宋文》共收其文章48篇,主要有赋、书、论、记、铭等,内容较为广泛,充分体现出李廌论兵、论学、论道及论人生社会的不凡识见和才华。同时,其诗歌成就也不容忽视,《全宋诗》收入李廌诗歌281首,多为写景、绘物以及游赏山水之作,诗中充溢着诗人豪迈英杰之气,郁结着自己不得志的彷徨与困惑。《四库全书·济南集提要》云:“廌才气洋溢,其文章条畅曲折,辩而中理,大略与苏轼相近,故轼称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李之仪称其如大川东注,昼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周紫芝亦云自非豪迈英杰之气过人十倍,其发为文词何以痛快若是?”[2]731可见人们对李廌文章评价之高。因此,李廌能与北宋大文豪苏轼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并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一方面,是由于李廌出众的才华,另一方面,也出于苏轼对人才的爱惜和赏识。
2.念及故交,关怀帮助李廌。
从苏轼写给李廌的信中不难看出,苏轼对李廌的关爱具有父爱成分。李廌是苏门弟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比苏轼小23岁,算是晚辈。李廌父亲李惇,与苏轼为同年进士和挚友。苏轼《李宪仲哀词序》云:“同年友李君讳惇,字宪仲。贤而有文,不幸早逝,轼不及与之游也,而识其子廌有年矣。”[3]1333故人早逝,苏轼不能与之叙旧,而其遗孤又恰恰是自己的门生,一向宽厚仁慈的苏轼怎能不对这位故人之子给予更多的关怀。首先在经济上,李廌终身布衣,与其他苏门弟子相比,其经济是最困难的,他“家素贫,三世未葬”[1]13117,苏轼便尽力帮助李廌度过难关。苏轼《李宪仲哀词序》写道:“适会故人梁先吉老闻余当归耕阳羡,以绢十匹、丝百两为赆,辞之不可。乃以遗存,曰:此亦仁人之馈也。”[3]1333当时在汝州的苏轼经济并不宽裕,“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4]657,可苏轼却把朋友的帮助转赠给了李廌,足以显示出苏轼对李廌的关怀。其次,在感情上,苏轼也像慈父般关心着李廌。《苏轼文集》中收有苏轼写给李廌的信件19篇,在这些书信里,苏轼像父亲一样对李廌问寒问暖,诉说着阴晴寒暑、衰病起居,谈论着诗词文赋、书法药方,让人能处处感受到慈父般的关怀与温情。
3.传承师德,批评教导李廌。
苏轼能同李廌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与苏轼作为老师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密不可分。“东坡尝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5]44欧阳修将文坛盟主的责任交给苏轼,希望他能担负起振兴文坛的责任,而苏轼也不负重托,时时勉励栽培后生。而对于自己的门生,苏轼的要求更为严格。苏轼尽管厚爱李廌,但对其缺点从不包庇、纵容,而是给予耐心指引和教导,有时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如对于李廌对自己赞誉过当的缺点,苏轼的批评极为直率、严厉,他多次用“见誉过当”、“粉饰刻画”、“虚华粉饰”、“过相粉饰”等词来指出李廌的过分吹捧,并用“愧悚”、“悚汗”、“愧汗”等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故人见爱以德,不应更虚华粉饰以重其不幸,承示谕,但有愧汗耳”[4]1580,“但过相粉饰,深非所望,殆是益其病耳。无由往谢,悚汗不已”。[4]1580总之,正因为苏轼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而对李廌才爱之深,期之远,责之切。正如苏轼自己所言:“轼于足下非爱之深,期之远,定不及此。”[4]1420苏轼对李廌的批评也正是他们深厚师生情谊的体现。
二、李廌对苏轼的敬仰和感激
苏轼对李廌如此厚爱,生活中慷慨相助,治学上悉心指引,做人上耐心教导。而李廌也非常感激老师的谆谆教诲和知遇之恩,对苏轼极其尊敬。他事师如事父,于苏门弟子中奉师最勤,经常登门拜访,或书信问候。不管苏轼官位显赫,还是被贬他乡,李廌向老师的请教、问候从不间断,连苏轼都感念不已:“无状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4]1576可谓尊师的典型。
1.凛凛风霜操,优优雨露仁——对苏轼品德的盛赞。
苏轼为人豪迈豁达,正直磊落,他与人交往重德才而不重权势。李廌对苏轼的为人也是发自内心的敬佩,多次在文章或诗歌中盛赞苏轼的品德修养。如《上翰林眉山先生苏公》云:“严凝气刚劲,謇谔性忠纯……黼黻文华国,渊源德润身。”[7]13620组诗《送杭州使君苏内相先生旧诗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为韵作古诗十四首》同样是写给苏轼的赞歌,诗中屡次将苏轼称为“至人”,如“至人本无我,与世初无方”,“至人孰可测,跨世富英亮”[7]13569等。并称赞苏轼“忠清秉全德,日月可争光”,“精诚贯白日,孤忠横北辰”。[7]13569甚至将苏轼与周公、孔子相比较:“周公非汲汲,仲尼岂皇皇。”[7]13569李廌还专门写赋对苏轼进行盛赞,元祐元年(1086),苏轼返回朝廷,官拜中书舍人,李廌作《金銮赋》赞美其事;元祐四年,苏轼又拜为翰林学士,李廌又作《金銮后赋》对二苏进行褒扬。在《金銮赋》中,李廌称苏轼为“超然先生”,并赞曰:“为超然之先生,冠百世而称杰。操忠而秉哲,执义而全节。文章鲜丽于古今,德行争光于日月。”[6]107虽然有些粉饰之词,但也显示出其内心的敬慕。而其最感天动地的经典赞誉,则要算苏轼逝世时李廌所撰的祭文。在这篇祭文中,李廌高度概括和评价了苏轼的道德风范和文章才学,道出了自己对苏轼的仰慕和缅怀之情:“德尊一代,名满五朝”,“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系斯文之兴废,与吾道之兴衰。”[6]196他认为苏轼德高望重,才华盖世,当时文章的兴废、道德的兴衰,都系于苏轼一人,这可算是对苏轼道德、才学的最高评价。如果对苏轼没有倾心的仰慕,没有真挚的情感,又怎能写出如此经典而又感人肺腑的名句呢?
2.高才映今古,妙学洞天人——对苏轼才学的赞叹。
苏轼是北宋重要的文学家、政治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好读书,精通经史子集,而诗、词、文、赋、书法、绘画又无所不通。如此有才学的老师,怎能不让李廌赞叹、钦佩。北宋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五载:“东坡作文字中,有一条以彭祖八百岁,其父哭之,以九百者尚在。李方叔问东坡曰:‘俗语以憨痴骀騃为九百,岂可笔之文字间乎!’坡曰:‘子未知所据耳。张平子《西京赋》云:乃有秘书小说九百。盖稗官小说,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医厌祝及里巷之所传言。集为是书。西汉虞初,洛阳人,以其书事汉武帝,出入骑从,衣黄衣,号黄衣使者,其说亦号九百,吾言岂无据也?’方叔后读《文选》,见其事具《文选》注,始叹曰:‘坡翁于世间书,何往不精通耶!’”[8]136体现出他对老师博学的由衷赞叹。
李廌对苏轼的政治才能也十分欣赏。他在诗中赞颂苏轼:“佑圣生贤佐,天心在抚民。昌期应治运,谷旦降元臣。”[7]13620将苏轼称作佑圣的“贤佐”、盛世的“元臣”。在《师友谈记》中同样多次赞扬苏轼的政治胆识,如其中记载:元祐七年,苏轼随圣上在太庙祭祀,仪卫甚肃,而皇后及其太夫人却驾着车马于此乱行,其他大臣都因中宫颜面不敢上谏,惟“坡曰:‘某自奏之。’即于青城上疏皇帝曰:‘臣备员五使,窃见二圣寅畏祗慎,昭事天地,敬奉宗祧,而内中犊车,冲突卤簿,公然乱行,恐累二圣所以明祀之意,谨弹劾以闻。’上欣然开纳”。[5]42这体现出苏轼的敢谏敢言,因而李廌称赞苏轼曰:“东坡不惟文章可以盖代,而政事忠亮,风节凛凛,过人远甚。”[5]42。
3.循循教不倦,启发亲持扶——对苏轼的教诲铭记于心。
李廌虽然很有才华,但其为人、修养等方面也存在着年轻人常有的一些缺点,如浮躁鲁莽、急功近利、褒誉过当等。但他对于老师的教诲总能铭记于心,并不断改过自新。例如针对李廌急功近利的缺点,苏轼劝导他说:“如子之才,自当不没,要当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门何必时曳裾也。”[5]14并告诫他:“至于富贵,则有命矣,非绵力所能必致。姑务安贫守道,使志业益充,自当有获。”[4]1578经过苏轼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诲,李廌“尔后常以为戒。自昔二三名卿己相知外,八年中未尝一谒贵人。中间有贵人使人谕殷勤,欲相见,又其人之贤可亲,然廌所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变也”。[5]14后来李廌在《下第留别陈至》中写道:“吾生三十年,二十九年非。末路各相望,奋庸会有时。贵如未可求,守余北山薇。”[7]13592表现出李廌对自己之前急进功利思想的反思,以及对功名乃至人生的达观认识。可见经过苏轼的教导与感化,李廌在道德修养上有了很大进步。在苏轼指导下,李廌在文学上的进步也显而易见,这从苏轼对李廌文章的点评中就能看出。如:“录示《子骏行状》及数诗,辞意整暇,有加于前,得之极喜慰……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4]1420“承示新文,如子骏行状,丰容隽壮,甚可贵也。”[4]1578“益闭门读书,又数年,再见轼,轼阅其所著,叹曰:‘张耒、秦观之流也。’”[1]13117从苏轼的点评中,我们能看见李廌的刻苦努力以及在苏轼的指导下所取得的可喜成就。
4.青云有伯乐,俯识千里驹——对苏轼知遇之恩的感激。
苏轼是最早发现、欣赏李廌的才华并大力向人推荐的人。李廌非常感念苏轼的知遇之恩,珍惜这份难得的真挚情谊,因而与苏轼患难相从,互相勉励。如李廌乡试中榜后非常高兴,对前途充满信心,便在《谢解启》中写到:“比缘秋试,偶尔计偕;辄生妄心,窃有荣幸。此盖伏遇某官久垂教诲,曲赐题评;恩等丘山,义同卵翼。致滋昧陋,有望亨衢。敢不益厉操修,上副眷予。”[6]130书启中虽未指明“某官”是谁,但从措辞来看,很显然是指苏轼。他认为自己能够顺利通过乡试,主要得益于苏轼的谆谆教诲和题评,言语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元祐后期以后,苏轼长期被贬、宦迹多变,李廌当时虽避居乡野,彼此联系颇多不便,但对苏轼的关心、担忧从未间断。如哲宗元符三年(1100),被贬长达七年的苏轼自岭南返回,李廌作《次韵东坡还自岭南》:“凭陵岁月固难堪,食蘖多来味却甘。时雨才闻遍中外,卧龙相继起东南。天边鹤驾瞻仙袂,云里诗笺带海岚。重见门生应不识,雪髯霜鬓两毵毵。”[7]13628首联是对苏轼在海南的艰苦生活的同情和安慰,中间两联流露出对苏轼归来的欣喜以及掩饰不住的仰慕之情,尾联想象师生久别重逢,历经磨难的苏轼已经不识门生,雪髯霜鬓,体现出李廌对老师久经坎坷的同情与辛酸之情。诗中既有同情,又有安慰,既有辛酸,又有欣喜,饱含着患难之中与苏轼的深厚情谊。李廌视苏轼为知己,因而当惊闻苏轼去世的噩耗时,极为悲恸,“轼亡,廌哭之恸,曰:‘无愧不能死知己,至于事师之勤,渠敢以生死为间!’即走许、汝间,相地卜兆授其子。”[1]13117并作祭文来缅怀歌颂苏轼,文辞极为感人,一时广为传诵。
三、李廌对苏轼的误会和抱怨
元祐三年,朝廷诏苏轼与孔文仲、李觉同权知礼部贡举,主持这一年的进士考试,这对当年应考的李廌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李廌却不幸落举。《宋史·李廌传》载:“乡举试礼部,轼典贡举,遗之,赋诗以自责。吕大防叹曰:‘有司试艺,乃失此奇才也!’”[1]13117《鹤林玉露》云:“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8]129之后李廌再次科考,又一次落榜,遂绝意仕进,终身布衣。对于自己此次落举,李廌对苏轼曾有过怀疑与误会。首先,从苏轼的回信《与李方叔书》中就能看出:“累书见责以不相荐引,读之甚愧。”[4]1420可见李廌写过抱怨苏轼的书信。其次,李廌《师友谈记》有连续四则专门记载苏轼自述同父亲与弟弟三人受到欧阳修、韩琦举荐而声名大起、中举授官之事。如第二十一则:“东坡尝云:顷年文忠欧公荐其先君,荐章才上,一时公卿争先求识面,交口推服,声名一日大振。盖欧公之言,既取重于世,而当时之人,亦有喜贤好善之心,无纷纷翕訾之间言也。”[5]21在记述中苏洵因为受到欧阳修的举荐,才声名大起,李廌认为原因在于欧阳修位居要职,说话能“取重于世”,其言外之意是苏轼当时也身为翰林学士,并为礼部贡举,且德高望重,若是能稍稍举荐自己,那肯定也是声名鹊起,仕途腾达。为此,李廌还专门写过一篇《举荐论》,认为“荐得其人则受赏,荐非其人则被罚”[6]169,而人们“慎无举贤”的原因在于国家“用罚之意严,用赏之意简”[6]171和人们喜赏畏罚的心理。李廌对举荐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也并非专门针对苏轼,但也能看出他对事情认识过于简单化、理想化,对苏轼确实存在着误解。
苏轼不举荐李廌,并非嫌朝廷没有赏赐,或是害怕举荐非人连累自己,而确实有自己的原因与苦衷。首先,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当时朝廷政治复杂,新旧党派斗争非常激烈,党派成员共升迁、同遭贬。而苏轼也时时处于政治风暴之中,就连自己引荐的黄庭坚、王巩、秦观等都在政敌的攻击之列。其次,苏轼引荐人才以“德”为标准,认为“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4]1420,并认为李廌道德修养还没有达到一定标准。再次,苏轼作为李廌的老师,且如此欣赏李廌的才学,又怎能置李廌的前途于不顾,据《宋史·李廌传》载:“轼与范祖禹谋曰:‘廌虽在山林,其文有锦衣玉食气,弃奇宝于路隅,昔人所叹,我曹得无意哉!’将同荐诸朝,未几,相继去国,不果。”[1]13117可见苏轼是有过举荐李廌的打算,只是时机不成熟,没有机会罢了。
虽然李廌对苏轼有过误会与埋怨,但也是人之常情,我们不能就此而否定李廌的为人或怀疑李廌与苏轼的师生情谊。而叶梦得《石林诗话》载:“廌自是学亦不进,家贫不甚自爱,尝以书责子瞻不荐己,子瞻后稍薄之,竟不第而死。”[8]129说李廌从落榜后“学亦不进”、“不甚自爱”以及苏轼“后稍薄之”,此纯属误言,与事实不符。首先,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尤其是宋朝,引荐对文人的仕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苏轼本人就受到韩琦和欧阳修的大力推荐,苏轼门下的陈师道虽未考过进士,但也通过苏轼推荐而担任徐州教授、太学博士、颍州教授等职。可见荐引也确实是步入仕途的捷径。其次,宋人对科举考试非常看重,苏轼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也都先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再加上李廌父亲早逝、家庭贫困,科举考试无疑是改变其命运的关键,李廌对此也付出了全副心血。再次,李廌确实很有才华,其师友及李廌本人都对中举寄予了很大希望,据《直斋书录解题》载:“东坡知贡举,得试卷,以为荐也,置之首选,已而不然,赋诗自咎。”[9]510两次名落孙山对李廌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再加上李廌正年轻气盛,性格又比较急躁、鲁莽,说出一些对苏轼误会、抱怨的话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这并不影响李廌对苏轼的尊敬。相反,李廌却因一时的唐突鲁莽而获得了苏轼的谆谆教诲,从而受益匪浅,更增加了李廌对苏轼的景仰之情。再结合李廌的一生来看,李廌确实从两次落举的打击和苏轼的劝导下对功名和人生有了达观的认识。中年以后,李廌弃绝科举仕途,安贫守道,精心从事文学事业,虽终身布衣却取得了与其他苏门弟子同样可喜的成就,这得益于他对老师的理解、尊敬和学习,而他的尊师之情也成为一个典范而被后人传颂。
综上所述,苏轼对李廌极其赏识、关爱有加,对他耐心教导、无私帮助;而李廌对苏轼也非常景仰尊敬,他钦佩苏轼的修养才学,谨记苏轼的谆谆教诲,感念苏轼的知遇之恩。尽管李廌自身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两次应举失败的巨大打击下对苏轼曾有过误解与抱怨,但在苏轼的教导和感化下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加深了对老师的尊敬与仰慕之情,并从此谨记老师教诲,奋励修身致学。他对老师的关怀和牵挂也使身陷险恶政治漩涡的苏轼的生活多了一些温暖;他追荐苏轼的挽联“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被人们认为是对苏轼最经典和最准确的评价。李廌不但以他的文学成就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他的尊师之情与关中地区古老的尊师重教传统密不可分,也成为后人传诵的典范。
]
[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清]纪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115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3][宋]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宋]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宋]李廌.师友谈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7]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颜中其.苏东坡先生轶事汇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4. [9][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