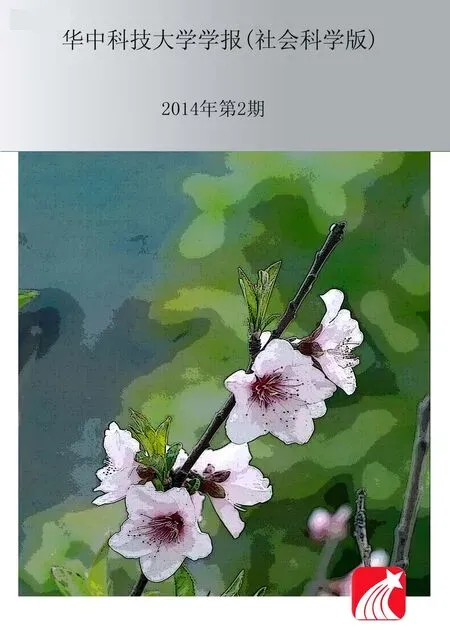卢梭的幸福哲学探析
2014-04-01李蕾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李蕾,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在哲人与诗人那里,“幸福”这个词汇将会带来一个永恒的话题,同时,几千年来幸福的观念历经无数次的流变,从古希腊哲人的美德幸福观到中世纪神学人欲的禁锢,从现代功利主义者的“避苦求乐”幸福观到后现代的多元与虚无。多数学者均认同幸福这个概念象征着人类的终极目标,许多学科都将幸福作为其价值追求的最高原则,于是近些年来政治、经济、法学这些看似冷酷远离感性的学科逐渐将这个非纯粹科学的概念添加进入各自学科的理论阵营之中,而所谓自由、民主、正义、财富这些理念不过都是实现幸福这个终极目的的手段而已。即使人类社会为谋求幸福创造出了各种获得幸福的政治、文化、科技手段,但伴随着人类的幸福难题依然存在。经济高增长的过程带来的可能会是痛苦,拥有巨额的财富的人却不是最幸福的。笔者期待在这位历经苦难与折磨却具浪漫主义气质的古典共和主义者这里寻求答案。
卢梭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思想家,革命时期的大人物们曾经宣称卢梭是革命的导师,哲学家称人类自由的灵感源归功于卢梭①罗伯斯庇尔曾经宣称卢梭是革命的导师,康德视自己所提出的“自由是人类的特性”的灵感来自卢梭。。但却又有人批判他“爱人类而仇亲族”,甚至还有人将他与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画上等号。在卢梭去世后的数多年间,世界反复重现着有关他的批判或者是申辩,这也说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卢梭都是每一时代学者们绕不开的话题,我国学者对卢梭的研究始于20 世纪70年代,中国人对卢梭的热情在近四十年的时光中从未减退,他的学说与著作中充满着对人类幸福的感悟与思考,但却被许多学者所忽视。本文试图从卢梭的作品集中挖掘其对幸福与痛苦的感悟,审视与反思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生活方式。
一、宁静与沉思——卢梭对幸福的描述
卢梭在其著名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中详细且具体论证了幸福的内涵。他认为没有人能体会绝对的幸福与绝对的痛苦,它们混杂在了人生之中,每个人都有幸福与痛苦,不过程度不同,遭受痛苦最少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同样感受快乐最少的人就是可怜的人。人的真正幸福道路,不在于减少人的欲望,因为人的欲望如果少于人的能力,那么人的能力就有一部分处于赋闲状态,人因此就不能完全享受自我的存在。如果欲望继续扩张,那么人只会更加的痛苦,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那些超过人的能力的那些愿望,“使能力和意志两者之间得到充分的平衡”[1]74。要使能力与欲望获得平衡,必须依托于卢梭所描述的原始、自然状态,因为自然、原始状态下的人其欲望与想象力是处在沉睡中的。
“真实的世界是有限的,想象的世界则没有止境,我们既不能扩大一个世界;就必须限制另一个世界,因为,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才产生了使我们感到极为烦恼的种种痛苦,除了体力、健康和良知以外,人生的幸福是随着个人的看法不同而不同的,除了身体的痛苦和良心的责备以外,我们一切的痛苦都是想象的。”[1]75
卢梭认为人的精神上的痛苦是由个人的偏见所导致,而时间与死亡是医治人们痛苦的良药。有一种思绪被卢梭称为“远虑”,这种思绪不停地促使人们做其力不能及的事情,从而去向往他们永远无法达到的地方,这种思绪也是种种痛苦产生的根源。人拥有着短暂的一生,如果时刻向往这些渺茫的未来,而轻视现在,对卢梭来说这都是疯子的行为。人需要获得幸福,自身起着关键的作用。过多的欲望与难以控制的意志都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获得,独处、深居简出是卢梭长期的生活方式,奢华、物欲的生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18 世纪的上流社会充斥着淫靡,卢梭断然与那种沉溺于肉欲的享乐生活划清了界线。从他平实且真实的自传《忏悔录》中看出:除了短暂欢畅的童年,他的一生在世俗看来并非是幸福的,他没有拥有过完整的爱情也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友谊和亲情。但是这些痛苦、孤独的历程并不阻碍卢梭本人对幸福生活的独到诠释。
作为《忏悔录》续篇的《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是卢梭的垂暮之作,展现出老年的卢梭对宁静、自由、浪漫生活的向往,这部作品也是其所有作品中最浪漫、最诗化的一部。在孤独一人静静沉思状态下的卢梭无匮乏之感,也无忧愁之感,仅仅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卢梭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在圣皮埃尔岛度过,他时常将自己的生活定格在这种状态。如他所说,他曾经住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像圣皮埃尔岛那样真切地使他感到快乐”[2]99,能给他留下那么温馨的怀恋与幸福的感觉。那种生活几乎与世隔绝,很少有他人的介入,在他的房间里摆放的不是文稿与旧书而是各种花草植物。他沉溺于对植物的组织、结构繁殖的研究之中,他将此形容为“心醉神迷”的事物,偶尔间他会静静躺在船上,船下即是一片如镜的湖水,他不时欣赏着岸边秀丽的山色,沉湎于无限的遐想,思绪万千纷至沓来。这种幸福观与他年轻时代对自然状态的一种完美诠释是截然不可分割的,这种思想的力量异常强大,一直持续到他遭受残酷迫害的人生最后岁月。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必然从自然那里寻求庇护。他认为既然不能在尘世间做对己对人有用、有益的事情,却能在这种自然、宁静的状态中感受幸福,这是命运从他那里无法夺取的补偿。这种特殊的人生阅历给他的浪漫思想增添了一股凄凉的美。
二、科学、艺术与道德的断裂导致人类幸福流失
《论科学与艺术》是卢梭从人类社会与科学、艺术之间关系角度阐述幸福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作品曾被视为美学理论的新高峰。他将科学与艺术与道德、风尚联系在一起,并对那些德行缺位的科学与艺术行为进行批判。
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没有给人带来幸福,科学和艺术虽然日臻完美,道德却渐渐地消逝。《论科学与艺术》中不乏卢梭对科学、艺术的贬斥,其缘由是科学与艺术均是从人类恶劣的品质与罪恶之中诞生:
“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所有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的;如果他们的诞生是出于我们的德行,那么我们对于他们的用处就可以怀疑得少一点了。”[3]21
追逐科学与艺术的同时也助长了邪恶的品质。例如,科学让人懒惰、闲逸、不务实。艺术导致人变得奢侈与虚荣。这些性情最终导致人的意志消磨,软弱无能,堕落。他引用了古代埃及、希腊,甚至中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均是在对科学与艺术的追逐历程中衰落的。而那些崇尚道德风尚的国家,没有沾染上追逐科学与艺术的浮躁,成为人人向往的礼仪之邦①这些国家包括:波斯、塞族、日耳曼、贫穷与蒙昧时代的罗马、乡居的民族——瑞士。。卢梭其实并不是攻击科学与艺术本身,而是要借助它们揭露当时的时代,道德品质的丧失,骄奢、淫逸之风盛行。如他所说:
“我自谓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忠诚对于善人要比博学对于学者更可贵的多。”[3]5
如果科学与艺术诞生于人类的美德之中,那么卢梭对它们的怀疑可能将会减少。美德、德行本身就是纯朴灵魂的崇高科学,它刻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我们要认识它只需倾听我们自己的心声即可,而不是转而追求那些所谓的名誉,幸福的获得在每个人的自身,而并非从他人的意见中获取。
从《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卢梭非常强调美德对人类幸福的影响力,追求科学与艺术进步,必然消耗了许多时间与精力让人忽略了对人类自身美德的挖掘与探索,从而陷入浮躁与虚荣,最终与真正的人类幸福擦肩而过。这也正说明了科学、艺术、伦理、道德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卢梭以其灵敏的认知发现了人类的意志(道德)领域与知识(科学)领域的断裂。科学本身是中立的,无法传递价值,在整个西方进入工业现代之后,人类逐渐反思科学技术的异化,解决科学技术的异化可以有效地防止与杜绝人类走向灾难。反思科学技术的异化是当代社会的当务之急。而这种反思的起源我们其实可以追溯到卢梭这里。由于这部作品对艺术与科学进行了过多的贬斥,因此卢梭遭到了许多非议,甚至其观点被视为奇谈怪论、标新立异。整部作品论证逻辑也略显稀疏而经不起严谨、慎密地推敲,卢梭本人也认为与《爱弥儿》、《社会契约论》、《新爱洛漪丝》等作品相比较这篇文章略显平庸①卢梭在《忏悔录》中曾经提到《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是其论证最薄弱、文笔最不协调的作品。。但这些瑕疵丝毫不减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这部作品也成为今后卢梭全部学说的萌芽与根基。
三、公民社会中的人并不一定比自然状态中的人幸福
卢梭的大部分作品都洋溢着对自然的讴歌与赞美。这种回归自然的思想让人不禁联想他与中国古代哲人庄子思想的惊人类似。“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1]3
人越是接近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就愈小,因此,就越接近幸福。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感受的痛苦是最轻微的,痛苦的缘由不在于缺少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正式阐述了自然状态等理念,这篇论文也是卢梭理论体系逐渐走向成熟的政治学著作,从这部著作开始人们才将卢梭与政治思想家联想在一起。卢梭从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出发论证了文明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使人泯灭自然本性。自然、蒙昧的状态的是美好与幸福的,那时的人类更加健壮,并不比文明人不幸。即使是没有宗教信仰与政治制度,那时的人类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在文明社会中的美德却能在原始自然的生活中找到。
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彻底独立的,公民社会中的人却是存在依赖性的。初始阶段的人类社会是人类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类没落的最初象征也开始显露。人类的不平等源于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原始本性的丧失。人在文明进步中逐渐堕入深渊并不断异化。卢梭视私有制为万恶之源,在《忏悔录》中,他坦然承认自己还偷一点“小玩意儿”,财产私有的原则在他那里毫无用益,而他所养成的偷窃习惯要归咎于社会的不平等。富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借助社会集团的缩地的契约创造出一个国家,这种契约是骗人的契约,卢梭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真正的契约来代替它们。
无论是“自然状态”还是“社会契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的表达完全与《社会契约论》遥相呼应。相比而言《社会契约论》将卢梭一直固守的原则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由于之前若干著作为这部作品做了坚实的理论奠基,并且书中的观念脱离了之前的所有政治学的羁绊,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了卢梭在其政治学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卢梭借助自然状态关照社会状态,以“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4]31,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除了保护公共的幸福之外就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回归现实社会,自然状态的设想也许只是卢梭的一厢情愿。卢梭幻想的自然状态或者野蛮人都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乌托邦梦想,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详尽的历史资料做奠基,行文结构充满遐想与游离。现代社会中的人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原始人的生活方式,新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依然可能成为人类获取幸福的途径。卢梭作品对我们当代人的启示在于,在文明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物质丰沛的历史时期下的人不能被这些进步的假象蒙住了双眼而丧失应有的天性与美德。卢梭将人类的各种制度比喻为“流动的沙滩上一种建筑物”[5]68,这些都是稍纵即逝的事物,我们的使命是去掉建筑物周围的灰尘和沙砾,看到这一建筑底层不可动摇的根基。
四、公民幸福的起点:公意与自由
如果说《爱弥儿》、《忏悔录》较多关注个人的幸福,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是界定了人类社会的公共幸福。公共幸福的起点在卢梭看来即是自由与公意。其中“公意”是卢梭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即以此学说为前提,它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
“只要有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这时国家的全部精力是蓬勃而单纯的,它的准则是光辉而明晰的;这里绝没有各种错综复杂、互相矛盾的利益、公共福利到处都明白确切地显现出来。”[4]131
卢梭认为公意是不可摧毁的,永远稳固、不变且纯粹的,是全体公民的幸福根基。他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是瑞士各乡村的州的村民,因为那里常被诗人们描述为风景如画物产丰富,人们宽厚纯朴,几乎是梦幻般的田园生活。公意在那里体现的非常完善,村民时常在橡树下规划国家大事并且处理明智,完全不必考虑所谓看似精明却是玄虚的伎俩。
公意在卢梭的眼中永远是公正的、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人们希望自己幸福,但是也许不能看清楚幸福。人们在受欺骗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出不好的选择。公意之所以公正,在卢梭看来是因为公意来自人的天然本性,人们期待他人幸福的同时也是在为自我的幸福效劳,当公意沉默的时候,人人只被私利所引导,卑鄙的利益会被无知地伪装上公共幸福的名义。
卢梭的公意观是否真正贴合每一个个体的幸福,这一点始终被质疑。他将公意与私意对立起来,仅当私人的意志被消灭了公共意志才能产生,私人领域的意愿完全被剥夺,让人怀疑极权①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认为如果任何人拒绝服从公意,那么全体就应该强迫他服从,这种强迫被一些学者视为滥用强权,这种公意的结果必然导致专制与独裁。的诞生,哈贝马斯认为卢梭公意的诞生欠缺批判与辩论,这样的公意是缺少包容性与纠错功能的。卢梭的公意观太过抽象,公共意志应当不排斥个人的意志与私人的利益。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被许多学者进行了各式的补充,现代社会的公意观念正逐渐完善。
卢梭崇尚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强制,不受物质的限制,没有妥协。他宁肯过着困苦冒险的自由生活,也不愿意过安乐的奴隶生活。对他来说,爱自由,比爱什么都深切。只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5]6。《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由主要指向的是政治自由,他认为:
“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的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4]12
卢梭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信条和封建道德对个体的束缚,主张以个人的感情、兴趣,为中心与出发点。他指出所有法律体系目标的全体成员的最高幸福应该集中于:自由和平等。政府应该是一个负责法律的执行以及维护个人的和社会的自由的中介体。
进入社会状态的人类失去了自由,社会状态的自由被公意所束缚着,人们为了约定的自由而放弃了原先天然的自由。社会状态下的自由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与政治决策的自由。这种自由理论同时也是一个矛盾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了调和公民的自由与被统治的矛盾,使人们获得从前同样的自由,解决之道便是他的“公意”理念。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
卢梭的自由观与他的公意观一样,同时遭到了类似的攻击与质疑,一些学者指出,卢梭的建立在公意根基之上的政治自由,完全忽略了私人生活的快乐与幸福②较早站在自由主义角度对卢梭的自由观进行批判的人有贡斯当。贡斯当曾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他认为古代的自由主要在参与公共事务与政治生活,而现代人的自由中心在私人的自由至上。贡斯当认为,现代人过于追求古代的政治自由,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丧失所有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念是非常有局限性的。现代人的都意愿将大部分的时间消耗在私人空间之中,从私人空间中获得的快乐与幸福感要强于公共政治生活①认为政治生活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学者很多。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在《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中曾总结:民主制度并不一定会带来幸福。就民主的过程而言,它充满了痛苦。亲情和友谊却是人们追求幸福的归宿与寄托。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在多年以前也提到过与莱恩类似的想法:“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更不用说它的失常,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受着‘物欲’的损害与支配,并且满怀恐惧。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那些关于‘真正的’民主、‘完全的’自由和‘真正的’正义的狂呼乱喊,便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那不过是宴会散去之后的余辉罢了。”。卢梭强化了政治自由,但这势必导致对私人的自由进行了干涉与限制。
五、卢梭预言与我们时代的幸福
卢梭的政治学说虽然不断遭到挑战与质疑,但其作品字里行间对痛苦与幸福的感悟却已经跨越了历史,值得现代人回味与反思。即使晚年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也丝毫没有阻止他在自然中寻找生命幸福的真谛。他运用的文字与语言从不晦涩,他也不试图用冗长、复杂的思维说服人们接受他的观念。他对自然的酷爱让人感动与怜惜。这就是卢梭。他对自我是忠诚的,他对整个世界更是忠诚的。卢梭所描述的幸福与我们的时代的幸福应是同一种幸福,它是全人类共有的感受。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身痛苦与不幸的渊源,我们时代的症结之一就是人们不愿意倾听自我心灵的声音,不愿在人类知识的海洋中沉思。人们不断在欲望、诱惑与名利场之中穿行。种种欲望的膨胀,仅会让人感觉更加的痛苦,这与卢梭所倡导的自然、宁静的状态背道而驰,这种行为在卢梭眼中与疯子无异。
我们时代的科学与艺术依然与道德、伦理疏离,这种疏离带给我们的是劫难。处处充满着信任的危机:随处可见的食品安全事故;政府工程质量堪忧;媒体弥漫着狂躁、低俗的艺术娱乐;古典艺术与文化遭到冷遇,取而代之的是快餐文化与网络文化。人们在碎片化的感官刺激中获得生命的存在感与快感。不仅科学艺术与道德疏远了,人与道德也疏远了,街道上是冷漠而缺乏同情感的人群,慈善组织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由于自然状态的构思被学者质疑,致使卢梭对自然的崇敬与热爱经常被人不屑。自然是卢梭获得幸福感受的源泉。我们时代的人们利用自然胜于热爱自然,改造自然胜于回归自然我们在悬崖、苍松、莺啼中陶醉与沉思的机遇少,驻足于高崖峭壁下、深谷溪流边的时间太短暂。自然带给我们摄人心魄的美,我们却时常来不及去感受。我们只会在旅游与闲暇的缝隙中感受片刻的惬意与快乐,我们的心始终难以搁置下那蠢蠢欲动的欲念。
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回望历史,回顾卢梭的箴言,重新认识我们的时代与我们幸福。我们的时代是科技的时代,是娱乐的时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却非一个人文、历史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追求功利的时代,却非追求完善的时代。我们的时代远比卢梭所生活的18 世纪法国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物质财富,但我们的时代却依旧是一个幸福感欠缺的时代。我们行走的步伐太快以致经常遗忘历史,我们不断接受新兴的事物,混淆了真实的美德与善恶。
[1]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巫静译,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3]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