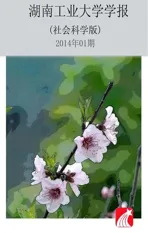对现代启蒙的坚守*
——论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
2014-03-31舒欣
舒 欣
(长沙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湖南长沙410003)
对现代启蒙的坚守*
——论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
舒 欣
(长沙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湖南长沙410003)
鲁迅于“左联”时期创作了5篇历史小说,其被收录在他的第三部小说集《故事新编》中。对于这些中国历史题材小说,鲁迅作了最具现代意义的创造,并深化了其早期进行的现代启蒙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所表现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启蒙与革命之间的艰难的承担与整合,使得鲁迅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启蒙与革命互动的中心位置,最大限度地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冲突的痛苦与代价。
鲁迅;《故事新编》;现代启蒙;传统文化;现代性
1935年底鲁迅完成了他的第三本小说集《故事新编》,共有8篇小说,这中间除《补天》写于20年代初,《铸剑》《奔月》写于1926年底外,其余都是在左联时期的1934-1935年写成的,有《理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整部小说集的完成,前后持续了13年。他在这本小说集的序言中写道:“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罢。”[1]
一
我们知道鲁迅从1926年以后就停止了小说创作,在整个左联时期,他把很多精力花在了支持和指导左翼文学运动上,先后参与了与“民族主义文学”“新月派”及“第三种人”的论争,并创作了大量富有战斗力的杂文以抨击时政,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旗手。为何在1934-1935年,时隔8年之后,也就是在其生命即将结束的前一、二年,鲁迅又重操旧业,写起历史小说来,延续着其20年代创作的思路?
鲁迅的这一举动,一方面与他同当时的左联领导人关系恶化有关。鲁迅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遭到革命作家的猛烈批判,但他在30年代初之所以同意加入左联,就在于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救民于水火的献身精神正契合他反对专制主义、反对独裁政治的愿望。所以,他能够捐弃前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左翼文学的队伍中来。因此,他自然重视文学和实践的关系,认为文学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生活,脱离革命而独立。“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2]418但同时,鲁迅也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文艺作用毕竟有限,“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2]417。“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对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2]423他反感把文艺变成政治的附属品。在鲁迅看来,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世界观也不等于创作方法,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并不能保证就创作出革命的作品来。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或指导他人创作的评论中,更多地注意文学艺术特征,并希望创作达到革命的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对只有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号式作品的倾向,他是反对的。他说:“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3]他因而不时对左翼文学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提出批评。况且,鲁迅从自身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出发,对左联中原来的理论对手并不看好,对左联本身也并不十分满意。1931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就把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主张放到上海“才子+流氓”的现象中加以严厉批判。1934年12月10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而现在连这也做不到。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因为生活大抵是苦的),这于战斗是有妨碍的。”[4]1936年8月5日,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中指出:“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5]显然,他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不可避免地要和左翼阵营里的那些在他看来充当“奴隶主”及“工头们”的言论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作为“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鲁迅早年就从中国的社会现状出发,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立人”的主张,并一直坚持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立场,坚守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即使加入左联后,他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但也不愿因加入左联而泯灭自我,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阅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但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当时的一些左翼文学理论家大不一样。1930年他在《习惯与改革》一文中就断言:“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6]他并不因民众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就认为民众已经觉醒,他依然认为民众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1934年,他在内山书店的一次聊天中说,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的强制一方搞得很厉害的时候,就会发生有名的东西——革命。这个革命一旦巧妙获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现了”;它在最初阶段,当然要“说点新事情,但是不知不觉问又跑到以儒家思想强制庶民的地方去了”;待到它“搞得很凶的时候,下次革命就又会一下子发展起来……”[7]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对现代革命的成效心存疑虑。
鲁迅的这些言谈,无疑表现了这位“五四”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之间的“彷徨”的境地,他既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怀有某种希望,又对左翼革命队伍的现状感到失望;既希望革命的集体力量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又从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艰巨性和长远性出发,对现代革命的现实效应产生怀疑,体现出坚持启蒙的长远目标与实现革命的现实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随着他与左联中的一些负责人的矛盾加剧以及左联在他看来是面临溃散的局面,鲁迅这位一生都在启蒙与革命中苦苦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老人,又一次体验到了20年代《新青年》团体解散后遭受各方面攻击时的孤独处境,他感到“无聊”“焦烦”“疲乏”“悲愤”。在这种状况下,他又延续着20年代创作《补天》《奔月》《铸剑》时的思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1]341连续创作了《理水》《非攻》《采薇》《出关》《起死》5篇历史小说。所不同的是,此次他将审视目光由中国的古代神话转向了中国古代传说和历史中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事迹,这种审视既带有现代启蒙的思想,更夹杂着作者个人在当时的复杂的心境。诚如鲁迅自己所言:“……新的文章,就不再做了,这几年真也够吃力了。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8]他力图通过这些人物事迹的抒写,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因此,他借古书上的一点缘由生发开去,有意识地将古今打通,使读者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和事情的真实面目。
二
纵观鲁迅在左联时期创作的《故事新编》中的5篇小说,《非攻》《理水》可以归为一类,小说以代表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墨子、大禹原型,分别讲述了他们阻止战火和战胜自然灾害的事迹。在鲁迅的笔下,他们都是属于为民请命、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实干型的人物,救民于危难之中,然而他们生存的人文环境是恶劣的,他们在小说中的结局令人深思。
《非攻》中的墨子是平民阶级的代表,他主张兼爱,且身体力行,坚决阻止楚国伐宋,他批评儒者子夏“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指责公输般“义不杀少,然而杀多”,都显得理直气壮。但鲁迅却不仅让他一向形单影孤,连他的弟子们都不实践他的主张,而且还特意让他在大功告成,拖着肿胀的双脚疲惫地回到被他所拯救的宋国时,竟使他接连被“搜”、被“募”,最后只落得一身空空地站在城门下避雨,却又被兵士赶开,结果“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墨子虽然成功地阻止了楚人伐宋,但却无力逃脱宋人的募捐与搜身。这对于施爱于无爱之人间而不得所爱的墨子,不是莫大的嘲讽吗?墨子的处境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呐喊》中的狂人、夏瑜,他们为唤醒民众,却被民众当作了疯子。这也何尝没有鲁迅自身的写照,“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9]尤其是其身处左翼文学阵营,因不满左联某些负责人的作风而受到本阵营内部人的攻击时,让他体验到的是如墨子一般的“寂寞”“疲惫”,“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10]而在《理水》中,大禹的形象却只只有几个若隐若现的剪影,大禹治水的过程完全以“传闻”的方式来表现,甚至大禹连自己做人的身份都受到了怀疑。而小说中占去相当篇幅的却是文化山的学者对禹的不伦不类的非议,水利局大员们对灾情的不关痛痒的考察,下民推选代表的畏葸以及那个头有疙瘩的代表的一身奴气,还有京都酒宴上对灾民进奉的民食及匣子的品评,京师的阔人、富翁以及包括禹太太在内的市民的生活的日渐奢糜。在这种环境下,大禹不顾各种非议,始终执着于治水,而当大禹治水成功,从艰难困苦的奋斗中回来后,却在“万人称颂”的阿谀中不知不觉地走入了贵族的行列。大禹最终仍是为历史的阴影所吞噬。这使我们想到鲁迅一再说过的,改革事业一旦为“毫不相干”者以至反对者所“歌呼”,“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11]。大禹的悲剧,不仅是他本人的转化,更是历史和环境使他如此。小说中大禹的这些变化,鲁迅是有着个人真切感受的,他在《范爱农》中就记录了辛亥革命时期绍兴光复后,革命党人王金发的变化,“他(王金发,引者注)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特别是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变化,让鲁迅感到痛心,“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12]因此,鲁迅深深地体会到:在中国,“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然而究竟怎样才能“脱离包围”呢?鲁迅苦苦求索,“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13]。
1925年,鲁迅就曾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写道:“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征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14]此话不是正印证了像墨子、大禹这类代表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的最终命运吗?鲁迅对墨子、大禹身体力行的实干作风是认同的,对于他们悲剧性的结局透露出了一些无奈与悲凉,在他看来,抗击权贵、批判庸众、拒绝庸俗,对革命者而言是比洪水、战争更艰巨的精神之战,启蒙未完成,革命也难以有成效。同时,鲁迅似乎也从墨子、大禹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他既感到了现代启蒙的艰难,又隐隐地为自己在革命阵营中的生存境遇担心了。
三
如果说《非攻》《理水》是通过对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悲剧性处境的描绘,来影射现实,揭示现代启蒙的艰难,那么鲁迅接下来创作《采薇》《出关》《起死》则转向了其早期的以现代理性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此次他将批判的目光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通过对代表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至圣先贤人物的行为举止的嘲讽,让他们的人生道路、人生理想在现代文明的返照下曝光,来到达其深化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采薇》中,作为儒家道德观念的倡导者和躬行者,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宁死不悔,在历史上颇受嘉奖:孔子称赞他们是“古之贤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儒夫有立志”,称之为“圣之清者”。然而,在小说中,两位圣贤坚守先王之道的过程却成了步步退让的逃避之旅,他们已无高风亮节的仙风道骨,面临的却是无尽的生存烦恼,处处显得迂腐可笑。最后,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嘛”的诘问,让他们只能饿死在首阳山。伯夷、叔齐虽然以死来挑战巨大的邪恶环境,但却无力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出关》中,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虽有高深的哲学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虚弱无力、任人摆布,为了出关老子“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于是,无奈被抓到关上,“免不掉”被迫讲学,“免不掉”被迫编讲义;而讲学时,想要听点恋爱故事的听众有的大打呵欠,有的干脆睡着。更为可笑的是,其编写的《道德经》最后只是和盐、大豆等充公之物混丢一处。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成了徒作大言的空谈。《起死》中的庄子口口声声“齐生死”“无是非”,欲超凡入圣、返璞归真,但却又想“起死回生”,让不幸的人“骨肉团聚”。然而,被“起死”汉子,其生命欲也“回生”了,当汉子死死缠住庄子索取包袱时,这位自诩明“天地大化”的人也不得不大谈“是非”了,并终于不得不借助官府的力量才得以脱身。在鲁迅看来,伯夷、叔齐、老子、庄子这些古代至圣先贤人物的人生理想是与现代文明的新的人生观相悖离的,他认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15]在小说中,伯夷、叔齐、老子、庄子的形象无疑被作者“漫画化”了。正是在这种漫画化中,鲁迅通过展现这些人物言行之间的矛盾,剥去其身上的神圣光环,恢复其本真的面目,来进一步对中国的主流文化——儒道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小说创作中,还有意识地将现代生活的“新事”移置到古代生活的“故事”中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古今杂揉”的特点。于是,我们看到小说在对历史人物的描绘中,也夹杂着大量的具有现代生活气息的词组,如“大学”“幼稚园”“文化山”、“图书馆”“时装表演”“募捐救国队”“莎士比亚”“古貌林”“OK”“遗传”“饮料”“卫生”“维他命”“警棍”“警笛”等,形成了一个古今交融的世界。这正是鲁迅所说的“油滑”写法。虽然他深知将“油滑”运用到创作中,“是创作的大敌”,“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但是,“油滑”多是讽喻与戏谑,多指向鞭挞的对象,而且它深深植根于鲁迅对社会历史——现实的认识之中,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他曾在《随感录·五十四》中感慨道:“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合,也只能煮个半熟……”[16]在鲁迅看来,尽管新思想、新名词充斥着整个社会,但整个社会运行方式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仍然跟古代一样,没有多大变化。对此,鲁迅也曾多次说道: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相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17]“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18]因此,鲁迅将古今交融在一起,为的是让“故事”发生在当下,把它带入现代语境,将它从沉睡中唤醒,使它重新对现代人的灵魂发生启示作用。小说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重视传统在其中的作用,新事物也同样应当接受分析与批判,不是凡是新的就是好的。要使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完成现代革命的目标,改造国民性是首要的,其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概言之,鲁迅在左联时期创作的这5篇历史小说,不仅和他20世纪20年代创作3篇历史小说一起,完成了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最具现代意义的创造,而且深化了其早期进行的现代启蒙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所表现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启蒙与革命之间的艰难的承担与整合,使鲁迅的小说创作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启蒙与革命互动的中心位置,最大限度地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冲突的痛苦与代价。
[1]鲁迅.故事新编·序言[M]//鲁迅全集: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42.
[2]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M]//鲁迅全集: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文艺与革命[M]//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4.
[4]鲁迅.致萧军、萧红341210[M]//鲁迅全集: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93.
[5]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M]//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7.
[6]鲁迅.习惯与改革[M]//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3.
[7]内山完造.上海漫语[G]//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1029.
[8]鲁迅.致萧军、萧红35104[M]//鲁迅全集: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
[9]鲁迅.两地书·九五[M]//鲁迅全集: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9.
[10]鲁迅.致萧军、萧红34206[M]//鲁迅全集: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84.
[1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社,1981:163.
[12]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M]//鲁迅全集: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45-547.
[13]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M]//鲁迅全集: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86-487.
[14]鲁迅.这个与那个(二)[M]//鲁迅全集: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40.
[15]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M]//鲁迅全集: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
[16]鲁迅.随感录·五十四[M]//鲁迅全集: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
[17]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M]//鲁迅全集: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9.
[18]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M]//鲁迅全集: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
责任编辑:黄声波
Stick to the Modern Enlightenment——On Lu Xun's Novel Old Tales Retold
SHU X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410003 China)
Lu Xun created five historical novels in Left League period,and they were included in his third anthology of storieswhich named Old TalesRetold.Lu Xun showed themodern sense in his Chinese theme historical fictions,and deepened his thought ofmodern enlightenment in early stage.More importantly,his novels presented the conflict and tens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and undertaking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whichmade hisworks always stand in the center of the conflictbetween tradition andmodernit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nlightenmentand revolution,and bear the pain and price of Chinesemodernization to the utmost degree.
Lu Xun;Old Tales Retold;modern enlightenment;traditional culture;modernity
I210.6
A
1674-117X(2014)01-0131-05
10.3969/j.issn.1674-117X.2014.02.024
2013-06-15
舒 欣(1969-),男,湖南湘乡人,长沙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